書(shū)寫(xiě)“紅色圣地”:世界新聞史上的“中國(guó)時(shí)刻”*
■ 曹培鑫 薛毅帆
1938年,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guó)》以《西行漫記》之名在上海“孤島”出版。80年后的今天,用一種新的視角來(lái)重新審視以斯諾為代表的一大批美國(guó)作家在1930至1940年代進(jìn)入中國(guó)西北一角進(jìn)行的采訪活動(dòng),可以對(duì)那段新聞史產(chǎn)生新的理解。
在傳統(tǒng)的新聞史體系中,我們習(xí)慣于把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人的新聞活動(dòng)納入中國(guó)新聞史體系當(dāng)中。這當(dāng)然是在中國(guó)近代革命的歷史框架下來(lái)理解美國(guó)記者群在華新聞活動(dòng)的結(jié)果:美國(guó)記者群的新聞活動(dòng)“使各國(guó)民主人士對(duì)中國(guó)人民反對(duì)和抗擊日本帝國(guó)主義表現(xiàn)出的勇敢、堅(jiān)定和不屈不饒的精神而感動(dòng),從而支持和幫助中國(guó)人民的革命斗爭(zhēng)。”①這一史學(xué)書(shū)寫(xiě)(historiography)將美國(guó)記者們的采訪活動(dòng)作為中國(guó)革命的“國(guó)際精神支持”納入“中國(guó)新聞史”的述評(píng)范疇,成為“革命的”中國(guó)新聞史的有機(jī)組成部分。
但是,上述歷史書(shū)寫(xiě)的視角消解了對(duì)以下重要議題的探討:為什么在這一時(shí)期,美國(guó)(事實(shí)上是歐美多國(guó))記者群會(huì)如此集中地關(guān)注中國(guó),關(guān)注中國(guó)的西北角上的一座蕞爾小城②,關(guān)注這一隅上的一個(gè)紅色政權(quán)?為什么美國(guó)記者群會(huì)對(duì)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社會(huì)由于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立而既成的“一般所描繪的赤匪”的形象產(chǎn)生質(zhì)疑,而有興趣跋山涉水,去書(shū)寫(xiě)另一種“意想不到的赤匪”的形象?③以及,他們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正面書(shū)寫(xiě)不僅突破先前廣泛存在于西方媒體與國(guó)民黨媒體上的負(fù)面形象,更突破了在一個(gè)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軸上西方世界對(duì)整個(gè)中國(guó)原有的“黃禍”“東亞病夫”的整體負(fù)面形象,原因?yàn)楹危?/p>
本文力圖轉(zhuǎn)換記述與分析的視角,將這一段充滿魅力卻未被充分探討的新聞史“軼事”放置于美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的歷史框架下重新審視,以期還珠于櫝。
一、 美國(guó)記者群的紅色書(shū)寫(xiě)
美國(guó)人瑪格麗特·史丹利(Margaret Stanley)于1987年編纂了一本名為《1949年之前共產(chǎn)黨管轄區(qū)內(nèi)的外國(guó)人》的小冊(cè)子。這本小冊(cè)子的第三部分是1935至1949年期間,在延安、保安及其他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控制地區(qū)進(jìn)行活動(dòng)的外國(guó)人名錄。史丹利根據(jù)時(shí)間順序給這些外國(guó)人進(jìn)行了編號(hào),一共統(tǒng)計(jì)出了145位外國(guó)人④,并提供了這些人的國(guó)籍、職業(yè)、去留時(shí)間。在這份名單中,可以確定為美國(guó)國(guó)籍的人士有92人,占總?cè)藬?shù)的63.9%,他們中有66人到訪過(guò)延安,占總?cè)藬?shù)的45.8%。⑤
這份名單以1942年的“珍珠港事件”為節(jié)點(diǎn),分為前后兩部分。由于“珍珠港事件”的爆發(fā),美國(guó)與中國(guó)正式結(jié)成反法西斯同盟。因此在隨后的日子里,這份名單上的大部分人,包括記者、軍人和政府官員,開(kāi)始大批地進(jìn)入延安。所以“史丹利名單”的前半部分中涉及到的美國(guó)人有20人,當(dāng)中新聞?dòng)浾吲c編輯有9人。⑥這9人可稱為真正報(bào)道“紅色中國(guó)”的先行者,斯諾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1936年,紅軍剛剛長(zhǎng)征結(jié)束,在陜北落腳。在蔣介石的軍事包圍、經(jīng)濟(jì)封鎖、新聞隔離和形象丑化之下,共產(chǎn)黨意識(shí)到了必須將政權(quán)的真實(shí)面貌展現(xiàn)給外界。于是,共產(chǎn)黨委托宋慶齡推薦一名外國(guó)醫(yī)生和一名外國(guó)記者到根據(jù)地來(lái),以便將紅色政權(quán)與紅色根據(jù)地最真實(shí)的故事講給外界。埃德加·斯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lái)到了陜北。實(shí)際上,在宋慶齡與中共把目光投向斯諾之前,斯諾自己也“早就打算去了,而且已經(jīng)到上海來(lái)想實(shí)現(xiàn)這個(gè)計(jì)劃”⑦。這次“一拍即合”使得斯諾成為“第一個(gè),也是最后一個(gè)”在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訪問(wèn)中共所在地的西方記者。⑧當(dāng)時(shí)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陜西保安,斯諾來(lái)到保安后,受到了中共高層的熱情接待,“周恩來(lái)親自前來(lái)歡迎,毛澤東開(kāi)始同他長(zhǎng)談時(shí),埃德的情緒十分高漲”⑨。隨后,斯諾在這里開(kāi)展了將近四個(gè)月的采訪活動(dòng)。1936年10月,斯諾從根據(jù)地返回北平,并開(kāi)始為外媒和國(guó)內(nèi)的外文報(bào)紙撰寫(xiě)有關(guān)他在紅色根據(jù)地所見(jiàn)所聞的報(bào)道。這些報(bào)道散布在《密勒氏評(píng)論報(bào)》《每日先驅(qū)報(bào)》《救國(guó)時(shí)報(bào)》《生活》雜志、《亞洲》雜志等新聞媒體上。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所有的報(bào)道寫(xiě)作。隨后,英文版的《紅星照耀中國(guó)》(Red Star Over China)于1937年10月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紅星照耀中國(guó)》“旋即被選入左翼圖書(shū)俱樂(lè)部文選中,在出版第一個(gè)月內(nèi)重印了3次”⑩。1938年1月1日,《紅星照耀中國(guó)》在美國(guó)出版。同年,莫斯科也出版了該書(shū)的俄文版。《紅星照耀中國(guó)》的出版具有非凡的意義,“在世界各國(guó)中,恐怕沒(méi)有比紅色中國(guó)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shuō)了”。而《紅星照耀中國(guó)》的流行,把紅色中國(guó)的獨(dú)特面貌展現(xiàn)給世界,開(kāi)啟了西方世界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的“新紀(jì)元”,也拉開(kāi)了美國(guó)眾多新聞?dòng)浾吒吧怼凹t區(qū)”的序幕。
美國(guó)記者們走進(jìn)紅區(qū)的路途困難重重、險(xiǎn)象環(huán)生。困難與危險(xiǎn)首先來(lái)自陜北的自然地理?xiàng)l件。盡管斯諾在遠(yuǎn)觀時(shí)可以用一種浪漫的審美眼光將千溝萬(wàn)壑的陜北高原形容成“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奇美的世界”,然而,置身于其中,走在去往保安的“河邊懸崖上的羊腸小道”上時(shí),斯諾面臨的卻是“掉向下面巖石嶙峋的峽谷中去”的危險(xiǎn)。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她的書(shū)中寫(xiě)到了她在去往一個(gè)八路軍駐地的途中,遇到的是“樹(shù)枝與稻草搭成的橋梁”“湍急的河水”“多石的山坡”“幾條極窄的山谷”和“黃土的山壁”。這些對(duì)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年過(guò)六十的斯特朗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巨大的挑戰(zhàn)。其次,來(lái)自于國(guó)民黨或日軍的威脅也使得通往蘇區(qū)的道路充滿坎坷。這些威脅,對(duì)于斯諾的旅行尤其真實(shí)。斯諾1936年第一次進(jìn)入紅區(qū)時(shí)“西安事變”尚未發(fā)生,國(guó)共還沒(méi)有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因此,國(guó)民黨軍隊(duì)對(duì)西安到陜北的道路控制極其嚴(yán)格。斯諾知道在這段路途上“土匪早已在那寂靜的黃土山壁后邊跟蹤我了——只不過(guò)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同時(shí),國(guó)民黨軍隊(duì)還對(duì)紅區(qū)進(jìn)行軍事打擊,“當(dāng)時(shí)每天都有飛機(jī)從那個(gè)機(jī)場(chǎng)起飛,到紅軍防線上空去偵察和轟炸”。疾病與語(yǔ)言隔閡也使得采訪活動(dòng)困難重重:“寄生在人體的虱子能傳播斑疹傷寒,得了這種病的外國(guó)人死亡率很高。”“一知半解的普通話幫不了大忙,因?yàn)殛兾鞣窖允峭燎弧!?/p>
這些困難并沒(méi)有妨礙美國(guó)記者們向黃土高原的深處挺進(jìn)。紅區(qū)的物質(zhì)生活同樣異常艱苦。史沫特萊在《中國(guó)在反擊》(China Fights Back)一書(shū)的自序中記錄了當(dāng)時(shí)生活條件之艱苦:沒(méi)有紙張,缺少糧食,沒(méi)有取暖燃料,交通工具基本是雙腿與少量騾馬,大部分人只有腳上穿的那一雙鞋。但是,她也寫(xiě)到:“我向你們談到的所有這一切情況,毫無(wú)抱怨訴苦之意。相反,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而斯諾認(rèn)為“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gè)外國(guó)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xiǎn)嗎”。
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幸福與現(xiàn)實(shí)的困境的巨大張力中,美國(guó)記者群的紅區(qū)活動(dòng)成就了新聞史上的一段佳話。那么,美國(guó)記者群能夠克服巨大的現(xiàn)實(shí)困難與危險(xiǎn),甚至將這段經(jīng)歷視為“最有意義”的事業(yè),動(dòng)力何在?我們可以在史沫特萊的書(shū)寫(xiě)中一窺問(wèn)題的答案。在《中國(guó)的戰(zhàn)歌》中,她寫(xiě)到這些美國(guó)記者們所講述的故事當(dāng)中的人“不是一般的中國(guó)人,他們是新中國(guó)的人”。正是對(duì)這個(gè)處在內(nèi)憂外患之中卻能夠給中國(guó)人帶來(lái)新希望的新政權(quán)的憧憬,帶給了他們無(wú)盡的力量與理想。
那么他們筆下這個(gè)“新中國(guó)”“新”在哪里?與“舊中國(guó)”有何不同?這個(gè)“意想不到的赤匪”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樣的?
二、 中國(guó)形象的三個(gè)轉(zhuǎn)向
美國(guó)記者群筆下的“新中國(guó)”是一個(gè)之于“舊中國(guó)”的相對(duì)概念。通過(guò)將美國(guó)記者群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中國(guó)書(shū)寫(xiě)——尤其是對(duì)“紅色中國(guó)”的書(shū)寫(xiě)——與此前大約從“啟蒙時(shí)代”開(kāi)始(至于為什么將這個(gè)時(shí)間段的上限定在“啟蒙時(shí)代”,將會(huì)在第三部分回答)對(duì)中國(guó)的書(shū)寫(xiě)相比對(duì),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其中經(jīng)歷了諸多方面的巨大轉(zhuǎn)變。但從總體上講,這些對(duì)于“新”“舊”兩個(gè)中國(guó)紛繁復(fù)雜的描摹,可以大致概括為三對(duì)轉(zhuǎn)向:專(zhuān)制趨向民主,停滯轉(zhuǎn)向進(jìn)步,野蠻走向文明。
1.從“專(zhuān)制”到“民主”
西方人視野中的中國(guó),并不總是一個(gè)“專(zhuān)制的帝國(guó)”形象。伏爾泰就將中國(guó)奉為最可以為楷模的“開(kāi)明君主制”的國(guó)家。但是,啟蒙時(shí)代以降,中國(guó)逐漸被收編進(jìn)一個(gè)專(zhuān)制國(guó)家的隊(duì)伍中——這個(gè)隊(duì)伍曾先后容納了波斯帝國(guó)、莫臥兒帝國(guó)、韃靼、沙俄。到了黑格爾口中,中國(guó)已經(jīng)是“君權(quán)神授的專(zhuān)制政制。國(guó)家是家長(zhǎng)制式的,它由一個(gè)家長(zhǎng)統(tǒng)治,這位家長(zhǎng)同時(shí)決斷一切,也包括我們看作是良心領(lǐng)域內(nèi)的事情”。
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外國(guó)的傳教士、商人、官員、記者開(kāi)始大批進(jìn)入中國(guó)。在他們的眼中與筆下,中國(guó)儼然是一個(gè)完全的“專(zhuān)制的帝國(guó)”。《美國(guó)的中國(guó)形象》一書(shū)中記錄了一種在十九世紀(jì)對(duì)中國(guó)“很流行”的看法:“他們長(zhǎng)時(shí)間屈從于專(zhuān)制暴君的統(tǒng)治,以及腐敗而肆無(wú)忌憚的統(tǒng)治者們幾乎無(wú)處不在的暴虐。”
直至1928年蔣介石角逐國(guó)家元首的時(shí)候,《紐約時(shí)報(bào)》的著名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仍在“專(zhuān)制的帝國(guó)”的譜系中繼續(xù)斷言:“如果蔣介石獲勝,那么他就會(huì)成為一名真正的操縱中國(guó)的獨(dú)裁者,而且南京依舊會(huì)是一個(gè)高度集權(quán)的中央政府的首都。”蔣介石當(dāng)權(quán)后,阿班在1930年出版的《痛苦的中國(guó)》中討論蔣介石政權(quán)的性質(zhì)時(shí)寫(xiě)到:“中國(guó)始終是在國(guó)民黨一黨專(zhuān)政統(tǒng)治下的獨(dú)裁國(guó)家,蔣介石集團(tuán)只是通過(guò)一場(chǎng)又一場(chǎng)的戰(zhàn)爭(zhēng)謀求生存并維持其獨(dú)裁專(zhuān)制。”
從這一條自啟蒙時(shí)代開(kāi)始的“中國(guó)形象”的觀念譜系來(lái)看,中國(guó)一直是一個(gè)在“專(zhuān)制的帝國(guó)”之底色上的“痛苦”的國(guó)家。
但是,就在阿班做出“專(zhuān)制帝國(guó)”斷言之時(shí),另一種對(duì)中國(guó)的書(shū)寫(xiě)悄然興起。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美國(guó)的記者們開(kāi)始關(guān)注一個(gè)偏居中國(guó)最閉塞地區(qū)的共產(chǎn)主義的紅色政權(quán),并將其描繪為一個(gè)嶄新的“民主政權(quán)”。這在蘇聯(lián)建立后,包括美國(guó)在內(nèi)的西方世界對(duì)共產(chǎn)政權(quán)充滿恐懼與敵意的歷史情境下,尤其令人匪夷所思。
在斯諾筆下,“紅色政權(quán)”是一個(gè)“‘農(nóng)村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某種民主政權(quán)”。在這個(gè)政權(quán)中,“代議制政府結(jié)構(gòu)是從最小的單位村蘇維埃開(kāi)始建立的”,而“年滿十六歲的,普遍都有選舉權(quán)”。所有的社會(huì)組織“是由農(nóng)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決定、吸收成員、進(jìn)行工作的”,而且都與“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chǎn)黨、紅軍”的領(lǐng)導(dǎo)“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一個(gè)具有最廣泛意義的大民主政治體制躍然紙上。
在“黨、政、軍”領(lǐng)導(dǎo)下的人民,并不是一種被迫的歸順。在斯諾看來(lái),他們似乎是發(fā)自真心的認(rèn)可了“人民的政權(quán)”與“人民的領(lǐng)袖”。斯諾經(jīng)常用“懸賞金額”來(lái)說(shuō)明共產(chǎn)黨首領(lǐng)與人民之間的關(guān)系。“蔣介石懸賞八萬(wàn)元要周恩來(lái)的首級(jí),可是在周恩來(lái)的司令部門(mén)前,只有一個(gè)哨兵”;“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wàn)元要他(毛澤東)的首級(jí),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他(林彪)的首級(jí)的賞格高達(dá)十萬(wàn)元,但是他仍然神奇地沒(méi)有受傷,身體健康”;“把那些(紅軍大學(xué))鼎鼎大名的學(xué)員的首級(jí)賞格加起來(lái)總共超過(guò)二百萬(wàn)元”。尤其是對(duì)于毛澤東:“雖然每個(gè)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méi)有——至少現(xiàn)在還沒(méi)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
因此,斯諾意識(shí)到,“幾百年來(lái),中國(guó)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駕于人民之上,躋身于高高在上的統(tǒng)治人民大眾的一小批官僚階級(jí)之列——所憑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shí)據(jù)為己有,以此來(lái)作為控制鄉(xiāng)村的愚昧的武器”,但是共產(chǎn)黨所做的卻是“震撼、喚起中國(guó)農(nóng)村中的億萬(wàn)人民,使他們意識(shí)到自己在社會(huì)中的責(zé)任,喚起他們的人權(quán)意識(shí)……強(qiáng)迫他們起來(lái)為‘人民當(dāng)家做主’——這是中國(guó)農(nóng)村中的新氣象——而斗爭(zhēng)”。
斯特朗在1937年來(lái)到根據(jù)地,她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支“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見(jiàn)”的軍隊(duì)。這只軍隊(duì)在斯特朗的筆下是一支民主的軍隊(duì),領(lǐng)導(dǎo)人對(duì)架子“漠不關(guān)心”,“不存在內(nèi)部?jī)A軋,沒(méi)有吵架,也沒(méi)有粗暴的行為”,“對(duì)八路軍來(lái)說(shuō),每個(gè)普通士兵都是寶貴的”。
如果說(shuō),斯諾在1936年保安之行中寫(xiě)下的“民主共和國(guó)”還摻雜著對(duì)于一個(gè)方興未艾的新生政權(quán)的美好遐想的話,那么他在1939年重回陜北的延安之行就應(yīng)當(dāng)是以更成熟、更理性的態(tài)度來(lái)審視這個(gè)紅色“國(guó)度”的。斯諾注意到了根據(jù)地的政制改革的新進(jìn)展:蘇維埃政府承認(rèn)了各村鎮(zhèn)的自治能力,選舉權(quán)是普遍而平等的,四十二種雜稅廢除了,基層群眾組織紛紛建立,還有各種農(nóng)民愿意參加的運(yùn)動(dòng)。斯諾將這一切稱為“民主政治的實(shí)驗(yàn)”。
延安的民主氛圍對(duì)于長(zhǎng)期處于專(zhuān)制社會(huì)中的中國(guó)人民來(lái)說(shuō)難能可貴。美國(guó)記者哈里遜·福爾曼(Harrison Forman)記錄了一個(gè)離延安大約兩小時(shí)車(chē)程的小村子進(jìn)行村參議會(huì)選舉的場(chǎng)面。一處細(xì)節(jié)描寫(xiě)言明了“延安式的”民主對(duì)于中國(guó)人民的可貴:“那些對(duì)奴隸生活記憶猶新的老年人,對(duì)這些事情(民主選舉)似乎是奇怪得不可理解……我差不多理解他們的心情,那是一種為難、不信任以及感激真正關(guān)心一般人民福利的政府的混合感情。”在福爾曼眼中,根據(jù)地的民主政權(quán)是在一個(gè)漫長(zhǎng)的“專(zhuān)制”的母胎中成長(zhǎng)出來(lái)的可貴的新社會(huì)。而這種復(fù)雜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折射在人的思想層面,就形成了這種混合情感。作為一批來(lái)自大洋彼岸的美國(guó)記者,他們也從對(duì)中國(guó)的復(fù)雜的印象與想法中積極地“分揀”出一種新的、正面的、不同于以往“專(zhuān)制的帝國(guó)”的態(tài)度。
2.從“停滯”到“進(jìn)步”
“停滯的帝國(guó)”,這是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名著《停滯的帝國(guó)——兩個(gè)世界的撞擊》中對(duì)清帝國(guó)的定位。這個(gè)定位大約從啟蒙時(shí)代開(kāi)始就被用于對(duì)中國(guó)的描述。黑格爾說(shuō)中國(guó)“歷史本身沒(méi)有表現(xiàn)出任何發(fā)展和進(jìn)步的地方”。而且,后世的西方哲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政治學(xué)家也都從各自的角度提供大量的新史料來(lái)論證這個(gè)舊觀點(diǎn)。
周寧認(rèn)為:“進(jìn)步是啟蒙思想中的核心觀念之一,它表現(xiàn)為一種知識(shí)化的信念:人類(lèi)文明已經(jīng)、正在而將會(huì)朝著一個(gè)可以預(yù)期的方向演進(jìn)。這個(gè)方向可能是科學(xué)知識(shí)、民主制度與物質(zhì)財(cái)富最終導(dǎo)致的幸福,也可能是一種絕對(duì)精神的實(shí)現(xiàn)。”但是中國(guó)似乎在這些可能的維度上都停下了步伐。從啟蒙時(shí)代以來(lái),中國(guó)在西方眼中就逐漸褪去了富庶、文明的大汗之國(guó)的面貌。中國(guó)在經(jīng)濟(jì)與物質(zhì)財(cái)富上“停滯取代了繁盛,經(jīng)濟(jì)急劇衰退,缺乏進(jìn)步”;在心靈上“對(duì)他們(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變化是令人厭惡、反感的……心靈便處于停滯狀態(tài)……進(jìn)步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上“這個(gè)帝國(guó)是一具木乃伊……它體內(nèi)血液循環(huán)已經(jīng)停止,猶如冬眠動(dòng)物一般”;在藝術(shù)與美學(xué)上,“似乎沒(méi)有超過(guò)每一個(gè)民族早期文明的階段,在純粹形式的觀念上,他們甚至落后于新西蘭人”。近代的日本在進(jìn)行民族命運(yùn)抉擇的時(shí)候,選擇了“脫亞入歐”。“脫亞”的關(guān)鍵是脫離亞洲的代表——中國(guó),因?yàn)橹袊?guó)“在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歷史之后……缺乏自由的生機(jī)、進(jìn)步的動(dòng)力”,以至于“停滯在世界歷史的起點(diǎn)上或者世界歷史之外”。
這些對(duì)于中國(guó)形象的描繪似乎都在為黑格爾的那句論斷背書(shū)。形象越描越深,已成為一種文化。以至于,斯諾自己都“有一段時(shí)間認(rèn)為,沒(méi)有什么事情會(huì)使一個(gè)中國(guó)人起來(lái)斗爭(zhēng)”。但是當(dāng)美國(guó)作家群親臨根據(jù)地的時(shí)候,所看到的卻是一幅充滿朝氣的革命進(jìn)取之地的景象。
在經(jīng)濟(jì)方面,斯諾用了一種“殘忍的”對(duì)比,雄辯地道出了根據(jù)地的進(jìn)步。在邊區(qū)紅色政權(quán)建立之前,“西方世界幾乎沒(méi)有人注意到”的災(zāi)難里,斯諾看到了“成千上萬(wàn)的男女老幼在我(斯諾)眼前活活餓死”,“二十歲的年輕人……像個(gè)干癟的老太婆”,“兒童們……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滿了樹(shù)皮鋸末像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里等死”,“萬(wàn)人冢里一層層埋著幾十個(gè)這種災(zāi)荒和時(shí)疫的受害者”。“許多土地荒蕪”的同時(shí),陜西的農(nóng)民“所付土地稅和附加稅達(dá)收入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稅捐‘又占百分之二十’”。接下來(lái),斯諾對(duì)比了紅區(qū)在經(jīng)濟(jì)上的進(jìn)步與變革:“在新區(qū)中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稅租”,“大片大片地開(kāi)‘荒’”,“沒(méi)收有錢(qián)階級(jí)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給窮人”,還進(jìn)行了貨幣改革。放置在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史的框架下,在一個(gè)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封建社會(huì)的帝國(guó),一個(g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都已經(jīng)習(xí)慣了森嚴(yán)的等級(jí)界限的帝國(guó),一個(gè)古老且頑固如“化石般的”帝國(guó)中,這場(chǎng)從黃土深處所爆發(fā)出的變革堪稱偉大。在這樣的對(duì)比鮮明的事實(shí)材料面前,斯諾得出了結(jié)論:“當(dāng)紅星在西北出現(xiàn)時(shí),無(wú)怪有千千萬(wàn)萬(wàn)的人起來(lái)歡迎它。”
在政治方面,美國(guó)記者們認(rèn)為中共是一個(gè)積極抵抗侵略、爭(zhēng)取民族獨(dú)立的進(jìn)步政權(quán)。斯諾和福爾曼巧妙地使用歷史的隱喻闡明觀點(diǎn):“在唐朝和金朝的時(shí)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邊防要塞”;“在古代它(延安)是防范北方胡人入侵的重鎮(zhèn)。”這些看似波瀾不驚的描寫(xiě)是新聞寫(xiě)作中對(duì)于背景材料的巧用。此時(shí)的保安縣依舊是“抵御”侵略的“要塞”,只不過(guò)入侵者變成了“日本”。這一系列與歷史的有意勾連,將中國(guó)塑造成了一個(gè)與曾經(jīng)那種任人宰割、龜縮自保、畏懼反抗的中國(guó)截然不同的國(guó)度。這個(gè)“新”中國(guó)充滿了反擊敵人的勇氣和謀略。這種變化不僅是膽量與能力的進(jìn)步,更是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主權(quán)國(guó)家國(guó)際意識(shí)的覺(jué)醒。
在斯特朗與史沫特萊的新聞作品中,對(duì)“女性”的描寫(xiě)也昭示了一種新的社會(huì)氣象。婦女們開(kāi)始“參加識(shí)字班、學(xué)習(xí)小組,討論抗日救亡是怎么一回事,婦女如何出力”。史沫特萊預(yù)言“新”中國(guó)的“新婦女”從此成長(zhǎng)起來(lái),莊嚴(yán)地走上歷史舞臺(tái)的正面:“從此以后,她們不是過(guò)去的鍋臺(tái)轉(zhuǎn)后門(mén)坐的深閨屋里人了,而是關(guān)心民族興亡、復(fù)興的出門(mén)跑的新婦女了。”
美國(guó)作家群們還注意到了一種“新文藝”——完全為抗戰(zhàn)服務(wù)的進(jìn)步文藝。一方面,文藝被用來(lái)反映中國(guó)軍民革命斗爭(zhēng)的事跡,“都是士兵們所熟悉的生活的寫(xiě)照”,比如丁玲的劇團(tuán)用有北平風(fēng)格的“大鼓戲”表演了“平型關(guān)戰(zhàn)役”,而“該村在場(chǎng)的觀眾中有一半人曾參加過(guò)平型關(guān)戰(zhàn)役;他們?nèi)褙炞⒌貎A聽(tīng)著有關(guān)他們自己勝利的故事”。另一方面,文藝也被當(dāng)作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士兵們需要學(xué)習(xí)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和當(dāng)時(shí)的日本侵華簡(jiǎn)史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戲劇做媒介教給他們的”。
美國(guó)記者群筆下的紅色邊區(qū)發(fā)生了“換了人間”似的巨大變革。“誰(shuí)夢(mèng)想得到在那社會(huì)停滯了兩千年的貧瘠的陜西黃土巖中”,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生活、文藝各個(gè)方面都呈現(xiàn)出一種與曾經(jīng)停滯不前的那個(gè)古老帝國(guó)完全不同的進(jìn)步新面貌。
3.從“野蠻”到“文明”
與“專(zhuān)制”和“停滯”不同,“野蠻”既不是形容某一個(gè)政治體制的獨(dú)裁性,也不是將一個(gè)社會(huì)定義為不思進(jìn)取的懶惰,而是對(duì)一個(gè)社會(huì)與其成員的全面指稱。“只有在野蠻的概念下,中國(guó)形象才全面陷入黑暗,野蠻作為套語(yǔ)的概括性,遠(yuǎn)勝于專(zhuān)制或停滯,野蠻所指的社會(huì)與人的否定性特征,幾乎是無(wú)所不包的。”
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隨著中國(guó)的國(guó)門(mén)打開(kāi),大量的西方人目睹了迥異于自身的中國(guó)人的生活習(xí)慣與習(xí)俗。在西方人眼里,中國(guó)疏遠(yuǎn)文明的野蠻形象是于一系列具體的社會(huì)生活中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溺殺女?huà)搿⒖嵝獭⑿∧_、豬尾巴辮子、淫亂的一夫多妻制、吸鴉片、動(dòng)物般的大量繁殖、滿街的糞便、異教徒等等。似乎中國(guó)與中國(guó)人的一切都可以與“獸性”“未開(kāi)化”“墮落”聯(lián)系在一起。
一個(gè)美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人的童年回憶是“邪惡的;危險(xiǎn)的;他們綁架孩子;從事白人奴隸買(mǎi)賣(mài);在電影中總是壞人;古怪;可怕;他們會(huì)把你砍碎;陰險(xiǎn)的;他們吃大老鼠;吸鴉片……”。中國(guó)人的“野蠻”不僅是社會(huì)文化、習(xí)慣、習(xí)俗等層面的“不文明”,更令西方人產(chǎn)生恐懼。因?yàn)橹袊?guó)人的“野蠻”被與暴力、殘忍、人口眾多等特點(diǎn)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中國(guó)人的“野蠻”就成了一種對(duì)“文明的世界”,也就是西方世界的嚴(yán)重威脅。比如西方人就對(duì)俄國(guó)征服中國(guó),并利用中國(guó)人征服歐洲的想象充滿恐懼;再比如,馬爾薩斯把“野蠻繁殖”的中國(guó)人當(dāng)作世界糧食的無(wú)底洞,最終也會(huì)使文明國(guó)家陷入貧窮;十九世紀(jì)的若干起暴力教案也給中國(guó)人披上了一層頑固不化、不肯接受基督教文明的野蠻異教徒外衣。上述野蠻形象,在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的猛烈沖突之中,喚醒了歐洲人對(duì)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恐怖記憶而走向高峰:“無(wú)數(shù)丑陋兇殘的黃種人,頭上腰上纏著血腥的紅布帶,揮舞著長(zhǎng)矛大刀,野獸般嚎叫著,蝗蟲(chóng)般漫山遍野地涌來(lái),所到之處,火光沖天,過(guò)后便是廢墟一片。”中國(guó)人似乎永遠(yuǎn)都不會(huì)“文明”起來(lái)。
但是,當(dāng)美國(guó)記者們來(lái)到紅色根據(jù)地時(shí),卻看到另一幅景象:“在陜西北部的二十幾個(gè)蘇維埃化已久的縣里,中國(guó)大部分地方常見(jiàn)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而且新區(qū)的居民中間也在進(jìn)行大力的宣傳,要在那里進(jìn)行同樣的基本改革。陜北已經(jīng)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gè)杰出的成就。事實(shí)上,我(斯諾)一進(jìn)蘇區(qū)以后就沒(méi)有看到過(guò)什么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近乎是從來(lái)沒(méi)有聽(tīng)到過(guò)。乞丐和失業(yè)的確像共產(chǎn)黨所說(shuō)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qū)旅行期間沒(méi)有看到過(guò)一個(gè)乞丐。纏足和溺嬰是違法的,奴婢和賣(mài)淫已經(jīng)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斯諾的這些見(jiàn)聞幾乎逐一撕掉了曾經(jīng)與“中國(guó)”或“中國(guó)人”捆綁在一起的野蠻標(biāo)簽。
由于政治與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對(duì)立,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蘇區(qū)所實(shí)行的很多“文明開(kāi)化”的改革措施在國(guó)民黨的媒體上被形容為新的“紅色野蠻”,比如“共妻”“婦女國(guó)有化”等丑化宣傳。而斯諾稱這些謠言“一望而知是荒謬可笑的,不屑一駁”。他還用了一種“西方的尺度”——法制,來(lái)評(píng)價(jià)共產(chǎn)黨在陜北的婚姻改革。法制是現(xiàn)代國(guó)家治理文明的標(biāo)志。他用1936年在保安重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婚姻法》來(lái)證明,共產(chǎn)黨所建立的婚姻制度并非是“共產(chǎn)主義式的”野蠻,而是一種具有現(xiàn)代政治色彩的文明。《婚姻法》中的規(guī)定也的確有利于掃清中國(guó)傳統(tǒng)婚姻中的一些封建意味濃厚的規(guī)約:“禁止婆婆虐待媳婦、買(mǎi)賣(mài)妻妾以及‘包辦婚姻’的習(xí)慣。婚姻必須取得雙方同意……禁止彩禮……離婚雙方財(cái)產(chǎn)均分。”
教育事業(yè)也是共產(chǎn)黨在根據(jù)地重點(diǎn)發(fā)展的“文明”事業(yè)之一。斯諾記錄下這里開(kāi)辦的形形色色的學(xué)校:為小學(xué)教師開(kāi)辦的師范、農(nóng)業(yè)學(xué)校、紡織學(xué)校、工會(huì)學(xué)校、黨校、技術(shù)學(xué)校、無(wú)線電學(xué)校、醫(yī)科學(xué)校,以及一種發(fā)揮著重要社會(huì)教育功能的“社會(huì)教育站”。在這種教育站里,群眾由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或識(shí)字的人當(dāng)組長(zhǎng),憑借有粗糙簡(jiǎn)單插圖的識(shí)字課本來(lái)學(xué)習(xí)。
這只軍隊(duì)似乎不像歷史上的其他軍隊(duì),他們遵守“三大紀(jì)律八項(xiàng)注意”,就連日本人也要承認(rèn)這支軍隊(duì)的“文明”。對(duì)于普通日本士兵,“上級(jí)一直對(duì)他們說(shuō),如果他們被捕,他們會(huì)受到嚴(yán)刑拷打,并被處死”。所以日本人會(huì)因?yàn)楸苊獗环此揽购狻1热缭谄叫完P(guān)戰(zhàn)役中,中國(guó)軍隊(duì)傷亡主要來(lái)自于解除日本俘虜武裝的時(shí)候,而不是實(shí)際戰(zhàn)斗。但實(shí)際上,一位日本戰(zhàn)俘的敘述提供了一個(gè)完全相反的受到“禮遇”的故事:“我們受了傷,當(dāng)了俘虜;我們想這下子完了。過(guò)去我們被告知,中國(guó)軍隊(duì)很殘忍。可是事實(shí)上他們待我們很好,我們過(guò)著自由的生活。”一個(gè)叫做岡田吉雄的俘虜本來(lái)等待著受刑和被殺,但是卻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最好的待遇,甚至提出要遣送他回自己的部隊(duì)。岡田拒絕回去后,不僅在延安的日本工農(nóng)學(xué)校學(xué)習(xí)了一年,還為王震的部隊(duì)建了一所日式風(fēng)格的招待所,評(píng)上了勞動(dòng)英雄,更在1942年加入了八路軍。
在這些社會(huì)“文明”的改變之外,美國(guó)記者們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就是中共領(lǐng)導(dǎo)人們的“文明”。從1927年的“第一次國(guó)共合作”破裂之后,國(guó)民黨就開(kāi)始了對(duì)共產(chǎn)黨人的負(fù)面宣傳,比如“無(wú)知土匪”“強(qiáng)盜”“放火犯”。然而在美國(guó)記者群的筆下,周恩來(lái)的形象是“一個(gè)行動(dòng)同知識(shí)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shí)分子”,“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賀龍不讓自己的部下“強(qiáng)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讓他們抽大煙”;毛澤東是“精通中國(guó)舊學(xué)的有成就的學(xué)者,他博覽群書(shū),對(duì)哲學(xué)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與寫(xiě)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zhuān)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朱德的眼睛“閃爍著智慧和判斷力”。這一系列“文明的領(lǐng)袖”的形象與國(guó)民黨的宣傳——用斯諾的話說(shuō)——“形成了奇特的對(duì)照”。
總之,在美國(guó)記者們的筆下,“野蠻的帝國(guó)”文明化了。這種“文明”的根據(jù)地形象,是對(duì)包括國(guó)民黨這些年來(lái)的政治丑化與西方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種族鄙視”的雙重否定,在他們的寫(xiě)作中,中國(guó)被寄予了成為嶄新的現(xiàn)代文明發(fā)源地的期望。
通過(guò)閱讀美國(guó)記者們作品當(dāng)中一種新的“中國(guó)肖像”,我們發(fā)現(xiàn)了潛藏在這些文本當(dāng)中的“三個(gè)轉(zhuǎn)向”:從專(zhuān)制到民主,從停滯到進(jìn)步,從野蠻到文明。這些嶄新的中國(guó)形象顛覆了貧窮落后、野蠻停滯的中華帝國(guó)的刻板印象,紅色政權(quán)成為新中國(guó)的希望,預(yù)示著中華民族更美好的未來(lái)。
那么,此時(shí)我們不得不深思:為什么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正面書(shū)寫(xiě)能夠極大地突破此前在一個(gè)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自啟蒙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的歷史中——西方世界對(duì)中國(guó)整體的負(fù)面形象書(shū)寫(xiě)?什么樣的美國(guó)(或者說(shuō)西方)歷史語(yǔ)境能夠產(chǎn)生敦促美國(guó)記者群在三四十年代如此熱衷于構(gòu)建一個(gè)“民主”“進(jìn)步”“文明”的紅色中國(guó)形象的動(dòng)力?
三、 作為“他者”的紅色圣地
索緒爾說(shuō),意義是在與其他事物的關(guān)系中被確定的。中國(guó)形象——關(guān)于“中國(guó)是什么樣的”的描繪——而非中國(guó)本身,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歷程中持久地發(fā)揮著“功能性的他者”的作用。正如英國(guó)學(xué)者博埃默所述:“正因?yàn)椤摺拇嬖?主體的權(quán)威才得以界定。”此處強(qiáng)調(diào)“功能”與“持久”恰好因?yàn)?西方、現(xiàn)代性等主體觀念本身是變動(dòng)不居的,因此作為“他者”的中國(guó)形象,就不得不在文化表征層面“相時(shí)而動(dòng)”,不斷提供西方主體性建構(gòu)所需的對(duì)立性的文化觀念與元素。
周寧說(shuō),中國(guó)歷史形象“作為西方現(xiàn)代性想象的他者,具有重要意義,從文藝復(fù)興到啟蒙運(yùn)動(dòng)到帝國(guó)主義時(shí)代,中國(guó)歷史形象貫穿西方現(xiàn)代歷史敘事始終”。因此,欲探討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美國(guó)記者的紅色書(shū)寫(xiě),探討其建構(gòu)的嶄新的中國(guó)形象的文化與歷史語(yǔ)境,研究者就必須重訪作為“功能性的他者”的中國(guó)的文化再現(xiàn)的歷史。
伴隨啟蒙運(yùn)動(dòng)與西方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到來(lái),中國(guó)形象從遙遠(yuǎn)陌生卻充滿魅力的東方古國(guó)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文明的對(duì)立面。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新的社會(huì)與文化價(jià)值體系互為表里。這種西方現(xiàn)代性文明的話語(yǔ)體系是由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白杂伞薄捌降取薄安?ài)”“理性”“民主”等觀念建構(gòu)起來(lái)的。彼時(shí)的中國(guó)正好在時(shí)空的雙重維度上為西方的現(xiàn)代性價(jià)值觀念提供了一個(gè)自我認(rèn)知與確認(rèn)的參照物。東方與西方、古老與現(xiàn)代成了絕妙的兩副對(duì)子。“‘古今之爭(zhēng)’確立了現(xiàn)代優(yōu)于古代的觀念,確立了西方現(xiàn)代性的時(shí)間秩序;‘東西之爭(zhēng)’確立了西方優(yōu)于東方的觀念,確立了西方現(xiàn)代性的空間秩序。”隱藏在共時(shí)與歷時(shí)雙重對(duì)仗中的,是文明之間的尊卑優(yōu)劣秩序。這種秩序所外化的社會(huì)表征,是西方話語(yǔ)中的中國(guó)形象的轉(zhuǎn)變:“中國(guó)從過(guò)去那個(gè)被稱頌的文明優(yōu)越的國(guó)家變成了一個(gè)被鄙夷的停滯、落后、野蠻的專(zhuān)制帝國(guó),西方的中國(guó)形象從此便開(kāi)始黯淡了下去,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然而,經(jīng)歷了世界大戰(zhàn)的洗禮、經(jīng)濟(jì)大蕭條的沖擊,西方文明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jī)。此時(shí)的中國(guó),再次成為西方文明反思自身、想象可能的未來(lái)的文化坐標(biāo)。而美國(guó)記者群正是在這種總體性的迷茫與尋找答案的社會(huì)文化氛圍下出發(fā),去探索一種未知卻充滿可能性的“另一條道路”。
他們?cè)趯ふ沂裁?又能夠看到什么,就取決于他們經(jīng)歷了什么,反思了什么。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西方歷史“昨日”與“今日”的界線,“‘昨日’是一個(gè)安全、溫馨、繁榮、充滿信心和樂(lè)觀精神的世界,‘今日’則是一個(gè)滿目瘡痍、頹敗不堪、充滿動(dòng)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的世界。”對(duì)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反思,使得西方開(kāi)始質(zhì)疑一直以來(lái)引以為傲的代議民主制。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直指代議制本身,戰(zhàn)爭(zhēng)是由“西方政府一手導(dǎo)演的沒(méi)有民眾參與的秘密外交”造成的;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認(rèn)為根源在于此前讓西方各國(guó)引以為傲的民族主權(quán)國(guó)家,“國(guó)際社會(huì)的無(wú)政府狀態(tài)……源于民族國(guó)家的絕對(duì)主權(quán)”。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本身的價(jià)值受到質(zhì)疑。
其次,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打擊中喘息過(guò)來(lái)的西方世界又在十年后遭遇了經(jīng)濟(jì)上的大潰敗。一戰(zhàn)給歐美發(fā)達(dá)國(guó)家造成了1700億美元的損失,而經(jīng)濟(jì)大蕭條卻造成了2500億美元的損失。始于1929年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讓人們?cè)陴囸I之余開(kāi)始對(duì)美國(guó)自由放任的經(jīng)濟(jì)制度進(jìn)行反思,尤其是在與大蕭條時(shí)代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jì)狀況的對(duì)比之下,美國(guó)人開(kāi)始用一種新的眼光打量這個(gè)社會(huì)主義政權(quán)。大蕭條期間正值蘇聯(lián)的第一個(gè)五年計(jì)劃,到1932年底,蘇聯(lián)的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一戰(zhàn)前增長(zhǎng)了334%。此間更有10萬(wàn)美國(guó)人申請(qǐng)移居蘇聯(lián)。“一次大戰(zhàn)的發(fā)生,再加上大蕭條的爆發(fā),使自由主義陷入危機(jī),許多人對(duì)它喪失信心,不相信它能解決社會(huì)面臨的崩潰問(wèn)題。”舊問(wèn)題沒(méi)有解決,新問(wèn)題卻接踵而至。在1930年代,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guó)元首后,法西斯恐怖與新的戰(zhàn)爭(zhēng)陰云又籠罩了西方。西方國(guó)家在“何以解憂”的歷史憂慮中再一次被迫反思自身,并通過(guò)尋找新的文化坐標(biāo)重新確立自身的意義。
彼時(shí)的中國(guó)之于美國(guó)來(lái)說(shuō)就是一個(gè)新的文化坐標(biāo),“另一種可能”。面對(duì)自身制度的缺陷,在“末路”憂患意識(shí)的驅(qū)動(dòng)下,美國(guó)重新開(kāi)始去了解那個(gè)既熟悉又陌生的東方國(guó)度,甚至還出現(xiàn)了有一定官方組織背景的“美國(guó)記者團(tuán)”對(duì)中國(guó)的集中訪問(wèn)——開(kāi)始了又一次書(shū)寫(xiě)中國(guó)的“神話”工程。
因此美國(guó)記者們將目光投向中國(guó)西北一隅、黃土深處的、與自身制度截然相反的新生政權(quán),就顯得順理成章。不僅“因?yàn)樵谑澜绺鲊?guó)中,恐怕沒(méi)有比紅色中國(guó)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shuō)了”(斯諾語(yǔ)),更因?yàn)檫@個(gè)新生的紅色政權(quán),以及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所描繪的更加民主、進(jìn)步、文明的新中國(guó)的美好未來(lái),正是一個(gè)可以追求的“新的可能”。而這種可能充滿魅力,正如冉冉升起的紅星照耀中華大地。
至此,我們就能夠?qū)γ绹?guó)記者群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不遠(yuǎn)萬(wàn)里的來(lái)到中國(guó)的西北角,并用熱情和贊美的筆調(diào)來(lái)書(shū)寫(xiě)一個(gè)共產(chǎn)主義新政權(quán)產(chǎn)生出一種超越于現(xiàn)有的中國(guó)革命新聞史的述評(píng)結(jié)論——在這種述評(píng)中,這些西方記者被做為中國(guó)革命的國(guó)際精神支持者被記述和評(píng)價(jià)——而呼喚出一種“美國(guó)社會(huì)新聞史”的新理解。這種新的理解需要回歸到當(dāng)時(shí)的美國(guó)社會(huì)歷史情境中來(lái)獲得。在這種新的視野中我們才能夠更完整地理解他們的動(dòng)機(jī)、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本和他們的傳播行為。
注釋:
① 胡龍:《試論抗戰(zhàn)時(shí)期國(guó)際友人對(duì)中共形象的建構(gòu)——以“三S”為代表》,《新西部》,2016年第6期。
② 自從1937年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進(jìn)駐延安,延安便成為美國(guó)作家群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城市。但是,美國(guó)作家群活動(dòng)范圍不僅限于延安一城,如《紅星照耀中國(guó)》的主要內(nèi)容是1937年前對(duì)保安的采訪。
④ 由于編號(hào)41的Pyotr Vladimirov和編號(hào)65的Peter Vladimirov是同一人,蘇聯(lián)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的作者,所以有效人數(shù)為144人。崔玉軍:《抗戰(zhàn)時(shí)期到訪延安的美國(guó)人及其“延安敘事”》,《齊魯學(xué)刊》,2017年第5期。
⑤ 崔玉軍:《抗戰(zhàn)時(shí)期到訪延安的美國(guó)人及其“延安敘事”》,《齊魯學(xué)刊》,2017年第5期。
⑥ 包括:埃德加·斯諾(Edge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維克多·基恩(Victor Keen)、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Foster·Snow)、厄爾·利夫(Earl Leaf)、菲利普·賈斐(Philip Jaffe)、畢森(T·A·Bisson)、哈多斯·漢森(Haldors·Hanson)、陸茂德(Maud Russell)。
⑧ 譚天:《斯諾、毛澤東與〈紅星照耀中國(guó)〉》,《中國(guó)國(guó)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10期。
⑨ [新西蘭]路易·艾黎:《對(duì)埃德加·斯諾的回憶片段》,載劉力群編:《紀(jì)念埃德加·斯諾》,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頁(yè)。
⑩ 胡步芬、陳勇:《〈紅星照耀中國(guó)〉的對(duì)外傳播途徑與影響研究》,《東華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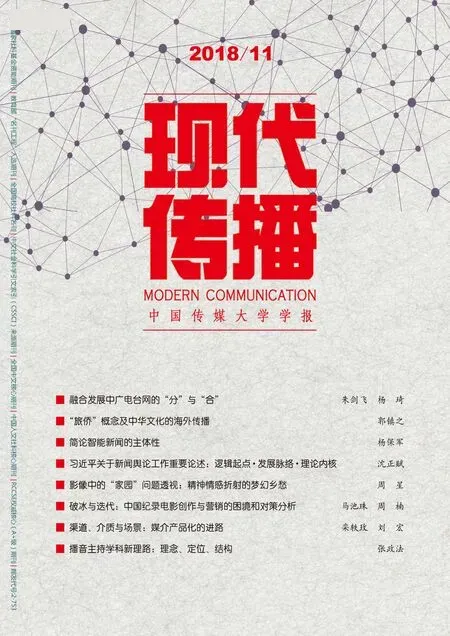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年11期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年11期
- 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中社交媒體內(nèi)容與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對(duì)轉(zhuǎn)發(fā)行為的影響*
- 品牌危機(jī)傳播中的信息回流模式研究*
——以百度的三次信任危機(jī)為例 - “邊緣媒體人”的職業(yè)變遷與社會(huì)階層*
——基于新聞民族志的觀察 - 破冰與迭代:中國(guó)紀(jì)錄電影創(chuàng)作與營(yíng)銷(xiāo)的困境和對(duì)策分析*
- 中外電視情感調(diào)解類(lèi)節(jié)目話語(yǔ)方式的對(duì)比分析
——兼論文化語(yǔ)境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如何影響傳播主體的話語(yǔ)策略 - 社交媒體時(shí)代新聞生產(chǎn)的事實(shí)核查方法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