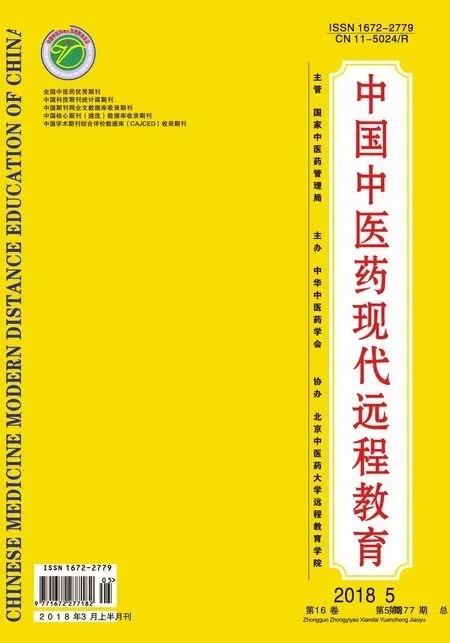論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章茂森 余 苗 陶湘云
作為一門以人體健康為研究與服務對象的學科,醫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兼具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屬性。身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人能夠逃脫神的支配,卻始終和自然與社會緊密相連。人的身體來于自然,且終將歸于自然,而人的精神,包括人之為人的尊嚴和自我認可,則成為了人區別于自然界其他動物的重要特征,整個人類社會,從古老的從前到現在,再到遙遠的將來,都是它有且僅有的生存土壤。人體健康是所有人類活動的基礎——無論是人的自然活動還是社會活動,而醫學就是人類在長期與疾病作斗爭的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如果說科學精神是只問是非,以人本為物的理性態度對待疾病以及病患,與之相對地,人文精神則是兼計利害,秉持著人不等同于物的觀點對醫學行為進行人文闡釋及引導。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兩條不同方向的道路,他們在名為“人”的路口交匯,也在此分野,呈現出漸行漸遠之勢。
伴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醫學迅猛發展,在科學精神一路高歌前行的同時,人文精神卻走向式微。科學至上論在包括醫學在內的諸多領域都獲得了極大認可,對科技的依賴、對科學精神的推崇使人們對許多潛在的或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與弊端重視不足,科學逐漸成為了唯一的評判與衡量標準。當我們將目光回歸到“人”的本身,會發現由于人文精神在醫學領域的缺失,越來越多的矛盾開始凸顯,而若是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僅僅寄托于科學精神本身,對于緩和矛盾的益處并不大。醫學要想朝著更加健康長遠的方向發展下去,不得不重新審視人文精神的地位與作用,并積極探索促進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統一融合的途徑。
1 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關系
“醫乃仁術”,自古以來,醫療行為就被賦予了極強的人文含義,行醫者正是在此基礎上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信賴。所謂“大醫精誠”,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貫穿于醫學發展的全過程,共同引領著古往今來的從醫者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除了醫術之外,醫德是人們用以評判醫者的一個重要標準。“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疏”,庸醫固然無法得到患者的信任,有的甚至會背上害人性命的惡名,但醫生若是背離了醫德,忘記了自身救死扶傷、濟世活人的天職,縱然有回春妙手,也無法修補與患者之間斷裂的信任紐帶,而醫患間缺乏了最基本的信任,各種矛盾自然接踵而來。因此,醫術與醫德事實上蘊含于人們對醫生這一職業的總體要求與期盼之中。
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主要是基于醫學的整體性。人在面對生死時難免脆弱,而醫護人員在面對疾病時也并非無所不能,所以醫療行為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治療動作,它以人為對象,不斷延伸成為一張互相勾連的復雜的網,當面對該不該做、該怎么做這樣的問題與選擇時,人常常會陷入這張網中,難以掙脫。也正是因為這張網,醫學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綜合體。科學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本質上始終是同人道有關的,只有依靠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雙軌發展才能讓醫學更好地應對難題,然而,這兩者本身因差異而產生的互斥以及因所受重視度的不同而導致的發展失衡嚴重破壞了醫學的整體性,制約了它的健康發展。
2 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發展現狀分析
“醫患矛盾”在當下醫療環境中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對于病人及家屬來說,醫務工作人員的態度成為了許多矛盾的導火索和觸發點。現代醫學常給人以“冰冷”之感,一方面來源于各種現代醫療器械帶給患者的直觀感受,更主要則是因為醫學的科學精神以理性思維為基礎,排除個人情感因素是對醫務人員專業性的要求之一。只是,當這樣的理性過度發展成為一種職業冷漠時,難免給群眾帶來“冷血”、不近人情的冰冷感受。當患者及家屬的情感訴求得不到滿足,就容易將自己的負面情緒發泄在醫務人員身上。雖然當今的醫患矛盾狀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但醫務人員對待病患、對待生命的態度無疑是醫患關系鎖鏈中的重要一環,也是醫學人文精神發揮作用的關鍵。
以醫患矛盾為突出代表的系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向我們展示了現代醫學所面臨的困境。即使醫療技術水平在不斷地提高,即使我們對醫學人文精神的探索并沒有停下過腳步,從醫人員的生存環境卻日趨惡劣,群眾對整個醫療行業的偏見和誤解也越來越深。若是從數據上看,隨著一個個醫學難題的破解,現代醫學征服了一個又一個高峰,可謂獲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在對科學精神的贊美和推崇聲中,它的雙刃效應也日益凸顯。無可否認的是,隨著科學精神的發展,人類對生命的敬畏感在漸漸消逝,人們習慣用科學來解釋一切、解決一切,生命的神秘性在這樣的認知過程中被消解。“在醫學科學的視野中,人是客觀存在的生物有機體,是一切機制都可以用科學的理性去加以剖析的。”[1]尤其在傳統生物醫學模式的影響下,病人成為了“機器”,人的生命有時也被完全地具象化為人的肌體。作為醫學的研究對象,生命的概念變得更加物質化了。
醫學科學力量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如今醫學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飛速進步,在攻克了許多難題的同時,也面臨著打破禁區的風險與誘惑。沒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但科學本身并不包含道德評判,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股越來越強大的力量若缺乏有力的約束與引導,極有可能成長為可怕的威脅。這種威脅不僅包含了付諸實踐的行動,更有對人們思維方式的“洗腦”。當越走越遠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展開正面博弈,人類對于“人之為人”的堅守就會變得更加艱難,或是走上更危險的異化之路,而醫學最終或與守衛人類生命健康的使命背道而馳。
當然,使現代醫學陷入“科學迷信”的做法絕不可取,而脫離科學精神談論人文精神的回歸卻也同樣是無益的。“單獨提升科學精神,必然會使科學主義泛濫起來;不用科學精神來定義人文精神的界限,人文精神就會淹沒在神秘主義和信仰主義中。”[2]醫而無術,何以生人?同科學精神的“實化”特征正好相反的是,人文精神容易陷入空泛化的窠臼,虛化它的研究對象,使自己變成空中樓閣,看起來高高在上,卻缺乏與現實的連接,而這也是造成當下醫學人文精神邊緣化處境的原因之一。沒有醫學科學實踐作為基礎,對醫學人文精神的宣揚只會變成一場脫離實際的空洞說教。因而無論是科學精神還是人文精神,在獨自面對醫學發展中的諸多難題時,總是不免暴露出自身的有限性來。
3 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融合趨勢探討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特魯多醫生的這句墓志銘是許多醫務工作者的信條,它告訴了我們在醫學局限性的前提下,醫者應該如何對待身為“人”的病患,更向我們說明了,在捍衛人類健康這場永無止境的戰役中,技術支持與人文關懷是同樣重要的武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逐漸取代生物醫學模式的地位,作為醫療服務的對象,人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特征也越來越得到現代醫學的重視,這就要求我們的醫務工作者更好地做到以人為本,以人為先。
事實上,在我國傳統醫學的探索發展過程中,就處處滲透著以人為本的思想。《素問·寶命全形論》中提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認為人是天地間最為寶貴的,濟世之道,莫大于醫,因而活人之業至關重要。人命至重,唐朝孫思邈在《大醫精誠》篇中強調,“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展現的是對生命一視同仁的尊重。晉朝楊泉在《物理論》中提出,“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認為醫者必須兼具仁善、明達、廉潔的品質,對從醫人員的整體素質尤其是道德水準提出了高要求,體現了傳統醫學對醫德的重視,對“仁術”的推崇。仁者愛人,在傳統醫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看來,對生命懷有大愛,才能對患者負責,才有資格真正地從醫。在醫學這個人道精神和人道思想最早產生的領域內,缺乏人文精神的醫生違背的是醫學的精神內涵。
在如今各單位都越來越注重追求軟實力的背景下,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發展成為了一種引領趨勢。如今大力提倡的“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醫學的人文關懷,將聚焦點從疾病轉移到患者身上來也體現了醫學的人文反思,包含了對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所處位置的思考。“‘情’與‘理’導引著醫學科學和醫學人學的行為選擇”[3],醫學的初衷是造福人類,而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激化的沖突與矛盾既是現代醫學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更是促使醫學不斷完善自我、探尋正確方向的一種鞭策,對于謀求人類共同福祉這一根本來說自有其存在的正面意義。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挽回失衡局面、維持新的平衡的努力中,更加深入地認識與思考醫學的本質和意義,努力順應并推動醫學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發展趨勢,為人類健康事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加寬容的環境,奠定更加牢固的根基。
總之,在醫學這艘大船上,如果說科學精神是槳,是現代醫學發展的動力,那么人文精神就是帆,是醫學前進的方向。他們既不能互相同化,也不可互相替代,更不該互相責難,只有通過溝通消除對對方的片面理解與二者間的現實對立,實現融通共建,才是現代醫學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無論是到以中醫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人文精神,還是在對醫學整體性的把握中重塑科學精神,我們都應當凝心聚力,營造和諧,為創造更好的醫療環境作出每個人應有的努力。
[1]張艷萍,張宗明.醫學科學精神與醫學人文精神交融——實現現代醫學模式的轉換[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8(3):164-166.
[2]高冀蓉,孫國平,黃朝陽,等.淺談醫學教育中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融合的意義[J].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增刊:156-157,160.
[3]董平,王曉燕.現代醫學發展中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J].醫學與哲學,1997,18(8):4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