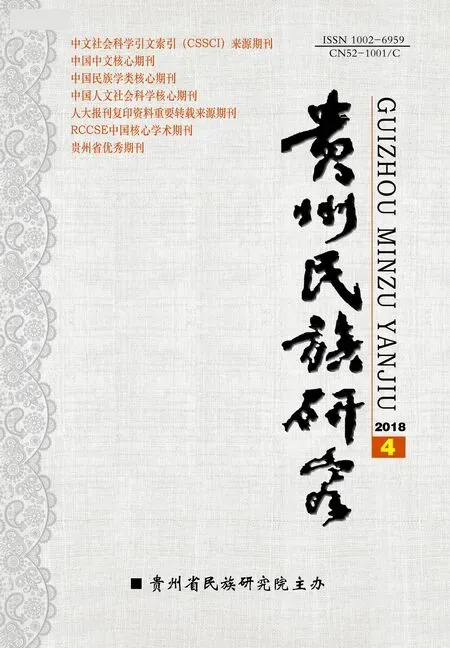“全球城市”的族群權利
姚尚建
(華東政法大學 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伴隨著資本的全球流動,城市從政治中心逐漸演變為資本中心。1938年,沃斯從城市作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提出人口規模、人口密度和文化異質性這三大城市核心特征對于城市性(Urbanism) 構建的作用。[1]在世界范圍內,城市資本與人口的流動既顯示了國家權力的重構,也意味著社會權利的變遷。在國家與族群的互構中,在國家的政治邊界中,“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關系成為了多族群國家認同研究中的‘元問題’。”[2]資本尤其是全球資本的流動進一步復雜化了這種認同,并在人口與資本相對集中的城市中,形成公共治理的多重困境。
一、資本、國家與族群的穿越
從國家的視角,治理體現為整體性與局部性治理的契合;從族群的視角,國家是族群生活外在的政治邊界。但是族群與國家的邏輯性差異決定了國家治理與族群治理的不同形態,當國家權力趨于開放時,族群的社會界限對國家的邊界的影響越小,反之,當國家權力趨于閉鎖時,族群的蔓延就會被政治隔離所橫亙,從而形成國家與族群的內在沖突。
首先,國家對于族群遷徙的規范性約束。德國民族學家李峻石(Günther Schlee) 在觀測肯尼亞北部和埃塞俄比亞南部以畜牧業為主地區的行政秩序和行政區劃時發現,由于族群自決納入憲法,因此行政單元往往沿著族群的界線展開。在這種新邊界出來之前,基于畜牧業的遷徙往往借助一些傳統機制,但是當新邊界出來之后,敵意和遷徙的限制便出現了。[3]政治邊界形成族群的內部的政治結構,也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中形成族群社會屬性向政治屬性的轉換。如果說作為社會學意義上的族群相處尚有傳統農業社會的彈性機制,那么在這一轉換中,建基于工業基礎上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剛性機制正在消弭這種社會彈性。
在一般意義上,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國家與族群通過身份互構實現的,這種互構也為國家治理的公正原則所確認:“國家有理由對人們出于種群、信仰、族群以及(最近出現的)性取向的理由而進行歧視的自由加以干預,正如非歧視所規定的一樣。”[4](P61)在一般的語境中,非歧視與區別容易區分,但是在國家制度的設計中,族群區別的背后有可能隱藏著歧視,歧視的背后則無法遏制沖突。在民族國家的內在邏輯中,沖突論是一種重要的觀點,“沖突論的核心思想是通過忽視、壓制乃至消除民族認同,來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統一。”[5]也就是說,在民族國家體系,當國家的框架無法容納族群的差異性時,族群有可能通過最終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形式來捍衛差異。
其次,國家對于族群生活的規范性約束。即使在國家的體系中,沖突依然存在。學者對于北愛爾蘭的敵對群體研究中發現,文化的同質性遠不足以保證人們和平共處。[3]因此,試圖通過建立民族國家來解決權利差異的問題有可能挑起新的社會沖突。在世界范圍內,跨民族國家是常態的政治模式,國家對于社會生活的基本規范在于,無論何種族群,在國家的框架中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利,任何族群不得擁有凌駕于國家政治框架之外的特權。在國家的治理原則中,平等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平等主義反對精英主義(elitist)、貴族主義的(aristocratic)、種族主義的(racist)和其他的觀點,這些觀點宣稱,有些人天生就優越于其他人。”[4](P93)國家通過法律捍衛這種平等原則。
社會善治的前提是良法,在不平等依然存在的國家,法律本身不過是不平等的社會規范的文字體現,“一個體面社會就是一個其社會組織不羞辱人民的社會……組織的羞辱分為法律的(如紐倫堡法案或其他種族隔離法所規定的)和運行方式的(如1991年洛杉磯警察毆打黑人羅德尼·金) 兩種。”[6]在國家的剛性邊界中,族群必須服從國家的政治規則。在爭取權利平等的斗爭中,族群的社會行為不停沖擊國家的政治體系,迫使國家逐步后退,從而促使國家由權力的共同體逐步演變為權利的結盟。
第三,資本激勵下的國家與族群的穿越。“族群性是集體身份認同的一種形式,它與宗教、親屬宗族、部族或者階級歸屬等現象屬于同一類別。族群性意味著,某一族群的成員意識到自己屬于該族群,而且確信別人屬于其它族群。”[3]在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中,族群的身份認同是一個重要變量,對于國家來說,在宏觀政治上追求國家認同,在微觀政策上確認族群身份,往往意味著更少的政治與行政成本。
非洲是現代國家制度發育較晚的地區,民族對于國家的理論證明尚需要制度的支持。族群的歷史往往伴隨著特定的傳統的興衰,對于擁有悠久游牧傳統的族群來說,國家的邊界限制了遷徙,并把流動的社會形態固定下來,從而形成國家與族群的政治張力。而在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上,這種族群的張力與國家的張力往往并不一致。李峻石發現,蘇丹人之間對于土地的爭奪較為激烈,但是蘇丹政府卻樂意將10萬英畝的土地提供給埃及,一個合理的懷疑就是這些擁有權力的蘇丹人更加認同淺膚色的埃及人。[3]也就是說,國家與族群之間,政治的邊界有時候并不吻合,借助于身份想象和文化標識,族群往往可以穿越國家的邊界,并在他者那里尋找自我。
國家和族群的邊界沖突并不僅僅受到身份的挑戰,資本的崛起以其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了工業革命確定的國家邊界,加快了族群的全球遷徙。阿馬蒂亞·森強調,在勞動市場的自由被法律、法規或傳統規范所否定的情況下,即使非洲裔美國人在做奴隸時可以得到與自由農業工人得到相同的收入,但是奴隸制本身就意味著基本的剝奪,自由市場的發展是重大的歷史進步。[7]市場保障了勞動的自由,全球市場保障了全球勞動的自由,借助于資本的全球流動,原先的國家、族群的邊界逐漸模糊,人們在共同的利益驅使下進入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共同體之中,從而給國家與族群的邊界重構形成新的變量。
二、全球城市社會的族群治理
城市是人類歷史中一個重大的成果。從農業社會的城市到工商業社會的城市,從中世紀的自治城市到現代工業時期的全球性城市,城市日益集聚大量的人口,并不斷挑戰現代國家與傳統族群的政治與文化邊界;而國際移民與國內移民一道,加劇了社會融合的復雜性,并深刻影響著城市治理與族群治理的邏輯演進。
首先,城市的復雜性與“全球城市”的話語轉換。從雅典到中世紀的城市,從簡單的圍墻合圍到城墻的拆除,城市在迅速地變化,“城市角色的轉換不是及時的,而是通過幾個進程,但這種改變就像一股快速的潮流,讓我們看到了1850年后的一百年內城市地理的巨大轉變,導致了復雜城市的形成,在形態、經濟、社會、文化上呈現多種多樣的變化。”[8]在交通與資本革命的驅使下,那些與鄉村嚴格區分的城市逐漸模糊了地理和政治邊界。一些雖處于特定國家之內,卻受到全球規則約束的城市開始出現。
全球城市的概念有個變遷的過程,弗里德曼和沃爾弗(Friedmann&Wolff)首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此后沙森(Saskia Sasen)則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加以修正。總體上來說,“全球城市”(或曰“世界城市”) 是指那些具有國際市場地位的城市。在這樣的視角中,那些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東方中小城市容易被忽略。正如彼得·紐曼和安迪·索恩利在《規劃世界城市:全球化與城市政治》中清晰指出:“我們不討論非洲和亞洲的一些城市,這些城市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系很少,她們只在自己民族國家的疆域內扮演有限的經濟角色……我們關心的是城市經濟功能的量級,以及能夠設定城市全球地位的聯系。聚焦這些世界城市意味著我們僅僅關注發達世界。”[9](P3)
其次,“全球城市”生活的族群屬性。全球資本的流動支持了全球性城市的存在,也瓦解了國家與城市的政治聯系。由于資本的介入,城市的形成與發展消弭了城市工商業與人口流動的可控性,從而使城市形態日益多元。雖然彼得·紐曼、安迪·索恩利并不過多關注東方的城市,但是他們也承認,“世界城市”假說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將城市的重要性按照功能而不是簡單的大小來區分,即是城市在全球網絡中的功能,而不是城市的大小決定了城市的地位。[9](P28)在“全球城市”論者看來,伴隨著全球資本的推進,作為次國家的城市的獨立性日益強化,并日益挑戰民族國家的政治等級,甚至挑戰國家與城市的利益互動。[9](P50-51)
在公元11世紀,西方城市借助于工商業重新崛起以后,城市就與資本的流動緊密聯系。“在全球化加速進程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是有其內在邏輯的。由于全球化的過程起源于地域經濟的擴展,因而全球化現象在地域經濟的集結點——城市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具體講,經濟的全球化在地域上產生了一種復雜的二重性:經濟活動在地域上的高度分離與全球范圍內的高度整合。這就產生了對高度分散化的經濟活動進行控制與管理的需要,而城市,特別是在區位上具有獨特優勢的大城市,無疑是進行這種控制與管理的最佳空間集結點。”[10]
“全球城市”的邏輯強調了城市在資本流動中的節點作用,卻容易忽視城市形成以來最基本的判斷——社會生活,從早期城邦到簡·雅各布斯對于城市理性主義的批判,都說明這一判斷確實存在。即使是資本的運作,也需要人力資源的參與,因此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是人力資源的全球流動。這些人口既流向世界城市論者所謂足以控制全球資本的城市,也流向了那些擁有全球市場的城市。在這些資本的流動下,不同的族群不但跨越了國家邊界,也跨越了文化邊界,從而使全球城市具有不同族群共同生活的屬性。
第三,全球族群生活的城市屬性。在民族國家的論證中,族群的邊界確認往往兼顧文化與地理。事實上,在波普爾看來,國際屬性早已存在,“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所有的歐亞文明國家都成了帝國,包括無數有著混合血統的人口。歐洲文明及其所屬的所有政治組織,此后一直帶有國際性,或者更為準確地說,帶有互為部落的性質。”[11](P97)波普爾在對民族國家的原則進行批判的時候,一定沒有充分想象在全球資本的沖擊下,當代“全球城市”的革命性意義,因為在波普爾的論述中,族群多沿著地理邊界歷史性地、緩慢地變遷,但是在民族國家已經成為基本政治原則之后,全球性的族群移民共同開展的城市生活遠非“互為部落”所能闡釋。
在全球資本的沖擊下,在白天的喧囂過后,夜晚降臨時,一些城市中以特定族群為服務對象的——諸如義烏市“土耳其餐廳”等——餐飲服務業開始繁榮,無不揭示了在資本的沖擊下,在“全球城市”之中,社會生活依然和特定族群緊密相連,不過是,那些波普爾所謂的“互為部落”已經演化為異地生活,這種異地生活本身既是族群性的、也是城市性的。
三、族群社會的城市治理
“全球化傷害了我們的城市嗎?經濟的起伏動蕩動搖了城市經濟的基礎嗎?隨著自由蔓延的資本和日趨擴張的國際競爭對地方重要性的削弱,地方民主能得到保證嗎?城市之間日益復雜的關聯性和依賴性將對地方民主的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12]在這一連串的追問之后,我們仍然要反思的是,當全球化成為一種現實,當城市借助資本與人口的遷徙成為常態之后,資本的撤離與人口的離開,哪一種會對城市形成新的傷害?
首先,確認城市社會中的群體權利。在國家與族群的關系上,波普爾的質疑具有代表性:“民族國家的原則,也就是說,每個國家的領土與一個民族的領土要相一致的政治要求,決不像今天它向許多人呈現的那樣是自明的……民族國家的原則不僅是不適用的,而且從來就沒有被明確地考慮過。它是一種非理性的、浪漫的和烏托邦的夢想,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和部落集體主義的夢想。”[11](P98)
波普爾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在民族國家理論的背后,是已經形成的國家與族群關系;而在國家與族群的關系背后,存在多數權力與少數權利的博弈。一般認為,公共領域的完整性要求國家漠視少數權利,但是在現代政治學中,作為整體治理主體的國家必須正視差異性群體及其權利的存在,“如果注意到所有可設想的群體權利,我們就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些問題結合起來。有些權利或許有這種效果,它們授予群體以與廣大社會相關的、重要程度的自主和自治。也就是說,它們允許群體退出廣大社會的事務,從而建立或多或少自給自足的小圈子。”[4](P275-276)
其次,促進城市族群的社會融合權利。多數權力與少數權利的結合是國家政體必須面對的制度性困難,也是一個城市政府所要直面的政策性困境。尊重少數權利會刺激城市乃至國家的瓦解嗎?羅伯特·L.西蒙的判斷是否定的。他引用了加拿大的一個案例,在這個案例中,錫克教徒(Sikh)不必遵守皇家加拿大騎警的行為規范,卻加強和促進了少數群體更強烈的政治包容意識。因為“它傳遞這樣的信息:他們參與廣大社會公共制度是受歡迎的,他們不需要放棄自己特定的身份也可以被認可為完全意義的公民。”[4](P276)
當然對于全球城市來說,成為國家公民并不是地方治理的首要選項,但是成為城市居民卻是城市治理的事實起點。歷史已經表明,只要人口匯聚,只要具有了工商業性質,城市注定就是一個異質性的組織存在。在抽象的公共利益背后,是大大小小的群體乃至個體利益。正如盧梭所判斷的那樣,“社會的組成可說是普遍性的傾向;只要個人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就組成社會——永久性的或暫時性的——每個社會都具有總意志來調節其成員的行為。大的社會不是由個人直接組成,而是由較小的社會構成;每個包括范圍更大的社會規定其組成的較小社會的義務。”[13]
第三,城市族群權利的實現機制。在列斐伏爾(一譯勒菲弗) 那里,進入城市意味著權利,這種權利是普遍、正義的,“將群體、階級、個體從‘都市’中排出,就是把它們從文明中排出,甚至從社會中排出。拒絕讓一個歧視性的、隔離性的組織將它們從都市的存在中排出,進入都市的權利為這種拒絕提供了合法性。”[14]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中,城市權利的實現取決于城市個體的城市角色,在戴維·哈維看來,這些問題恰恰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只有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后,哈維才堅信,“城市權利遠遠超出我們所說的獲得城市資源的個人的或群體的權利。另外,改變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賴于城市化過程中集體力量的運用,所以城市權利是一種集體的權利,而非個人的權利。”[15]從薩拜因的城市利益到列斐伏爾、哈維的城市權利,從個體到群體,城市理論完成了權利的轉變。
“全球城市”意味著權利概念的擴張,在民族國家邊界彌散之后,在全球公民社會仍然停留在理論爭鳴階段時,“全球城市”是否標志著更為廣闊的“全球權利”,那么在國家依然剛性存在的歷史階段,人們將如何確認這種權利的邊界及其實現機制?我們認為,在城市權利的理論轉變中,族群的權利實現并不矛盾,在全球資本裹挾著人口穿越民族國家邊界的時候,那些操著不同口音、有著不同文化傳統的族群人口在城市定居,城市政府應該尊重其城市社區“居民”的角色,并通過社區權力開放吸納不同族群人口的城市融入,即以社區理解城市、以城市認識國家、以居民吸納公民,從而實現城市權利的整體實現。
結論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eler)強調,“所有偉大的文化都是從城市中誕生的(city born),這是一個極為確定但卻從未被深入研究的事實……世界歷史與人類歷史不同,它的真正標準在于,世界歷史就是城市人的歷史。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這些都依賴于人類生存的基本形態——城市。”[16]全球化沖擊了民族與國家的雙重邊界,沖擊著人們建基于民族國家之上的城市體系,資本與權力相互聯合,改造著我們熟悉的城市。在城市的進程中,由于缺乏制度的捍衛,那些卑微的少數往往無法維系自身的權利,但是“城市權利即是一種對城市化過程擁有某種控制權的訴求,對建設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種控制權的訴求”[15](P5)。當我們認識到權利的集體屬性時,那些基于多數與少數、權力與權利的沖突才可能弱化,那些基于人類共同命運的政治主題才可能重新回歸我們的城市與生活當中。
:
[1]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4(1):pp.1-24.
[2]郝亞明.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共生:理論述評與探討[J].民族研究,2017,(4).
[3](德)李峻石.何故為敵——族群與宗教沖突論綱[M].吳秀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4](美)羅伯特·L.西蒙.社會政治哲學[M].陳喜貴,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5]盧鵬.邊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以中越邊境哈尼族果角人為中心的討論[J].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6](以色列)阿維沙伊·馬加利特.體面社會[M].黃勝強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引言.
[7](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13.
[8](美)詹姆斯·E.萬斯.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態學[M].凌霓,潘榮,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340.
[9](英)彼得·紐曼,安迪·索恩利.規劃世界城市:全球化與城市政治[M].劉曄 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0]周振華.全球化、全球城市網絡與全球城市的邏輯關系[J].社會科學,2006,(10).
[11](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M].陸衡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2](美)漢克·V.薩維奇,保羅·康特.國際市場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歐城市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葉林,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19.
[13](美)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冊) [M].劉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657.
[14](美)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M].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5](美)戴維·哈維.叛逆的城市[M].葉齊茂,倪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6]Oswald Spengeler,Der Unitergangdes Abendland es,轉引自(美)羅伯特·E.帕克等.城市[M].杭蘇紅,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