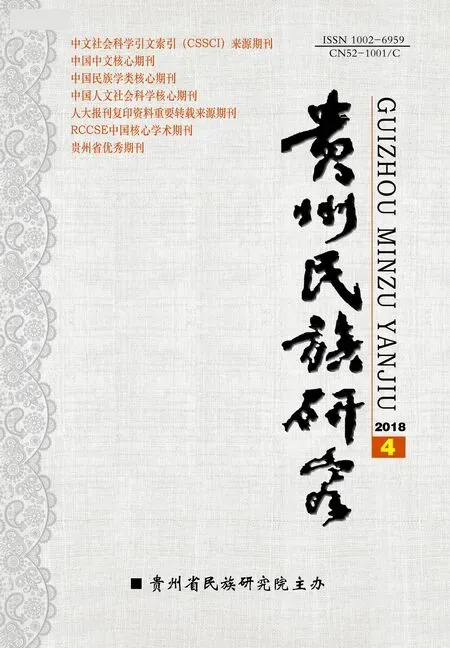苗族“亞魯文化”再認識
盧 勁
(貴州師范大學 學報編輯部,貴州·貴陽 550001)
201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苗漢雙語本的苗族英雄史詩《亞魯王》;2012年,貴州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亞魯王書系》。著名學者樂黛云、馮驥才、余未人、索曉霞、曹維瓊等為這兩套書作了評價和推薦。一經(jīng)紙質(zhì)圖書出版流布,《亞魯王》史詩,終于走出了深藏千年的苗疆麻山地區(qū),走入民眾的視野,古老、神秘的苗族的精神世界,震動了中國文化界。研究者們從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學、神話學、文學語言學等方面探索《亞魯王》的成就、地位,樂黛云概括認為“從中提煉出‘亞魯文化’的概念”[1]。
“亞魯文化”是以文化生態(tài)學理論為先導,把《亞魯王》史詩本體、傳頌者、流傳地的自然與文化生態(tài)狀況等關(guān)聯(lián)的文化事象進行提煉研究。就內(nèi)涵來說,“亞魯文化”蘊藏的上古史資訊繁多,古遠的歷史氣息深厚,是中國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今天民族凝聚力的意向圖騰。“亞魯文化”打破學科藩籬,其研究的對象,不再是孤立的亞魯王的詩歌讀本,而是把自然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與文本系統(tǒng)地構(gòu)建起來進行整體研究,原本的平面敘述變成立體化,原本碎片式的記載變成綜合性的文化記錄。
關(guān)注亞魯王史詩流傳背后的歷史環(huán)境,重視苗族與本地自然環(huán)境、文化語境的關(guān)系,這是我們解讀“亞魯文化”的一把鑰匙。
一、《亞魯王》是一部“活態(tài)”的苗族百科全書
今天的苗族,在東亞和東南亞分布廣泛。在我國境內(nèi),主要生活在貴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廣西、海南等省區(qū)。在境外不僅有越南、泰國等地有苗族居住生活,二戰(zhàn)之后,東南亞的苗族更廣泛移民到歐洲和北美等發(fā)達地區(qū)。
在苗族的民間口頭傳說中,中國上古時期九黎部落首領(lǐng)蚩尤是苗族的先祖。從生活在黃河中下游的九黎部落傳承到三苗部落,三苗主要生活地是長江以南的漢水流域。隨著中原華夏民族的不斷擴張,苗族開始向西南方向遷移,最終在云貴高原的山區(qū)定居。苗族定居麻山后,作為蚩尤后裔的亞魯王的神話故事日漸完整、豐富,《亞魯王》史詩于清朝末年完善定型。
亞魯王作為苗族的第十八代王,是具有神性的苗人首領(lǐng)。英雄史詩《亞魯王》開頭部分的敘事勾勒出苗族族源。
“是歲月之前/是歲月源頭/哈珈生了哈澤/哈澤生了哈翟/……他們是天上神圣的祖宗/他們是地上神威的始祖……”[2](P28)這是苗族創(chuàng)世紀的開篇。在宏大的開篇之后,接下來的整個結(jié)構(gòu),流暢大氣,程式規(guī)范莊重。細細讀來,便會進入遠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艱苦卓絕的生活氛圍中。
據(jù)《苗族古歌》記載,當蚩尤失敗后,苗族開始向西、向南遷移,經(jīng)五次大遷徙后,終于來到貴州高原的南部,在一個六縣交界被稱為麻山的地方安頓下來,這里雖然僻閉、荒瘠,但亞魯王這樣唱道:“這是狹窄的地域,這是陡峭的山區(qū)。這方能躲避追殺,見不到戰(zhàn)地烽火。”[3]最后在納岜立國,從此在“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喀斯特王國安身、勞作、繁衍……
《亞魯王》記錄了亞魯和他的族群的創(chuàng)世、征戰(zhàn)和遷徙的歷史。在苗語中,“楊魯”和“亞魯”以及“牙魯”皆是指同一個祖先。《亞魯王》對亞魯王之前九黎部落的17代王,每一代都作了簡略的描述。而主角亞魯王更是長詩的重點。在亞魯出生之后,“人家抓雞來取名/人家撿蛋來喊名/取名亞魯/喊名亞哈”[4](P94)。英雄的出身總是不平凡,亞魯不僅是“別人一天識三個字/亞魯一個時辰識三本書”,而且更能不學而知:“老師講天下/亞魯曉得天上”[4](P97)。他多才博聞,從上山擒鳥射獸到行軍布陣無不精通,更重要的是他還極負領(lǐng)袖的擔當,他在長詩中這樣表述:因為我的勇猛,我們才得到這塊棲身之地;因為我的智慧,我們才能守住這塊來之不易的領(lǐng)地。“亞魯命矮,亞魯命短”[4](P95),這是《亞魯王》中的一種傳唱,看上去頗有些與英雄氣質(zhì)不符的消極。但亞魯王是生活在民間的英雄,他與平常的苗人并無人神之隔,他是有血有肉、接地氣的膜拜對象。
在苗疆的現(xiàn)實生活中,《亞魯王》通常出現(xiàn)在葬禮上,是歌師(東郎)口頭吟唱的作品。讓逝者回歸,是整個《亞魯王》敘述的主要線索,在這條線索之上,貫穿亞魯王的生平事跡。學者朝戈金認為,“《亞魯王》具有類似‘指路徑’的社會文化功能”[5],在苗族先民面對生命的死亡與再生的關(guān)鍵點上,在傳承與延續(xù)的時間節(jié)點上,它的社會功能非常重要。吟唱《亞魯王》作為苗族葬禮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部分,給苗人帶去了非常重要的人生儀式,這種儀式感的提供,是《亞魯王》能夠流傳下來的重要社會原因。
上萬行的《亞魯王》是一部歷經(jīng)千年隱忍、苦難遷徙、血腥征戰(zhàn)的英雄史詩。《亞魯王》成果面世,為中國多元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給后代留下了一部“活態(tài)”的民族百科全書。正如馬克思早在1857年《〈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中就指出了藝術(shù)發(fā)展與物質(zhì)生產(chǎn)的不平衡關(guān)系[6],在中國古代,苗族物質(zhì)生產(chǎn)落后,他們悲壯、激越的史詩,是對現(xiàn)實困境的最大超越。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可以稱《亞魯王》是一個民族的標本。《亞魯王》使苗族這個民族鮮活起來,豐滿起來,字里行間,我們看到苗族是一個頑強、堅韌、不畏強暴、英勇善戰(zhàn)、不屈不撓的民族。信仰讓他們擁有尊嚴和骨氣!《亞魯王》是活在苗人心中的歷史,一個流動的、有生命的民族傳承。同時,《亞魯王》這部英雄史詩的宏大敘事,也體現(xiàn)并完成了它在民族學上的典型意義。
二、“亞魯文化”彰顯英雄史詩恢弘的架構(gòu)
民族民間敘事詩貌似與民族史詩同類,但史詩不同于敘事詩。無論在規(guī)模上、體量上、結(jié)構(gòu)上,表達方式上,史詩都自有其獨特性。史詩結(jié)構(gòu)宏偉,卷帙浩繁,內(nèi)容豐富,氣勢磅礴,流傳廣泛,這是民族民間敘事詩遠不可比擬的。史詩是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同時也是人類早期生活歷史的一種反映,在沒有文字記錄的時代,史詩就是歷史,是無法替代的人類早期精神作品。《亞魯王》及其背后的“亞魯”文化,對我們今天的價值意義也在于此。
中國是個史詩大國,從南至北,都流傳著大量的口頭史詩,不少獲得搜集整理和研究。其中著名的《格薩爾王傳》 (藏族)、《江格爾》 (蒙古族)和《瑪納斯》 (柯爾克孜族),它們都可與荷馬史詩媲美。貴州苗族的《亞魯王》的出現(xiàn),是中國史詩譜系中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重要精神作品。
苗族史詩《亞魯王》的架構(gòu)具有豐富的民族文化內(nèi)涵,包括創(chuàng)世史詩、征戰(zhàn)史詩、遷徙史詩三個要素。這個架構(gòu)特征,集中地映射著一個民族探索人生、寄托理想的精神世界和歷史觀。以下簡敘這三個要素。
(一) 創(chuàng)始史詩(Creation Epic) 要素
在許多的民族史詩中,都有過多個太陽并存的傳說。在《亞魯王》中,創(chuàng)世的亞魯王指派兒子創(chuàng)造了十二個太陽和月亮,又讓兒子射落多余的日與月而只各保留一個,這是亞魯王神性能力的集中表現(xiàn)。與其他民族的創(chuàng)始傳說不同,亞魯王同時具備了太陽創(chuàng)世與月亮創(chuàng)世兩個傳說的因素,亞魯王作為泛神崇拜的對象,其神性能力更被提高。同時我們也要注意,這是苗族人民從一般神靈崇拜向自身崇拜的升華。
“女祖宗她們一次又一次地造人/男祖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造物/女祖宗她們造成了歲月的開始/男祖宗他們接著造歲月的輪回/造天造九次/造人造九次/得了歲月的開始后來的歲月就跟隨/有了天才有地/有了太陽才有月亮/有了種子才有枝椏”[2](P77)。“十二棵樹生于一個樹樁/十二棵竹生于一個根兜/十二只鳥飛出于一個窩”[2](P80)。遠古創(chuàng)世,是所有史詩共同涉及的。《亞魯王》“創(chuàng)世紀”部分,用大量篇幅講述宇宙起源、日月星辰形成,還記錄了大量的神話、傳說、歌謠和諺語。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主席馮驥才認為,在自然條件極其艱苦的麻山地區(qū),苗人的生活狀態(tài)也非常原始,這時,精神信仰成為了苗人最重要的生活支持力量,而亞魯王就是這種精神力量和精神信仰中最核心的基點要素。“這便是亞魯王數(shù)千年傳唱不絕的根本緣故。”[7](P4)
(二) 征戰(zhàn)史詩(Campaign Epic) 要素
從古至今,人類社會的重大轉(zhuǎn)折都是由戰(zhàn)爭引發(fā)。亞魯王從來不好戰(zhàn),而是被迫轉(zhuǎn)戰(zhàn)。《亞魯王》歷數(shù)亞魯王征戰(zhàn)的多次戰(zhàn)役,但并非一味贊頌其武功之強大,《亞魯王》記敘的征戰(zhàn)極具悲劇色彩,因為大部分的戰(zhàn)爭結(jié)果都是悲慘的失利。其中以亞魯王攻打盧咼王國一戰(zhàn),最為壯烈。史詩中,即使亞魯王使盡渾身解數(shù),戰(zhàn)爭過程更是流血漂櫓、尸橫千里,但結(jié)局卻是悲劇。
“亞魯王叫歐德聶帶兵朝前去/亞魯王叫岡塞谷點將護衛(wèi)在后/亞魯王的兵拽著牛尾倒退朝前走/亞魯王的將反穿著草鞋朝前去/亞魯王帶兵來到了江岸/亞魯王帶將來到了灘邊/亞魯王的兵牽著牛來渡了江/亞魯王的將換下了反鞋來渡船/亞魯王的兵爬上了船渡去了下方/亞魯王的將爬上了竹筏渡去了下方/……公龍藏身在江中央/公兔藏身在浪濤里/公龍來撞亞魯王的船底/掀翻了亞魯王的三群兵去江底/公兔來撞亞魯王的筏底/掀翻了亞魯王的三群將進浪里……”[8](P247)
“我?guī)砹耸f兵/我?guī)砹似呷f將/亞魯王的馬兒長嘯破空蕩/亞魯王飛奔鐵蹄環(huán)繞著弘炅的將群”[9](P142)。征戰(zhàn)、失敗、再征戰(zhàn)、再失敗,苗族的創(chuàng)世者并非戰(zhàn)無不勝。“哀哀吾父魯王門生,悠悠蒼天而今逝矣”,他們砍馬祭祀,就是要給靈魂找到一條回歸到祖先榮土的道路。死亡是一種回歸,成為苗族信仰中的一個恒常不變的命題。在戰(zhàn)場上跟隨亞魯王殺伐的苗疆勇士,以戰(zhàn)死為榮。死亡不是一個終點,而是跟隨亞魯王走向神圣的永恒。艱苦卓絕的戰(zhàn)爭殺伐由此可見一斑。
《亞魯王》史詩貫穿的是嚴酷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
與在葬禮上口頭傳唱《亞魯王》相伴隨的,常常是一個“砍馬”的儀式。在進行完莊嚴慎重的葬禮儀式之后,一匹用來犧牲的“戰(zhàn)馬”會被砍馬師砍死。通常這個砍馬儀式伴隨著古老的銅鼓聲進行,在銅鼓聲中,馬匹會被砍得血流滿地轟然倒下。據(jù)苗族傳說,“戰(zhàn)馬”的犧牲,是用來紀念亞魯王當年在戰(zhàn)場上的殺伐。通過這種血腥的場面,讓后輩記住亞魯王所經(jīng)歷的生死考驗[10]。
亞魯王是苗疆人民世代歌頌的開拓者,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神,而是具有神性,但又在民間有血有肉的創(chuàng)世者。他智慧深遠,性格豪邁,為苗疆人民開疆拓土。所以在苗疆世代的頌揚中,他與他的子孫們休戚相關(guān),在東郎歌師的吟唱中世代流傳。
(三) 遷徙史詩(Migration Epic)) 要素
歷史上,戰(zhàn)爭與遷徙多發(fā)性地聯(lián)袂而行。《亞魯王》濃縮了征戰(zhàn)與遷徙悲壯。亞魯王為率眾遠走他鄉(xiāng)篳路藍縷,充滿艱辛。對于苗族而言,他們的歸途并非是超脫俗世的和平天堂,人世間的離合悲歡也并沒有終結(jié)。他們總是朝著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前行,這是他們漫長的回家之路,也是亞魯王遷徙征伐的足跡。苗族人就是這樣用《亞魯王》為精神地圖,穿越歷史時空,指引亡靈回歸。
當年蚩尤與黃帝在河北的涿州大戰(zhàn),蚩尤戰(zhàn)敗,被迫南遷。最后亞魯王帶領(lǐng)70名王妃和初生的王子,遷徙到貴州,先后開發(fā)定都在“商都卜、扁甘”(貴陽)和“阿代卜、霧路”(安順),最后定都麻山,刀耕火種,重新開始生活。
《亞魯王》從一個方面記載了這段歷史:
“亞魯王攜妻兒跨上馬背/亞魯王穿著黑色的鐵鞋/亞魯王族群的孩子啼哭聲哩啰呢哩啰/亞魯王族群的嬰兒啼哭聲哩啰呢哩啰/亞魯王放棄了家園帶著干糧就上路/亞魯王舍棄了村莊帶著糯米飯就上路/亞魯王帶著撕碎了心的族群踏上了渺茫征程去前方路漫漫/亞魯王領(lǐng)著裂碎了肺的族群踏上了浩瀚去前方路長長……”[11](P264)
“亞魯王帶著族群來落到了哈榕吶英/這是一片寬闊的領(lǐng)域/這是一個平坦的村莊/水源豐富/糧食豐盛/可是躲避不了追殺/也躲避不了戰(zhàn)爭/亞魯說了將來這里不能養(yǎng)我兒我女/亞魯說了這里不能養(yǎng)我族群……”[10](P265)
苗族是一個長期遷徙的族群。其遷徙歷史之長,地域之廣,為世界之罕見。
苗族的遷徙,不止于遷徙,更是一種生活方式與文化的再繁殖。遷徙遠方的目的,不是逃亡,而是在新的家鄉(xiāng)墾荒深耕,甚至發(fā)展商業(yè)。史詩中記載的亞魯王不僅是苗族農(nóng)耕文明的開創(chuàng)者,也開創(chuàng)了以鹽、鐵為核心產(chǎn)品的苗族商業(yè)文明。他最早開鑿了山里苗人最稀缺的鹽井,還發(fā)明了最早的冶鐵技術(shù)。同時,亞魯王以十二生肖為單元,建立十二個集市,輪番經(jīng)營。至今,貴州農(nóng)村的一些定期的集市,還保有牛場、馬場、豬場、猴場、狗場等原有名稱。這種涉及到商業(yè)文明的早期記錄,在其他民族的史詩中并不多見。
《詩經(jīng)·衛(wèi)風·氓》中曾有“氓之蚩蚩,抱布貿(mào)絲。匪來貿(mào)絲,來即我謀”的吟唱。所謂“抱布貿(mào)絲”就是你拿布來換我的絲。這是遠古時期的商品交易方式。苗族的亞魯王帶領(lǐng)的制鹽、賣鹽,也是商業(yè)的雛型。
一部史詩往往就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寶庫。《亞魯王》完整呈現(xiàn)的苗族先民的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其原始史料的價值之高不可衡量。
三、“亞魯文化”呈現(xiàn)彌足珍貴的口頭活態(tài)傳播
《亞魯王》不是純粹的文藝作品,一開始就沒有固定文本。它的形成是從苗族歌師口頭的吟唱開始,經(jīng)過無數(shù)的歌師不間斷的口頭再創(chuàng)作、再傳播,吟唱-創(chuàng)作-傳播是很難區(qū)分的一體化文化行為,所以,其發(fā)掘、整理、翻譯,是艱難曲折的,是一個個奇跡。《亞魯王》再次證明,口頭文學是一個民族文學的源頭。
歌師,在苗族當?shù)胤Q為東郎,他們的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傳遞是形成《亞魯王》的關(guān)鍵所在。麻山地區(qū)有二十五個鄉(xiāng)鎮(zhèn),十八萬人,會唱《亞魯王》的歌師,每個村寨大約都有四五人,歌師總數(shù)約為三千人。千百年來,是他們以自己的歌喉、他們的記憶傳承、豐富、發(fā)展著古老的英雄史詩。這形成了《亞魯王》口頭傳播的活態(tài)路徑。
唱誦是程式化的,還有程式化的重復吟詠、疊唱,才能口口相傳至今。東郎們在每一場葬禮上都要唱誦,有的唱七天七夜,有的唱三天三夜,至少也得唱一天一夜,在殺雞、砍馬的氛圍中,唱誦激越、悲愴的英雄史詩。他們以口頭活態(tài)的旋律、程式來構(gòu)建自己心中的史詩,他們的每一次唱誦,是在唱誦中創(chuàng)作,他們屬于傳統(tǒng),同時又是創(chuàng)造性的民間藝術(shù)家個體。千百年來,東郎們的“即興創(chuàng)作”,讓逝者沿著先祖亞魯王作戰(zhàn)、遷徙的漫漫長路,返回祖靈所在地。
既是“即興創(chuàng)作”,就包含了許多個性化的不穩(wěn)定因素,呈現(xiàn)常有的變異。東郎們長期處于交通閉塞的大山間,有的識字,有的不識字,他們在肅穆的唱誦氛圍中,個人意志、情緒的表達每次都不可能雷同,唱誦的長度、停頓,從來沒有固化。由于個人記憶各異,自行發(fā)揮,一些語詞的含義他們自己有時候也不甚清楚。在一種慣性推動下的唱誦,特定語境中口頭敘事,與古詞語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不一定具有邏輯性,這在客觀上為語義闡釋構(gòu)成了一定障礙。但是,這種充滿流變的口頭傳播,提供了珍貴的研究價值,尤其是對研究苗族的文化語境和社會情境來說,是異常難尋的。
被授予“中國民間文化守望者”的苗族青年學者楊正江,曾用苗文記錄了16000多行唱誦,對自己親自記錄的詩行的含義,領(lǐng)悟也頗費周折。記錄工作也如此浩繁,深奧。《亞魯王》因為流傳的地區(qū)相對比較固定,所以帶有明顯的“地方性”。因此,《亞魯王》更具有“小傳統(tǒng)”的稀有樣板意義。
從口頭語言到文字語言,存在語言轉(zhuǎn)換的問題。苗族歷史上,在本世紀初貴州威寧地區(qū),英國傳教士從苗族服裝的圖案里得到啟發(fā),用苗族圖案和拉丁字母創(chuàng)制了一套簡單易學的苗文,雖然流布有限,還是用這套文字編印了《苗文基礎(chǔ)》《苗族原始讀本》,這在民間被稱為“老苗文”。由于時間、空間的錯位,麻山地區(qū)一直沒有苗族文字。要將歌師的口頭唱誦,以拼音式苗文筆錄下來,并譯成漢文,難度可想而知。而且,記錄的抄本,要盡可能還原、保持為麻山東郎的口傳風格。這是《亞魯王》的傳承和傳播的難度。
董仲舒曾提出“詩無達詁”之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華》)。“達詁”的意思是確切的訓詁或解釋。古代的《詩經(jīng)》也沒有通達的或一成不變的解釋,因時因人而有歧異。《亞魯王》的口頭創(chuàng)作變化不定是常態(tài),傳承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希望《亞魯王》成型是一種好意,要求每次唱誦不變卻不現(xiàn)實,也不可能。上千位東郎們的唱誦莊嚴肅穆,追求本真,不帶有娛樂性,這就決定了唱誦走向相對穩(wěn)定的一種經(jīng)驗性路徑,既為創(chuàng)作,也就不存在辨?zhèn)巍?/p>
《亞魯王》的口頭傳播與葬禮儀式密不可分,吟誦《亞魯王》并非娛樂,而是為亡靈引路。《亞魯王》所具有的史詩一般的神圣性,與肅穆的葬禮合為一體,豐富了史詩研究的內(nèi)容。同時,整理成苗漢兩種文字的《亞魯王》圖書的出版,更為今天的民族學、文學的研究者提供了生動的現(xiàn)代案例:《亞魯王》敘事風格的多重性,使這部苗族史詩包羅了傳說、故事、神話等口頭文化遺產(chǎn)的精華。
中國其他民族的史詩,往往都有文字而以手抄本的方式傳播流行。比如西藏地區(qū)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蒙古地區(qū)的史詩《江格爾》和在湖北神農(nóng)地區(qū)流傳的漢族史詩《黑暗傳》。沒有文字和抄本的苗族《亞魯王》,依靠眾多東郎的口口相傳而傳承至今。這也導致了《亞魯王》的版本繁復、內(nèi)容多樣。口頭文學活態(tài)存在的特征,是《亞魯王》另類的傳播學意義。
民間文化是我們民族凝聚力的沃土,民族的凝聚力在民間就是一種親和力。同時,挖掘、傳承民間文化,也是面對傳統(tǒng)的一種回歸教育。民間文化傳統(tǒng)的活力與精髓,才是真正的“活著”的民族精神遺產(chǎn)。《亞魯王》精神遺產(chǎn)的傳承,極大豐富了苗族的公共精神遺產(chǎn)。
2011年5月23日,《亞魯王》列入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第三批)。這再次證明它的史詩價值。它對苗人心靈的征服力是最強悍的,它不愧為苗族精神與生活的歷史經(jīng)典。它昭示了苗族文化達到的歷史高度,其歷史意義遠遠超出史詩文本本身。
“亞魯文化”,對民族學、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學、神話學的學者極具啟示價值。面對浩瀚的歷史長河,面對我們許多未知的地域,文化學者不能停下探索的腳步。“亞魯文化”的挖掘、整理與提煉,就是民族文化領(lǐng)域鮮活的探索實例。
[1]樂黛云.史詩頌譯總序[M].亞魯王書系:史詩頌譯,楊正江,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2]楊再華,口述.亞魯王降世[M].亞魯王書系:史詩頌譯,楊正江,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3]盧惠龍.一個民族的標本——讀苗族史詩《亞魯王書系》[N].貴陽日報,2014-01-21(A11)
[4]陳興華,黃老金,口述.亞魯王落到地方[M].亞魯王書系:史詩頌譯,[M]楊正江,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5]朝戈金.《亞魯王》:“復合型史詩”的鮮活案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03-23(A05).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2.
[7]馮驥才.發(fā)現(xiàn)苗族英雄史詩《亞魯王》(序)[M].苗族英雄史詩:亞魯王(史詩部分).北京:中華書局,2011.
[8]陳興華,陳小滿,口述.血紅大江[M].亞魯王書系:史詩頌譯,楊正江,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9]陳興華,黃老金,口述.亞魯王征戰(zhàn)[M].亞魯王書系:史詩頌譯,楊正江,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10]余未人:發(fā)現(xiàn)苗族英雄史詩《亞魯王》[N].貴州日報,2011-03-17.
[11]陳興華,口述.亞魯王遷徙[M].亞魯王史詩頌譯,楊正江,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