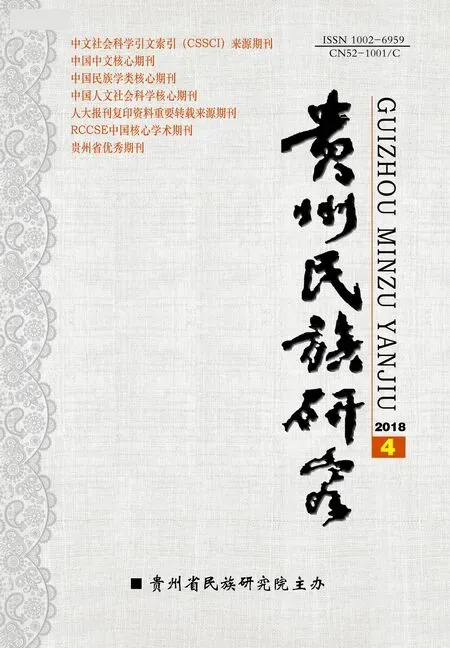新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與創新
鄢秀麗 戎龔停
(阜陽師范學院 音樂舞蹈學院,安徽·阜陽 236041)
新時代語境下,外部音樂文化在與獨特、鮮活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接觸時,呈現出相互頡頏的面貌。由于歷史原因,外部音樂文化在改變少數民族音樂生存環境的同時,以其強勢的傳播模式和傳播速率引發了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模式的變遷。相對于外部音樂文化作為異質文化,在接觸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時,會引發其原有文化模式變化的這一涵化過程,包括文本化在內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自覺而非自發的傳承,則多的是被動、搶救性質的保護,是面對飛速發展的技術手段與劇烈變遷的社會環境的一種抗御。本文試圖通過厘清新時代語境下外部音樂文化對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涵化及新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對外部音樂文化沖擊的抗御這個一體兩面的傳播過程及影響這個過程形成的因素,探索新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傳承與創新之道。
一、新時代語境下外部音樂文化對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涵化
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是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弘揚和發展面臨著諸多問題。這其中不僅包括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由于獨特性、少數性和異質性所面臨的個別問題,還包括在面對外部音樂文化強勢沖擊時,由于通訊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所導致的中華民族傳統音樂所面臨的共性問題。
(一)沖出封閉區:彌平區域傳播隔閡的媒介傳播
長期以來,我國少數民族以大雜居、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崇山峻嶺、高原低谷間,天然封閉的地理區隔造就了其文化藝術獨特的形態、樣貌和別有風情、自成一脈的形式。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作為少數民族文藝的最主要形式之一,承擔著區域及族群內部情感交流、生活娛樂、宗教祭祀的重要作用,形塑和強化了少數民族內部的地緣感和親緣感,并以其不僅融匯少數民族特色語言和特色內容,而且具有超語言、超民族表達的交流能力的優勢,作為民族名片聲傳廣遠。可以說,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對內起到加強該民族內部個體對族群認同及少數民族人民對自身民族身份體認的作用;對外則起到塑造、介紹該民族的民族形象、民族性格的作用。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是民族生活情境的反映,是民族生活的重要研究素材。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封閉的地理環境都成為了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存留和傳承的天然屏障,在高山深谷中雜居或聚居于偏遠邊陲的少數民族,通過自然傳播的方式保存和積累了大量頗有價值的原生態音樂。
然而,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地理上的區隔被迅速彌平,新媒體真正實現了麥克盧漢“地球村”的創想,外部音樂文化以不可一世的姿態無差別地隨著電波流動投射到每個用戶的終端上,作為強勢文化的外部音樂文化擠占了原屬于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的注意力,同時隨著信息總量的增加,在浩如煙海的信息中淘洗、保存和傳襲純粹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難度越來越大。這些珍貴而稀少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作品不僅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自然風化,在空間上也不再具有因封閉空間所形成的遺世獨立的自然保護,甚至由于受眾零和的注意力,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新時代語境下,媒介傳播彌合了空間障礙,導致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難度不斷提升。
(二)話語權剛需: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失根斷流的巨大隱患
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所依賴的自然傳承和自然傳播不斷被外部音樂文化侵蝕,如火般的攻勢間,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保護已經由自發進入到自覺階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文本化等工作在內的記錄工程速度越來越趕不上其消失的速度,文本化項目工程、系統性的志書編纂作為一個個系統工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原始形態仍在流失,面臨后繼無人、失根斷流的窘境,其主要原因是無法有效利用媒介傳播、教育傳播等手段,橋接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日常化的傳承、傳播與項目化的保護工程與措施,這二者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使保護工作事倍功半,費力而不討好。
教育傳播為這種外部音樂文化對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攻城略地,一律化、標準化的義務教育因目前條件所限而缺乏因地制宜的靈活性,少數民族適學齡兒童作為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潛在傳承者一旦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就開始脫離原來的語言環境與生活環境,學習普通話和西方音樂、現代流行音樂,這種系統化、程序化的義務教育使校園內的藝術教育在起到提升適學齡兒童音樂素質、音樂素養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卻也異化為“遺產化”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過程。某種程度上可直言,僵硬的藝術教育導致了全民缺失對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可能在藝術地位上失去話語權的警惕,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警鐘不斷鳴響,在新時代語境下,越來越刺耳的嗡鳴在催促和召喚學者和業者做出努力,從政策層面、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重視重奪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傳承主動權和總體音樂評價體系話語權的問題,推動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創新發展。
二、新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對外部音樂文化沖擊的抗御
(一)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志書編纂
“盛世修史,明時修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集成志書”的編纂工程成為進入少數民族傳統文藝形式與內容記錄和保存的“后集成時代”的時間節點,至今的三十余年以來,不少學者一直筆耕不輟,致力于深入少數民族地區積累采風,記錄下了大量珍稀的優秀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本。這種自上而下展開的系統工程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上的優勢,趕在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消失前先將其進行文本化,就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搶救意義上講,對保存和傳承難以為繼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三十余年的這次大規模的音樂記錄與保存工程,是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對變遷中的中國的數字化和城市化的抗御過程。伴隨通訊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賴以為生的自然傳播環境被破壞,傳播形態被迫改變和延伸,學者和業者逐步意識到了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傳承需從自發到自覺,重整困境下傳承創新的新思路。因此,無法否認的是,盡管在三十年來志書編纂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留下許多不可替代的成果,這次“后集成時代”的志書編纂工作,仍不可避免地帶有越來越明顯的搶救性,我們所得到的成果,正是迅速消逝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迅速退出歷史現實的表征。
這種被動的抗御充滿著衰弱的氣息,盡管這種抗御是必要的,但卻并非積極的,這提示我們,在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和保護中,還要另找新路。
(二)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參與外部音樂文化
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是否也嘗試主動參與過同外部音樂文化的合作與競爭呢?事實上,就競爭層面來說,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相對于外部音樂文化作為弱勢異質文化,并不具有競爭的量級,多數時候,盡管二者共同分享了受眾的注意力,但由于其比重的懸殊,學者和業者也難以就競爭的角度來分析二者的關系。但許多業者卻為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參與外部音樂文化的合作頻頻嘗試,這當然不僅是源于業者對于民族音樂文化的社會責任感,而且還源于當代外部音樂文化的商業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使其可以包容也愿意包容這些色彩鮮明、具有生命力的優秀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許多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以其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特點被引入到流行音樂中,成為豐富流行音樂曲調和樂感的元素。長調和呼麥被音樂人發掘,加入到《歌手》等音樂競演電視綜藝節目中,在音樂真人秀中作為音樂元素和宣傳元素雙管齊下,起到了豐富節目內容的作用。
勾連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與現代流行音樂、外部音樂文化的主要共同利益點其實仍是在于具有商業效益的媒介產品的生產和傳播。《歌手》等極具商業效益的媒介產品需要足夠的傳播力度,因此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作為看點被納入了現代流行音樂中,在編曲風格一致、意境相協的作品中,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成為作品主體錦上添花的存在,但在這一過程中,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所能主宰的部分相當有限,多是作為音樂元素參與到競演節目中,因此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和作品背后的內容、思想、文化意涵均難以展現。簡單來說,這個過程是現代流行音樂、外部音樂文化為主,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為用的過程,它的確使一些優秀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被普通人所知,但力量非常有限,因為它背后的邏輯還是商業邏輯,于商業利益有用的部分就會被拿來,沒有用的部分則會被摒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作為參與者,事實上則缺乏話語權。
三、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傳承與創新策略
(一)少數民族傳統原生態音樂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元素區別對待,分開保護
面對外部音樂文化強勢東漸,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成為了當務之急。學者、業者對于少數民族音樂傳承與面對市場時的態度分為了涇渭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少數民族音樂的傳承保護最重要,少數民族音樂的特色和魅力就在于其原汁原味、獨一無二的本來面貌。保持少數民族音樂原有樂器和語言演繹、原有曲調記錄是少數民族音樂傳承和保護的必由之路。即使加入創新,進行再創作時也絕對不能喧賓奪主,應該在保留其原有特色的基礎上進行較少的修飾,絕對不能盲目迎合流行與市場。另一派則認為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保護和創新先要使其得到傳承,無法使這些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聲音聲傳廣遠,無法使更多的受眾認識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魅力,主動成為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者,就無法進行下去。因此應該與市場達成和解,首先要推廣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元素,使其具有傳播力。這兩種觀點其實并不沖突,其實質和目的,都是為了最大限度上留存這些珍稀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內容。只不過一方的觀點頗具精英眼光,充滿了對原生態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純粹性的渴望;另一方則更現代、更圓融,更具傳播者的視角,渴望橋接傳播力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
筆者認為,現代的一些概念可以被引入到分析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保存及傳承的思路中來,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也應當被“細分”。在學者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志書編纂、文本修訂的過程中,可根據該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功能進行辨別和分類,對于具有傳播潛力的音樂元素,可以參照長調和呼麥,進行流行化推廣。對于瀕危的樂器、器樂、音樂文本、技巧等則要考慮早做記錄,保持其原生態性。這二者怎么辨別?可以從功能等角度來區分,用于生活娛樂、表達感情的“娛人”類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一般來說更適宜大范圍傳播,主要功能用于宗教、祭祀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如儺戲則多形式肅穆、沉重莊嚴,氣氛可能難以與現代流行音樂相適應,當然,這只是較粗略的辨別手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需要有經驗的學者和業者進行深入和仔細的辨別與思考。
(二)注重技術傳播,充分橋接新媒體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
新媒體的參與的確彌平了外部音樂文化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傳播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區隔,致使強勢文化的涵化效用進一步延展,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生存空間,帶來了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傳播與發展的危機。但同時,新媒體使用的門檻廣泛降低,這對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新媒體具有聲、視等多種表現形式,作為“人神經的延伸”相較于以往的傳播形式而言具有無與倫比的表現力,在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傳播中,這種豐富的表現形式可以用于在進行音樂表演本身時同步顯示字幕、并配合專題記錄、彈幕互動等方式推廣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背后的文化意涵。此外,大數據可以抓取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表演視頻觀看的基本數據及進度條拖動的情況,技術人員可通過搜集這些數據及時將受眾的觀看反應及時反饋給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學者和業者,在此基礎上,通過技術手段充分橋接新媒體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實現傳播閉環。
(三)依托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資源,加強戰略部署
在制度層面和戰略層面,我們已依托少數民族豐富優秀的傳統音樂資源取得了一些成就。“支持民族教育事業發展、突出高等院校教學特色和民族文化傳承”作為教育部在2007年制定的國家教育事業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的11個專題之一被納入研究視域,標志著對于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國家級層面的思考。在此基礎上,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納入音樂教育體系,橋接志書編纂工作與教材編寫工作成為當務之急。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就在編纂文藝集成志書,但是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編志書,僅僅將這些優秀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本塵封起來就覺得完成任務,無異于讓珍珠蒙塵,是資源的二次浪費,那么志書有何用、怎么用,就成為在推動經典傳承工作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因地制宜地在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開設藝術教育試點,依托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資源,同時使志書成為藝術教育試點教材的指導書目,將二者工作勾連起來,真正讓志書活起來、動起來,同時為重塑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在藝術教育體系中的地位積極準備。
總之,在新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實質上是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在抗御外部音樂文化的沖擊并利用外部音樂文化及傳媒技術自我豐富、自我改革的過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傳承需要學者和業者積極創新思路,在厘清當前問題的前提下,尋求解決之道,在開拓中謀發展。
[1]田元.可持續發展視角下少數民族音樂的傳承創新[J].貴州民族研究,2016,37(11):99-102.
[2]葛姝亞.論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與創新[J].貴州民族研究,2014,35(12):68-71.
[3]李松,等.對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的反思——“第三屆全國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傳承與學術研討會”主題發言[J].中國音樂學,2013,(1):1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