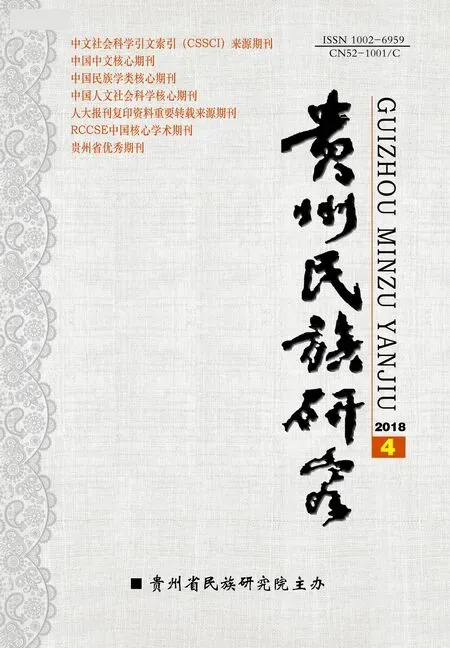試論我國鋼琴作品的民族特色及其風格體現
邵 楊 周澄嫣
(南昌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院,江西·南昌 330022)
鋼琴原本是西方國家演奏時常用的樂器,在19世紀中期才傳入我國,至今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我國產生了很多具有中國特色的鋼琴作品,這些鋼琴作品在借鑒西方國家音樂作品的同時,也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充分體現出了我國民族音樂的特色和風格。
一、我國鋼琴作品的民族特色
(一)我國鋼琴作品作曲風格的民族特色
鋼琴在我國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之后,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鋼琴作品,與外國鋼琴作品產生了很大的區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鋼琴作品調式和調性的多元化風格。很多西方的鋼琴作品都是采用關系大調或者關系小調的調式。我國的鋼琴曲中調式比較多,主要包括宮、商、角、徵、羽五個調式,使我國的鋼琴作品調式類型非常豐富[1]。我國很多的鋼琴作品在一首組曲中,還包含不同的調式與調性,以桑桐《內蒙古民族主題曲七首》為例,第一首《悼歌》采用的是商調式,第二首《友情》、第三首《思鄉》、第四首《草原情歌》采用的是羽調式,第五首《孩子們的舞蹈》、第六首《哀思》采用的是宮調式,第七首《舞曲》采用的是羽調式,由此可見,我國的鋼琴作品以我國民族民間各具特色的調式,創作出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鋼琴作品。
我國鋼琴作品在創作過程中還使用了比較先進的作曲方法和配器理論,并使用中西方音樂的優勢來為鋼琴作品服務,把我國的民族五聲音階和西方的七聲調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傳統的民族音樂配器主要采用純音程和聲,比如純四度、純八度等,要么就是大二度或者小七度,但是在我國現代的鋼琴作品中,很多都是使用大三度、小六度或者小三度、大六度,并且經常在一段樂曲結束之前使用屬七或者減七和弦。在比較具有特色的鋼琴作品中,還使用了純和聲音程結構,或者把大二度、小七度等不協和的音程應用于鋼琴作品的編配之中。在我國的鋼琴作品中,既借鑒了我國各民族傳統的音樂特色,也兼具了現代鋼琴作品的時尚性和新穎性,在配器方面科學而又精煉,在鋼琴作品演奏中達到了和聲功能、音響效果以及音樂作品情緒抒發的極致體現。
在我國鋼琴作品中,思想內容的表達非常具有邏輯性,并且思想內容的表達向著多層次以及多方面發展,使不同的鋼琴曲式在演奏中能夠使用不同類型的陳述結構[2]。比如我國的鋼琴曲《婚禮場面舞》中每個小段都是采用不同的曲式來進行演奏,在《婚禮場面舞》的演奏過程中,通過重拍和弱拍的交替,加上民族管弦樂音調和鑼鼓打擊樂效果,在作品中表現出了既熱烈歡快,又具有濃重鄉土氣息的效果。在我國的鋼琴作品中,除了經常使用的主調式陳述單段或者主副部的形式外,還包含很多種不同類型的曲式結構,比如復合曲式、邊緣曲式、變奏曲式、回旋奏鳴曲式、套曲曲式等,這些曲式的使用使我國鋼琴音樂作品體現出不同的風格特點,表現出百家爭鳴的民族音樂作品特色。
(二)我國鋼琴演奏技巧的民族特色
我國鋼琴作品在演奏過程中,也具有獨特的演奏方式,比如從演奏者的手指技巧方面來看,包括雙指交替演奏、右手承擔旋律演奏以及手的跨越式演奏等。雙指交替演奏指的是演奏者在演奏鋼琴作品時一只手彈一個音,另一只手接著彈下一個音,并且在演奏過程中進行多次的重復演奏[3]。比如我國鋼琴家劉莊根據民族絲竹樂曲改變的《三六》鋼琴獨奏曲就是使用左手與右手交替演奏琶音,演奏出了古箏與琵琶的刮奏效果,在演奏過程中還使用雙手迅速交替輪指彈奏,演奏出了民族彈撥樂的效果,在鋼琴的中低音區,能夠演奏出二胡或者低胡的效果,在鋼琴演奏的高音區,能夠演奏出高胡或者竹笛的效果,在跳奏時,還能夠演奏出木器、柳琴的效果。西方的鋼琴音樂作品在演奏過程中經常使用右手承擔主旋律,但是在我國的鋼琴作品演奏中,并不全是右手承擔主旋律,很多時候都是左手承接左手,來承擔鋼琴作品主旋律的演奏。比較典型的有周廣仁的鋼琴作品《陜北民歌主題變奏》以及王建中的鋼琴作品《繡金匾》等,這些鋼琴作品在A段或者再現部使用右手演奏主旋律,但是在B段經常使用左手承擔主旋律演奏,從而產生明亮與渾厚、清新與深情的強烈對比,使我國的鋼琴作品具有極大的魅力。我國鋼琴作品還包括手的跨越式演奏,也就是在右手演奏過程中,左手在低音區演奏幾個音型后,跨越右手演奏高音區音型,這種演奏方式還包括右手跨越左手的演奏。比如我國鋼琴家王建中創作的鋼琴曲《百鳥朝鳳》就采用的是手的跨越式演奏方式,使鋼琴作品具有很強的變化性和對比性,充分襯托出了鋼琴的主旋律,大大增強了鋼琴作品的表現力。
優秀的鋼琴曲還包括豐富的節奏和速度變化,比如長短變化、快慢變化、強弱變化等,還有單雙音變化、單雙手和弦變化等,我國鋼琴作品在對長音進行處理時,經常使用全音符跨小節延音線,還有rit方法、小節延長、長短節奏變化等[4]。鋼琴作品的強弱對比也非常明顯,在強音時經常使用f、ff或者fz、Sf來進行演奏,在弱音時經常使用P或者PP來進行演奏,這些對比手法在鋼琴作品中的使用能夠使鋼琴樂曲充滿激情與活力,使鋼琴作品的表現力大大增強。在鋼琴作品演奏時,鋼琴演奏家經常會使用很多的演奏手段來對演奏效果進行美化,比如在進行裝飾音型或者琶音型的演奏時,能夠演奏出齊奏和弦表達不出的聲音效果。在我國鋼琴作品演奏時還經常使用控制音量的演奏方法,比如聲音的淡入或者淡出演奏等,這樣能夠達到畫龍點睛的演奏效果,充分展示出鋼琴作品的個性,增強鋼琴作品的表現力。
(三)我國鋼琴作品創作選材的民族特色
我國各民族在長期的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智慧,創造出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歌、戲曲、童謠和民謠等,這些都是我國鋼琴家在進行鋼琴作品創作時的靈感來源。在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奠基下,我國一代又一代的鋼琴家創作出了很多優秀的鋼琴作品,比如我國早期的鋼琴作曲家賀綠汀1934年創作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獲得了中國風鋼琴曲國際大賽一等獎。此外,我國還有很多具有特色的鋼琴作品,包括瞿維創作的《鳳陽花鼓》、王建中創作的《百鳥朝鳳》、儲望華創作的《二泉映月》、殷承宗等人創作的《黃河》等,都包含了豐富的民族特色,體現出了我國人民鮮明的民族性格。
二、我國鋼琴作品中的民族風格體現
(一)我國鋼琴作品中的民族語言風格
我國各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比較豐富的語言基礎,漢語是我國使用最為廣泛的語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漢語的語言風格也決定著我國鋼琴作品的風格[5]。在漢語中,有很多的一字多音或者一音多聲等類型,漢字聲調的不同對于漢字意思的表達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四聲在漢語中主要有表情達意或者渲染情緒等作用,一字多音也使漢語的字義和詞義產生很大的區別。漢語的語言特色在我國的鋼琴作品中具有很鮮明的體現,比如我國鋼琴家陳培勛創作的《賣雜貨》具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色,也包含著豐富的地方方言音調。《賣雜貨》是根據廣東小調和廣東樂曲改變而成的,它的旋律抑揚頓挫,節奏活潑生動、粗獷奔放,在中段則清秀優雅、速度和緩,整部作品呈現出A、B、A1再現單三部曲式。
我國很多的鋼琴作品都與民族音樂有較大關系,并且這些鋼琴作品的“語調”特性非常突出,比如我國鋼琴家汪立三創作的鋼琴曲《小奏鳴曲》就具有非常濃厚的湖南地區語調特征。《小奏鳴曲》采用的是非對稱式節奏,但是卻能夠清晰地聽出明顯的湖南民歌語調特點[6]。左手在彈奏過程中使用雙音伴奏方式不同的在A大調V和I級和弦上切換,能夠營造出獨特的民族樂器——笙的音響效果。我國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的語音和語調也具有很大的差別,對我國鋼琴音樂作品的影響也非常大,我國北方方言語音偏重,語調也比較直,而南方方言語音比較輕,語調比較軟,這也形成了不同的南北方鋼琴作品特色。
我國的藝術作品向來比較講究氣韻生動,文人雅士在進行藝術創作時,比較崇尚意象上的高、潔、優、雅等,這些特點也對我國鋼琴作品創作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使我國鋼琴作品包含著深厚的民族氣韻,比如我國鋼琴家儲望華創作的《箏簫吟》、趙曉生創作的《太極》以及黎英海改編的《陽關三疊》等,在演奏中能夠模仿出古琴或者簫的聲音,體現出“虛音”和“實音”之間的韻律變化,為我們營造出一幅唯美意境。黎英海改編的《陽關三疊》是根據《琴學入門》改編而成的,在改編過程中,保留了原曲的歌唱性旋律以及原曲中古琴和簫的音質特色,表現出作者對于友人即將遠行的關懷和留戀之情。
(二)我國鋼琴作品中民族音樂風格的體現
我國鋼琴作品調式主要為五聲調式,這與西方國家鋼琴作品的大小調式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不僅音級數目相差較大,而且在音響效果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比如我國鋼琴家賀綠汀創作的《牧童短笛》就是我國鋼琴作品無聲調性中復調風格的代表作。在《牧童短笛》中,我國的民間支聲復調和西方國家的對比復調技法相結合,使其成為具有我國民族五聲調式和韻律的鋼琴作品。《牧童短笛》的主體是自由對比的二聲部復調,五聲化旋律處理為自由對比位的形態,這兩個聲部的旋律都充分體現了我國的民族音樂風格。我國還有很多分解和弦以及平行四五度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鋼琴作品,這也是區別我國鋼琴作品和西方鋼琴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征[7]。
我國有很多種類型的民歌,不同地區的民歌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在我國鋼琴音樂作品中,也有非常明顯的表現。比如在我國有很多人在勞動時喜歡喊勞動號子,其具有非常明顯的口語化特點,在我國鋼琴家殷承宗等人創作的《黃河》中,就融入了我國民間船工號子的音調素材,運用領、合呼應的演唱形式,充分表現出了船夫與狂風大浪作斗爭的緊張場面。山歌也是我國一種比較優秀的歌曲類型,在朱踐耳創作的《山歌》鋼琴曲中,就是以我國的山歌作為基礎來進行創作的,山歌的影響使鋼琴曲煥發出了巨大的生命力[8]。在鋼琴曲《山歌》中,還使用了多聲配置方法,在作品中有很多的五度和音以及現行平行進行所組成,在三次相同的句尾旋律中具有不同的調式色彩與和聲音響。
我國戲曲同樣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在我國鋼琴作品中也有很多戲曲風格的體現,地方語言的不同也顯示出了不同劇種的音樂風格[9]。比如李其芳創作的《河南曲牌》就具有非常明顯的河南地方方言元素。唱腔也是區別不同劇種風格的主要標志,比如在朱曉宇的《戲曲組曲·京劇小段》中第二主題主要體現了二黃腔的腔調。鋼琴和戲曲原本是兩種非常鮮明的音樂形象,他們在表現形式和表達內容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差別,但是我國鋼琴作品把鋼琴和戲曲兩種形象組合到一起,不僅賦予了鋼琴作品更加強有力的表現,還對鋼琴作品的創作產生很大的促進作用。
(三)鋼琴作品模仿我國民族樂器的音響效果
在長期生存與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創造出了各種各樣不同類型的樂器,同時還吸收了很多的外來樂器,對他們加以改造之后變為我國的民族樂器,這些不同的樂器類型對我國鋼琴作品的創作也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我國所有的樂器類型中,洞簫和古琴是最具文人雅士之風韻的,他們的音樂古樸圓潤,氣質高貴典雅,對我國鋼琴作品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0]。比如在我國鋼琴家儲望華創作的《箏簫吟》中,就借鑒了很多的古箏和洞簫的音響效果,為人們譜寫了一曲高雅、幽靜的鋼琴樂曲。在《箏簫吟》的開頭部分,左手奏出洞簫空幽、圓潤的音色,樂聲中透露著一絲無奈和感傷,充分體現出了作者想要為我們呈現的意境。鋼琴家黎英海創作的鋼琴曲《夕陽簫鼓》第四節和第五節也是模仿簫的音色來進行演奏,為我們展示出了黃昏時分空幽、高遠的意境。竹笛也是我國鋼琴作品創作過程中喜歡模仿的民族樂器,竹笛的音色高亢嘹亮,氣質活潑生動,能夠為鋼琴演奏渲染一種比較獨特的氣氛。比如在鋼琴協奏曲《黃河》第三章引子就是模仿竹笛脆亮、悠揚的音色特點,為我們演奏出清爽、敞亮的樂聲。此外,我國還有很多的鋼琴作品都模仿了我國民族樂器的音響效果,比如崔世光的《鋼琴交響狂想曲》模仿了琵琶的音響效果;王建中的《繡金匾》模仿了揚琴的音響效果;儲望華的《二泉映月》模仿了二胡的音響效果等,這些音響效果的融入為我國鋼琴作品增添了很多的藝術表現力。
結語
在我國的鋼琴作品中,包含著很多的民族特色以及民族風格,民族特色風格的加入使我國鋼琴作品不單單是模仿西洋音樂作品,更加體現出了我國音樂作品的特色,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的欣賞需求,為我國民族音樂的繼承與發揚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賦予了我國鋼琴作品更大的藝術魅力和更加恒久的生命力,為我國鋼琴表演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胡月.論鋼琴曲《新疆舞曲》的音樂特點及民族特性[J].中國文藝家,2017,(3).
[2]楊斐,劉旭東.西樂為體,中樂為用——論中國風格鋼琴作品的實質在于技法與審美的“中西合璧”[J].音樂創作,2017,(3).
[3]鄧川.關于中國鋼琴改編曲演奏風格的幾點思考[J].文藝生活·下旬刊,2017,(4).
[4]張怡.少數民族音樂的鋼琴化實踐探索——基于少數民族音樂發展視角[J].貴州民族研究,2015,(2).
[5]高靜.儲望華鋼琴作品《箏簫吟》的民族風格特征與演奏技巧闡釋[J].音樂創作,2017,(1).
[6]張義瑤,楊婷.民族樂器音色在我國鋼琴作品演奏中的應用[J].高教探索,2017(1):237-238.
[7]王舒靜.淺析中國風格鋼琴練習曲對傳統戲曲元素的運用[J].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2017,(1).
[8]孫韻.指尖上的中國風——中國風格鋼琴作品的演奏特征及風格的探討[J].黃河之聲,2017,(10).
[9]尚艷.少數民族鋼琴音樂民族化實踐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16,(9).
[10]宋震.對中國鋼琴作品民族地域風格的思考[J].黑河學院學報,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