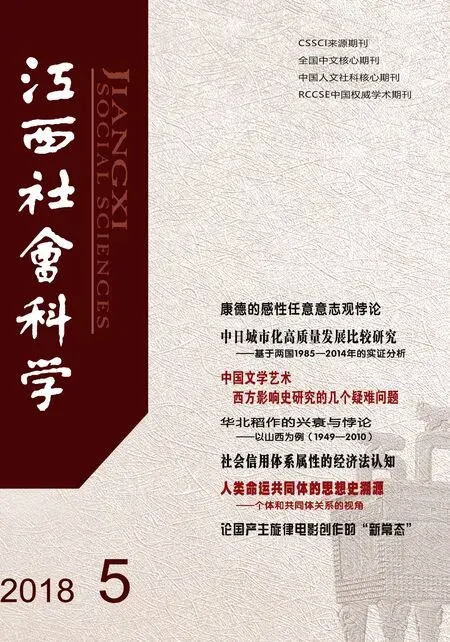自發性:馬里翁與海德格爾藝術理論的共同旨趣
海德格爾通過將現象定義為“就其自身顯現自身者”,開辟了一條關于不顯現者的現象學道路,而馬里翁則繼承了這樣一種現象學。他們兩人都將藝術視為自我給予者顯現自身的有效途徑,認為偶像或真理的發生是其顯現的方式。在兩人對藝術的闡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現象(從自身出發)在自身之中顯現自身的自發性是如何可能的。
一、純外觀和物性
馬里翁從繪畫的角度來理解藝術,“純外觀”(pure semblance)是他對繪畫的基本規定。所謂純外觀,實際就是繪畫呈現的圖像,看起來像是某個實在對象的影像,與實在對象相似,但卻不能如實在對象那樣被實際使用,也不能如實在對象那樣由科學研究來確定其成分、性質等。例如,卡拉瓦喬畫的水果無論看上去多么逼真,也不能拿來解渴或者研究其化學成分。這個外觀僅僅是提供給視覺的。有人會說,實在對象也給視覺提供了一個“外觀”,這與繪畫中的外觀有何不同?實際上,當我們說某個“蘋果的外觀”“房子的外觀”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蘋果和房子,而不是它們的外觀。我們首先預設了自己看到的東西,然后才在分析中采用一種“形式加內容”的模式,得到一種所謂外觀的理解。而繪畫中的外觀只是呈現自己,它并不從屬于某個預設的(卻沒有出現在視覺中的)東西,如果說某物的外觀屬于某物,那么,在繪畫中,外觀只屬于外觀自身;繪畫中的外觀并不意味著某種內容的同時存在,它并不來自于“形式加內容”的顯現模式,毋寧說它的顯現遵循另一種模式。那么,如果這種繪畫的外觀不同于某物的外觀,它是否是對實在事物的外觀的模仿呢?馬里翁明確否定了這種看法:“在藝術中……‘相似外觀’指明了畫出來的‘事物’是如何區別于‘原型’的;它指示的并不是一種(模型和復制,事物和圖像之間的)關系,而是這種關系中單獨的一方——‘相似外觀’。”[1](P58)這種相似外觀“不再與任何事物相似,卻從一切事物那里沒收其榮耀,集中到自己身上,獨自成為純外觀”[1](P58)。一種模仿關系實際涉及模仿者與被模仿者,我們意識到這一關系,意味著兩方都出現在我們的意識中,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何謂模仿。而繪畫中的外觀卻獨自占據我們的意識,吸引我們的目光,使我們忘記了那個作為原型的實在事物。被模仿者——原型事物——被驅逐出意識,因而模仿關系也就不可能顯現了,“相似外觀”由此成為“純外觀”。
純外觀不是任何事物的外觀,也不是對任何事物的再現,它是一個獨立的現象。我們把日常現實事物看作藝術作品的原型,因而以藝術作品對此原型的再現程度來判定其藝術價值,或者以看待原型的眼光來看待藝術作品,以至于有的美學家認為,原型必定要比藝術作品更美。但實際上,現實事物與藝術作品分別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現象,沒有可比性。朱光潛在討論審美對象時用“物甲”和“物乙”來區分二者,認為前者僅僅是一種可能成為審美對象的素材,只有當它與審美者的情意結合之后才能成為一個作為審美對象的物乙。如果我們依據現實事物來理解和評價藝術作品,勢必造成范疇上的錯誤。馬里翁對純外觀的強調正是要劃清藝術作品與現實事物的界限。在馬里翁看來,純外觀之區別于現實事物,主要是在于它“從現實事物那里竊取了贊賞(admiration)”[1](P58)。這種贊賞不同于我們對日常事物的觀看,后者不會在我們心中引起任何波瀾,因為它們實際產生于我們的構造,要么是認識性的,要么是實踐性的。它們因此已經完全融入以我們自己為中心的世界,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說,我們總是對日常生活中的現實事物視而不見,卻贊賞“靈魂中的一種意料之外的驚喜”[1](P59)。被贊賞的對象總是從周遭的事物中跳脫出來,一下子抓住我們的注意力,吸引我們的目光,以至于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跟隨它,并忽略掉除它之外的一切。因此,純外觀的獨立性不僅意味著它獨立于現實事物,更重要的是,它獨立于我們的主體性。
海德格爾對藝術的討論是從追問藝術作品的物性(thingly feature of the artwork)開始的。“藝術”是藝術作品的一種本質性規定使用,我們沒有辦法在藝術作品之外去發現藝術。即使掌握了足夠豐富和深刻的藝術理論、審美方法、創作技巧,我們也無法將藝術以某種非藝術作品的方式呈現出來。就像天生的盲人無論擁有多少關于色彩的知識也不能他看見藍天和彩虹一樣,沒有對現實藝術作品的欣賞就沒有對藝術的理解。因此,海德格爾引領我們從藝術作品最直接的現實出發來探尋藝術的本質。
當我們直接面對藝術作品時,首先照面的就是藝術作品的“物性”:“石頭用來建筑,木頭用來雕刻,色彩用來繪畫,話語用來制作語言藝術,聲響用來創造音樂。”[2](P145)這些物質性的因素難以從藝術作品之中排除,沒有它們,藝術作品也就消失了。因此,海德格爾甚至認為:“建筑存在于石頭之中,木刻存在于木頭之中,繪畫存在于色彩之中,語言藝術存在于話語之中,音樂存在于聲響之中。”[2](P145)前后兩種表述體現出的反轉并不是隨意的,也不是同意的反復。它們實際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理解藝術作品之中的物質材料的方式。就前一種理解方式而言,物質材料只是構成藝術作品的物質基礎,在其之上還要加上別的什么東西才會產生藝術作品。這種物質基礎是一切事物都具備的要素,因此,只有這個“別的什么東西”才是藝術作品成其自身的關鍵所在。通常我們將這個東西認作“形式”“理念”“意味”等等,它們與質料形成一個二元結構。但是,據海德格爾的分析,這樣一種二元結構實際來自于我們對日常生活中使用之物——用具(equipment)——的理解:“形式”“理念”“意味”等作為符合于人的目的的東西規定著質料,質料因此也要服從于人的目的。然而,藝術作品顯然不同于那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和使用的用具,它完全不具有用具的有用性。因此,我們也必然不能以用具的二元結構來理解藝術作品中的物質材料。這樣一來,就有了以上的第二種表述。它要求物質材料擺脫形式對自身的規定,獨自承擔起構成藝術作品的義務。在藝術作品中,質料并不服從于形式,因而也不會消耗和隱藏自身,“巖石能夠承載和持守,并因而才成其為巖石,金屬閃爍,色彩發光,聲響歌唱,語詞言說。所有這一切得以出現,都是由于藝術作品將自身置回到石頭的巨大與沉重,木頭的堅硬與韌性,金屬的剛硬和光澤,色彩的明亮和幽暗,聲音的鏗鏘和語詞的命名力量之中”[2](P171)。在藝術作品中,物質材料擺脫了日常事物,因而也擺脫了那制造和使用日常事物的人,終于以自身的方式讓自身出現在人的眼前。
藝術作品作為一種現實地直接向我們顯現出來的東西,它的物性只能在藝術作品這一背景中呈現出來,這種藝術作品中呈現的物性并不等同于用具的物性,因為藝術作品和用具是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要理解藝術作品的物性只能從藝術作品的藝術性出發,依靠后者來理解前者,而不是相反。“藝術作品普遍展示了一種物性特征,雖然是以一種獨有的方式”[2](P165),這種獨有的方式就是不同于用具的藝術作品自身的方式:用具在使用過程中并不會引起使用者的注意,物性在用具中是隱而不顯的,有用性是物性在用具中的直接顯現方式,且隨著其使用,這種物性會消耗殆盡。在藝術作品中則不一樣,物性得以展示自身,而不再是有用性載體,它也不會被消耗,不會被欣賞者的目光剝奪,卻會因為這種目光而愈加豐富和光彩奪目,凸顯自身。
在馬里翁對純外觀的分析和海德格爾對藝術作品的物性特征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兩者立場一致的地方。首先,他們都遵從現象學“回到實事本身”的原則,將對藝術本質的討論置入現實的藝術作品之中。這在海德格爾那里是清楚闡明了的,馬里翁則通過描述相似外觀向純外觀的轉換,表明自己的立場。其次,外觀和物性都是直接呈現的東西,似乎一切事物都共享這同一種屬性,但依據現象學顯現與顯現者相對應的原則,他們都區分出不同于我們日常觀照的顯現模式,將藝術與日常事物區別開來,并且都認為藝術品是比日常事物更本源的現象。馬里翁將純外觀稱作“原型的原型”“世界之物”,認為現象性要由藝術來掌控和生產;在海德格爾那里,藝術作品中顯現出來的是用具的有用性、物的物性,也就是說事物的本質或真理發生在藝術作品之中。再次,在這種對藝術的初步解說中,馬里翁和海德格爾都沒有首先強調藝術家的作用,甚至都強調的是藝術作品的自身顯現。馬里翁在解釋純外觀時說,它竊取了欣賞者的目光,將純外觀放置到一個主動作為的位置上;而海德格爾在將藝術的本質定義為“真理自行設置入藝術作品之中”時,實際也表明了藝術的自發特征。最后,海德格爾和馬里翁都放棄了胡塞爾式先驗主體的意向性對現象建構的主導性,讓現象成為自發形成的,走上同一條將現象學推向徹底化的道路。
二、偶像和真理的發生
在馬里翁看來,不可見者(l’invus)之所以不可見,并不是因為它被其他事物擋住了,就像一個立方體背朝我們的三個面被擋住了一樣,也不是因為它是過去發生的事,而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再一次見證它的發生。實際上,這些在空間或時間上由于某些原因不能直接呈現的東西,仍然可以通過別的方式呈現出來,比如隨顯和記憶。可見,這并非真正的不可見者。但這里的分析卻也提醒我們某種事物或現象的可見性離不開使其顯現的那種行為,那么,馬里翁所謂的不可見者想必就是沒有獲得恰當顯現方式因而不可見的東西,它“隱藏在一種前現象的模糊性之中,由于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它們而不能被看見或預見”[1](P68-69)。我們要如何才能“想到”這些不可見者呢?馬里翁區分了“看”(see)和“看見”(look)。人人都能看,并且在我們的世界中可以看的東西如此豐富,它們匯成一股可見流(the flux of the visible),隨時隨地包圍我們。它們出現在我們眼前,不需要我們去選擇或做出“看”的決定就會充滿我們的視野。它們沒有邊界或輪廓,也沒有靜止不動的時候,這種可見流的大量涌入反而使我們沒有辦法看見任何東西了,就像直視陽光會使我們眼花炫目一樣。為了“看見”,我們必須擺脫這種可見流給予我們的無邊界連續體,讓某種東西從中突顯出來,將可見者從這可見流中分辨出來,這就需要給這個連續體劃出邊界,引導我們的目光去看清邊界內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給這可見流加上邊界時,我們看見的就不再是那純粹的可見者了,而是將可見者從其背景中勾畫出來的邊界。這個邊界使得可見者對象化,用對象取代可見者。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所謂不可見者實際上就是“純粹的可見者”,它大量的、高強度的可見性只有在受到邊界限制進而被削弱的情況下,才能被我們的眼睛接受,變成某種對象化了的可見者。因此,在一般對象之中,純粹的可見者消失了,成為不可見者。但不難發現,這種純粹的可見者才是最后支持一切對象的那個事物本身,現象學所要回到的應當是這個純粹可見者,而不是可見的對象。馬里翁在繪畫中發現的正是一種回到這個純粹可見者的方式。
這個支撐一切對象的純粹可見者可以對應于海德格爾的“大地”(the earth)概念:“希臘人很早就把這種露面、涌現本身和整體叫自然……我們稱之為大地。大地是一切涌現者的返身隱匿之所,并且是作為這樣一種把一切涌現者返身隱匿起來的涌現”[2](P168),“大地作為不可還原的自發性,是不需費力,也不知疲倦的”[2](P172)。大地是涌現本身及其整體,一切涌現者要以它為前提,但一切涌現者都是大地的涌現受到限制或具體化之后的結果;作為涌現本身及其整體,大地從未現身,它從自身出發,連綿不絕,隨時隨地出現在我們周圍,卻一直沒有被我們把握到。這正是馬里翁所謂純粹可見者一直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卻從未能被我們看到的狀況。海德格爾舉例說,石頭的沉重并不能通過任何計算的方式顯現,只有在它并未得到解釋的時候,它才真正展示自身。他說雕塑家不會消耗石頭,只會讓石頭的特性展現出來,不像泥瓦匠在使用石頭的過程中消耗了石頭。石頭何以會被消耗掉?在建筑之中,石頭充當承重之物,它能承受的壓力強度決定了它的用途。在這里,石頭不再以自身的方式存在,而是以某種承受建筑物壓力的構件存在,石頭消失在建筑之中。但是,石頭本身作為一種自然之物,并不必然是建筑的構件,泥瓦匠對它的使用實際將它限制在建筑中,遺忘了石頭自己的物性,亦即其“沉重”。石頭變成了一種被“承受壓力者”這一界限框定的單面化的、隨時會被取代的東西。
馬里翁和海德格爾的目的都是試圖揭示這種支撐一切的純粹可見者或大地的顯現方式,認為它們才是最源初的現象。他們兩人對藝術的討論都是希望在藝術這種現象中發現那源初給予自身者如何在自身之中顯現自身,通過可見者或涌現者將通常并不顯現、不可見的東西帶到光亮中來。藝術中存在一種悖論式的關系,這種關系的雙方相互沖突又相互依賴,同時也在這種關系中得到顯現,其中一方就是純粹可見者和大地,另一方則是偶像(the idol)和世界。
偶像是馬里翁發現的一種溢滿性現象,是指現象的顯現并不是由主體的意識來構造,而是自身顯現。人的意識或目光被它捕捉到,無法穿透它,反而任由它來掌控和指揮人的目光。這是因為,偶像相較于日常貧乏的事物而言,可以給目光提供強度更高的可見者,因而充滿人的目光,使人無暇顧及其他。偶像提供給目光的可見者是這種目光從未在其他地方見識過的,因而吸引著目光反復去觀看它,不會將它當作某種類型化了的對象而忽略掉——類型化的東西并不需要我們的觀看,因為它出現在一種概念式的理解之中。而偶像在這里卻是作為純外觀的純粹可見者,除了觀看之外并沒有別的方式來使它顯現。
偶像的顯現得益于馬里翁所謂“畫框”(the frame)的作用。我們在前文中說過,純粹可見流自身其實無法在可見者的領域中出現,除非它受到一個邊界的限制。畫框在這里起到的就是邊界的作用。但畫框作為邊界卻又不同于我們對日常事物的輪廓的理解,它并沒有使純粹可見者消失在對象之中,而是為純粹可見者創造了一個不同于日常事物的時空,讓純粹可見者能夠從自身出發作為自身顯現出來。若沒有畫框,繪畫平面就只是日常事物的一個面,構成日常事物“顯現—隨顯”結構的一個部分。畫框則讓顯現單獨作用,拋棄了隨顯,畫框實現了日常事物向偶像的轉換。
偶像作為一種充滿和吸引欣賞者目光的東西,“將目光的尺度歸還給了目光”[1](P61)。這就是說,通過揭示我們的偶像,我們所能理解或所能看到的世界的尺度就會顯現出來。這樣的尺度是我們的目光去發現那純粹可見者的世界時自身帶有的,它為純粹可見者劃出邊界,讓一個對象世界呈現出來。我們能夠在繪畫作品中看到什么,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目光尺度。但另一方面,偶像作為一種純粹可見者之流顯現的溢滿性現象并不只停留在我們的尺度之下,它自身是一個完整而豐富的世界整體,純粹可見者以偶像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向我們顯現出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反復去看同一幅畫的原因:它擁有一個獨特的世界,這個世界有無限的豐富性,需要反復觀看和揭示;它教會我們用新的方式來理解純粹可見者,給予我們新的尺度。這樣一個世界整體實際就是純粹可見者本身,它顯現在作為偶像的繪畫之中,但卻不能被完全掌握,總是超出我們對它的觀看。正如馬里翁所說:“繪畫的生命展開為那些被它吸引的目光的調節理念(regulatory idea),也展開為一個絕對可見卻從未被看見的給予(given)。”[1](P72)
海德格爾所謂“世界”(the world)的概念與馬里翁的偶像概念具有同樣的內涵。
首先,“涌現者的世界使得尚未決斷的東西和無度的東西顯露出來,從而開啟出尺度和決斷的隱蔽的必然性”[2](P188),“由于一個世界敞開出來,所有的物都獲得了自己的快慢、遠近、大小”[2](P170)。世界給出決斷和尺度,這就意味著世界上的存在者以何種方式存在(或稱顯現)取決于世界自身給出什么樣的決斷和尺度。歸根結底,這個決斷和尺度又是由此在給出的。因為世界是此在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客觀自在的世界。給出尺度的世界,絕不是我們可以打量的對象,也不是許多為我們所見或所想的對象的集合,它跟偶像一樣,是讓一切得以顯現的視域,也就是人的視域。
其次,世界是在藝術作品中設立起來的,設立一個世界是藝術作品的本質特征之一。設立世界意味著開啟一個敞開領域(open region),世界就在這個敞開的領域中保持開放,一如畫框創造一個非物理的時空讓偶像在其中活動一樣。藝術作品設立的世界屬于一個與我們日常經驗不同的時空,因此,藝術作品可以將事物從日常的存在狀態中解放出來,讓其自身得以顯現,不再是作為人的工具,而是作為通達存在的入口。
再次,藝術作品在設立世界的同時,也制造了大地。這個世界的設立是在真理的發生之中實現的,它與作為一切事物的承載者的大地在藝術作品中被制造出來同時發生。設立世界和制造大地是藝術作品的一體兩面:世界建立在大地之上,大地則進入世界的敞開領域之中。然而,世界是“自行公開的敞開狀態”,而大地卻是那“永遠自行鎖閉者”,因此世界與大地實際處于一種永恒的對立之中,海德格爾稱之為“親密的爭執”。但在爭執中,一方超出自身包含著另一方。爭執總是愈演愈烈,越來越成為爭執本身。正是在這種本質性的爭執中,雙方才實現了各自本質性自我的確立:大地作為不知疲倦的涌現只有在一個敞開的自由領域中才能充分釋放自己的能量,大地作為自行鎖閉者的顯現只能在藝術作品中實現,正如海德格爾所舉的石頭在希臘神廟中顯現自身的沉重性一樣;而世界作為永遠自行敞開的狀態是照亮一切的東西,是一切顯現出來的領域,如果沒有大地的涌現,它將無所照亮,也無所顯現。真理,事物自身的澄明,就以大地和世界爭執的方式發生著。
正如馬里翁認為偶像將純粹可見者帶入可見領域之中一樣,世界將大地帶入澄明之中。海德格爾與馬里翁各自找到了一對概念,來解說源初的不可還原的實事是如何在自身之中顯現的,藝術對他們來說就是現象學的徹底化,是現象的自發性的典型表現。
三、藝術的自發性
藝術的自發性在馬里翁那里意味著藝術是一種溢滿性現象,而在海德格爾那里則指的是藝術是真理在藝術作品中的自行置入。作為一種溢滿性現象,藝術顯現的出發點是給予自身者,例如我們在上文提到的純粹可見流。在馬里翁看來,顯現自身者首先要給予自身,這種給予自身者的顯現是通過還原實現的,有多少還原就有多少給予,因此,馬里翁才會說繪畫實際上就是一種現實的現象學還原活動,它將可見流盡可能豐富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并通過繪畫本身的要求,揭示自身的豐富內涵和保持自身的給予性,證明了繪畫并不是由藝術家或欣賞者事先規定好的東西,它的顯現是自身顯現。藝術在海德格爾看來是真理的形成和發生,而“真理只有在由真理自身開啟的爭執和自由領域中才建立自身”[2](P186)。這個說法與他在《存在與時間》中將現象定義為“由自身出發在自身之中顯現自身”的說法何其相似,不難猜測,藝術在海德格爾那里就是一種自身顯現的現象。這不僅從字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且就海德格爾對真理的理解來看亦是如此。真理作為在大地與世界之間親密爭執中顯現的現象,歸屬于自身涌現的大地和自身敞開的世界,人作為它的揭示者,實際并不能改變大地和世界本身(揭示并不意味著改變)。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在馬里翁和海德格爾對待藝術家和欣賞者的態度中發現他們對藝術自發性的肯定。藝術家和欣賞者向來在對藝術的理解中扮演著使藝術成為藝術的角色,前者創造藝術,后者解讀藝術。如果取消了藝術家和欣賞者在藝術之成為藝術中發揮的作用,藝術將別無所憑,只能是自發的了。馬里翁和海德格爾在這一點上都沒有心慈手軟。
馬里翁說:“畫家在可見者之上增加可見者,因為他(她)獨自冒險抵達未知之域的最邊緣,尋找并喚醒不可見者的涌現——那種任何目光都沒能夠或者不敢去靠近的猛烈的新鮮事物。”[1](P69)馬里翁在這里賦予藝術家勇于冒險的精神和發現者的榮譽,但并沒有授予他們發明家或創造者的稱號,因為他們所帶來的可見者并不是他們憑空生造出來的,毋寧說是他們親眼看見之后記錄下來的,是他們在常人不可見的領域中的見聞。相比于創造者的稱號,藝術家更應該被稱作照亮者。在馬里翁看來,藝術家實際是一個受贈者(l’adonné),他的能力在于使由給予自身者給予他的東西現象化,他對給予自身者形成阻力,將它攔截下來,抵抗著純粹的、不可見的給予擁有的強力。他像三棱鏡一樣使不可見的(或純粹可見的)光變成人人都能看見的七種色彩。同時,這個受贈者也在使給予的東西現象化的過程中,自身現象化——讓自己變得可見了。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能夠理解海德格爾為什么說藝術是藝術作品和藝術家的本源。藝術家之為藝術家,需要由他的藝術作品來確證,但這可能面臨藝術作品又需要藝術家來為其背書的悖論。根據馬里翁的看法,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實際是同時產生、相互支持的。藝術現象的發生同時確證了作為受贈者的藝術家,及作為受贈物的現象化了的藝術作品。那么,我們又如何識別出藝術呢?通過偶像或真理的發生。
解構了藝術家的創造之后,欣賞者又如何呢?海德格爾認為,欣賞者在藝術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他們關涉藝術作品的保存(preservation)。但這里所謂的“保存”并不是將藝術作品當成一件物品存放在倉庫或保險柜里,以防破壞,恰恰相反,欣賞者通過他們的觀看保存藝術作品,因為藝術作品中發生的真理只有在欣賞者的觀看目光中才能激活,正如海德格爾自己看到梵高畫的農鞋,使其中承載的農婦世界向我們顯現出來那樣。馬里翁也十分強調欣賞者對于藝術作品的意義,認為藝術作品只有在無數的欣賞目光中才能實現自身,才能一次次地顯現為藝術作品(這實際與藝術家對藝術作品的作用是一樣的)。但這并不是說,欣賞者是憑自己的主觀好惡或預先就有的理解去附會藝術作品的意義。海德格爾認為這種想法是自我欺騙,因為被藝術作品深深吸引和占據的觀眾是無法同時逃離它來分析它的,就好像我們沉浸在哈姆雷特的悲劇故事中,不會去想這是一個杜撰的故事,直到幕布落下提醒我們故事結束之后,才會去注意這是一個演員表演的故事。
藝術家和欣賞者被排除在藝術作品之外的意思是,他們不再是藝術的決定性因素。就本質而言,馬里翁和海德格爾將人驅逐出藝術作品的本源,實際是驅逐人的主體性,他們要求的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之外,重新理解藝術。
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傳統美學把藝術作品當作人的感知對象,因而從人的感知來理解藝術的本質,藝術之為藝術的根據在于人:“人體驗藝術的方式,被認為是能說明藝術之本質的。無論對藝術享受還是對藝術創作來說,體驗都是決定性的源泉。”[2](P204)近代以來,西方美學依照笛卡爾建立的主體性范式來展開自己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成果就是“移情說”。在移情說看來,包括藝術作品在內的審美對象之所以成其自身,是因為人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本身無情感的對象之中。換句話說,審美對象實際是由審美主體建構起來的,人創造了審美對象。但是,這種移情說存在巨大的理論困難,它無法解釋為什么是這種情感投射到對象之中,而不是另一種;為什么是這一對象接受情感的投射,而不是別的對象;以及最根本的問題:人為什么可以將情感投射到一個外在于他的對象之中。對象由于一開始就外在于主體,因此,無論主體具有何等豐富的情感,他都不能憑借這情感通達一個外在于自己的對象。主體的審美實際根本不是朝向對象的,而是朝向自身的。人也就因此將自己困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遮蔽了事物本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里翁和海德格爾要將人懸擱起來,更確切地說,是給人的主體性加上括號。
懸擱是為了重新理解,是為了還原實事。反對以人的主體性來理解藝術,并不意味著完全否定人在藝術的誕生之中構成一個環節,也不意味著完全否定人在藝術作品中的出場。在海德格爾那里,藝術家“就像一條為了作品的產生而在創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2](P166),并沒有創造藝術作品,藝術作品只是借藝術家之手得以顯現而已。另外,“藝術作品之為自身,總是離不開保存者”[2](P192),這里所謂保存者就是欣賞者。因而可以說,藝術是離不開人的,但卻不是以人為根據。更重要的是,藝術作品設立起來的世界并不是一個與人無關的世界,而是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正如海德格爾針對梵高的畫作指出的那樣,藝術作品將農婦的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向我們揭示出來。農鞋之所以是農鞋,并不是因為它被如此這般地制造出來,而是因為它包裹著農婦因長期勞作而更加厚實的腳板,支持著這個飽經風雨的人踩在田埂、地頭、院壩以及山林之間。這也就是說,只有在農婦的世界之中,農鞋才成其自身。藝術作品之所謂揭示農鞋的物性或用具性,就必須將這個農鞋在其中獲得意義的世界帶到我們面前。盡管這個世界并沒有直接在場,我們已然預先直觀地領會了它的存在,因而才能將農鞋當成農鞋來把握。此外,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藝術作品,能夠保存它,也正是因為藝術作品揭示的世界,也是我們共同的生存世界。因此,海德格爾并沒有真的將人完全從藝術之中驅逐,相反,他在藝術作品中處處發現人的現身。
藝術自身顯現,顯現自身。可是,究竟顯現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那自發地給予自身者在藝術中顯現出的就是純外觀和物性,是這兩者的同時顯現。本來不可見的純粹可見流和自身鎖閉的大地在藝術作品之中變得可見,本來消失在對象之中的給予自身者在藝術作品之中擺脫了對象,顯現出自身。藝術作品的物性作為純外觀才得以顯現。畫布上的紅色完全不同于一件衣服的紅色。衣服的紅色完全被衣服所占有,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一件衣服,然后才會說這件衣服是紅色的,紅色在這里只是衣服的一個偶然屬性。紅色之為紅色對于衣服來說并不重要,相反,如果這個紅色顯得過于重要,也就顯得過于扎眼,我們反而覺得不適應,認為這不是一件衣服應該有的顏色,用通俗的話講,就是這件衣服的顏色很丑。但是,畫布上的紅色不依賴,也不屬于任何對象,它完全呈現自身,僅僅作為自身吸引著我們的目光。它此時變成了一片純粹的紅色,它的鮮亮、刺眼恰恰在這個時候毫無保留地展示出來,卻并不會招來任何非議,反而是驚喜的贊賞。不依附于任何對象的純紅色,以及它自身作為鮮亮、刺眼的物性在畫布上同時呈現出來,但并不是兩種性質的并列,而是合二為一,成為藝術作品。藝術作品越是純粹地呈現給我們的感官,其中的元素越是脫離日常事物對它們的約束,它們就越發地擁有藝術性。色彩、形狀、線條、筆觸越發地生動和引人注目,它們自身的閃耀、跳躍和結實就越是被我們理解。藝術作品并不消耗物,反而使物顯現自身,在它的外觀中輝映。
另一方面,是人生存的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在藝術作品之中顯現,但這種顯現采取的是一種非對象的方式。在海德格爾看來,人的生存世界是一切事物得以顯現的一個先在視域,是預先存在的。正是由于這個世界的存在,我們才能聽、看和理解。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舉書房為例,認為這房間里的書桌、稿紙、鋼筆、臺燈、門窗等都不是首先孤立地顯現自身,“在此之前,用具之整體已經事先被發現了”[3](P98)。這個作為整體的書房并不是房間里所有事物的集合,相反,書房中的用具之所以集中在這里,是因為書房作為一個整體視域在先地規定了其中的用具。正是因為我們事先理解了書房的意義,才會在房間里擺放紙筆、書桌等等,用“書房”來指導房間中應當放置什么樣的用具,以及如何擺放它們。考古發現中挖掘出來的許多器物在我們現在看來是十分奇怪的,不明白它們有何用途①,這正是因為那個器物歸屬的世界已經失落了,我們不再生存于那樣的世界。即便我們能正確地推斷出其用途,但再也不會去使用它們,因而它們向古人呈現的意義必然與向我們呈現的不同了:古人生活中最貼近的用具,在我們這里卻是博物館陳列柜中離我們最遠的收藏品了。
這樣一個在先的視域雖然時時刻刻都在發生作用,支撐著我們每一次對事物的發現,但它自身卻從來沒有出現在我們面前。就像我們的眼睛使得我們看到眼前的事物,但是眼睛卻看不見它自己。因此,我們說作為整體的世界是“不能見的”(invisable)②,它不能以一般事物的對象性的方式出場。然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樣,藝術作品卻可以讓這個不能見的世界變得可見,藝術作品的目的正是將這個不能見者帶入可見者的領域之中。
因此,藝術作品或者說藝術并不是一個對象,而是一種觀看的方式,是事物從自身出發顯現自身的方式,不可見者和不能見者依靠這一種顯現方式才變成可見者。馬里翁說“偶像表明了存在者的一種存在方式”[4](P7),其意義正在于此。海德格爾所謂世界之所以在藝術作品中被設立起來,得到揭示,顯現自身,憑借的就是作為偶像的藝術作品。偶像的顯現是一種非對象性的顯現,作為偶像顯現出來的并不是人的目光的尺度以內的事物,而是不能以人的尺度來測度的東西,馬里翁稱之為“神圣者”(the divine)或“不能見者”。“在偶像中,神圣者實際獲得了人的目光守候已久的可見性:但是,這種降臨的限度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視力所能達到的程度,取決于每一次(朝向神圣者——引者注)瞄準能夠要求多少可見性,目光才認為自己完全實現了自己。”[4](P14)由此看來,在偶像中,神圣者并未完全呈現自身,否則的話它將變成人的目光能夠完全把握的一個對象。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有一部分可見,另一部分仍不可見,就像琵琶背后露出的半張臉那樣;神圣者的顯現必定是作為整體的顯現,就像一座深淵總是完全暴露在瀕臨深淵的人面前,但人的目光永遠無法穿透其中的幽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偶像是一種非對象性的顯現方式。對象總是處于人的目光尺度之內,因而能夠完全呈現自身,成為一個被人的意向性建構的對象;神圣者卻并不服從人的意向性,相反,它暴露這種意向性的極限。偶像作為使神圣者可見的可見者,“打開了神廟所佇立的場所”[4](P14);神廟或神的塑像并不能使我們看見神的模樣,它也無意于此,但神的確憑借它們降臨在我們面前。
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當然不是一個神,但它作為一個不能見者卻與神是一樣的。因而,它在藝術作品中的出場或顯現也絕不是對象性的,而是既隱且顯地將自身給予藝術家和欣賞者:隱是因為它并非一個對象,顯則因為它實實在在地出場了。總的來說,藝術作品使得不可見者——純粹可見流和大地——作為純外觀和物性顯現出來,也使得不能見者——神圣者和世界——顯現出來,藝術作為偶像或真理就是這種顯現的發生方式。
注釋:
①“有何用途”式的追問總是十分自然地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可見海德格爾強調物的用具性其實別有用心,但是,它是否是最好的追問方式卻是可疑的,也就是說,物是否源初地呈現為用具,仍可以討論的,海德格爾寫作《藝術作品的本源》或許正是為了進行這樣的討論。
②“不能見者”(the invisable)是馬里翁自己造的一個詞,指人眼無法看見的事物,區別于原則上人眼可以看到的“不可見者”(the invisible)。不可見者之不可見是因為沒有獲得邊界,這個邊界可以由人的目光給來給予;不能見者之不可見則是因為它超過了目光的尺度,不能被人的目光規定。
[1]Jean-Luc Marion.God without Being.trans by Thomas Carl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2]Jean-Luc Marion.In Excess.trans by Robyn Honor&Vincent Berraud.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2.
[3]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s.David Farrell Krell(ed).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3.
[4]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 by 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