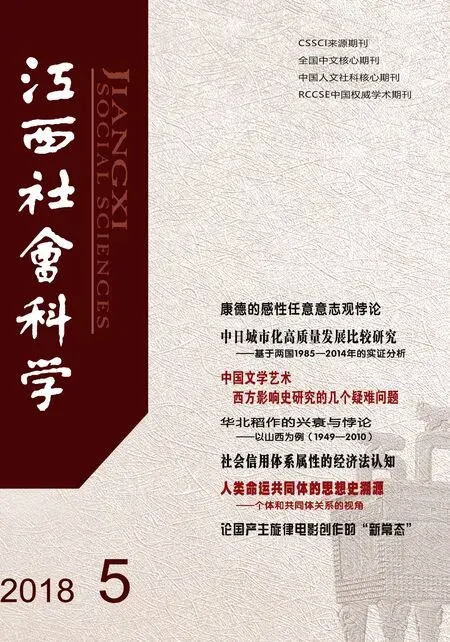政治、空間與城區變遷:清末民初天津的河北新區
晚清以降,中國城市的近代化之路在政治激蕩的氛圍中緩慢起步。受西潮影響,中國城市也開始著力于城市空間的重構①。近代中國城市的空間重構,一方面在于改造老城,拆毀城墻,打破了城市內的傳統空間布局;另一方面在于擴建新區,城區的擴展既促成了新的城市格局,同時也利用新區的內部空間塑造了新的城市形態。清末天津的河北新區②即是中國城市近代化歷程中擴建新區的鮮明例證。
近代天津的河北新區是1903年由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主導興建的一片新市區。新區所在的河北一帶在開建新區前還是“人跡罕到之處”[1](卷五《輿地(坊巷)》,P10),但在袁世凱主政期間得以快速營建。新區內街道規劃整齊,房屋林立,近代化的市政設施一應俱全,一時間被譽為“天津新世界”[2](P87)。清末的河北新區生機勃勃,大有抗衡租界之勢,但卻在進入民國之后意外消沉。其從無到有、從興盛到落寞的歷史變遷值得關注。目前學界關于河北新區的研究,尚以地方志為主③,側重于記述城區史話。其他關于天津的城市研究中對河北新區也有涉及④,但多為概述。此外建筑學領域對于河北新區也有相應關注⑤,其研究視角則集中于城區規劃和城市形態的演變。本文則旨在從政治與空間的雙重因素入手,對天津河北新區興建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做一梳理。
一、城市變革與空間訴求:開發河北新區的最初決定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始于1860年天津開埠,租界將城市近代化的因子帶入天津。而在此后幾十年間,華夷兩立。盡管在當時國人的眼中,租界區“街道寬平,洋房齊整,路旁樹木,蔥郁成林”[3](P121-122),但天津華界卻依然固守成規,變化緩慢。不僅如此,開埠后城市人口激增,規模擴大,華界的城市管理卻在“走向失控”[4],以致20世紀前的天津華界,道路“狹窄且骯臟”[5](P41),加之失修嚴重,一遇雨天“行人斷絕,全市就像死一樣的沉寂”[6](P20),同時衛生情況堪憂,“所有污穢之物無不傾棄溝內,以致各處溝渠盡行堵塞”[7]。連彼時旅華的外國人也將天津稱為“是一個我們從來沒有到過的最骯臟、看上去最貧窮的地方”[8](P32)。如此惡劣的城市狀態急需整治,但在天津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下,卻難以有效解決。
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變革,為天津的城市改造提供了新的契機。這一年7月,八國聯軍侵華后進占天津,聯軍在天津設立都統衙門,進行了長達兩年的殖民統治。八國聯軍設立的都統衙門,作為一個西式的市政管理機構,其在統治天津以后,迅速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法規、管理機構用于城市治理。都統衙門的管理顛覆了天津傳統時期的城市管理模式,將近代化的市政體系引入華界。對天津華界的城市改造也在此時開始起步,其首先改組了成立于1882年的公共工程局,由“都統衙門書記官雷那德任工程局主任,專門著手于道路的改良”[6](P20)。改組后的工程局在隨后的兩年時間內,填平了壕溝,擴建了城內的道路,設置了多條碎石馬路。還極具效率地拆毀了天津城的四面城墻,并在城墻的舊址上建設了四條環城馬路。城墻的拆毀成為打破天津傳統城市空間布局的第一步,而為了滿足城市近代化的需要,此后天津華界的城市改造,也在不斷地進行城市空間上的重塑。
1902年8月,袁世凱奉命代表清政府接管天津。接管后,按照協定,都統衙門的許多管理措施和行政機構得以保留。在此基礎上,袁世凱繼續致力改革,其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決心:“擬趁此變亂之后,將從前各項積習,痛于刷除,務期弊去利興,庶以仰副圣朝整頓地方至意。”[9](P621)袁世凱的天津改革同樣涵蓋從政治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改革的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天津因此成了“新政權興之地”,“四方之觀新政者,冠蓋咸集于津”[10](P3)。袁世凱依然延續了都統衙門時期對于城市建設的重視。天津于1902年9月設立了新的工程局,主要參與整修道路、疏浚河道、新建橋梁,并管轄田畝的注冊、道路路燈安裝、街道綠化等。新工程局裝備精良,職責明確,成為城市建設的主要力量。天津自庚子年后在城建機構上的系列改制和人員、設備的引入,為其后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提供了政治與技術上的可靠保障。
此外,在袁世凱的改革中,作為其新政的主要內容,大量的新式機構、工廠、學校紛紛設立。在最初的一段時間內,這些新設的機構多置于老城廂內,但隨著空間需求的提升,如工藝總局“限于地勢,無可開拓”[11](P684)之類的情形十分常見,天津城發展空間不足的形勢嚴峻起來。
清末天津城的空間困局源于歷史形成的城市形態。天津城始筑于明永樂二年(1404),筑城時僅按衛城的規格修建,清雍正朝城墻大修后,“東西長五百零四丈,計二里八分;南北長三百二十四丈,計一里八分五厘”[1](卷一《輿地·城垣一》,P9),即天津老城廂面積僅約1.76平方公里。至道光年間,城內共有“一大街、四小街、四衖巷、一百有六鋪……共九千九百一十四戶”[12](《縣城內圖說第一》,P435),已然十分擁擠。天津依水運而興,因而更靠近河流的東門外和北門外最先得以開發,并迅速形成了商業聚集區,尤其是北門外,“商旅輻輳,屋瓦鱗次,津門外第一繁華區也”[12](《北門外圖說第五》,P439)。而與市面鼎沸相對應的是空間利用上的飽和,當時《直報》就曾形容天津城“街道已極狹窄,更兼東洋車、地排車、小推車每日在各街走者絡繹不絕,尚遇擁擠,無立足之地”[4]。此外,天津城地勢北高南低,城南多是水洼之地,西門外也同樣“地稍荒僻,圍城多積水”[12](《西門外圖說第三》,P437),加上距作為轉運中心的三岔河口頗為偏遠,這兩片區域雖一直閑置,但卻難以利用。這樣一來,環顧20世紀初的天津城,老城的四周已無交通便利、地勢平坦的空間可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改革中的空間訴求,天津城就必須穿過河流去開拓新的城市空間。位于金鐘河以北、新開河以南的河北地區被首先選中。這片區域西連北運河,東接京奉鐵路,直到開建新城之前還“向系貧民居住,地臨曠野,荒冢累累,縱有田園,值價無多”[13]。決定在這片“人跡罕到之處”開拓新區的主要原因則在于直隸總督行署的遷移和河北新車站的設立。
在庚子事變中,原本位于老城外的總督衙門被戰火焚毀,袁世凱接管后,“查新浮橋北舊有海防公所一區……即于十二日駐扎該處,作為辦公之所”[14]。如此,直隸總督行署最先遷至河北。天津政治中心的遷移,立即提升了河北的空間地位。與此同時,庚子年后各國租界分別設立,已有的老龍頭車站毗鄰俄租界,這樣無論是官員往來,還是經營發展,都必須經過租界,十分不便。“天津鐵路舊設車站貨廠,地方逼近租界,開拓經營,諸多窒礙。”[15](P839)于是袁世凱飭令在河北添設新車站,新車站通車后,“北來官員多在該站下車”[16],“車行數月,商民稱便”[15](P839)。河北新車站的修建是為了打破租界對老車站的封鎖,同時也讓官方對這個車站給予厚望,希望其能成為新的轉運中心,以替代老車站。而新車站與老城區之間的河北地區也因此變得重要起來。
督署行轅的遷移提高了河北地區的政治地位,新車站則為其帶來了充滿希望的經濟價值,河北地區整體空間價值的迅速提升,使其很自然地成了新城區的不二之選。由此,1903年初,袁世凱正式批準了由天津工程局擬定的《河北新開市場章程十三條》(以下簡稱《十三條》)[17],建設河北新區的序幕正式拉開。
二、行政效力與空間形塑:清末河北新區的快速營建
圍繞著河北新區的開發在《十三條》頒布后迅速展開。對于在新政氛圍中營建的河北新區而言,其建造既需要有效的行政推動,同時還需考慮如何形塑好新的城市空間。行政效力著眼于解決建設中的具體事務,而如何形塑空間則關乎河北新區的基本內在。這兩者在清末河北新區的開發過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應對。
在行政效力上,受袁世凱新政的影響,此時天津的市政機構已被革新,并在新區的建設中展現出積極務實的行政作風。從直隸總督衙門到天津府縣,再到工程總局,相關機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套運作良好的管理體系,保證了新區建設中各項活動的平穩進行。
在開發之初,市政部門首先制定了管理城區開發活動的若干條例。1903年2月由袁世凱批準的《十三條》,是最早頒布的一份管理條例。《十三條》的內容涉及新區界內的土地征用、墳塋遷葬和稅收問題,同時還專門針對私人的建設活動作出了若干規范。此后隨著城區開發的進行,不同的情況開始出現,“隨時考察,證以原定章程其中有辦法未宜,情形稍異之處,以及原章之外,續經稟定,蓋房取土各章程自應因時制宜,分別增改,量為變達,以期盡利便民”[18],所以在《十三條》頒布兩年之后,新的《變通現行新章十三條》[18](以下簡稱《新十三條》)頒布。《新十三條》涵蓋了《十三條》的絕大部分內容,并對之前的內容做了一些細化和變通。《新十三條》頒布的宗旨是“盡利便民”,其在許多方面寬限了一些原定的期限,同時強調“其有未盡事宜,隨時察看情形,分別稟辦”[18],也體現了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
官方的行政效力還體現在處理新市區的征地、拆遷和遷墳等棘手問題上。在這一過程中,市政部門同樣保持了一定的靈活性和務實性。新區內有大量土地歸私人所有。對于私有土地的征用,通常由工程局先行勘驗,依據規劃決定征地的范圍,然后工程局會將詳細的征地情況,“其所分之地段、號數,詳注繪圖一面……懸掛工程局門首,以備商民人等,照圖細看分明”[19]。同時被征用土地會依照土地優劣,分段標注對應的征地價格。在不同的工程項目中,土地價格則因地制宜,被標注不同的價碼,如修建種植園的征地中,土地的價格被分為了六種[20],而在籌建海防公所時,土地則被分為了三等[21]。此后,工程局會要求界內的業主攜帶土地的契據到工程局注冊。雖然早在建設之初的《十三條》中就要求新市區界內的所有業主都需要到工程局對所屬土地進行注冊,但實際上土地的注冊工作一直進展緩慢,以至于在實際的征用過程中,工程局仍然需要頻繁地公示告知被占用土地的業主到局注冊。在河北窯洼的土地征用中,呈契注冊的時間就被迫改期[22]。業主完成了土地的注冊后,工程局會派員隨同其一起前往勘驗確認。業主對注冊工作并不十分配合的一個原因是作為曠野的河北地區,很多地戶原本就沒有契據,因此便無從注冊,而針對這種情況,工程局也給出相應的對策,其在征用建設種植園的土地時就曾給出公示,允許“無契地戶赴局聲明,準其取具甘結照數領價,以示體恤”[23]。
在房屋拆遷時,官方除了為拆遷的民戶補償房屋款項外,還會為其提供必要的安置。河北賈家大橋一帶的民居拆遷共涉及90余家[24]。在發款補地之后,該處居民仍“聯名稟求緩期遷移”,天津縣因此決定“其房地銀價及移費均行加增”,同時將該處居民暫時安置在西南角廣仁堂。[25]界內墳塋的遷葬也十分棘手,盡管府縣反復飭令界內墳塋遷葬,但和征地注冊時的情況類似,實際的遷墳往往是在冢墓的確影響到建設時才會進行。工程局只能一再示令要求有主墳自己遷葬,對于無主之墳則一般由義阡局完成。如河北窯洼一帶的遷墳工作即是如此。[26]市政部門耐心程度如此,連《大公報》也感嘆:“今地方官不避嫌怨,不憚煩勞,苦心經營,無非為民興利。”[23]
官方務實且靈活的行政效力促成了新區開發中諸多事務的平穩推動,而對于新政氛圍中開拓的新城區,官方顯然也更希望利用他們的行政力將新的城市空間完全革新。因而在他們看來,新的空間就需要制造新的城市形態,而中國傳統的筑城理念已經過時,租界成為他們所營建新區的模板。
早在大規模的建設活動開始之前,天津工程局就很快完成了對河北新區的建設規劃。《大公報》曾對此次規劃做了較詳細的披露:“河北一帶開修馬路建造市場等情已志本報,茲聞現經工程局繪畫詳細總圖,東至鐵路,西至北運河,其東西兩頭距離四里余,南至金鐘河,北至新開河,其南北兩頭距離亦約四里,新開河開建南北大街十三道,直達金鐘河及河北窯洼一帶,以便商民居住云。”[27]河北新區最初的四至被限定在東至京奉鐵路、西至北運河、南至金鐘河、北至新開河的范圍內。在工程局的規劃中,新車站與總督衙門連接起來的馬路成為新區的中軸線,其將新區切割為南北兩個部分。以中軸道路為基準,十三條南北向、六條東西向的馬路,將中軸線以北的城區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方塊。中軸線以南的地區則同樣被三條南北向、八條東西向的馬路分割開來。道路網和被馬路分割開的方格狀土地,構成了新市區的基本空間形態。這種學習自租界的城市規劃理念,顯然已經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城市建造的制式,它擺脫了傳統城市空間中的城墻和壕溝,也不再以官署府衙為中心,一切以道路為基礎。
界內道路的命名,也頗有特色。新區由總督衙門至新車站的中軸線被命名為“大經路”。以“大經路”為基準,所有與其平行的東西向道路被稱之為經路,與其相交的南北向馬路則被稱為緯路。大經路以北的七條經路,被以數字為首命名,如“二經路”、“三經路”等,以此類推。大經路以南,平行的經路依然以數字命名,但都以“東”字為首以示區分,分別是“東二經路”、“東三經路”等。緯路的命名則取自“天、地、元、黃、宇、宙、日、月、辰、宿、律、呂、調”,共十三條。大經路以南,與之垂直的三條緯路則命名為“陽緯路”⑥、“昆緯路”、“岡緯路”。新區道路的命名方式,雖字面多取自中國傳統文化,但其形式上的統一性,也與傳統城市的道路命名中強調以城中為核心、四方分開的命名方式不同,同樣體現了西式城市規劃的特性。
新空間的產生一方面促成了新的城市形態,同時也成了新設施的載體。新政中由官方主導的各類新式機構,如新式衙署、新式工廠、新式學堂等,在新區開發后迅速或遷入,或新建于河北新區。正是這些新機構組成了河北新區內的空間主體。
隨著總督行署向新區的遷移,大量附屬的行政機構首先遷入新區,其后在清末各項改革的推動下,產生了許多新置的行政機關,也多數設于河北新區。如:天津巡警總局,1902年設立,是新式的警察機關,位于總督衙門旁;學務公所,1905年設立,是直隸提學使的辦公場所,位于河北公園內;直隸禁煙局,1907年設立,主管直隸省的禁煙工作,位于地緯路,等等。根據1911年《天津指南》的記載[28],河北地區的全部行政機構共分11類,總數達到42所之多。這其中除了單獨管理河北新區治安的部分警察局所,以及京張、津浦鐵路的管理機構外,多數是直隸省屬機關,以及官辦實業機關。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機關在新區內的集聚,迅速強化了河北新區在空間上的政治屬性,也使之成為天津城市空間布局中的政治中心。
新區內同時新置了各類實業。在袁世凱推動新建的實業中,影響力最大的要屬直隸工藝總局。其在成立之后,“凡學堂工廠、勸工陳列所及勸業會場,與夫本郡、本省之各廠所、各堂場為總局倡導而創辦者,遠近向風,咸次第林立”[1](卷九《工藝》,P39)。在工藝總局的主導下,由其設立的工藝學堂、實習工廠、考工廠、教育品制造所、北洋勸業鐵工廠、勸業會場紛紛成立,皆駐于河北新區。這些官辦實業有些側重于制造實物,有些在于教授技能、展示模范。它們設立的近代化意義非凡,也促成了河北新區作為一個新經濟空間在清末的快速崛起。
大量官辦的公立學校也在新區內紛紛設立。在我們的統計中,清末新建于河北新區的學堂共有18所⑦,其中以專門性的學堂影響力最大,共有5所。如:北洋軍醫學堂,1906年6月遷往河北黃緯路;北洋巡警學堂,1902年設立,位于河北堤頭村;北洋法政專門學堂,1907年設立,位于新開河新橋以北。此外的新式學校還包括各類師范學校和女子學校,共有5所。如:北洋師范學堂,1906年設立,位于新開河新橋北;北洋女子師范學堂,1906年設立,位于天緯路。除了這些專門性的新式學堂外,還有大大小小的中小學堂在河北地區新設,這些學堂是新政中教育改革的重要一部分。
除此之外,官方還力求在新區內塑造更具近代性的公共空間,于是諸如公園、種植園、圖書館、電影院、展覽館等公共的文化設施也在新區內紛紛設立。界內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設施是籌備于1905年的“勸業會場”,其作為一個近代公園,早在籌備之時,袁世凱就對其寄予厚望,希望它“非漫為俗塵之游可比”[29]。勸業會場于1907年正式完工,開放后的勸業會場不僅是一個風景獨特的游覽地,而且包括市場、展覽館、照相館、會議廳、電影院、西餐廳等公共娛樂場所。官方對于勸業會場的精心構建使得勸業會場成為天津華界中首屈一指的公園,其“二門以內所有山亭花木、曲沼游廊、洞口流泉、籠中禽鶴,均任游人隨意觀覽,不取分文”[28](卷五《園林》),這種保持對民眾開放的姿態進一步促進了其作為公共空間的近代意義。此外界內還新建有種植園和李公祠等,種植園于1906年設立,位于新車站以東,占地十余頃,種植園設立之初在于培育植物,輔助工業,后對外開放,可供民眾游覽。李公祠,原本是為了紀念前直隸總督李鴻章而修建的祠堂,位于河北金鋼橋北岸以西,后亦逐漸成為商界以及自治團體集會的重要場所。教育和公共設施在新區內的涌現,成為活躍河北新區文化活動的助力,顯然也幫助提升了新空間的文化屬性。
不僅如此,市政部門在主導了新區的大格局和主要建筑的同時,還力圖塑造新空間的細節。比如,為了加強河北新區與老城區的聯系,市政部門對界內的橋梁進行了大的改造,主要的橋梁如新浮橋和賈家大橋都被改造為新式鐵橋,分別被命名為“金鋼橋”和“金鐘橋”。自來水和電燈照明也被應用于新區。城區綠化很受重視,樹木的栽植一直在進行,如北洋銀元局在建設新廠時就“種植樹木二百余株,羅列內外,以待成蔭”[30]。為了繁榮城區經濟,官方也大力提倡工商,勸業會場建成后就曾專門蓋房70余間,用于鋪戶租用。[31]
從衙署、實業到學堂、公園以及各類公共設備,這些官方主導下的新式設施,在河北新區嶄新的空間形態中,成為新城市空間中的實體。它們的快速營建,填充了新市區的內在,幫助河北新區完成了早期的空間形塑。而這些設施本身所具有的近代性,也使得河北新區以一種更活躍、更文明、更近代的形態展現出來。河北新區因此成為中國城市近代化的標桿。
總之,清末的河北新區在官方的推動下,日漸興盛,房屋林立。《大公報》曾載文評論:“河北賈家橋及窯洼一帶向系貧民居住,地臨曠野,荒冢累累,縱有田園,值價無多,自添修馬路后,日日興隆起蓋樓房無數,添設生意日多。該處之地,自三百兩一畝漲至五六百兩一畝。現時紅樓處處,種柳栽花。大有各國租界之風致。”[13]此時旅華的日本人也感嘆:“中國街亦不愧為直隸總督所居之地,中國洋式之華麗建筑亦不少。……其華麗,其殷賑,天津為北清之門戶絕無可羞之處。”[32](P4-5)
三、政治動蕩與空間劣勢:民初河北新區的最終落寞
河北新區的發展在民國肇建之后再次因為政局的變動發生巨變。1912年后,帝國威權的喪失引起了各種派系之間的政權之爭,政局動蕩的局面貫穿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受政治局勢的影響,天津城的整體形勢表現萎靡。因政治助力而興的河北新區,受制于此,很快暴露出其在城市經濟空間上的劣勢,新區發展陷入低迷。
對于河北新區而言,首先由政治動蕩引發的軍事沖突,為其帶來了直接且暴力的沖擊。在軍閥混戰的數年間,界內修建的大量官私房屋,常被進駐天津的士兵侵占,“區中多闊老公館今則□數遷入租界,且稍大住房亦多數為軍隊本部所占,客棧旅館欲罷不能,更較其他為棘手,衙署局所多在區內,大小學堂亦多屬之,大半因軍隊占用不能開學”[33](《區域(西區)》,P2)。新區內如華北博物館“惜為軍隊占用,幾等于廢”,天津公園“樓房多為官兵所占,從前景象變更殆盡”。[33](《名勝》,P17)此外,在戰爭威脅的環境下,出于自保,華界的商民不斷向租界轉移資產,1922年直奉戰爭期間,“河北一帶及中國界之富戶,無不日夜搬箱運篋遷往租界,以冀趨吉避兇”[34]。商民向租界的轉移進一步拉大了租界與華界的差距,而原本還希望能與租界抗衡的河北新區在這樣的環境中形勢一落千丈,一時間難有起色。
戰爭的威脅可能僅延續數年,但受北洋時期政局不穩的影響,清末強有力的行政效力已經消失,政府的管理幾近停滯。政治上的內耗首先體現在不斷的人事更迭上,在1912年至1930年的十八年間,天津共出現了十四位軍政長官,另外還有十五位兼任或單獨擔任的民政長官,即便是天津縣的長官也有八位。政府行政長官的頻繁更迭顯然意味著城市發展很難有持續性的行政推動,河北新區在行政助力消失之后,城區的發展也很自然地跌入谷底。
在整個北洋時期,乃至南京國民政府初期,河北新區市政建設都處于停滯狀態,以至于界內道路、衛生等狀況都差強人意。據1930年《天津市政調查匯志》統計,河北新區內只有大經路一帶因為道旁左右官署較多,商店房屋集中,“尚比較齊整”,但即便這樣大經路也“小坑亦不為少”。[35]相對之下,界內其他路段就很糟糕了。三馬路⑧與天緯路的交叉口為往來要道,因而“界內馬路之損壞,亦以此二路為最,界內衛生,尚差強人意,于午后八鐘起首,各臟水車分取各戶臟水,傾于市府西旁河內”[35]。海河歷經幾次裁彎取直工程后,金鐘河成為廢河,成了傾倒垃圾的地方,“皆任意傾倒廢水,臭不可近”[36]。界內的中山公園在北洋時期內“毀壞程度太鉅,殊非易于整頓”[37]。
整體來看,北洋時期的河北新區,因為市政上的不作為,整個新區除了東南大經路一帶因為在清末就已得到了很好的開發以外,其他地區,尤其是西北一帶一如民國前的情形,發展幾乎可以忽略。市政調查中也這樣反映:“自宇緯路直至車站,東界大經路,西界新開河……因近年時局不靖之影響,始終未見繁榮,界內馬路,除大經路尚敷衍可觀外,余如三馬路之下游,及各緯路,均損壞不堪,坎坷不平,西北角空地尚多,未曾建筑,亦自民十以來,市政未有進步之明征也。”[36]
行政助力的消失促使了河北新區開發活動的停滯,隨之而來的是市政的衰落。而對于城區自身的發展而言,缺乏了有效干預,河北新區則被迫進入自然生長的狀態。在此狀態下,河北新區既表現出固守已有空間格局的特點,它依然作為天津的政治中心存在,同時新區在經濟空間上的劣勢也隨之暴露,其已經距離成為天津城經濟中心的最初定位相去甚遠。
國民政府時期,地方行政結構多因襲前制,天津多數的衙門機構僅作名稱上變動,職權和駐所多未有變化,河北新區依然是天津大部分政府機構所在。1928年之后,天津一度成為河北省省會,在此期間“河北省之機關,自由平遷津后,增加甚多”[38](第三編《政治》,P127)。新增的政府機構仍然大量設置于河北新區。根據《天津志略》[38](第三編《政治》,P126-142)的統計,當時天津市共有省屬機關23所,其中12所位于河北新區,市屬機關有11所,其中5所位于河北。民國時期河北新區政治中心地位的強化,首先是由于舊衙門駐所仍然需要利用,其次也是人們對河北作為行政中心一種心理上的默認,時人亦認為:“該項地帶,前清即為總督衙門,民國以來,地方長官,均以此為衙署,有此悠長之歷史,市民心目中已認此為全市精神上之行政中心區域。”[39](P33)
盡管民初的河北新區在城市的空間布局中,依然作為華界的政治中心存在,但此時空間上的政治屬性并沒有引發如同清末時期的示范效應,河北新區在設立之初就隱藏著的經濟空間上的短板,使得它的城區經濟失去活力。在河北新區的最初規劃中,“自光緒庚子而后,津埠商業漸趨于租界一帶,河北地面空曠,當道籌劃振興市面之策”[40](P30),官方原本計劃提振河北新區從而使之能抗衡租界。為此,市政機關力促籌建河北新車站,望其能替代老車站,成為新的轉運中心,但這種設想顯然忽略了經濟距離的巨大影響。雖然鐵路的接通為天津的貨運帶來了新的交通方式,但天津龐大的貨運往來依然有相當部分依賴于水路,所以即便是有新的馬路和鐵橋將新車站與老城區聯系在了一起,但新車站與水路的遙遠距離還是成了其發展的最大障礙。在這個方面,距離河岸更近的老車站依然具有天然的優勢。這一情形實際上在清末已有所隱現,其時的常關報告中就曾評論:“該站(北站)因貨運量小,倘不計客運,則較為次要;再者,水路之遠隔,即此或令該站無以成為貨物的集散要地。”[41]正因如此,新車站顯然沒能為河北新區帶來預設中的助力,而華界傳統的商業布局又依然集中在老城區的城東與城北,與河北新區始終保持隔河相望的態勢。總覽民國時期天津工業發展的概況,此時的工業分布仍以河道布局為主,老城的北門外和西門外都成為工業的重要聚集區,甚至南門外區域也成為地毯業的聚集區,相比之下河北新區在工業布局中就僅僅以幾家紗廠、面粉廠散布,并沒有大面積的工廠聚集[42](P116)。而根據1929年的調查,天津共有工廠2186家[42](P117),河北新區在我們的統計中卻僅有33家⑨,占比極低。此外,我們還利用1921年的《天津指南》和1930年《天津志略》中的統計⑩,對駐區的若干項小工商業進行了簡單對比,這一時期界內的小工商業也十分匱乏,除了客棧業有一定占比之外,其余各業都十分低迷。這些也都恰恰印證了河北新區經濟發展中的空間困局。
回顧民初河北新區的發展際遇,動蕩的政治環境成為城區失勢的最主要原因,它在直接破壞城市的同時,也加速了華界與租界的差距,直接導致了河北新區的一蹶不振。但從河北新區發展的內力來看,空間距離上原生的劣勢,使得河北新區在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后,隨之也喪失了與租界抗衡的空間資本。河北新區在經濟空間上的巨大不足,成為民初河北新區頹敗的內因。
四、結 語
總的來看,清末民初天津的河北新區,其從無到有、由盛轉衰的歷史變遷一直伴隨著政治的干預和空間因素的影響。清末天津城在政治上的變革,提供了城市近代化的需求和條件,先進制度和優秀技術的引入使得城市改造成為可能。而面對歷史遺留的城市空間困局,開拓新空間成了破解困局的最優方案。政治力在這中間也表現得極具魄力,很快促成了河北新區的誕生。不僅如此,高效的行政能力還成為河北新區在晚清時期快速營建的重要保障。官方在保證新區內各項建設活動平穩進行的同時,也行之有效地塑造了新的城市空間。他們在新空間內既制造了新的城市形態,也建設了新的城市內容,河北新區也因此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化城區。在清末數年間,顯然是政治一直在塑造空間,進而改變了城市的近代化歷程,而這種影響顯著且積極。
但是進入民國以后,政治與空間兩重因素的交合,其作用力卻在數十年間發生了由正向到逆向的轉變。北洋時期的政局動蕩,不僅讓河北新區失去了必要的政治支持,還迫使新區暴露出了其在經濟空間上的劣勢,從而導致了河北新區的最終落寞。事實上,河北新區的空間劣勢早在其設立時便已經存在,只不過彼時強大的政治力幫助掩蓋了它的不足,但當政治助力消失時,空間上的缺憾卻成為城區頹敗的重要原因。
由此,從河北新區的興衰變遷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城市新區的發展歷程中,政治因素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能否提供持續的行政支持關系著城區發展的成敗。但是當政治力過于強大時,又很容易忽略城區發展中的空間合理性。雖然強有力的行政干預能夠彌補城區發展中的空間劣勢,但一旦行政力消失,空間上的不合理就會成為制約城區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此情形在形勢激蕩的清末民初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事實上,倘若我們正視當代中國城市的現代化之路,在層出不窮的城市新區中,如河北新區這樣重政治干預、輕空間合理性的情況還在不斷上演。如何從歷史中得以警醒,值得我們思考。
注釋:
①圍繞著近代中國城市的空間重塑這一命題,學界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其中,周錫瑞強調城市的空間重塑影響了人際關系的變化,參見:周錫瑞《華北城市的近代化——對近年來國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2002年Z1期)、《重塑中國城市:城市空間和大眾文化》(《史學月刊》2008年第5期);陳蘊茜則強調國家權力對城市空間重塑的巨大影響,參見:陳蘊茜《國家權力與近代中國城市空間重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3期)。
②在河北新區設立之初并無“河北新區”這一概念,官方文件中以“河北新開市場”具體指代,其他場合,如晚清民國的報刊等指代也常簡略為“河北”。“河北新區”概念作為一種特定指代,最常出現于近年學者們的研究論述中。本文則沿用這一提法,指代1903年《河北新開市場章程十三條》中確定的“河北新開市場”這一區域。
③比如:天津市河北區地方志辦公室編《天津河北簡史》(內刊,1995年)、天津市河北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區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④比如: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李森《天津開埠前城市規劃初探》(《城市史研究》1996年Z1期)、劉海巖《空間與社會:近代天津城市的演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⑤比如:傅東雁《中國城市近代化的縮影——20世紀初的天津河北新區》(天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靳潤成、劉露《明代以來天津城市空間結構演化的主要特點》(《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張秀芹、洪再生、宮媛《1903年天津河北新區規劃研究》(《多元與包容——2012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15.城市規劃歷史與理論)》,中國城市規劃學會,2012年)。
⑥“陽緯路”一名又因諧音不雅被改為“新大路”。
⑦統計數據來自(清)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記》(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4頁)。
⑧河北新區界內“經路”在此時已改稱為“馬路”,如“三經路”改稱“三馬路”。
⑨統計數據來自天津市河北區地方志辦公室編《天津河北簡史》(內刊,1995年)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河北地區工廠一覽表》,第143-146頁。此數據雖不精確,但也能反映河北新區工業情況。
⑩統計數據來自《天津指南》(新華書局1921年版),以及1930年宋蘊璞編《天津志略》(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清)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記[A].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2]津門精華實錄[A].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一冊[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3](清)張燾.津門雜記[M].丁綿孫,王黎雅,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4]陳克.十九世紀末天津民間組織與城市控制管理系統[J].中國社會科學,1989,(6).
[5](日)坪谷善四郎.北清戰地地志[A].津沽漫記[M].萬魯建,編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6]二十世紀初的天津概況[Z].天津:天津地方史志編修委員會總編輯室,1986.
[7]通溝除穢[N].直報,1895-05-15.
[8](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圖本)[M].許逸凡,趙地,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9]袁世凱.恭報抵津日期接收地方情形折[A].袁世凱奏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清)李映庚.北洋公牘類纂序[A].北洋公牘類纂正續編: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11]工藝總局稟酌擬創設考工廠辦法四條[A].北洋公牘類纂正續編: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12]津門保甲圖說[A].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13]新開馬路[N].(天津)大公報,1906-06-27.
[14]袁世凱.駐扎天津海防公所辦事片[A].袁世凱奏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5]袁世凱.天津車站接修西沽岔道撥關內外鐵路借款折[A].袁世凱奏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6]馬路告成[N].(天津)大公報,1903-02-03.
[17]再紀河北一帶開筑馬路市場章程十三條[N].(天津)大公報,1903-02-28.
[18]道府工程總局回街告示[N].(天津)大公報,1905-04-05.
[19]地段繪圖[N].(天津)大公報,1903-05-03.
[20]具領地價詳紀[N].(天津)大公報,1907-06-10.
[21]驗領地價[N].(天津)大公報,1908-02-08.
[22]呈契改期[N].(天津)大公報,1903-03-30.
[23]展期領價[N].(天津)大公報,1907-01-31.
[24]續紀開修馬路[N].(天津)大公報,1903-01-18.
[25]移民善政[N].(天津)大公報,1903-01-11.
[26]工程局示[N].(天津)大公報,1904-05-06.
[27]紀開修市場事[N].(天津)大公報,1903-03-14.
[28]石小川.天津指南[M].天津:文明書局,1911.
[29]銀圓局總辦周詳遵飭會勘公園地址及工程局繪圖呈督憲文[A].直隸工藝志初編:上[M].天津:北洋官報總局,1907.
[30]補種樹木[N].(天津)大公報,1904-04-02.
[31]提倡工業[N].(天津)大公報,1907-05-17.
[32](日)宇野哲人.中國文明記[M].張學鋒,譯.北京:中華書局,2008.
[33]甘眠羊.新天津指南[M].天津:絳雪齋書局,1927.
[34]戰事結束中近聞[N].(天津)大公報,1922-04-15.
[35]天津市政調查匯志(六)[N].益世報,1930-07-12.
[36]天津市政調查匯志(九)[N].益世報,1930-07-15.
[37]炎威逼人中之清涼世界[N].益世報,1930-07-14.
[38]宋蘊璞.天津志略[A].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39]梁思成,張銳.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A].梁思成全集:第1卷[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
[40]京奉鐵路管理局總務處編查課.京奉鐵路旅行指南[Z].天津:京奉鐵路管理局,1917.
[41]吳弘明.試論京奉鐵路與天津城市的發展[J].城市史研究,1998,(Z1).
[42]劉大鈞.中國工業調查報告:上冊[A].李文海.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近代工業卷·上[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