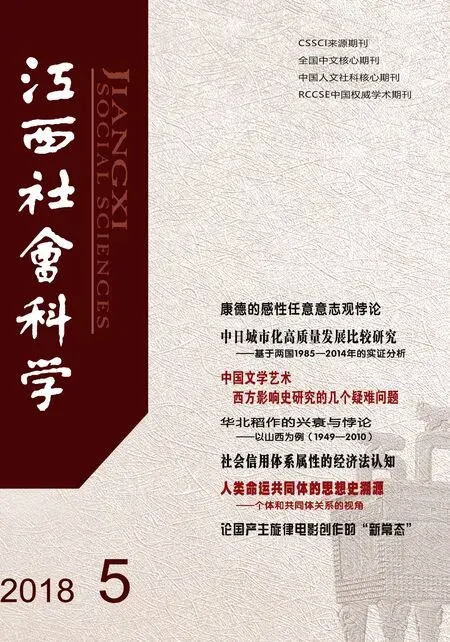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罰沒分成”的證券監管有獎舉報制度構建
隨著金融市場的縱深發展,證券違法行為的數量也日趨漸長,行為的隱秘度以及復雜程度逐步提高。從內幕交易到基金經理“老鼠倉”,從欺詐發行上市到虛假信息披露,證券市場層出不窮的違法違規事件不停“鞭打”著本就脆弱的“三公原則”,嚴重傷害了投資者的信心。[1]受制于人力、物力、財力和技術手段,監管者要憑一己之力實現完全有效的監管,并不現實,違法違規行為的頻發與證券監管執法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越發顯著。[2]作為擴充證券稽查線索來源的方式之一,對于舉報人的物質激勵可以提高公眾參與證券執法的積極性。但自2001年《關于有獎舉報證券期貨詐騙和非法證券期貨交易行為通告》頒布實施以來,實踐反響平平。雖然證監會于2014年發布了《證券期貨違法違規行為舉報工作暫行規定》,對內幕交易或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操縱證券或期貨市場、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欺詐發行證券等行為,知情人都可以通過實名舉報的方式獲得一定數額的物質獎勵。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由于缺乏足夠的物質激勵和配套措施,舉報人的積極性普遍不高,通過知情人舉報來獲取相關線索和證據的比例依然偏低,這也是導致違法違規行為屢禁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3][4]為此,以“罰沒分成”為核心構建證券監管有獎舉報制度,可以充分調動舉報人參與提供證券期貨違法違規線索的積極性,并助力于實現監管效能的最大化。
一、法理論:證券監管中有獎舉報的法理基礎與監管邏輯
監管對象的激增,監管要求的提升,都在考驗著本就有限的證券監管資源的承受力。如何改變過去“保姆式”的監管方式,合理配置監管資源并提高監管效能,是在監管轉型下證券監管機關所面臨的重要考驗。在這其中,有獎舉報制度的推出便是法律實施中私人監督的重要表現方式之一。
(一)私人舉報涉入行政監管的立法依據
立法依據的確定,事關制度設計的思路、架構、內容。從法學視角而言,證券監管中私人舉報的立法依據大致有“權利說”和“權利義務綜合說”兩種學說。[5][6]在“權利說”的學者看來,私人舉報源于憲法上的監督權,但這多指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舉報。[7]在“權利義務綜合說”學者看來,舉報既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多指向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內的,對任何違法行為的舉報。[8]在我國,向行政機關舉報對法律實施的私人監督是一種重要的憲法權利,同時也是一種法定義務。但同時,私人舉報的立法根源又較為復雜,需根據舉報主體和對象來探查。[5]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舉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公民監督權的表現,但如果是公務員就內部不當行為的舉報,因為涉及對內部舉報是否屬于其法定義務的判斷,所以這類舉報行為的性質尚未有明確定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6年“塞巴洛斯案”(Garcetti v Ceballos)中就認為:“如果政府公務員基于其職務身份舉報,因為所舉報的內容與其職責有關,因此被其所服務的機構解雇的,不可以尋求憲法的保護。”[5]事后雖然國會迅速通過法案以消除上述案件的影響,但小布什總統卻對此法案發動否決權。直至2012年奧巴馬總統簽署 《揭發者保護加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Enhancement Act of 2012)后,才將保護的范圍擴大到聯邦職員。其實,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學者們在對各國公法實施問題的研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私人監督與公權力監督的關系以及公法框架下私人的訴權。[9]如何將證券監管中私人舉報與公權力監督聯系起來,尋求公私合力執法體系搭建的法理依據與制度的正當性,就成為有獎舉報制度入法,以及制度順利推行的保障。
(二)有獎舉報的監管邏輯:法律實施中的私人監督
法律實施是社會關系的參與者在出現法律規范所調整的法律事實的情況下,按照法律規范的要求所建立起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的活動。[10]在這其中,守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是法律實施的主要途徑。同樣,在英美法系語境下,雖然與我國關于法律實施的定義不同,但從其所包含的監督被法律約束主體的行為、對違法行為起訴、對是否違法作出裁判、對違法者進行懲處在內的四塊具體可供細化研究的內容中,也可以看出法律監督在法律實施中的重要作用。根據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編纂的《法學辭典》對于法律監督的闡述,其一方面可以被解釋為實施監督法律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包含著對法律實施的監督。[11](P272)從狹義上說,法律監督多出現在國家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和權限所為的對立法、司法、執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監督活動。但從廣義上而言,也是從法律實施的制度規范角度來看,在法律監督中,以社會組織和公民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的監督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英美法系也認為,法律監督是一個公權與私權交融、混合交錯的綜合體。只有將國家機關監督和社會力量監督有機結合,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實施監督體系。[12](P452)國家并非法律監督的專斷者,我國法律也同樣認可私人監督的概念。包括私人、社會團體等在內的私法主體是法律所允許的對國家、對其他私人的違法行為以及違法信息的發現者和法律監督的發動者。對此,我們可認為,私人監督是作為違法行為案外人的私權主體對違法行為人違法行為的監督,包括但不限于發現違法行為、收集違法信息、采集違法證據,并提供給公權力機關供后者進行追究法律責任的行為。[6]
幾千年的中華文明一直在道義上鼓勵私人監督,但依靠道德驅使的監督行為卻因無法提供足夠的補償和激勵機制而在現實生活中“舉步維艱”。雖然應該對私人參與共建公私合力的監督和執法體系大加褒獎,但若制度的設計僅僅是建立在對個人道理主義的非理性期待上,那么就完全喪失了制度規范本身所應具有的意義。[13](P10)
(三)私人參與分享執法權的法經濟學分析
在域外實踐中,違法行為舉報者具有監督并調查違法行為、代表政府起訴、分享罰款和賠償等兼具公權和私權雙重屬性的權能。這種公私共同參與分享執法權的做法可以被理解為執法權在公共機關和私人之間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分配和共享。[6]盡管很難解釋清私人在罰沒分成中的行為和權力性質,但這樣一種理論上的闡述困難并未對實踐中制度的順暢執行帶來阻礙,并且正是由于這種私人在法律實施和監督中角色的異化,而給法律實施帶來了活力。[6]在傳統法學理論無法為私人參與公權力執法提供太多的論證支撐的背景下,若從法經濟學視角來揣摩該制度的內涵,大致能得到較為恰當的解釋路徑。
在經濟學家們看來,執法權的法律歸屬并不是一個問題,在古代社會,并不存在任何公訴機關。肩負履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組織還不夠健全,法律也常會賦予公民以政府名義執行某些公權力職能,以彌補政府執法能力和執法力量的不足。[14]可以說,法律實施的最初形態就是依靠私人執行,警察實質上只是被允許的私人法律實施者,其所有的公共性也僅是名義上而已[15](P780),如何尋求執法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才是制度探查的著眼點[16]。經濟學家們認為,執行法律的社會成本與收益并不會影響到公共機構的自身利益。既然執法者不能夠從降低執法成本、提高執法效率中受益,也不會因為不積極作為而受到利益上的減損,那么其在執行法律上漠不關心或是缺乏效率就有因可循了。[17](P167)所以要想在現有社會背景下尋求執法效率的提高,一個切實可行的路徑就是擴大執法的主體范圍并給以激勵,將執法權恰當地在公共機關與私人間分配。若私人執法主體能夠從執法效率提高中持續獲得利益,其在利益的享有上便能更好地與全社會利益相協調并保持一致,有助于最佳執法效果的實現。[18]
二、比較論:域外有獎舉報制度的經驗借鑒
在證券監管中采用舉報獎勵并非新鮮事,這在域外實踐中早已有之。從其發展歷程來看,該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相關配套制度相伴成長。我國在構建以“罰沒分成”為核心的證券監管有獎舉報制度的過程中,既不能盲目照搬域外經驗,也不能搞“單兵突進”,而是應該將相關配套制度同步推進,避免證券市場淪為令人咂舌的“檸檬市場”。
(一)國際組織在內部人舉報制度上的努力
作為私人監督法律實施的一條重要路徑,對有獎舉報制度的研究要與內部人舉報制度聯系起來。從域外實踐來看,國際組織一直致力于對內部舉報人的行為加以規范,并構建對其利益保護的法律規范,以促使公共和私營機構更加透明而負責的機制的實現。[5]就國際組織規范制定而言,《聯合國反腐敗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第8條規定:“各個締約國應當基于本國法律的基本原則,通過相關制度的制定,來便于公職人員在履行公務活動的過程中對所發現的腐敗行為進行舉報。”[5]OECD在2000年修訂的 《跨國公司行為準則》(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總方針中提到:“企業應克服對善意的向管理者、合適的公共機構舉報企業違反法律、行動準則、企業方針的企業從業者進行歧視或懲戒。”[5]OECD緊接著在2004年《公司治理準則》中又指出:“利害關系人可不受拘束地向董事會告知其對違法或不合理的行為的疑慮,前者權利并不得因此而受減損。”
(二)美國對于內部人舉報立法的兩大路徑
美國是較早對內部人舉報進行立法的國家,其大致包括了兩大路徑。[2]一是旨在保護國家財產不受不當減損的《反欺詐政府法》,該法案允許不隸屬于政府的公眾,代表政府向在政府項目中有意對政府錢財不當占有而為欺詐行為的人提起訴訟并追討,舉報人可根據訴訟所裁定的賠償額獲得15%~30%的獎金。[5]另一路徑是旨在維護雇員權利的有關舉報人保護的系列法案,這其中又分為針對政府機構的內部舉報和針對民間機構的內部舉報兩種方式。從1978年《文職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of 1978)正式提出對政府內部揭發者的保護措施,并設立了專職機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來擔負日常職責開始,美國正式拉開了對內部舉報人保護的立法序幕。1988年《軍隊內部揭發者保護法》(Military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1988)和1989年 《揭發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1989)的制定進一步強化了對內部舉報人的法律保護,后者還被視為世界上第一部專門保護揭發者的法案。[18]1994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意在減輕舉報人舉證壓力的《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再授權法》,從而形成了對政府機構內部舉報的舉報人保護制度體系。相比而言,雖然對于民間機構的內部舉報人保護沒有形成一部較為完備的法案,但在涉及環保、證券、核能等領域的多部聯邦法中,依然可見對于內部舉報人法律保護的制度安排。[19]特別是在“安然事件”后,美國國會快速通過了《公司舞弊責任法案》(Corporate and Criminal Fraud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2),對涉事公司施加了較為嚴苛的規定,用以防止因舉報而遭解雇員工的利益受到不當減損。
(三)英美法系其他國家關于內部人舉報的立法歷程
英國對于內部舉報人的保護較早見于1975年頒布的 《雇傭保護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EPA),該法規定,雇主對披露工作環境中健康安全問題的勞工的解雇是不公正的,雇主不得對上述勞工報復。[5]但該法所關注的內部人披露和舉報僅限于有關工作環境的健康安全問題,對于其他內部舉報暫不涉及。之后,英國又于1998年通過了《公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of 1998)。該部法律擴大了《雇傭權利法》(Employment Right Act)對于“勞動者”范圍的界定,將派遣員工、研修生、公務員等均納入其中。在適用范圍上也十分廣泛,突破了以往就具體類型和事項的特別立法,而是不分行業和公私性質的對進行舉報的內部人適用同一標準的規范保護,且披露對象不僅包括發生在英國本土境內的違法行為也同樣適用于境外的違法行為。當然,《公益披露法》出臺的目的并非鼓勵或抑制舉報,而是減少企業對舉報的限制,保護善意舉報人不會因為舉報或披露而遭受不利的對待。[20]同為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亞在最近幾十年來也相繼出臺了有關內部人舉報的法律[21],但遺憾的是,制度規范的重點主要針對基于政府機構違法行為、腐敗和不當行政的舉報,僅有個別法律將保護范圍延展到私人企業。不過在2004年澳大利亞《公司法》修改中,也為公司員工內部舉報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5]該法與2013年通過的《公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of 2013)一起構成了澳大利亞對內部人舉報保護的法律框架。
(四)以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在內部人舉報上的立法概覽
再將視野轉到大陸法系國家,日本最初是通過判例來保護內部舉報人的。日本最高裁判所于1983年9月16日在一則裁判中曾指出:“在雇主行使懲戒權或解雇權時,如果欠缺合理理由且也無法得到社會一般觀念的認同,那么雇主的行為就可能因為濫用權利而無效。”②在2003年著名的大阪和泉市民生活協會內部告發案中,法院認為:“內部告發在內容失當時,具有對被告發者造成名譽、信用減損之風險;但在告發內容真實時,又可為被告發者組織運營方法改善提供契機,并且后者不得因為內部告發而對舉報人進行懲戒或解雇。”③之后,日本又于2004年在借鑒英國《公益披露法》的基礎上,針對日本社會實際情況,制定了《公益通報者保護法》,其對以往法律所提及的“內部告發”概念進行了小幅修正,排除了內部告發字面所可能具有的公報私仇、自首告發的概念外延,將法律所保護的告發嚴格限制為基于公益的告發,但在規范內容上,該部法律又與英國《公益披露法》相似,對內部舉報人實施的是不分公私、不分事項的綜合性特別保護。包括企業和事務單位中的勞動者、公務員在內的內部舉報人均可以得到法律的“庇護”。[22](P1-2)在《公益通報者保護法》中,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犯罪行為也屬于公益通報的事實之一。
三、監管論:建立有獎舉報制度的必要性與或然性風險
目前在我國,對證券違法行為查出的有效性和執法效率還不能完全適應監管和市場需要,突出表現為在調查和取證上的困難,而有獎舉報制度的建立毫無疑問對擴大違法線索的搜集來源大有裨益。但與此同時,一些缺乏基本線索的“冗余”舉報以及惡意失實舉報也會給本就有限的監管資源造成浪費,帶來資源分配上的難題。
(一)證券監管轉型下推行有獎舉報制度的必要性
法律所調整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多樣性以及實施難度的日漸增高,使得越來越難以通過公權力機關的一己之力來推動,所以通過擴大法律實施的參與主體,以有獎舉報機制來分散證券監管的成本,并分擔因法律實施錯誤導致的實施失敗的風險,無論是從歷史傳統還是現實需要來說,都是必要且可行的。
第一,證券監管機關在證券稽查和執法中具有天然缺陷。證券違法行為具有復雜、多樣且隱蔽的特點,證券監管部門作為外部公權力監管者,很難獲得違法信息。政府對于證券商事活動,往往存在信息偏在的情況。即使依靠專業調查和審計等手段,依然難以和掌握實質信息的內部人相比擬。對于后者而言,他們有信息獲取的獨特優勢,通過物質激勵來擴大法律監督隊伍,對削弱公權力主體與市場主體間信息不對稱有很大幫助。且在利益俘獲理論者看來,公權力機關的官員也是追求個人利益的“理性人”,極有可能被利益集團收買,從而在查處違法行為上多有懈怠。故而通過擴大執法主體的范圍,將私人監督有效運用到證券違法行為的查處中去,可以起到對公權力機關及官員的社會監督的效果,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官員在法律執行中不作為或不合理作為發生的概率。
第二,知情人在證券違法行為的情況掌握上具有天然優勢。雖然在社會責任的承擔上,企業應當遵紀守法,但法律的維護與執行依然離不開知情人的參與和配合。內部知情人因知曉內部信息而具有天然的維護法律的優勢。若能本著社會良知的觀念去關注企業發展,恪盡職守的維護社會安全,便可以及早披露相關企業的違法信息,成為行政監管的有效支持者。按照一般道德觀念,在股票發行注冊制下,當信息披露存在欺詐、虛假等違法行為時,知情人應當對此積極舉報并加以遏制,而非放任自流的任憑其發生。但事實上,知情人對于證券違法行為的舉報并非是一種揭露和遏制不法行為的有效方法,這在欠缺對舉報人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激勵的我國更是如此。
第三,擴大執法參與主體是監管資源匱乏下監管效率提高的需要。在資本市場發展的過程中,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組織體規模擴大且復雜程度提高,被監管者違法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以及監管者對上述違法行為的查處難度也在日益增大。包括內幕交易和虛假披露等在內的對證券違法行為罪與非罪的認定,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已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有研究指出,對于實踐中證券違法行為的禁止和打擊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并成為衡量一國金融法治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23]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監管水平、提升監管效率就成為監管層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加強監管固然重要,外部監管也可以對證券違法行為起到威懾效果。但在機構精簡的大環境下,有限的執法主體卻常常因為難以獲得被監管者隱秘的違法信息而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使得監管缺乏成效,并且還可能因為過分加大監管或是懲處力度而與行政比例原則相悖。[24](P26)所以作為對證券監管執法效能提高的積極促進因素,建立在舉報獎勵制度上的公私合力執法模式的推行,是對監管資源匱乏的一個有力補充。
第四,私人監督在證券監管領域往往比公權力監督更有效。在證券法實施中,依靠公權力監管者憑借自身調查去發現證券違法行為,并掌握其中證據,往往需要花費大量成本,甚至還會一無所獲。受制于編制、人力、經濟等軟約束,稽查局每年派出人手參與具體線索搜集的案件也較為有限,這直接導致了執法人員的水平和執法質量與監管需求不匹配。所以,如何在有限的預算下使得監管效果得到最大程度體現就成為監管部門的困擾所在。有學者指出,正是因為案件執行效率的低下,部分受公共預算約束的國家機關會刻意對某些案件淡然處之,將有限的預算投入能獲得較好監管效果的工作中去。[17]然而,在證券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的當下,證券監管部門無法對現存問題視而不見,他們也在努力調動各方力量來降低違法行為的發生頻率。從法律的私人監督視角出發,證券違法行為的知情人毫無疑問可以用比外部監管者低得多的成本發現違法信息,違法者也將因為擔心被內部人舉報而內心受到強大震懾,故而調動知情人參與證券執法的積極性就成為有效遏制證券違法行為發生的一條可行路徑。
(二)有獎舉報制度實施的或然性風險
一方面,有獎舉報制度實施可能導致舉報量激增,對監管資源帶來挑戰。來信、來電、來訪是證券稽查最主要的舉報渠道,但在這其中,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有用,也可能無用,甚至是虛假的舉報。一旦舉報激勵機制建立后,可能會出現相當一部分抱著“中獎”心態的舉報。在監管者看來,如果對所有舉報一一核實,監管者自身和被調查對象都將“被負擔“較高的監管成本,但由此是否會帶來高監管收益存有很大質疑。舉報核查任務量的增大,會耗費監管機構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會對本就有限的監管資源造成很大壓力。如何合理分配既有的監管資源,成為有獎舉報制度推進的一大難點。
另一方面,有獎舉報制度實施可能招來惡意失實的舉報,浪費監管資源。在中立的觀察者看來,對證券違法行為的舉報并非一定出于道德因素,而是富有爭議的,甚至可能導致破壞性的出現,所以舉報本身所蘊含的正義性也就大打折扣。[25]在有獎舉報制度較早實行的美國,舉報者不需要承擔足夠使監管者信服的證明責任,法律在匿名舉報制度下,又對舉報者施以額外的制度保護措施。即使存在舉報不實的情況,公司也不敢隨意懲戒作為舉報者的員工,受損失的只能是涉事公司和監管資源,這其實大大降低了舉報的可信度。[26](P186)就我國實踐來看,在對上市或擬上市公司的輿論監督中,也不乏濫用舉報政策的情況。一些不良用心的人可能捏造事實、制造麻煩,將舉報作為不正當競爭的手段,惡意侵害競爭對手或他人的商業信譽,甚至發生欺詐、敲詐的行為。這無疑浪費了監管資源,影響社會和諧穩定。雖然最后無辜的公司會得到“清白”的裁決,但其中的調查和核實會占用大量時間和資源。
四、構建論:完善以“罰沒分成”為核心的證券監管有獎舉報制度
以“罰沒分成”為核心的證券監管有獎舉報制度,對于監管資源的節約、違法線索的獲取、監管效率的提高等確有良好的促進作用,不過要想讓這一工具真正成為“治市利器”,仍有待制度設計的進一步細化和合理化。
(一)厘清舉報內容的正當性判斷標準
在以“罰沒分成”為核心的證券監管舉報制度下,舉報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是舉報人當否獲得法律保護,乃至享受“罰沒分成”的重要前提。所以對于舉報行為正當性的判斷,是在制度設計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筆者建議,應主要圍繞舉報內容的真實性和舉報目的的正當性兩方面來做探查。鑒于不同舉報人在證據搜集上的能力存在天然差異。公權力機關在判斷舉報人所提供線索真實性的時候,應當將舉報人信息收集能力的差別考慮進行。只要善意舉報人提出了支持其舉報內容真實性的一定理由,其舉報就當然的具有正當性。故而對于影響舉報行為正當性的舉報內容真實性的判斷,指的是善意舉報人基于一定理由對于所舉報內容真實性的內心信服。在對舉報目的正當性的把握上,只要舉報事項確定真實,涉案主體所為行為被法律明確禁止,舉報人的舉報就應當被認為帶有公益性,并符合舉報目的的正當性。
(二)明確舉報獎金來源的兩條路徑
根據國際慣例,用以獎勵舉報者的資金一般來源于罰款收入的分成。但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證券監管部門的罰沒款收入要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上繳國庫,具體需要開支費用時再按照收支兩條線的原則由財政部門撥付,所以包括對舉報人獎勵在內的證監會各項行政支出都必須事先得到財政部門的核定和批準。從實踐來看,有獎舉報的資金來源需要進行跨部門的協調,存在一定的難度,罰沒款全額上繳財政的現行做法無疑是有獎舉報制度推進中的一大阻礙。借鑒美國投資者公平基金制度的實踐,建議我國可以考慮建立投資者公平基金。一方面可以對因證券違法行為而遭受損害的投資者進行補償,另一方面還可以作為對舉報人獎勵的一個資金池,將來源于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中的罰沒收入歸入該基金。此外,對于證券違法行為的行政罰款,建議在滿足一定程序后,于收支兩條線之外,由證監會直接按照一定比例獎勵給舉報人,以“罰沒分成”機制解決目前獎金來源需要跨部門協調的困擾。[27]
(三)增加舉報獎勵金額
在證券違法行為的調查取證中,私人監督的成本固然比公共機關低,但隱藏在之后的潛在成本不可小覷。這其中,作為私人監督的潛在成本之一,舉報人面臨著被打擊報復的危險,且對其來說,這一潛在成本比直接成本大得多。若完全依靠舉報人的道德自發和無償自愿行為,會導致私人監督成本與收益顯著失衡,長此以往,是對監督動機養成的破壞。[1]以內幕交易為例,內幕交易知情人往往也是參與人或潛在參與人,與內幕交易可以或可期待獲得的非法所得相比較,目前我國實行的1%的獎勵標準、10萬和30萬的封頂額度對于承擔了很大風險的知情人來說,確實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獎金數額對于舉報人來說雖然只是一種激勵,但若獎勵太低,勢必無法彌補舉報人所面臨的社會風險和精神負擔。對于監管部門來說,可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技術手段都相當有限,單憑一己之力很難實現完全有效的監管,因而全民監督就顯得尤為必要。所以物質獎勵作為促使舉報人進行舉報的關鍵,不僅要對舉報人所承擔的私人監督成本以補償,還要將這個補償程度提高到足以抵消困擾舉報人的潛在的監督成本承擔,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通過有獎舉報的利益導向機制,將捆綁在違法行為人和舉報者身上的利益鏈條割裂,以減少證券違法行為的發生。
(四)罰沒分成數額的確定
為了防止舉報人為了獲取更多獎勵而知情不舉、放任違法行為的道德風險的發生,在計算應得獎勵時,要注意將舉報人知道或應當知道違法行為發生的時間考慮在內,對于在知道或應當知道違法行為發生日之后產生的、因損失擴大所應當處以的罰金,在計算獎勵金額時,不應納入罰沒分成的計算基數內。[6]此外,還要將獎勵金額的多少與以下因素結合起來確定:(1)被舉報信息的重要性,包括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關聯性;(2)被舉報行為的復雜性和社會危害性;(3)依靠公權力機關調查取證的困難性;(4)舉報人的舉報行為對于阻止違法行為所帶來的制度利益;(5)舉報人的舉報行為對于具體案件稽查的幫助程度。還應賦予監管機構進一步結合市場情況、監管能力對分成比例做出適當調節的權力,給舉報人穩定的可得利益期待。
五、結 語
證券監管中有獎舉報制度在美國運行已有三十余年,司法實踐的良好效果充分顯現了執法權公私共分體制的積極作用。從我國現有規定來看,已出臺的規范立法層級較低,獎勵條件和梯度規定模糊且獎勵金額偏低,在配套規則上也無法給舉報人以充分保護。因此,有獎舉報制度在我國資本市場“落地生根”后能否“枝葉繁茂”,還有賴于相關規則的完善。參考域外市場的制度經驗,以既存問題和風險為導向,厘清對舉報內容的正當性判斷標準,擴充獎勵金來源并提高獎勵數額是在已有制度改進上需多加關注的。同時,圍繞制度的或有風險,明確影響罰沒分成數額確定的若干要素,更有利于提升監管效率,防止舉報人道德風險的發生。
注釋:
①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學術觀點,與所任職單位無關。
②參見《判例時報》第1093號。
③參見日本大阪地方裁判所大阪府堺市支部判決2003年6月18日,《判例タイムズ》第1136號。
[1]潘清.構建“全民監督”新防線 A股“有獎舉報”效果待觀察[EB/OL].http://finance.chinanews.com/stock/2014/07-01/6339394.shtml.
[2]劉沛佩.論我國證券監管中有獎舉報制度的完善[J].證券市場導報,2017,(5).
[3]武俊橋,劉沛佩,邢梅.2014年證券市場法治述評[A].黃紅元,徐明.證券法苑(第1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4]李虹.美國證券違法舉報者“罰沒款分成”機制及借鑒[J].證券市場導報,2012,(12).
[5]王貴松.論公益性內部舉報的制度設計[J].法商研究,2014,(4).
[6]李俊峰.法律實施中的私人監督[J].社會科學,2008,(6).
[7]賴彩明,賴德亮.加強公民舉報權的制度保障[J].法學,2006,(7).
[8]湯嘯天.舉報人的權利與我國《舉報法》的制定[J].人民檢察,2004,(1).
[9]William E.Kovacic.Whistleblower Bounty Lawsuits as Monitoring Devices in Government Contracting.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1996,(9).
[10]吳淑賢.反壟斷法私人實施制度研究[D].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2010.
[11]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律辭典編委會.法律辭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沈宗靈.法學基礎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13](日)田中英夫,竹內昭夫.私人在法實現中的作用[M].李薇,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4]蔡巍.美國“公私共分罰款之訴”及其評析[J].法商研究,2007,(4).
[15](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下)[M].蔣兆康,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16]徐昕.法律的私人執行[J].法學研究,2004,(1).
[17]桑本謙.私人之間的監控與懲罰[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18]Mark A.Cohen, Paul H.Rubin,Private Enforcement of Public Policy.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1985,(3).
[19](日)境新一.內部告発者保護制度に關する諸問題[Z].東京家政學院大學紀要,2003,(43).
[20]David Lewis.Ten Years of 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1998 Claims: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tatistics and Recent Research?.Industrial Law Journal, 2010,(39).
[21]Parliament of Australia.Whistleblowing in Australia[EB/OL].http://www.aph.gov.au/binaries/library/pubs/rn/2004-05/05rn31.pdf.
[22](日)小西啓文,角田邦重.內部告発と公益通報者保護法[M].東京:法律文化社,2008.
[23]UtpalBhattacharya, HazemDaouk.TheWorldPriceofInsiderTrading.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
[24](日)阿部泰隆.內部告発(ホイッスルブロウワァ﹢)の法的設銒[M].東京:信山社,2003.
[25]繆因知.反欺詐型內幕交易之合法化[J].中外法學,2011,(5).
[26]Jonathan Macey.Corporate Governance, Promise Kept, Promise Brok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7]李季先.當下重塑資本市場法律信任的有效選擇[N].上海證券報,2014-07-30(A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