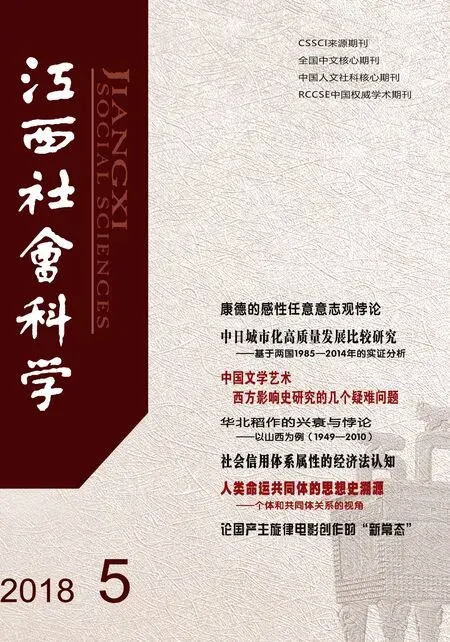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學理意義和建設思想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深刻把握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一系列重要場合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引發了國際社會成員的熱烈反響,也為新時期的國際關系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我國愿擴大同各國利益的交匯點,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1](P20)這一倡議提出之后,我國在現實空間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并進一步拓展到網絡空間。
當今國際社會,網絡將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各國均十分重視網絡科技的發展,對網絡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并發表重要的講話,正式提出了“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一倡議并強調:“網絡空間是人類共同的活動空間,網絡空間前途命運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各國應該加強溝通、擴大共識,深化合作,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2]“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表明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審時度勢,不錯過新科技革命的發展機遇的睿智決策,也在國際舞臺上彰顯了我國的大國形象,而中國作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者,也將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一概念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得到強調,并且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正式寫入憲法。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他國共同發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正是這一指導思想在互聯網領域的具體體現。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世界越發緊密聯系成一個整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有著豐富的內涵。
首先,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互聯網領域的延伸和具體表現,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依托于國際社會成員在互聯網問題上通過磋商合作達成共識,具體的進程是由具體的人來推動進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必是磋商方在互聯網領域的深化溝通達到了良好互動之后才能產生的效果。在互聯網領域內的溝通與互動,提供了一種新的交流思路和解決辦法,反過來也有利于其他領域問題的解決。
其次,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利益共同體,更是責任共同體。網絡空間具有開放性,為人類活動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問題:網絡中信息浩瀚,難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網絡詐騙、網絡暴力、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給全世界帶來了新的挑戰。網絡恐怖分子對外發布一條消息,在世界上任何一臺接入互聯網的終端上都可以完成,不僅具有十分的隱蔽性,而且使得信息傳播的廣度大為提升,沒有一個國家面對恐怖主義在網絡空間蔓延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維護國際社會網絡安全,也是維護國家自身的網絡安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將國際社會成員在網絡空間的利益和責任綜合到一起,共同擔負維護國際互聯網和平穩定發展的責任,維護國際社會在互聯網領域的共同利益。
最后,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對互聯網大會提出的“互聯互通,共享共治”這一宗旨的提升。通過網絡,我們共享信息,互通有無,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信息的傳遞。如果網絡利用方式不當,不僅不利于全人類共享互聯網發展的福祉,還會危及現實社會。例如,恐怖主義分子彼此間的溝通與行動協調,大都通過移動互聯網APP來進行,2017年6月在倫敦發生的恐怖襲擊就是一個典型。為避免這種悲劇的再次發生,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就顯得尤為重要。國際社會成員之間緊密聯系,榮辱與共,才能更好地應對國際社會發展和平與安全的網絡新威脅。
回顧過往的三次工業革命,有兩個顯著特點值得注意:一是新的技術手段促進了一系列新發明的出現,大大提高了人類生產力,拓展了人類的活動范圍;二是通過新技術手段的出現,人類進一步探索了自身潛力,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革新。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技術,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依托于電子計算機技術蓬勃發展實現了網絡時代,借助日益發達的網絡技術和智能設備,使軟件與硬件,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連接更加便利。世界各國紛紛采取措施,抓住這次技術飛躍的發展機會,謀求國家的最大利益。
當下中國在互聯網發展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績,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7年8月4日發布的第40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7年6月,中國的網民規模達到7.51億,占全球網民總數的五分之一。互聯網普及率為54.3%,超過全球平均水平4.6個百分點。互聯網的發展促使我國涌現出阿里巴巴、騰訊等一大批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的互聯網企業,政府也積極利用網絡技術轉變服務理念,不斷提升政務處理能力。每每出現新的技術革命,人類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便會發生深刻變革。[3](P36)我國提出建設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跳出了單一國家發展的局限,把全人類在網絡空間中的利益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開創了一種全人類共同應對網絡空間中的挑戰與共同開創網絡科技發展的新未來的新理念。[4]
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學理意義
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基于自身發展和國際社會需求所提出的倡議,不僅具有現實意義,更有學理上的必然性。其學理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國際社會的發展需要是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動力
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5](P35)時至今日,這種思想仍然富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從工業革命到新科技革命,國際社會一直在不斷發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在不斷演進。近年來,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促進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高科技應用與發展。互聯網的出現,提供了以極低的成本進行全球溝通的工具;萬維網創造了一個魔術般的虛擬世界,每個人都能夠把自己的數字化信息傳到網上,其他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到這些信息,互聯網技術的革命推動了世界的扁平化、去中心化過程。[6](P48)網絡空間使得國際社會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技術支持,而網絡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國際社會的發展需要。在國際社會中,國家實力的不同造就了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的不同,超級大國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相對較低,而相對的小國同其他國家的依賴程度更高。[7](P171)從威斯特伐利亞格局到維也納格局,再由凡爾賽——華盛頓格局到雅爾塔格局,再到“一超多強”的格局,國際格局不斷演變。國際社會處在和平時期時,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可以得到良好的發展,反之就會遭受破壞。國際秩序表現人類社會整體的基本價值取向以及這種取向的實現程度。[8](P16)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社會深知戰爭所帶來的災害,無比渴求和平。《聯合國憲章》的序言中強調了“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類兩度慘不堪言之戰禍”,國際社會均渴望和平,只有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各國才可以增進交流,共同發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同樣需要在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中,這不僅是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條件,也是國際社會的整體需要。
(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是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紐帶
關于利益,先賢學者們多有論述。龐德認為:“它是人類個別地或在集團社會中謀求得到滿足的一種欲望或要求,因此人們在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和安排人類行為中,必須考慮到滿足這種欲望和要求。”[9](P81-82)盧梭也指出:“如果說個別利益的對立使得社會的建立成為必要,那么,就正是這些個別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會的建立成為可能。正是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點,才形成了社會的聯系;如果所有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點的話,那么就沒有任何社會可以存在的了。因此,治理社會就應當完全根據這種共同的利益。”[10](P49)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是指一切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和精神需要,與其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的諸多因素的綜合。[11](P62)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行為體,需要將行為體的主觀利益和客觀利益相互協調。[12](P228)綜合以上關于國家利益概念的闡述,可以得出結論:國家利益指的是在國際交往中,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生存和發展中所反映出的與其實力相適應的需求。[13](P15)
國際社會的早前時期,受困于交通方式和科技水平,各個國家大多處于封閉狀態,和其他國家的交往十分有限,并沒有形成完整的國際社會,更談不上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商業分工在全球范圍內精細分布,世界各國越發成為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凸顯出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突破了一國的范圍,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相關國家因為共同利益而緊密聯系在一起,一系列國際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隨之出現的各類組織規章和條約,制定了保護共同利益的國際規則。新的科技革命下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促進了國際社會的交往,也使得國際社會各成員的聯系更加緊密。與此同時,本就存在的一些全球性問題也借助于網絡提升了影響,跨國犯罪,恐怖主義也開始進入網絡空間,借助網絡工具,產生了更大的危害性,出現了跨國的網絡犯罪、國際網絡恐怖主義、網絡病毒傳播等問題。因為網絡空間具有全球性,網絡問題造成的危害,受損害的不僅僅是一國,而是網絡連通的相關利益國家。網絡空間存在的問題,既關系到人類社會的和平發展,也關系到人類社會未來發展中的重要利益。因為國際社會成員在互聯網領域存在著共同利益,才促進了雙方的交流與合作,進而通過這種合作,推進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三)國際社會的基本規則是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前提
國際政治缺乏明確的秩序和等級制的安排,從而使普遍系統方法難以適用。[7](P62)經過長期發展,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套基本的規則體系,這種現存的基本規則,是構建網絡命運共同體的前提。
現存國際規則中,國際法發揮著重要作用。國際法是國際社會成員在國際交往中形成的,用于調整國際關系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原則制度的總稱。[14](P3)國際社會各國,為了維護彼此之間共同利益,驅使它們之間發生廣泛交往從而形成團體,而文化、經濟結構或政治制度的不同本身并不影響國際社會作為國際法的基本要素之一的存在。[15](P6)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促進各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一系列領域的深入交流與合作。國際法治是人類社會在國際社會范圍內的政治文明發展訴求,作為一種人類文明進步的目標和愿景,既是理想國際政治秩序的核心價值,也是理想國際政治秩序實現的法治保障。[16](P189)國際法從產生到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套國際社會中通行的規則體系,涵蓋陸地、海洋、天空、外空等領域,維持國際社會基本秩序。任何現行法律制度必然是現狀的盟友,法院也只能是他的衛士。[17](P471)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政治格局,國際社會中現有的基本規則,保證了國際局勢的穩定,也保證了構建網絡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推進。
三、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思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指導思想,是習近平同志站在全人類前途與命運的高度,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根據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所提出的[18],旨在構建一個和平、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實現互利共贏,完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為解決全球性挑戰指明了一條合作共贏的道路[19],對于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一)重視網絡安全,促進網絡治理的國際共商
共商,即各國共同協商,深化交流,共同解決所面對的問題。網絡安全,是國際社會所共同面對的互聯網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網絡空間的安全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保障。中國十分重視網絡安全,在國際交往中,積極開展雙邊、多邊合作,促進網絡安全問題的國際共商。2001年我國主導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發布了《反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公約》,其中重點關切了利用互聯網等先進手段來進行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行為,體現了我國對于網絡安全問題的預判,同時,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成員國共同商議網絡安全問題,促進解決。中國與中亞國家定期舉行網絡安全演習,對我國的網絡安全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國針對《網絡犯罪問題綜合研究報告草案》提出專家意見,認為國際社會需要加速國際合作,彌補空白和沖突,促進各國打擊網絡犯罪法律和實踐的協調一致。[20]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我國舉行的 “一帶一路”高層論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層齊聚一堂,共同商討發展大計。會議再次強調與會國家有著眾多的共同利益,要在包括互聯網在內的眾多領域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通過網絡問題的國際共商,消除分歧,達成共識,推進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二)著力外交舞臺,開展網絡合作的國際共建
共建,即各國共同參與,擴大共同利益,建立起有效的交流協作機制和利益共同體。我國積極參與網絡空間領域的外交活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雙邊層面上,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定位,深化了兩國的交往,建立起了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中俄兩國在互聯網領域內加深合作,共同促進網絡環境的和平與穩定。在多邊層面上,響應“一帶一路”的號召,中國同東盟建立起了穩定的網絡安全合作機制。2015年1月,在中國——東盟電信部長第九次會議上,中方提出建立中國——東盟國家計算機應急響應合作機制,為網絡安全領域合作提供優先的信息共享和事件處理通道,提升跨境網絡安全事件的處置速度,完善網絡安全響應體系。除此之外,中國——東盟電信部長會議還通過發表聲明、簽署諒解備忘錄等方式建立起網絡司法協助的合作機制。
在國際層面上,中國重視聯合國的作用,在聯合國現有制度規則的前提下,建立更廣泛的網絡問題交流機制。2011年9月12日,中國、俄羅斯等國聯名致函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請其將上述國家共同起草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作為第66屆聯大正式文件散發,并且呼吁各國在聯合國框架內展開討論,早日達成共識。[21]2015年中國再次提交該文件的新版本,呼吁在聯合國主導下建立國際網絡領域穩定的協作機制。
(三)通過自身發展,推動網絡成果的國際共享
共享,即共同分享。我國緊抓互聯網革命的發展機遇,取得了眾多成績:我們有著內容蘊藏量超過傳統百科全書的百度百科,有比傳統通訊運營商服務更加全面細致的APP微信,有互聯網理財方式余額寶,有阿里巴巴、京東主導運營下的電子商務市場,有比傳統公共自行車更加方便的摩拜單車,有革新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滴滴打車,有當日達隔日達的網絡商務物流配送服務等。我國的網絡科技成果,已經跨越了國家的范疇,走向世界,將我國的發展成果與全世界共享。
我國互聯網發展成果在世界范圍內共享,包含了三個層次。首先,是成果共享,即世界各國人民共同享受中國便捷先進的互聯網服務,微信在即時通訊APP的使用份額穩步提升,他國人民可以從中國的電子商務網站上購物,也可以享用便捷的共享單車,是成果共享的表現。其次,中國網絡成果的共享是機會共享。我國的先進互聯網服務進入外國,會促進當地相應產業結構的革新和優化,最終達到互利互惠。支付寶和微信二維碼支付方式進入海外市場,促進當地金融科技的升級。共享單車在國外推行,不僅為當地帶來了就業機會,也促使傳統城市公共單車服務的改革。雙方共享發展機會,最終達到雙贏。最后,中國網絡成果的共享是責任共享。我國先進的互聯網服務在世界范圍內流行,需要遵守當地法律,并且受到當地法律的保護。例如支付寶、共享單車等一系列網絡科技成果便利了人們的生活,應該更好地去維護它,保證運營的良性循環。雙方共享科技成果,共享發展機會,更要共享維護的責任。
(四)建設一帶一路,實現網絡治理的國際共贏
自習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以來,“一帶一路”作為我國頂層合作倡議持續發揮著作用。它源于古代水路兩條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依托于中國與沿線國家現有的雙邊多邊機制,通過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深化合作內容,建設穩定的的區域合作機制,促進沿線的共同發展。2017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加深了沿線各國的理解與交流,號召各國加強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全面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開放性與兼容性,蘊含著共同發展的共贏理念。各國通過簽訂網絡合作協議,共同促進沿線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加強網絡信息的交流,提升了共同應對沿線區域網絡安全的能力;通過網絡科技的進步擴大沿線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維護各國發展的共同利益。沿線各國的網絡交流,是推進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不要部分,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也將進一步加強沿線各國的交流廣度與深度。“一帶一路”的建設,離不開網絡治理,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治理理念指導下,中國推進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促進“一帶一路”國家的共同發展,最終實現共贏。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治理理念,為我國促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同時,這一理念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對于推進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也具有深厚的指導意義。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同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本質上具有相通之處,在網絡空間中,通過共同協商解決相互分歧,通過共同建設擴大共同利益,通過發展促進成果共享,最終走向互利共贏,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
通過目前我國在國際網絡外交中的地位可以預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中國提出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方案,和我國一起推進更加公平的網絡空間國際新秩序,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四、和平崛起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
構建網絡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國必將率先垂范,通過和平崛起道路,在互聯網領域不斷增強自身實力,在網絡空間發出中國聲音,參與和領導網絡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有國家戰略的指引。2016年3月我國正式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計劃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實施網絡強國戰略”“積極參與網絡、深海、極地、空提案等領域國際規則制定”。隨后,在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網絡強國的六個加快要求之后,我國相繼頒布了《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與《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作為指導我國網絡外交的綱領。要求積極參與網絡空間問題的全球治理,在國際網絡外交中發出“中國聲音”。
顯而易見,中國和平崛起這一國家方向與帶有根本性的外部戰略機遇期密切相關。[22](P217)這一理念,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又蘊含全人類共同利益,獲得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23]
中國的和平崛起,根植于中華民族悠久的傳統文化。習近平主席指出:“圍繞中國和世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24](P17)中國傳統文化講究以和為貴,講究仁者愛人。國際社會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其危害性范圍超出了單一的國家,我國傳統文化講究以和為貴,就是國際社會成員在和平的前提下,通過積極溝通協商,共同面對和解決國際性的問題。
同時,中國的和平崛起也貫徹了《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思想。我國和平崛起,不謀求任何霸權,主張通過和平的方式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在國際互聯網領域內也同樣如此。中國的和平崛起,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國的發展,也是對傳統的國際社會強權政治環境的挑戰。國際互聯網空間新的規則亟待建立,和平崛起的我國,必會發出更加有力的“中國聲音”,使國際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更好地造福我國,也造福廣大發展中國家。
發出國際網絡空間的“中國聲音”,一方面,要以國內人才培養建設為基礎。我國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參與網絡問題的全球治理,增強網絡領域的國際話語權,需要高素質的人才作為基礎支撐。如果我國在國際網絡空間領域沒有一支高端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網絡空間國際法強國就只能是空中樓閣。[25]而且,參與國際網絡外交不單是技術的問題,也不單是法律的問題,更多的時候,它是科技、外交、法律、外語的綜合問題,這也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過長期的積累,我國政府和高校已經在復合型人才的培養上做出了成績,國家高端智庫、國家級協同創新平臺、重點高校跨學科人才培養計劃等為我國的網絡外交事業培養出前赴后繼的人才。未來的中國將繼續推進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必將更加重視人才培養的基礎性作用。
發出國際網絡空間的“中國聲音”,另一方面,要在網絡外交中堅定地維護我國的網絡空間主權。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互聯網大會的發言中,已經明確提出“尊重網絡主權”是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的四項原則之首。[2]在我國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也明確規定了“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是我國首次將網絡主權這一概念提升到法律高度。網絡主權問題,在網絡空間國際政治格局中有著十分特殊的重要性,只有在網絡主權這一問題上消除分歧,達成共識,才能進一步促進國際合作。[26](P49)只有堅定維護我國的網絡空間主權,中國才能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領域內的網絡事務,在國際舞臺上能夠平等地同他國進行交流。中國必將繼續以科學的手段維護國家網絡主權,不斷增強我國自身的網絡科技發展水平,通過和平崛起,獲取網絡空間話語權,發出“中國聲音”,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的講話[EB/OL].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16/c_1117481089.htm.
[3](德)克勞斯·施瓦布.第四次工業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4]惠志斌.全球治理變革背景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J].探索與爭鳴,2017,(8).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美)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肖瑩瑩,郝正非,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7](美)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M].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潘忠岐.世界秩序:結構、機制與模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美)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M].沈宗靈,董世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0](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1]蔡拓.國際關系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
[12](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3]劉勝湘.國際政治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4]梁西,王獻樞.國際法[M].曾令良,修訂.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15]奧本海國際法[M].(英)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16]高英彤.理想國際政治秩序探尋[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17](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M].徐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8]林伯海,劉波.習近平“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7,(8).
[19]陳建中.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具有深遠意義[N].人民日報,2017-09-12(7).
[20]中國關于《網絡犯罪問題綜合研究報告(草案)》的評論意見[EB/OL].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Cybercrime_Comments/Contributions_received/China.pdf.
[21]張新寶.論網絡信息安全合作的國際規則制定[J].中州學刊,2013,(10).
[22]時殷弘.國際政治與國家方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3]王毅.攜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N].人民日報,2016-05-31.
[24]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5]黃志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勢態與因應[J].中國信息安全,2018,(2).
[26]黃志雄.網絡主權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