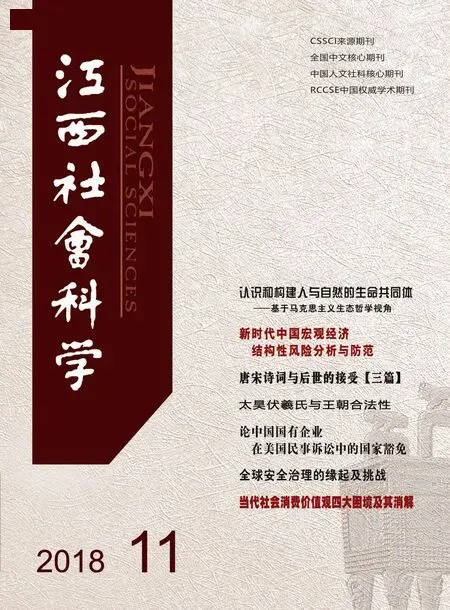建構與再接受:聞一多與當代唐詩文獻學的形成
聞一多在唐詩文獻學研究中,改變了古典形態唐詩文獻學的研究方式,擴展了唐詩文獻學的史料范圍,給唐詩整理與研究特別是清編《全唐詩》的整理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他以作家考證、作品甄辨、作品輯補為核心內容,采用史料爬梳、文獻整理、文字訓詁等文獻考據的方法進行研究,建構了嶄新的唐詩文獻學學科體系。這種新的研究理路對當代闡釋唐詩歷史風貌與詩學藝術,對唐詩在新文化背景下的再接受都帶來重大啟發,也對當代唐詩文獻學學科的形成與發展、唐詩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建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聞一多的唐詩文獻研究涉及作家生平考辨、唐詩選本的編纂、《全唐詩》的整理等方面。研究范圍涵蓋了唐詩文獻學的各個領域,深入唐詩文獻整理與研究領域的核心區域。他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學術視野確立了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唐詩文獻學發展的基本路徑,構建了當代唐詩文獻學的學科框架,并為后人以新的視角接受唐詩帶來了啟發。他在唐詩文獻學方面的巨大成就引起了當代學者的重視。1986年,傅璇琮發表《聞一多與唐詩研究》一文,全面介紹聞一多唐詩學研究的成果和特點,指出聞一多對唐詩的整理是基于對唐詩文獻的爬梳和整理,但并未展開論述其唐詩文獻學。21世紀初,陶敏 《聞一多與唐詩文獻研究》《聞一多唐詩文獻研究的學術史批評》二文,分別探討了聞一多在清編《全唐詩》整理工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全唐詩人小傳》所取得的成就,但亦未對其唐詩文獻學的整體成就及影響進行闡述。2003年,楊天保發表《聞一多整理唐代文獻的一般思路及特色》一文,將研究對象定位于聞一多對唐代文獻整理的總體考量,并未深入論述聞一多的唐詩文獻學思想及成就。基于上述研究現狀,本文擬對聞一多在唐詩文獻整理與研究過程中涉獵的文獻范圍、研究方法以及構建唐詩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嘗試等方面進行探析,揭示他在唐詩文獻學從傳統形態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做出的重大貢獻。
一、文獻范圍的擴大
傳統形態的唐詩整理與研究所運用的文獻資料范圍較窄,一般包括唐人作品文本、正統史書、筆記小說及詩話等。王國維在評論張爾田《玉溪生年譜會箋》時曾批評清代以前“注玉溪詩者,僅求之于二書(按指新、舊《唐書》), 宜其于玉溪之志,多所捍格”[1](P4)。明末清初仇兆鰲的《杜詩詳注》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唐詩文獻學的史料范圍,但也基本上不出上述各種文獻之范疇。康熙、雍正年間,王琦撰寫《李太白文集》,除上述文獻外,還采用了《楚辭》《文選》等文學總集,《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地理志以及《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等類書。而清人所編唐人年譜,如:溫汝適《張曲江年譜》、趙殿成《王右丞年譜》、汪立明《白香山年譜》、黃本驥《顏魯公年譜》、朱鶴齡《杜工部年譜》、錢謙益《少陵先生年譜》、顧嗣立《昌黎先生年譜》,等等,所用文獻范圍也僅僅從兩《唐書》擴展到了詩文集和部分詩話、筆記之中。直至清末民初,這種情況方有所改觀。正如在張爾田《玉溪生年譜會箋序》中所說的,此時的唐詩文獻整理,在資料上“旁蒐遠紹,博采唐人文集說部及金石”[1](P4)。在此基礎上,聞一多從多領域進一步拓展了唐詩文獻學的史料范圍。
第一,聞一多擴大了唐詩整理與研究中可資利用的地理書范圍。除兩《唐書》中的《地理志》以及《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大型綜合地理文獻外,他還關注各種方志。唐宋以來的地方志質量良莠不齊,加之地方文獻傳播不廣,因此治唐詩文獻者大多不關注這些史料。但方志中本地先賢的生平史料、名家的詩文作品、文學典故的歷史背景、地理名勝資料等記載,足以彌補史傳、別集、總集、類書等文獻的缺憾。近代以來,隨著交通運輸方式的進步,公共圖書館的普遍建立,為學者獲取方志提供了便利。聞一多撰寫《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時,除前輩學者常用的地理文獻之外,還利用了《鞏縣志》《河南府志》《唐兩京城坊考》《長安志》等方志資料,為考證杜甫生平提供一些重要證據。如杜甫之籍貫,歷代撰譜者皆引《舊唐書》本傳,稱自襄陽遷徙至河南鞏縣。而聞一多則考證說:
《河南府志》:“鞏縣東二里瑤灣,工部故里也。故鞏城有康水去瑤灣二十里,與逸事合。”又曰:“康水,即康店南水。工部故里在瑤灣,去康店南二十里外。”[2](P39)
這一新材料的運用,為杜甫占籍鞏縣提供了新證據,更加準確地定位了杜甫故里在鞏縣的具體位置,也為我們重新認識杜甫提供了文獻支持。
在編纂《全唐詩人小傳》時,他運用了更多的地方志材料。諸如《成都記》(薛稷傳)、《雍錄》(沈佺期傳)、《長安志》(王翰傳)、《嘉定鎮江志》(張暈傳)、《大清一統志》(祖詠傳)、《南昌郡乘》(王季友傳)等。這些方志記載了一些名聲不甚顯赫的中小作家,彌補了正統史傳記載的不足,對糾正清編《全唐詩》詩人小傳中存在疏漏、舛誤、失考等問題具有極重要的價值。此外,他還從方志中尋求輯佚的資料,如從《漳州府志》所載《白石丁氏譜》中輯出了丁儒《歸閑二十韻》一詩。
第二,聞一多在唐詩整理與研究中,大量利用石刻文獻,尤其是剛出土的實物。除了利用常見的《金石錄》《集古錄》《廣川書跋》《寶刻叢編》、《金石文字記》《古刻叢鈔》《金石萃編》《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等石刻文獻資料之外,聞一多還十分注意發掘新的金石文獻。他在1933年曾致信饒孟侃說:
河南有新出土的唐碑務必請覓一張拓片寄給我。這類東西一到北京就貴了,所以我在這一方面沒有下手工作。但我信如果得到這類的材料,我必能利用,充分的利用他。[3](P267)
20世紀30年代初,張鈁曾在河南洛陽建立了千唐志齋。這一時點恰與聞一多此信件時間相近。顯然,聞一多注意到了當時金石考古學的最新學術進展,十分渴望獲得這些新出土碑志文獻。
第三,聞一多重視類書、敦煌文獻、海外文獻、書畫文獻等材料的價值。聞一多認為類書在詩歌從六朝向唐詩演變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他在《類書與詩》一文中提出:“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4](P7)又說:“太宗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4](P9)因此,聞一多在開展唐詩文獻整理工作時,十分重視從類書中發掘材料。他在《類書與詩》中列舉了《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瑤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覽》《事類》《初學記》《玉藻瓊林》《筆海》《文館詞林》《兔園冊子》等十余種類書。對類書的重視,使他在進行唐詩選本《唐詩大系》的編纂時,有了不少新發現。如《全唐詩》卷5、卷6收錄王勃《別薛華》一詩,歷代王勃詩集刻本亦多作《別薛華》,聞一多則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與本集的《秋夜于綿州群官席別薛昇華序》一詩考證此處薛華疑為薛昇華,而《文苑英華》(卷286)中此詩題恰做《秋日別薛昇華》。
聞一多還從古代書畫藝術類書籍中發掘唐詩文獻。他在《全唐詩人小傳》薛稷傳中,引用了多種書畫文獻,如:唐人韋續的《續書品》《九品書》、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北宋人編纂的《宣和畫譜》、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董逌的《廣川書跋》,等等,內容較之《全唐詩》小傳豐富了許多。如畢曜,《全唐詩》中其小傳僅提及“官監察御史,與杜甫善”[5](P643),而聞一多則從顏真卿《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中發現該人曾任司經正字一職。
此外,聞一多還將研究視野投向海外漢籍文獻。編《唐詩大系》時,他據《文苑英華》收入了王勃《圣泉宴》一詩,此詩傳世諸本皆無序。聞一多乃據日藏卷子本《王子安集佚文》補入。在《全唐詩匯補》中,除了日本學者市河世寧的《全唐詩逸》之外,聞一多還充分利用日本人大江維時編纂于中國唐末五代時期的《千載佳句》,該文獻成書較早,保存了不少詩歌的原始文本,是唐詩整理的珍貴資料。
從其《唐風樓捃錄》所列舉文獻來看,聞一多在唐詩文獻研究方面涉獵的文獻甚至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所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涉及的范圍,可以說,唐代唐詩文獻學的史料范圍在聞一多那里已經得以確立。另外,新史料的發掘,必將導致我們站在新的角度去重新認識作家、接受作品。
二、研究方法的新變與唐詩的再接受
面對浩如煙海的唐詩文獻,聞一多總能不拘一格地運用各種方法分析文獻材料來支撐其研究。他通過建立公式體系來檢索唐詩的重出誤收情況,對后世產生巨大影響。他在《〈全唐詩〉校讀法舉例》一文中,初步嘗試了這一研究方法。他提出,《全唐詩》中存在“甲集附載乙集,其題下的署名并入題中,因而誤為甲詩”[4](P467)這種普遍的錯誤現象。并以“錢起詩誤入王維集”等五個誤例證明了這一公式的合理性。這一研究方法值得稱道之處在于:“公式”二字并非我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詞匯。聞一多大膽引入這一西方學術概念,將其嫁接入唐詩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中,體現出明顯的現代性意識。后來,他的學生李嘉言在此基礎上將《全唐詩》中存在的錯誤類型細化為七個公式。這七個公式成為當今學界對《全唐詩》重出誤收情況進行考辨甄別的重要理論依據,為徹底解決《全唐詩》重出誤收問題帶來了希望。可以說,聞一多的公式法不僅使唐詩的甄辨工作產生了一次大的飛躍,更使唐詩文獻學的方法超出傳統考據學的范式,引發了一次研究方法的革命。
聞一多極重視對文獻的掌握。為了全面挖掘存世唐詩文獻里有價值的史料,他采用了“普查”這一最基本,也是最“笨”的手段。在文獻普查過程中,聞一多不僅大量查閱唐宋以來的書目文獻,還編纂了多個文獻目錄,列舉出所能找到的所有文獻,避免出現疏漏。眾所周知,宋代是唐集得到系統整理刊刻的重要時期,后世流傳的唐集幾乎都源于宋人的整理本。宋人書目文獻里的記載對梳理唐詩文獻,尤其是別集、總集的刊刻、流傳情況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諸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放翁題跋》等宋人書目文獻還有宋人撰寫的題跋、敘錄。這些題跋、敘錄中包含有大量作家事跡、詩歌甄辨的內容。不少史料為其他類型史料中所不見的,利用這些早期文獻研究唐詩的原初面貌,其價值更加不可估量。他的《全唐詩人小傳》凡遇到上述諸目已經著錄的唐集,皆抄錄原文。雖然《全唐詩人小傳》并非成稿,我們無從考察聞一多將如何裁剪、處理這些文獻,但這足以說明聞一多對書目文獻的重視。
針對全面整理唐詩計劃,他編纂了幾個大型唐代文獻目錄:《見存唐人著述目錄》(包括《本編所見叢書匯目》)《研究唐代用書目錄舉要》。在其未刊手稿中,還有《唐人遺書目錄標注》《唐人九種名著敘論》等多種唐代文獻的綜合性目錄,這些目錄涵蓋了傳世的大部分唐代文史文獻。利用這些大大小小的目錄,即可按圖索驥,爬梳其所需要的文獻。在計算機檢索技術出現之前,這一方法是史料搜集整理的最佳方法。民國至20世紀末期,不少學者都采用這一手段治唐詩文獻,唐詩文獻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大批目錄索引,諸如《唐集敘錄》《唐詩書錄》《唐五代人物資料傳記綜合索引》《全唐詩詩句索引》(未刊)等。佟培基即據《全唐詩詩句索引》梳理出大量重出誤收情況,完成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這一集大成之作。目錄索引的編纂為學者的文獻檢索工作提供了極大方便,為他們更深入挖掘新的唐詩文獻史料提供了線索,推動了20世紀后半葉唐詩文獻的研究。
聞一多還善于從新的角度去解析舊材料,讓大家熟知的文獻產生新的學術價值。比如在面對書畫史料時,他不僅從中尋找文獻資料作為考據材料,甚至還從這些史料出發,試圖去闡釋、還原作家性格、詩文內涵。他在《孟浩然》一文中引用張洎題寫的王維畫孟浩然像:
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4](P80)
從這一文字轉述的孟浩然畫像出發,聞一多從孟浩然詩歌中看到了詩人那種白袍布衣,“頎而長,峭而瘦”的形象,并由此推測出孟浩然的詩歌特點與人物形象的一致:
王士源應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錯,他在序文里用來開始介紹這位詩人的“骨貌淑清,風神散朗”八字,與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謂精朗奇素,無一不與畫像的精神相合,也無一不與孟浩然的詩境一致。[4](P80)
這段文字的表述實質上反映了他對孟浩然的理解,可視為孟浩然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唐詩人小傳》的《常建傳》中,他也提到房從真所畫的《常建冒雪入京圖》,可惜《全唐詩人小傳》未完能成,不知聞一多將如何利用這一資料展開研究。中國古代書畫文獻尚有不少存世,但迄今受到的重視仍然不夠,聞一多這一方法應當對我們有所啟發。
在研究形式上,聞一多的唐詩文獻研究亦不拘于論文這一種形式,他最早有關唐詩的著述《李白之死》是一首現代詩。詩歌的內涵顯然是用李白的悲劇人生來抒寫大時代背景下,作者個人甚至那個時代眾多詩人的孤獨感。詩歌充滿了感性色彩,并非嚴謹的論文,但聞一多將個人情感與李白詩句融為一體,突破了舊時代文人對李白及其詩歌的一貫認識,真實反映出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代詩人對李白及其詩歌的嶄新認識,展現出當時人們對唐詩的一種嶄新的接受形態。
聞一多在運用傳統學術方法進行唐詩史料爬梳與考據的同時,敢于突破傳統研究方法的窠臼,嘗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對文獻進行分析利用。其研究方法和裁剪史料的角度突破了唐詩文獻整理的傳統研究形態,更新了學界舊有的傳統研究理念,促使唐詩文獻學完成了從古典形態走向新形態的學術轉型,也啟發后人在一個新的視角中重新接受唐詩。
三、學科體系的建構
當代唐詩文獻整理與研究包括三大基本內容,即作家生平事跡研究、作品輯補和作品辨證。在20世紀上半葉,聞一多已全面深入唐詩文獻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中,在唐詩文獻研究的三大核心板塊方面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并確立了當代唐詩文獻學的學科體系。
唐代作家生平事跡的考證與研究是聞一多下手最早、用力最勤、成就最高的研究領域,對當代唐詩文獻學的影響也最大。在現代詩《李白之死》和傳記散文《杜甫》之后,他開始進行更具學術性的研究。《聞一多年譜長篇》稱: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杜甫》傳記發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六號。收《聞一多全集》。這是一篇只完成了一半的傳記散文,試圖給杜甫做一畫像,它是先生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嘗試之一,但此后沒有接著寫下去,而是著手去做杜甫的年譜會箋。[6](P372)
1930年4月,《杜少陵年譜會箋》發表于武漢大學《文哲季刊》。此后,他先后完成了《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岑嘉州系年考證》《岑嘉州交游事輯》等文章,對杜甫、岑參的生平事跡和交游情況進行了深入考證。這些研究得到了同時代學者的高度評價。朱自清即認為聞一多是唐詩考據家,其研究的視角集中在對詩人和詩歌中有關年代錯誤的考證上,并試圖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考證來改變人們對詩歌理解的認識。[6](P476)
1933年他曾致信饒孟侃說:“《全唐詩》作家小傳最潦草,擬訂其訛誤,補其缺略。”顯然他試圖重訂唐代所有詩人的傳記。為此,他對唐代詩人生平事跡的考證用力甚勤,曾先后完成《唐詩人生卒年代考》《唐詩人登第年代考》等著作。其《全唐詩人小傳》集中體現了他在這一方面取得的成就,雖然該著收錄不足二百位詩人,且有不少作家的生平考證僅為材料的羅列,并未成文,其中甚至還存在一些考證的錯誤。但從他已經完成的部分較成熟的小傳來看,無論是元代的《唐才子傳》還是清代《全唐詩》的作者小傳,都沒有他的研究豐富、翔實。如果以學術史的眼光來看,聞一多研究的重要價值并不止于正確考證、完善這些作家的生平事跡,更在于通過這一研究提出了徹底整理唐代詩人生平事跡的學術構想,給當代唐詩文獻研究帶來了重要啟發。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我們仍未實現先生整編全部唐代詩人傳記的宏偉構想,但不少學者都曾投身到這一學術領域中,涌現出像《唐才子傳校箋》《唐代詩人叢考》《全唐詩人名考》《全唐詩人名考證》這樣一些優秀的研究著作。這一研究領域受到了當代唐詩文獻學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并成為當代唐詩文獻學學科體系的三大核心板塊之一。
聞一多在詩歌輯補與考辨方面的研究對推動唐詩文獻學的進步和學科體系的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繼市河世寧、孫望、王重民等學者之后所編的《全唐詩匯補》收錄作家135人,《全唐詩續補》收錄作家157人。兩者相加,已經超越了前述諸位學者的成就,可謂晚近以來《全唐詩》輯補方面的集大成者。是陳尚君《全唐詩補編》成書前最為重要的著作。在唐詩考辨方面,聞一多的《全唐詩辯證》,對三百余首詩歌的真正作者、創作年代進行了考證。這一研究將自劉師培《全唐詩發微》開始的唐詩考辨工作推進了一大步。在佟培基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一書出現之前,聞一多對唐詩重出誤收以及辨偽方面的研究是最為深入的。再加上他對作家的考據,聞一多的研究涉及了唐詩的整理與研究的三個主要方面,并將各部分研究整合成了一個學科體系。
陶敏曾評價聞一多的唐詩研究,認為他打破了傳統唐詩學研究孤立、封閉的研究局面,形成了綜合性的、全方位的研究模式。[7](P157)這一論斷同樣可用來評價其唐詩文獻學研究。唐詩文獻領域三個核心內容的研究本就不應該是割裂的,他們能成為一個嚴密的學科體系是由學科本身的性質特點所決定的。但我們絕不能忽略聞一多對唐詩文獻學學科體系形成過程中進行的勾連、捏合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把這三項研究圍繞在《全唐詩》整編工作的周圍。這使得這些研究有了一共同的目的,研究內容可以互相滲透,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利用,避免了三者研究各自局限于自己狹小圈子的孤立局面。
聞一多這一研究思路,恰恰是當代唐詩文獻學者公認的研究形態。這是一個包含作家生平考證、詩歌文字校勘、詩歌輯佚、箋注在內的完整的學科體系,可以說今天唐詩文獻學學科所有的核心內容已經在聞一多手中建構完畢。20世紀30年代以來,我們都在圍繞這個學科體系不斷拓展唐詩文獻學的研究領域。從學科建設上說,聞一多毫無疑問是當代唐詩文獻學學科的奠基人。
四、結 語
聞一多在唐詩研究中,非常重視詩歌形成的背景。他提出了唐代“全面生活的詩化”。這一觀點與當代學者龔鵬程在《唐代思潮》中所提出的唐代已經成為“文學化社會”的觀點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唐代的種種社會現實,作家的人生軌跡,包括科舉、教育、政治關系在內的唐代社會政治、文化諸方面的變遷等唐詩形成背景就得到了他的特別關注。他在各項唐詩文獻研究中都非常重視文獻史料的開掘與利用,大力拓展唐詩文獻的史料范圍,將新的研究方法與傳統文獻學方法相結合,極大的推動了唐詩文獻學的發展,引領唐詩文獻學從古典形態演進到現代形態,初步建立了現代唐詩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另一方面,將社會歷史背景與文學的生成聯系起來,是迄今仍被人們所常用的一種詩歌闡釋手段。這種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詩歌的接受方式,啟發學者們從新的視角去重新理解詩歌的內涵。聞一多對新材料、新文獻的重視和發掘始終在提醒我們,方法與材料的更新是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唐詩,開啟唐詩文獻研究新局面的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