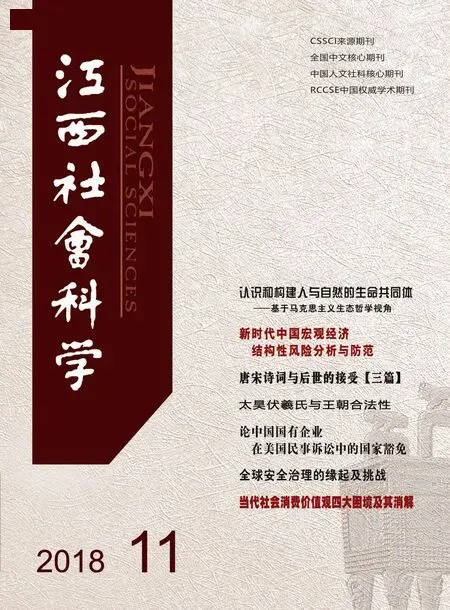“受過行政處罰”入罪類型的司法擴張及其限縮
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被擬制的犯罪不法行為類型,《刑法》中涉及四個罪名,但司法解釋對“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入罪條件予以了擴張,擬制入罪約30個罪名。“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入罪類型的司法擴張表現為標準的不統一、地位的不對等、罪量影響的不規則、刑罰質與量調節的不一致、主客觀因素的混同等。其主要原因在于對刑法典尊重的缺乏、科層制行政思維慣性和司法解釋權過度擴張。在司法謙抑理念下,有必要對其予以限縮:作為入罪條件的司法擬制及自然犯中“受過行政處罰”作為構成要件要素應當禁止;主觀要素認定之推定以“明知”為限;加大從重處罰或限制加重處罰的適用力度;加大限制性或禁止性從寬處罰的適用力度。
在行刑交叉案件中,“受過行政處罰”(也有稱之為“行政處罰后又實施”)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或者單獨不法行為類型被規定在罪狀中,成為非典型性入罪要素的核心。“受過行政處罰”本是與刑事犯罪無關的過程或者結果,但《刑法》特別是司法解釋在明確罪狀和確定構成要件要素的過程中,將“受過行政處罰”這一事實要素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條件之一,是行政處罰之事實或者結果深入到刑事犯罪構成內部的表現,增加了行刑交叉關系的復雜性,將本來作為判斷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因素,作為構成犯罪要件的要素予以規定,擴大了刑事犯罪的法網。在司法謙抑的理念下,必須在司法適用中予以限縮,否則有違罪刑法定基本原則之嫌,也不利于行刑并行銜接的貫徹。
《刑法》共有4個條文將“受過行政處罰”或“經行政處罰”作為犯罪的不法行為類型,分別是:《刑法修正案(九)》第31條第2款將“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行政處罰后仍不改正造成嚴重后果”作為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中新增的入罪法定構成要件要素;《刑法修正案(八)》第27條將“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后又走私”規定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入罪類型;《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將“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規定為偷稅罪的入罪類型;《刑法》第351條第1款第(二)項將“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種植”作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入罪類型。與《刑法》將“受過行政處罰”納入犯罪的不法行為定型的緩步發展不同,司法解釋走得更遠、更快,不僅大大擴張了“受過行政處罰”的適用范圍,且“受過行政處罰”在定罪量刑中地位和作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刑事優先原則有余,同步協調的行刑銜接原則不足。[1]經粗略統計,自97《刑法》實施以來,至少有40多個司法解釋或者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文件涉及“受過行政處罰”在犯罪中作為定罪量刑有關的因素予以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大大超出了《刑法》的規定,擴張了刑事法網。刑法將“行政處罰后又實施”作為某罪獨立的不法行為定型,表明下調了刑法的干預起點,擴張了刑法處罰范圍。[2]此類規定不僅關涉行政處罰與刑法的銜接,還涉及行政處罰結果在犯罪構成中的地位,是行政處罰嵌入犯罪構成的強有力的表現形式。
一、“受過行政處罰”入罪類型的司法擴張
《刑法》中只有4處明確了“受過行政處罰”可以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但在目前有效的司法解釋中,“受到行政處罰后又實施”某種行為作為入罪的擬制已近30個罪名,除極少數是作為緩刑適用等量刑情節外,絕大多數是作為犯罪成立的罪量要素。[2]司法解釋中這種“受過行政處罰”入罪類型擴張現象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類。
(一)標準的不統一
一是超出《刑法》條文的規定,將曾經“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入罪的認定標準。《刑法》只在4個條文中規定受過行政處罰可以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但司法解釋將受過行政處罰擴展到在30多個罪名中可以作為認定犯罪成立的構成要件。
二是在犯罪構成要素中地位各不相同,缺乏一致性。有的規定“受過行政處罰”是作為構成犯罪的積極的要素之一,即曾經因為同類行為受過行政處罰是積極促成當下行為構成犯罪的條件之一有的則將“受過行政處罰”作為阻卻犯罪構成的要素之一,即在受到行政處罰的情形下,當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如《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①。
(二)地位的不對等
一是將“受過行政處罰”與“受過刑事處罰”作為同等重要的要素看待。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管理社會生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4]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雖然均是公法上處罰的方式,但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懲罰方式,行政處罰對人的強制性與對事的嚴肅性遠不如刑事處罰。其作為對人身危險性或者對犯罪情節的影響因素,在同一犯罪中也應當有所不同。但司法解釋的諸多規定卻沒有體現這種差別,而是將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作為同等因素看待,如《關于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釋》和《關于辦理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前者將“受過行政處罰”認定為《刑法》第350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較重”,后者則作為危害安全犯罪從重處罰的情形。
二是“受過行政處罰”的次數作為定罪或量刑因素具有隨意性。有的規定受過(一次)行政處罰即可,如《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非法經營食鹽刑事案件的解釋》等,或者規定為一年,或者規定為兩年,或者沒有限制,次數則規定為一次、兩次不等。
(三)罪量影響的不規則
一是“受過行政處罰”時間段對定罪和量刑限制的不規則性。這又可以進一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規定為一年時間內的,如《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妨害國(邊)境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等均規定為受過行政處罰后一年內又實施。第二種規定為二年時間內的,如《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的司法意見》《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等均規定為二年內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第三種規定為三年時間內的,如《關于審理破壞草原資源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等規定三年內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
二是“受過行政處罰”對數額影響程度不同。第一種是規定行政處罰可以折抵標準數額的50%,如《關于辦理搶奪、敲詐勒索、盜竊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均分別規定搶奪、敲詐勒索和盜竊的“數額較大”時,將一年內曾因有搶奪、敲詐勒索、盜竊行為等受過行政處罰的,“數額較大”的標準可以降格按照規定標準的50%來確定,這實際將受過行政處罰這一事實擬制為定罪數額標準的50%。第二種是規定只有在犯罪數額接近規定定罪數額標準時,行政處罰才能作為構成犯罪的一個因素,如《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的司法解釋》等規定,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的,接近相應數額標準的,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第三種是規定在數額犯罪的情況,雖然沒有達到規定的數額標準,但如果“受過行政處罰”的可以降低對數額的要求,具體行政處罰能折抵多少數額,或者說在未達到的數額與標準數額相差多大時可以認定為達到了規定的數額標準,則不明確,如《關于依法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偽基站”設備案件的意見》和已經失效的《關于審理搶奪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的規定。
(四)刑罰質與量調節的不一致
第一種情形是作為刑罰加重處罰的要素或者法定刑升格的條件,如《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將行為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的行為規定為《刑法》第204條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第二種情形是作為從重處罰的因素,如《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均規定“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的”應當酌情從重處罰。第三種情形是作為限制或者禁止某種刑罰適用的因素予以規定,如《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二)》等規定“受過行政處罰”作為排除適用緩刑的條件,此外,《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則將“受過行政處罰”(三年內受到兩次以上行政處罰)作為阻卻從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要素。
(五)主客觀因素的混同
主客觀因素的混同表現為:“受過行政處罰”既作為客觀上認定犯罪數額或者情節的要素,又作為主觀上“明知”的判定要素。作為客觀上認定犯罪數額或者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要素的情形,在關于盜竊、搶奪、敲詐勒索以及關于走私、毒品、事故責任、破壞土地資源、非法行醫、侮辱、誹謗等犯罪的司法解釋中,都比較普遍地存在。受過行政處罰也被作為認定行為人具有主觀上“明知”的判斷要素或者推定的前提條件,如《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和《辦理走私刑事案件的司法意見》均規定相關行為曾經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可以認定為“明知”。
二、司法擴張的原因分析
司法解釋將刑法典規定之外的因素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與刑法分則關于罪狀的描述過于原則有關;另一方面與最高司法機關對中國法官個人智慧的不完全信任有關,還可能是出于統一法律適用的設想,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的法治思維不夠成熟,可以展開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刑法典缺乏應有的尊重
“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入罪條件的理由,理論上有刑法功能保障說、法律擬制說以及新的犯罪形態說等理論為其提供依據。但刑事司法解釋在將此入罪時往往忽略了教義學的以法律文本為闡釋的基本原則。對刑法教義學來說,不容置疑的教義就是現行刑法。[4]在司法解釋中過分擴張刑法條文本身的含義,有一些甚至突破了刑法的基本原理,會造成法的不安定性和國民的無所適從。
司法解釋中將“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認定犯罪構成要素,存在兩種情形:一是將行為人曾經因實施違法行為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再次實施同類行為時該行為犯罪化的依據;二是將因某類行為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該類行為犯罪化中降低構罪標準的依據。
這兩種情形在法律上均欠缺充分的理由。一是司法解釋如此規定缺乏立法上的授權和依據。根據《立法法》的規定,關于犯罪與刑罰的規定屬于全國人大立法的絕對保留事項,不容許任何機關單位染指,司法解釋超出立法范圍確定立法所不具有的新的犯罪的入罪類型,明顯屬于對立法權之侵害與剝奪,不符合司法機關作為法律適用機關和審判機關的憲法地位,《立法法》并未授予司法機關創制新的規則的權力,其只能在司法適用過程中就具體條文進行解釋。二是司法解釋的此種做法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之嫌。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構成要件上的明確性,司法解釋是一種事后法,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司法解釋溯及到法律開始實施之時,司法解釋中改變刑法條文規定的構成要件,不僅有違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而且由于刑罰法規不明確,國民常常對是否受處罰感到不安,于是不得不廣泛地抑制自己的行為,出現刑罰之前的“萎縮效果”;而且刑法法規的不明確給警察等法律執行機關留有廣泛的裁量余地,會造成恣意地、有差別地執行法律。[5](P31)
(二)科層制行政思維慣性的影響
根據韋伯的論述,科層制所關心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間因存在不同的對應關系而呈現出不同的組合樣態。行政化是我國司法系統久被詬病的缺點之一。以科層制為代表的行政思維不僅影響到我國的司法體系架構,也嚴重影響到司法權力的運行過程。司法機關在解釋法律的過程中,也明顯受到這種科層制行政思維的影響。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行政法上一種處罰狀態,本不應在作為保障法的刑法中成為關注的對象。司法機關在解釋法律過程中,可以將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實現刑罰個別化所要考慮的因素,但將其作為構成犯罪的要素或者作為行為不法定型的核心要素,均是過分強調行政處罰在刑事犯罪中的地位所致,也是刑法作為過度承載不屬于犯罪要素之外因素的具體體現。
科層制所關注的“合法性”要求解釋具有正當的合法性依據,而“合理性”則建基于對現實的回應,是某一時期特定價值觀的選擇。受過行政處罰作為犯罪構成要素,雖然可能“正確地”建構了基于社會現實的合理性,卻忽視了構成要件賴以存在的合法性,本質上缺乏“正當性”,這與我國法律文化中行政與司法長期不分的現實有關。司法解釋是法律賦予司法機關就具體法律條文進行闡釋的權力,其所解釋的結果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許可范圍之內,解釋的過程和結果都更多地強調其“合法性”,而不像行政權那樣可以允許充分的合理性考量。科層制下合理性考慮代替了合法性的考量是造成“受過行政處罰”在刑事司法解釋擴張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主要原因之一。司法為應對現實可以有一定的靈活和變通,但不管怎樣的靈活和變通,基于客觀主義立場所建構的刑法基本框架和原則是不能突破的。[6]
(三)司法解釋權的過度擴張
解釋法律是司法機關的職責,但解釋不能超越法律本身。司法機關解釋法律必須在罪刑法定原則的界域內進行嚴格的解釋或限定,不能超越刑法條文的基本規定。“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之一,是一種法律擬制,這種擬制必須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只能作為一種立法的手段而不能成為解釋的方法。[8]司法解釋權的過于擴張,導致行政處罰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嚴重超出刑法規定的范疇。
以2013年《關于盜竊罪的司法解釋》為例,《刑法》第264條對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構成盜竊罪的規定,其含義是非常明確的。但最高司法機關在對此數額較大做出解釋時,卻將在具備“受過行政處罰”的情形下,對盜竊罪“數額較大”的標準可以按照《解釋》第1條規定標準的50%確定。此種規定雖然避免了盜竊罪“唯數額論”的不足,較好地解決了依法懲治社會危害性嚴重的盜竊犯罪問題,更好地貫徹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從嚴的方面,是《解釋》規定盜竊罪數額標準的一大特點[8],但此種特點是以違反罪刑法定為代價的,實不可取。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在刑事立法者和最高司法機關沒有將曾經因某行為被行政處罰的事實作為違法行為犯罪化或降低構罪標準的依據時,司法機關不得擅自作此處理。[9]
另外,此種解釋內容具有類推適用的嫌疑。關于盜竊罪的司法解釋中“數額較大”規定“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的”“一年內曾因盜竊受過行政處罰的”,可以依據盜竊“數額較大”標準的50%確定該類盜竊入罪門檻,主要考慮:一是根據調研情況,當前盜竊犯罪分子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盜竊慣習、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人員;二是類似問題在《刑法》中也有規定,如《刑法》第153條(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規定:“一年內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后又走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8]由上可以看出類推解釋的痕跡非常明顯,類推適用已經被97《刑法》明令禁止,卻再次出現在新的司法解釋中,令人對司法權的過度擴張感到擔憂。
三、“受過行政處罰”入罪類型的司法限縮
要讓司法解釋關于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規定回歸到刑法本身,在司法解釋的過程中尊重罪刑法定的原則并體現刑法教義學的要求,就必須對超過刑法典和刑法教義學范圍的解釋行為予以適當的司法限縮,主要路徑在于對已經被擴張的犯罪類型進行法律適用上的限縮。
(一)入罪類型的司法擬制應當禁止
法律擬制是一種法律上的假定和虛構,是將本來不屬于此類的彼類情況擬制成屬于此類情況,立法者進行法律擬制時往往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量。對于“曾經受過行政處罰后又實施”某種行為的行為,在法律上本應給予行政處罰的,卻將其納入刑法的視野,以犯罪論處,屬于擴大犯罪圈的劃定,完全屬于立法權的當然范疇。行政處罰的適用與刑罰的適用應當有一個合理的臨界點。[10]如果“受到行政處罰”作為入罪的標準或者條件日益泛化,那么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具體犯罪,甚至連傳統的自然犯,都可以將受到行政處罰作為犯罪成立的條件之一,如此則將導致行政權對司法機關的刑罰權無限蠶食,使刑罰權成為對行政處罰的被動確認,不利于發現、發展刑法的真實含義[11](P36),使我國《刑法》演變為名副其實的行為人刑法。另一方面是司法權為行政處罰的刑罰化撐腰,純粹形式上的“受到行政處罰后又實施”可以入罪,行政執法機關在具體的行政執法過程中,特別是行政執法權相對集中的執法中,會基于行政復議、訴訟以及處罰的執行等方面的考慮,導致消極行政而影響行政處罰的力度,進而影響對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相同行為的減弱,甚至出現剝奪行為人違法能力或資格的處罰效果,還會因此而將本應由行政法調整的社會矛盾或者行政執法可以解決的問題轉嫁給司法部門,最終造成行政權的懈怠和卸責。以上兩方面均會造成司法權的弱化,故將“受過行政處罰”擬制為入罪類型時應當禁止超越立法的范圍。
(二)“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自然犯的構成要件要素應當禁止
不管是否承認自然犯與法定犯區分的理論,自然犯與法定犯的不同是刑事犯罪中客觀存在的現象。法定犯中,行為類型多以構成行政法上之違法為前提,之所以將行政法上違法類型作為犯罪處理,只是因為規則違反程度不能被行政法所容忍,故有刑事處罰介入的必要。當行為人因實施某種違法行為受到行政處罰,而后再次實施該同種性質的行為,說明僅對其施以行政處罰已起不到完全抑制的作用,此時就需要動用刑罰措施來加強效果。對違法行為是進行行政處罰還是刑事處罰,之間的一個有效界限就是對該行為的行政處罰已經無法抑制這種行為,國家只有動用刑罰措施才能抑止這種行為、才能充分修復被該行為所侵害的全部法益。刑事不法中的行政犯,這種犯罪是一種禁止惡,其惡性系源自法律的禁止規定,因而不同于自體惡的自然犯。因此,行政犯實際上是由行政不法轉化為刑事不法,它具有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的雙重屬性。[12]自然犯的存在是對人類基本感情和倫理的違反,并不以存在行政違法類型為前提,法律對符合自然犯的行為類型給予行政處罰,是非犯罪化的一種措施,但如果反過來將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認定構成自然犯的條件,則不僅有漠視人類基本情感和倫理的嫌疑,還有無限擴大自然犯范圍的可能,是國家權力過分介入個人生活的不當表現,對此應當予以重視,并在實踐中予以避免。
(三)主觀要素認定之推定以“明知”為限
在司法解釋規定以受過行政處罰作為認定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一的犯罪中,在主觀上都要求具備犯罪的故意,犯罪故意又是以明知——這一包括主觀認識因素和控制因素的概念——為前提的。除了主觀故意所要求的明知外,有的還要在刑法條文中明確要求構成所必須具備的明知,如刑法第144條、第214條、第312條以及第350條的規定。
“明知”是人的一種內心心理活動形式,其表現形式、方式及形成過程具有復雜性,司法實踐在認定的過程中,很難以有形的證據將其客觀地展現出來。因此,在關于行為人“明知”的證明方法和方式上,主要是采用推論的方法來對明知的進行證明和認定,其證明過程就是司法人員根據已經收集的證據,充分運用邏輯推論方法,結合社會實踐和司法經驗進行推斷,形成對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的過程中主觀是否存在明知的內心確證,這種內心確證必須是有可感知的證據作為依托的。一方面,在行為人因為實施同類行為受到行政處罰的情況下,說明在其實施此次犯罪行為之前,其就已經接觸到并形成了關于實施此類行為屬于違法的主觀認識,如果其再實施此類行為,說明其在違法性的認知上就具備“明知”的可推斷性,除非其能提供反證,否則就可據此作出初步認定。另一方面,如果某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前曾經因為實施相同類型的違法行為受到過行政處罰,在這一過程中其對違法行為所涉及的對象——如在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中,行為人對該商品屬于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這一客觀事實應當有完全準確的認識,根據“法律邏輯推論加實踐經驗推斷”的方式,基本上可以推定行為人對行為所指向商品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事實具備法律上所要求的明知。因此,因曾經實施與犯罪行為相同類型的行為受過行政處罰的,再實施此類構成犯罪的行為,不僅在主觀的法律認知或者違法性認識上可以推定為具有明知,在犯罪客觀對象上對行為所涉及的犯罪事實也可以推定為具有明知。
這種對明知的推定,在違法性認識推斷方面一般應當限于行政法與刑法條文規定重合范圍內,對于刑法與行政法規定的內容不一致的,只能做有限的推定;此外對于每個案件中的具體犯罪行為所涉及的客觀對象或者客觀事實,應當限于相同的對象或者事實,如果僅是行為類型同一——如行為人前一行為僅是實施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曾經受到行政處罰的行為中的商標和商品與當下所要評判的商標的種類和商品的類型均不同,就不能從曾經受過行政處罰中完全推出其對犯罪行為所涉及的對象或者事實具備法律所要求的明知。但總體而言,這一推定方法可以在《刑法》中部分犯罪的“明知”認定中推廣。[9]
(四)加大從重處罰與限制加重處罰的適用力度
在將“受過行政處罰”作為量刑從重處罰的場合,相關司法解釋做了很多的完善,為準確判定刑罰的輕重指明了方向。曾因受到行政處罰后又實施或者反復實施相同類型的不法行為,其違法行為所表現出的反復性情狀和深度,充分體現了行為人在實施此類行為時的主觀惡性比較大,相應的人身危險性也比較強。人身危險性與行為人的再犯罪可能性相關,也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本身相關,在認定犯罪和處以刑罰的過程中,必然影響刑事責任的判斷,進而影響行為人刑罰量的大小。
就我國《刑法》中所謂的行為人之人身危險性而言,并不是司法實際中認定犯罪的主要根據,其主要是作為量刑的根據而受到關注。行為人曾經因實施某類行為受過行政處罰,卻未從此類被處罰中受到教育,也未充分吸取其中的教訓,明知這種行為被法律所不允許,仍置法律和懲罰于不顧,鋌而走險地再次實施該類行為,相對于初次實施該類行為的人而言,其人身危險性無疑要大很多,在對被告人量刑的過程中,可以將受過行政處罰的事實在一定條件下作為對犯罪行為人從重或加重處罰的依據。在法定犯的場合,根據曾經受過行政處罰而加重或者從重被告人刑罰的情形,應當可以普遍地適用而不受到限制,即便是在自然犯的場合,這種量刑上從重處罰也有充分的根據。
必須注意的是,曾經“受到行政處罰”可以作為一個普遍的從重或者加重處罰的根據,但在對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加重處罰的事由進行認定時,應當予以嚴格限制,遵循謹慎嚴謹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曾經受過行政處罰一般不能單獨作為加重對犯罪行為人處罰事由,須將行為人曾經受過行政處罰這一事實與其他彰顯行為人客觀危害性、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事實結合才可作為加重處罰的事由在司法解釋中予以規定。
(五)加大限制性或者禁止性從寬處罰的適用力度
人身危險性是一種重要的處罰依據,作為司法上量刑的主要根據之一,對犯罪人刑事責任或刑罰的影響是雙向的,因為人身危險性大或小對于被告人刑事責任大小或刑罰量的大小應當有不同的意義。[9]在一定條件下,“受過行政處罰”可作為對行為人進行從重或加重刑事責任的根據,也可以作為刑罰從嚴的根據,與此相對,在一定條件下,“受過行政處罰”這一事實在司法處理上亦可作為非罪化處理的理由,也可以作為對行為人進行從寬處罰的限制性根據或禁止性事由。
“受過行政處罰”在實施相同的行為表現的是行為人人身危險性較大,對其在處罰上從重或者禁止適用某些較輕的刑罰,或者考慮到再犯可能性,不適用某些非監禁性刑罰(如緩刑)執行方法。對此可以在相應的罪名中予以適當的擴大。但必須要受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是曾受過行政處罰對當下犯罪刑罰的限制或者禁止適用應當有時間上的限制。前文關于行賄罪和知識產權犯罪的司法解釋中對禁止適用緩刑的規定上,對受過行政處罰的時間沒有限制,導致行政處罰在量刑中影響因素可能還要強過法定的累犯量刑情節,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從有關的司法解釋規定看,受過行政處罰對量刑限制或者禁止性影響的時間應當以兩年為限,即只有兩年之內受過的行政處罰才能產生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罰的適用。二是曾受過行政處罰對當下犯罪刑罰的限制或者禁止適用應當有次數上的限制。《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規定三年內受到兩次以上行政處罰,但逃稅罪規定的五年內受到二次以上行政處罰作為逃稅行為非罪化處理的例外。從立法精神看,一般應當以受到兩次以上的行政處罰為限,即只有受過兩次以上的行政處罰才能產生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罰適用的效果。
當前,“世界各國對于司法改革的模式方法、具體任務和技術進路都呈現出轉向趨勢,法制發達國家逐步由整體性改革轉向日益精密的技術性推進,而法制發展中國家則注重法律體系統一構建背景下的整體性改革推進”[13]。“受過行政處罰”作為入罪類型擴張現象的產生既與司法機關長期受到行政科層制思維模式的影響有關,也與司法機關對司法解釋權的濫用和過度擴張有關。“受過行政處罰”在刑事司法解釋中的尷尬地位,與我國司法現實有密切的關系,在法治國家的建設過程,司法機關應不斷規范司法解釋權,對刑法(典)保持應有的尊重和敬仰,同時也要維護司法權應有的謙抑品質,如此方能贏得社會的尊重和對司法的信仰。
注釋:
①因本文涉及的司法解釋較多,均采用《關于××的司法解釋》《關于××的司法意見》這一簡稱,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