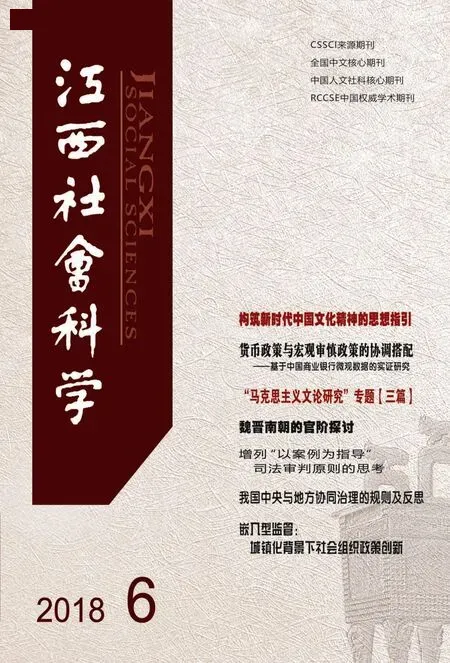本體闡釋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中國經(jīng)驗
馬克思主義如何直面現(xiàn)實并對其作出有效解釋的問題,一直是關(guān)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取得長足的發(fā)展,但在繁榮的表象背后也存在著一些隱憂,其中的一個突出難題是:如何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合理吸收西方文論與美學資源并將其與中國當下的文藝發(fā)展經(jīng)驗有效結(jié)合?這既是關(guān)系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美學本土化與民族化的核心問題,也是關(guān)系當代文論與美學健康發(fā)展的不可回避的問題,更是在有效歸納與總結(jié)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中國經(jīng)驗的過程中必須認真反思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有論者指出,文藝理論與美學研究應(yīng)該堅持“本體闡釋”原則。“‘本體闡釋’是以文本為核心的文學闡釋,是讓文學理論回歸文學的闡釋。‘本體闡釋’以文本的自在性為依據(jù)。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態(tài)自在的獨立本體,是闡釋的對象。”[1]本體闡釋由以文本意義為中心的“核心闡釋”、以作者創(chuàng)作為觀照對象的“本源闡釋”和以讀者接受為觀照對象的“效應(yīng)闡釋”三個部分構(gòu)成,三者呈由中心到外圍的輻射關(guān)系,其重要程度依次遞減。“本體闡釋”構(gòu)想“作為重建文學本體論的新實踐”,“具有邏輯的合理性和理論建設(shè)的可行性”。[2]
一、形而上學視域中的文學本體論
“本體闡釋”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積極介入當代批評所做的重要理論努力,試圖站在超越形而上學的立場上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哲學與本體論的關(guān)系問題,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反復出現(xiàn)的問題,可以說,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直接決定了馬克思哲學當代理解的理論范式……在馬克思哲學研究中,關(guān)于本體論的思考存在著三種基本范式:即物質(zhì)本體論、實踐本體論與存在論。這三種不同范式的更替,在一定的意義上恰恰映現(xiàn)了馬克思哲學研究中的基本邏輯進程。”[3]“本體闡釋”正是順應(yīng)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創(chuàng)新的潮流,努力以個別的文學文本為理論建構(gòu)的出發(fā)點和重心,在遵循文學的獨特邏輯和發(fā)展軌跡的基礎(chǔ)上審視文學的具體存在,進而把握文學的價值與意義,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規(guī)律。“本體闡釋”無論是對個別文本的生成及其獨特性的觀照,還是對文學的個性與共性之間的動態(tài)復雜關(guān)系的強調(diào),都與傳統(tǒng)形而上學完全不同。傳統(tǒng)形而上學往往“在邏輯學或本體論的意義上來理解可以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對象屬性”[4](P175),這一理論立場在處理個別性與普遍性的關(guān)系時,以普遍性為理論建構(gòu)的旨歸,不但無視個別性問題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個別性不過是普遍性與具體事物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
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在文藝理論與美學研究中的具體表現(xiàn)是,總是努力追問文學的“本質(zhì)是什么”或“本原是什么”等問題,試圖在鮮活多樣的文學經(jīng)驗背后找到一個普遍永恒的超驗存在,根本不關(guān)心文學的具體存在及不同文學文本的獨特精神體驗。20世紀80、9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研究基本上都堅持這種形而上學的立場,“認為文學中存在著某種‘文學本體’的東西,在思維方式上先驗地預(yù)設(shè)了‘文學本體’的存在,而文學本體論則是研究和探索‘文學本體’的一種文學理論”[5](P13)。從總體上看,當時以形式本體論、人類本體論等理論為主體的文學本體論研究努力以某種理論為前提從邏輯上推演文學的存在形態(tài),要么把文學的本體視為文學本身及各種描寫技巧,要么站在審美超越論的立場上分析文學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總是把文學的存在視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存在。這類形而上學的文學本體論分析既脫離文學存在的具體形態(tài),把文學的本體看作是某種具有同一性的抽象邏輯范疇,又導致關(guān)于文學功能與價值等問題的闡釋的抽象化,容易把文學與人以及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的復雜性歸納為一些簡單的概念和范疇,從而忽視對文學進行多角度分析的積極意義。
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文學本體論研究主要以形式本體論與人類本體論為代表,根本沒有注意到“本體”與“本體論”的復雜含義,甚至將“本體”等同于“本質(zhì)”。很多堅持形式本體論的論者把文學的形式本體等同于文學作品的具體形式。“形式是文學的存在方式……由于本體批評研究的著眼點是文學自身,而且的確對文學作品的形式技巧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6]形式本體論研究因?qū)π问降睦斫獯嬖诓町悾纬闪苏Z言本體論、敘事本體論與結(jié)構(gòu)本體論等理論形態(tài),但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知識分子的“使命意識”使“‘形式’作為一種文學的本體,擁有了形而上的、難以言說的意義”[7](P233)。與形式本體論相似的是,人類本體論以李澤厚人類學本體論美學為基礎(chǔ),順應(yīng)20世紀80年代文學主體論的時代風潮,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述關(guān)于人類本體論的看法。有論者將文學看作是反思人類生存的重要手段,努力超越具體的文學世界與閱讀體驗,探索其背后存在的人類本體。也有論者指出:“既然審美活動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動,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和形式之一,而文藝活動在本質(zhì)上是審美的,是審美活動的高級形態(tài)和典型表現(xiàn),那么,文藝活動自然也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動,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和形式之一。這就從根本上確定了文藝活動的人類本體論地位。”[8]這一觀點顯然以康德的先驗主體性思想為基礎(chǔ),把審美活動視為通向自由王國的必經(jīng)之途,實現(xiàn)對自然王國的超越,也摒棄了經(jīng)驗的自然。
朱立元和邵建改變了關(guān)于文學本體問題的提問方式,以活動本體論追問“文學為什么存在”“文學怎樣存在”等問題。朱立元認為:“文學是作為一種活動而存在的,存在于創(chuàng)作活動到閱讀活動的全過程,存在于從作家→作品→讀者這個動態(tài)流程之中。這三個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的全部活動過程,就是文學存在方式。”[9]邵建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以作者(writer)、作品(worker)和讀者(reader)為主體的“3R結(jié)構(gòu)”文學本體論。“文藝本體論的基本問題,就是解答文藝作為‘在’它如何存在、怎樣存在……欲回到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握文藝的形態(tài)構(gòu)成,這個構(gòu)成就是文藝作為在的存在方式,以文學為例就是‘三R結(jié)構(gòu)’。”[10]朱立元的“三環(huán)節(jié)說”與邵建的“三R結(jié)構(gòu)”從表面看都是以文學活動為基礎(chǔ),分析文學的本體存在,但前者顯然是“存在者”意義的存在,“指的是文學現(xiàn)象”;后者顯然是“存在”意義的存在,“指的是文學之‘On’”。因此,他們在“何為文學存在”問題上存在著根本分歧,出現(xiàn)了“作為‘存在者’的文學是如何存在的”與“作為‘在’(存在)的文學是如何存在的”[11]的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馬克思哲學與本體論關(guān)系探討的不斷深入,一批回顧與反思我國新時期文學本體論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xiàn)。王元驤與朱立元作為其中的重要代表,都努力站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最前沿,不約而同地從人的存在的角度強調(diào)文學本體論研究的重要性,努力從文學自身的獨特性出發(fā)還原并描述文學的本體存在。王元驤認為:“出于對超驗性層面在構(gòu)成人的生存本體的特殊地位的認識和理解,我們才肯定文藝在人的生存活動中的重要意義,以及文藝本體與人的生存本體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并把人的生存本體同時也視作文藝的本體,使審美、文藝與人生三者之間達成了有機的統(tǒng)一。”[12]他也許并沒有意識到,他從人生實踐的角度出發(fā)分析文藝本體的思路,已經(jīng)開始超越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強調(diào)文藝在促使人實現(xiàn)自我超越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無可替代的作用。朱立元則從實踐存在論的角度指出:“應(yīng)當從文學作為人的一種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實踐活動的高度,從文學活動區(qū)別于其他藝術(shù)和審美活動的特殊存在方式的角度,對從作者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到讀者的文學閱讀(接受)活動,重新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這才是文學本體論研究的任務(wù)。”[13]
二、走向后形而上學的本體闡釋
王元驤和朱立元的實踐論在對此前的文學本體論研究構(gòu)成有力沖擊的同時,也為蘇宏斌、張瑜和劉陽從超越形而上學的立場研究文學本體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蘇宏斌的《文學本體論引論》與張瑜《文學本體論新論》都明確表示受到王元驤和朱立元的文學本體論研究的影響,也都強調(diào)不應(yīng)該忽視以西方傳統(tǒng)本體論學說為代表的哲學本體論的價值與意義,認為要在充分分析哲學本體論的基礎(chǔ)上注意辨析其與文學本體論之間的差異。張瑜指出,王元驤、朱立元和蘇宏斌“力圖以存在論作為一種新的視角來建立文學基礎(chǔ)理論新的生長點”,“他們雖然沿用了本體論這個術(shù)語,但其意義并非要恢復回傳統(tǒng)的本體論學說視野下,而主要是指本體論的學科意義,即在文學存在論視野下,力圖尋找和建立新的存在論學說來推動當前文學基礎(chǔ)理論的變革和發(fā)展,這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5](P55)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陽的《小說本體論》盡管以“小說本體”為研究對象,卻是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本體論研究為基礎(chǔ),站在后形而上學本體論的立場上深入分析文學與哲學之間的對抗以及文學對形而上學的超越,并以此為基礎(chǔ)建構(gòu)起小說本體論的理論體系。蘇宏斌、張瑜和劉陽的文學本體論研究除了指明文學本體的具體存在形態(tài)之外,也為“本體闡釋”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了思路。
本體闡釋作為一個以文本為中心不斷向外擴張的闡釋系統(tǒng),首先強調(diào)文本是闡釋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并以此為基礎(chǔ)建立起對文本生成的外部語境以及讀者的反應(yīng)等問題的多層次闡釋系統(tǒng)。這一闡釋系統(tǒng)能否成立取決于如何看待以文本作為具體物質(zhì)載體的文學存在問題,因為文學文本既是有形的、具體的“物”,又不會僅僅停留在“物”的層面,而是以語音層、意義單元層以及圖式化層結(jié)合在一起構(gòu)成具體的“召喚結(jié)構(gòu)”,不斷促使讀者借助意義的不確定性以及空白等對其作出復雜的理解和闡釋。形而上學的文學本體論由于過于倚重哲學本體論,一方面依據(jù)某種本體論觀點將文學視為某種現(xiàn)成之物,認為文學要么能夠再現(xiàn)世界或表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情感,要么以獨特的形式結(jié)構(gòu)展示以作者為中心的復雜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則遮蔽了文學自身的獨特優(yōu)勢,使文學能夠在不同社會歷史語境中不斷追問人生存在的終極關(guān)懷價值無法得到彰顯。本體闡釋應(yīng)該以后形而上學的文學本體論為契機,借助其獨特的理論視野和分析路徑建立起核心闡釋、本源闡釋和效應(yīng)闡釋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為切實分析文學的具體存在并建構(gòu)有效的本體闡釋理論創(chuàng)造條件。
第一,本體闡釋應(yīng)該立足于后形而上學的理論視野。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對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展開內(nèi)在批判,努力建構(gòu)一種超越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如果承認形而上學的直接性引證傳統(tǒng),它也就必須承認它對歷史的精神狀態(tài)的依賴性。”[14](P373)阿多諾認識到傳統(tǒng)形而上學除了具有超驗的普遍性與永恒性等特點之外,也將各種易變、短暫的經(jīng)驗性特點納入到超驗性的本質(zhì)之中,使概念與對象、真理與事實之間形成無法回避的斷裂。韋爾默在評價阿多諾對形而上學批評時指出,“阿多諾的所有思考都是針對這種倒退的可能性”,并最終以審美經(jīng)驗來彌補這一斷裂。但是,“正因為審美經(jīng)驗本身不可能賦予任何經(jīng)受不住哲學批判的東西以可靠性,阿多諾就不可能放棄用哲學術(shù)語表達調(diào)和的審美破譯觀念的能力”,因此“在這種疑難的關(guān)系中,散播著(與批判補救相對立的)未改造的形而上學的碎片”。[15](P309-310)與阿多諾以哲學美學超越形而上學的思路不同,近年來的文學本體論研究主要從文學對抗哲學的優(yōu)越性角度分析形而上學的局限,強調(diào)文學語言所具有的重要本體論地位。本體闡釋應(yīng)該以此為基礎(chǔ),努力借助超越形而上學的文學本體論研究建構(gòu)起有效的闡釋路徑。
第二,本體闡釋理論要以文學存在論為理論基礎(chǔ)。從超越形而上學的理論視野出發(fā),文學本體論已經(jīng)不同于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的本體論,而是以文學存在為研究對象的文學本體論。這一理論在將文學與人的生存狀況建立起有效關(guān)聯(lián)的基礎(chǔ)上,努力拋棄傳統(tǒng)形而上學關(guān)于文學本體的超驗性追問,以文學如何存在以及文學怎樣存在等問題為分析對象,試圖多角度、多層次地審視文學的具體存在。這種關(guān)于文學本體的探討明顯具有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色彩。“此在”作為對“存在”的領(lǐng)悟,只有在與“存在”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過程中才能成為“此在”,也才能完成對“存在”的“去蔽”,在體驗存在的過程中揭示存在的意義。海德格爾關(guān)于此在的分析超越了傳統(tǒng)本體論的超驗訴求,但也經(jīng)常被誤解為只關(guān)注此在,而忽視對存在本身的意義分析。海德格爾后來轉(zhuǎn)向關(guān)于“詩”與“思”的思考,把語言作為“存在的家園”。“思想是原詩;它先于一切詩歌,卻也先于藝術(shù)的詩意因素,因為藝術(shù)是在語言之領(lǐng)域內(nèi)進入作品的。無論是在這一寬廣的意義上,還是在詩歌的狹窄意義上,一切作詩在其根本處都是運思。思想的詩性本質(zhì)保存著存在之真理的運作。”[16](P345)海德格爾重解詩與思的關(guān)系,為本體闡釋著力分析文學自身所具有的“真”“美”合一的特點提供了重要啟迪。
第三,本體闡釋應(yīng)該努力把握和追問文學的生成性存在。長期以來,“存在”一直因擁有兩個義項而使文學本體論的研究對象不明確。“存在概念還有一種普遍性,這在西文中比較明顯。以德語與英語為例,sein和be都既表存在,又是系詞‘是’。”[17](P31)文學的本體到底是“存在”還是“是”?從思想史的發(fā)展來看,文學的本體往往因局限于形而上學的視野而被視為文學的本質(zhì),文學本體的研究自然就變成關(guān)于文學本質(zhì)的研究。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理論則改變了這種追問方式,不再探討“存在是什么”,而是把存在當作一種顯現(xiàn)的方式。即便如此,德里達從解構(gòu)主義的立場出發(fā),仍然認為海德格爾并沒有完全超越形而上學。“存在的本義與‘存在’一詞之間的斷裂,意義與聲音之間的斷裂,‘存在的聲音’與‘語音’之間的斷裂,‘存在的呼喚’與它的發(fā)音之間的斷裂;這種確定基本隱喻而又在表明隱喻的不協(xié)調(diào)性時懷疑這種隱喻的斷裂,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爾在對待在場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方面的模糊立場。它置身其中而又違反它。”[18](P29)德里達為了擺脫海德格爾所面臨的這一難題,努力破除存在與詞語之間的同盟,不再試圖肯定并努力回到存在的本源,而是試圖探討某種指向未來或者要來的生活。“這樣一種始終保持在未來之中的思想、生活與未來,才是真正的本質(zhì),它生出一切可能性,但卻不可被對象化地、現(xiàn)成化、在場化地把握、居有。”[19](P384)解構(gòu)以既定之物作為解構(gòu)對象,其自身卻總是處于建構(gòu)過程中,是一種包含著諸多可能的延異狀態(tài)。
三、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中國經(jīng)驗
從表面看來,文學本體論的發(fā)展以及本體闡釋理論的提出,只要經(jīng)過從形而上學到后形而上學的理論范式的轉(zhuǎn)換,就能夠由傳統(tǒng)的文學本體論轉(zhuǎn)變?yōu)槲膶W存在論,進而對文學的具體存在予以有效的闡釋。但是,無論是本體闡釋理論還是晚近的文學本體論研究之所以能夠汲取當代西方文論的合理成分,是因為研究者有著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并努力根據(jù)時代要求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fā)展。“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xiàn)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fā)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0](P691)文學本體論研究在新時期的不斷發(fā)展也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具有的歷史活力。蘇宏斌認為,新時期以來的文藝學研究總是從認識論哲學的角度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將馬克思的思想理解為一種認識論。這既不符合認識論與本體論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西方哲學的歷史發(fā)展實情,也使以往的文學本體論研究難以擺脫認識論的制約,總是停留在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視域中,無法把已經(jīng)超越近代哲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xiàn)代形態(tài)與精神充分發(fā)掘出來。“在我們看來,要想真正把本體論的視角引入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關(guān)鍵就在于把反對和超越形而上學確立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本追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文學本體論發(fā)展成一種現(xiàn)代的理論形態(tài)。”[21](P12)本體闡釋以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的有效對話為基本訴求,首先以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快速發(fā)展的社會與文化為觀照對象,努力從人的生存與實踐的角度探索文學的具體存在。這一理論的提出和今后的發(fā)展,必將為進一步推動新時代美學的發(fā)展提供切實可行的經(jīng)驗。
首先,努力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各種經(jīng)典文本,明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思想史的整體演進中的獨特價值,厘清馬克思批判和反思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基本理論路徑。無論是自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xù)到新世紀的文學本體論研究,還是近年來本體闡釋理論不斷受到重視,都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不斷加強有直接關(guān)系。具有明顯形而上學色彩的各種文學本體論觀點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后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是因為當時的文藝理論研究要努力擺脫機械反映論的文藝觀念,改變長期以來左右我國文藝理論發(fā)展的過于簡單的認識論模式。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不斷發(fā)展,特別是從西方近現(xiàn)代哲學發(fā)展的角度審視馬克思的思想并不斷譯介各種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哲學本身所蘊含的后形而上學維度開始受到重視。馬克思哲學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反思主要表現(xiàn)為其對具體的歷史存在和質(zhì)樸的社會現(xiàn)實保持開放性,將抽象的理論推演建立于堅實的社會歷史之上,強調(diào)意識與存在保持同構(gòu)性關(guān)系的同時,也指出兩者之間存在著非同一性的可能。“這些內(nèi)容都只能以概括的或者說語言的方式進入到思中,而這種進入的方式本身就已經(jīng)將異質(zhì)性變成了同質(zhì)性,在這種情況下,保持這種異質(zhì)性之思,就必須堅持哲學之思與生活之間的開放性關(guān)系,這種開放性不是直接性意義上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而是通過理論有間距地反思現(xiàn)實,通過現(xiàn)實批判性地反思理論,這種雙重的批判性反思,才能保持哲學的‘活力’。”[3]本體闡釋理論作為充滿“活力”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重要理論成果,要注意非同一性思維在建構(gòu)多層次闡釋系統(tǒng)中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其次,深入探索馬克思主義與后形而上學哲學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本體闡釋理論應(yīng)以后形而上學文學本體論研究所堅持的生成論作為基本的理論立場。后形而上學的馬克思哲學除了能夠以非同一性的思維為文學本體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還能夠以生成論的理論立場重新分析文學本體的構(gòu)成和本體闡釋的形成。馬克思借助“實踐”即“感性活動”拆解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以“意識之內(nèi)在性的瓦解”的本體論革命發(fā)動“哲學革命”。“‘現(xiàn)實的個人’在感性活動的本體論定向中就是‘出離’自身的,也就是說,是在自身之外,并且一向已經(jīng)在外;它作為感性的、對象性的活動,是非主體的‘主體性’:它‘不是主體’,而是‘對象性的本質(zhì)力量的主體性’。”[22](P238-239)主體根本不是一個抽象化的現(xiàn)成個體,而是一個處于不斷生成過程中的“現(xiàn)實的個人”。具體的個體只有與對象和現(xiàn)實不斷地積極互動,才能在實踐中完成主體的生成并顯現(xiàn)為能動的主體存在。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學的本體也不再是現(xiàn)成論意義上的本體,而是在與處于“生成”過程中的主體不斷對話的過程中顯現(xiàn)的本體。后形而上學的文學本體論努力在文學的顯現(xiàn)過程中把握其具體存在,強調(diào)本體是一個不斷處于生成過程的“活”的本體。以文學文本為中心的本體闡釋,內(nèi)部也存在著多重的復雜生成過程,既要以作者和讀者的積極對話將處于“懸而未決”的可能狀態(tài)的文本呈現(xiàn)出來,又要以文本自身的生成性展示作者與不同歷史語境中的讀者對話的暫時性。
最后,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直面文學發(fā)展的獨特現(xiàn)實,厘清文學與哲學等其他學科之間的關(guān)系,增強文學理論直面現(xiàn)實并對其作出有效解釋的能力。文學與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也長期存在著關(guān)于哪一方對真理的把握更具有優(yōu)勢的爭執(zhí)。柏拉圖將詩人趕出理想國的主張昭示了哲學對文學的優(yōu)勢地位的取得,并且這種狀況一直延續(xù)到19世紀。隨著反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現(xiàn)代哲學的到來,文學對哲學的優(yōu)勢地位才開始顯現(xiàn)。“在詩與哲學之爭中,文學(詩)始終保持著超越形而上學的本色,并不存在主客對立之虞。哲學對文學的優(yōu)勢地位的形成,是基于本體論形而上學力量以及由此導致的主客對立思想方式,文學對哲學優(yōu)勢地位的逆轉(zhuǎn),也是基于文學對本體論的形而上學力量的反抗及由此發(fā)展出來的主客融合思想方法。”[23](P139)隨著后形而上學觀念的發(fā)展,文學開始憑借獨特的真理把握方式實現(xiàn)對哲學的超越。這是因為,文學既能夠借助情感世界實現(xiàn)對歷史的超前預(yù)判,又能夠借助鮮活的形象實現(xiàn)對現(xiàn)實的深度開掘,還能夠以超驗的審美判斷實現(xiàn)對人生價值的不斷追問。更為重要的是,文學能夠以較為綜合的方式將這些作用發(fā)揮出來,進而從多個層面不斷生成真理性的認知。本體闡釋作為以具體的文學文本為觀照對象的理論,要秉承馬克思主義直面現(xiàn)實的精神,充分注意文學本體論研究的最新進展,以便從多個層面對處于生成過程中的具體文本存在作出有效的闡釋。
文學本體論研究的不斷發(fā)展以及本體闡釋理論的提出都證明,中國當代審美經(jīng)驗和文學實踐的快速發(fā)展既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傳統(tǒng)的建構(gòu)帶來不竭的動力,也對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文化發(fā)展實際的結(jié)合不斷提出新的命題。隨著海德格爾、德里達、哈貝馬斯等西方哲學理論的持續(xù)涌入,馬克思的實踐本體論思想也得到豐富和發(fā)展。“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現(xiàn)代‘存在論’對傳統(tǒng)‘本體論’的突破,首先是對它的實體性思維的突破,由此引導我們?nèi)ニ伎紓鹘y(tǒng)‘本體論’之局限性,啟發(fā)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被長期遮蔽的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存在論維度’。”[24]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理論中的生成論思想,的確為理解馬克思的“實踐”觀念注入新的活力,從而使其既具有動態(tài)的生成性特點,又對人與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提出了新的理解。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充分吸收海德格爾與德里達等理論家的生成理念和非同一性思想,在人的現(xiàn)實感性活動基礎(chǔ)上把握人的存在的歷史性與空間性,本體闡釋理論必將在此基礎(chǔ)上能夠得到不斷深化和發(fā)展,這也將使馬克思主義美學能夠更為積極有效地介入當代批評。
[1]張江.當代文論重建路徑:由“強制闡釋”到“本體闡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6-16.
[2]楊建剛.新時期文學形式本體論觀念的演進、論爭與反思[J].人文雜志,2016,(6).
[3]仰海峰.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研究:回顧與展望[J].南京社會科學,2002,(8).
[4](德)哈貝馬斯.后形而上學思想[M].曹衛(wèi)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5]張瑜.文學本體論新論[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
[6]陳劍暉.走向本體的批評[J].文藝爭鳴,1989,(3).
[7]張婷婷.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shù)史(第四部)[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8]杜書瀛.論人類本體論文藝美學[J].文藝理論研究,1989,(3).
[9]朱立元.解答文學本體論的新思路[J].文學評論家,1988,(5).
[10]邵建.梳理與沉思:關(guān)于文藝本體論[J].上海文論,1991,(4).
[11]單小曦.新時期以來文學存在方式研究之反思[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
[12]王元驤.文藝本體論研究的當代意義[J].東方叢刊,2006,(1).
[13]朱立元.關(guān)于文學本體論之我見[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5).
[14](德)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M].張峰,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15](德)韋爾默.后形而上學現(xiàn)代性[M].應(yīng)奇,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16](德)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17]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4.
[18](法)德里達.論文字學[M].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19]朱剛.本原與延異:德里達對本原形而上學的解構(gòu)[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蘇宏斌.文學本體論引論[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6.
[22]吳曉明,陳立新.馬克思主義本體論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23]劉陽.小說本體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24]朱立元.海德格爾凸顯了馬克思實踐觀本有的存在論維度[J].社會科學,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