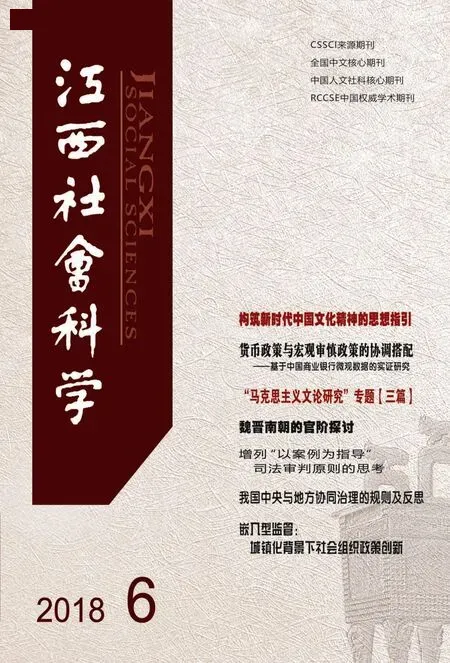魏晉南朝的官階探討
在魏晉南朝的職官管理制度中,同時存在著官班、秩石與官品三個體系,它們既相互配合又相互沖突和矛盾。較之漢代的單一官階制,這同時并用的三個序列顯然要復雜得多。對于當時何者為官階,史學界有官品說、官班說、祿秩說等不同觀點;閻步克提出,“兩晉南朝是官品與祿秩兼用,實行‘雙軌制’”;在蕭梁“使用班、品、秩三駕馬車。三種位階各顯其能”。[1](P29)黃惠賢認為,在魏晉南朝品、階、班并存,即“品班之外,另有官階”[2](P323-324)。這種眾說紛紜的局面表明,當時的官階狀況尚未明晰,需要進一步予以探討。本文擬通過對魏晉南朝的官品、秩石和官班的全面考察,力圖厘清當時的官階發展狀況及其原因。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一、官 班
古代官階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不僅具有豐富的內涵,而且不斷發展變化,要透徹理解它很不容易。閻步克通過多年對官階的深入研究,提出品秩由權責、資格、薪俸、特權、禮遇五個要素構成的理論架構[1](P37),對我們研究官階具有重要指導性。官階的外在表現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它最根本、最核心的實質應該體現為官職晉升的序列。因為官職的權責大小、薪俸多少可能會與官階的高低不一致,但官職晉升階梯一般要與官階保持一致,否則官職的晉升就會出現混亂。在魏晉南朝,官員升遷官職所遵循的序列既不是官品,也不是秩石,而是官班,對此史書有明確的記載。《隋書·百官志上》:官班制“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為前后”。這里明確說明官班就是官階,不僅上下班次的官職有高低之分,而且同班內的官職其前后位次也標志著它們的優劣貴賤。官員遷轉官職不僅體現在從較低班次的官職晉升到較高班次的官職,而且還可以在同一班次內從后邊的官職遷轉為前邊的官職,官員遷轉官職完全依據官班的次序,它是一套細密的職官管理制度。魏晉南朝時,官員官職的遷轉如果從官品而言,很多則是由高轉低;因而官班制是一項士庶起家與官員官職遷轉的官階制度。[3]蕭梁官班制由魏晉宋齊的官班繼承發展而來,因而整個魏晉南朝的官職遷轉都依據官班而不是官品。[4](P136-175)也就是說,官班制作為官員升遷官職的序列,是一項法定的官階制度。
有學者認為:“階指官品、勛品之間的分階。此制始于南北朝時期。”[5](P559)這一觀點可能不妥。官階指官班這不僅是制度性規定,而且得到魏晉南朝人的普遍認可。曹魏以來官員遷轉官職基本依據官班,當時人所說的“階”基本都產生在遷轉官職的語境中,因而可以斷定它們都指的是官班。曹魏時人邯鄲淳所撰的《后漢鴻臚陳君碑》記載:陳紀“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后文稱陳紀“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宋代的章樵對后文注釋說:“謂由五官中郎將而階升為天子左右近臣。”[6](卷19,P427、P429)這是非常準確的。此處的“階”指官職的升遷次第,因而指官班。歷任侍中、中書監的韋誕在《敘志賦》中說:“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嘆息,思損己而降階……歷文武于機衡,擁大珰以帝側。”[7](卷26《人部十·言志》,P471)由“歷文武于機衡”可知,此處的“階”也指官職的遷轉序列,即官班,“降階”即從較高的官職降低到較低的官職。阮籍《與晉王薦盧播書》言:“伏見鄙州別駕,同郡盧播……學不為人,行不求達,故久沉淪,未階太清。”[8](P66-67)道教有玉清、上清、太清的三清勝境,其中太清在玉清和上清之上。這里用太清比喻高官。盧播因為“學不為人,行不求達”,所以長期仕宦不達,僅官至州別駕,未能升遷至高官,此處的“階”也指官職晉升的序列即官班。大將軍司馬師病故后,正元二年(255)二月,謚曰武公,其弟司馬昭上表辭讓說:“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祗懼。”[9](卷2《景帝紀》,P31)官職升遷至丞相或相國,司馬昭稱之為“階歷”,即官職遷轉的階梯為官階。“常道鄉公即位,(鄭沖)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臺輔,而不預世事。”[9](卷33《鄭沖傳》,P992)鄭沖“位階臺輔”即官至太保,“階”也指官職升遷的階次即官班。東晉元帝時,庾亮自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升遷至中領軍,自稱是“遂階親寵”[9](卷73《庾亮傳》,P1916)。中領軍是禁衛軍長官,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擔任。庾亮身為明帝皇后之兄,由十班的黃門侍郎超遷十二班的散騎常侍,再超遷十四班的中領軍,自然是倍感“親寵”。而在晉官品制中,散騎常侍和中領軍則分別在三品的次位與倒數第三位。庾亮所說的“階”,顯然指官職升遷的序列即官班而不是官品。
南朝與魏晉類似,人們經常所說的“階”仍然指官職遷轉的官班。蕭齊初年,秀才劉璉上書為建平嗣王劉景素申冤說:劉景素辭去南徐州刺史,“請身東第,后求會稽,降階外撫”[10](卷72《建平王劉宏傳附子景素傳》,P1866)。南徐州刺史為十五班,會稽太守為十三班[4](P200-201)。南徐州刺史劉景素請求擔任會稽太守,顯然是官班的降低,即“降階”的“階”指官班。劉善明擔任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時,在上表中建議:“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11](卷28《劉善明傳》,P525)為獎勵“忠貞孝悌”的官員,可以不依照官職晉升的尋常次序提拔,即破格拔擢。“殊階”指優異的官階,即超遷、越階晉升。蔡法度主持制定蕭梁的《律》《令》《科》等法律制度,梁武帝直接提拔他守廷尉卿。沈約所撰的《授蔡法度廷尉制》中說:“尚書刪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宜加褎擢,弗系常階。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12](卷397《中書制誥》,P2015)尚書郎中為五班,廷尉卿則為十一班,蔡法度的官職晉升超遷了五個階次,所以梁武帝要下特詔施行,沈約也強調他的升遷是“弗系常階”。“常階”指逐階晉升,與越階晉升的“殊階”相對。
官階就是官職的等級階梯,所以史書和當時人又將官班稱之為“階級”或“等級”。西晉的吏部尚書劉頌,“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9](卷46《劉頌傳》,P1308)。始平王文學李重在上疏中推崇該制度說:“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9](卷46《李重傳》,P1310)后來李重又議論說:“漢魏以來……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臣以為今宜大并群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13](卷16《選舉四》,P387)官品只有九個等級,無論如何不等稱之為“階級繁多”;官員如果按照官品逐級晉升,也不可能會發生“遷補轉徙如流”的現象。這里所說的“等級”“階級”,都發生在官職遷轉的語境中,應都指官職遷轉的序列即官班。不僅上下班次之間構成官職遷轉的階梯,而且同一班次的前后官職也是遷轉的次第,因而導致官員“遷補轉徙如流”,任期短暫,不能有所作為。因為當時“階級繁多”,又經常在同一班次內遷轉,所以李重不僅建議“大并群官等級”,而且建議“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西晉官員遷轉官職的階級與蕭梁官班制若合符節。劉頌制定的“九班之制”即“選例九等”,是合并了現實生活中眾多的階級而成的官階制度,符合李重的“階級少”“久其事”的原則,所以受到他的推崇。
南朝延續晉朝的慣例,仍然稱官職升遷的官班為“階級”。中書通事舍人楊運長與臺直將軍高道慶,“密遣刺客,赍廢帝手詔,以金餅賜(荊州刺史沈)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10](卷74《沈攸之傳》,P1932)。太子詹事范曄說:“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10](卷69《范曄傳》,P1826)蕭齊的晉安王蕭子懋出任雍州刺史,齊武帝告誡他:“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11](卷40《晉安王蕭子懋傳》,P709-710)以上所說的“階”“級”和“階級”都用于官職的晉升,因而都指官職升遷的階梯——官班。張融在給從叔征北將軍張永的信中說:“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愿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11](卷41《張融傳》,P726-727)張融請求擔任郡丞不成,轉而請求郡太守,如果不成功,就再去請求郡丞,所以狡辯說自己不知“階級”,他所說的“階級”指官職遷轉的等級即官班。
在魏晉南朝,官職等級的序列則稱之為“階次”或“階序”。曹魏時劉寔在《崇讓論》中說:“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眾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9](卷41《劉寔傳》,P1192-1193)自漢魏以來,讓官員薦舉賢能的人,朝廷依據他們的才能高低升遷他們的官職,并且不受官階序列的限制。《南齊書·百官志》:“蔚宗選簿梗概,欽明階次詳悉。”這里的記載較為模糊,《舊唐書·經籍志上》的記載較為清楚明白:“《百官階次》一卷,范曄撰。《宋百官階次》三卷,荀欽明撰。”范曄字蔚宗。二者的記載相一致。顧名思義,“階次”就是官職的等級次序。范曄和荀欽明的著作都是記載官階次序的,與記載官班的《梁選簿》性質一樣,所以范曄的《百官階次》又稱《選簿》。記載官階的官簿稱之為“牒”或“階牒”。殷景仁自太子中庶子遷侍中,反復上表辭讓說,“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因而請求“回改前旨,賜以降階”。皇帝批準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為黃門侍郎。[10](卷63《殷景仁傳》,P1681)在宋官品制中,太子中庶子在五品的第六位,侍中在三品的首位,黃門侍郎在五品的第二位。殷景仁自太子中庶子遷侍中,按照官品是超遷了一個品級。而在官班制中,太子中庶子為十一班,侍中為十二班,黃門侍郎為十班。殷景仁由太子中庶子遷侍中只晉升了一個班次,他從十一班的太子中庶子降為十班的黃門侍郎顯然是“降階”。因此,他所說的“階”指官班,而不是官品。“階牒”指記載官班的官簿,其內容與范曄的《百官階次》、荀欽明的《宋百官階次》等官階著作相類似。南陳時,“及高宗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陸)瓊于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14](卷30《陸瓊傳》,P397)。皇弟皇子文學為五班,公府掾屬為八班,陸瓊的升遷跨越了兩階,故徐陵說“階次小踰”,此處的“階次”指官班的次序。
官員的官職越級升遷稱之為“超階越次”,或簡稱之為“超階”。西晉趙王司馬倫奪取帝位后大肆封賞,以親信“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并列大封。其余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9](卷59《趙王司馬倫傳》,P1602)。蕭齊的晉安王諮議參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謝朓,“啟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祭酒沈約稱“謝吏部今授超階”。[11](卷47《謝朓傳》,P826)蕭梁時,伏暅歷任永陽內史、新安太守,“征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托疾居家”[15](卷71《伏曼容傳附子暅傳》,P1732)。國子博士為九班,而黃門侍郎為十班,吳郡太守為十三班。伏暅與何遠原來的官階可能相同,何遠兩次超遷,伏暅的“循階”就是循序漸進地升遷,與“超階”相對,所以牢騷滿腹。
除了官職遷轉語境中的“階”“階級”“等級”“階次”“階序”指官班外,標識官職高低的“階”也指官班。劉宋的建平王劉宏,“太祖寵愛殊常”,故“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10](卷72《建平王宏傳》,P1858)陳朝的“嗣王府官減正王府一階”[16](卷26《百官志上》,P744)。在梁官班制中,皇弟皇子府長史和司馬為十班,嗣王府長史和司馬為九班;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和從事中郎為九班,嗣王府諮議參軍和從事中郎為八班。其他官職與此類似。嗣王府的官職恰好比正王府的同一官職低一班。因此,上述兩條史料中的“階”都指官班。
不僅“階”“階級”“等級”“階序”“階次”都指官班,而且當時人明確提到的“官階”也是指官班。蕭梁尚書令沈約說:蕭齊時由于百姓大量偽造戶籍,“于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15](卷59《王僧儒傳》,P1462)。愚昧無知的平民百姓,由于不知道皇帝年號的多少和前后順序,不清楚眾多官職的高低次序,因而偽造戶籍時訛誤百出,出現升遷的官職的官階反低于原來的官職。即此處的“官階”指官班。陳朝的徐陵任吏部尚書時,在公告中說:“永定之時,圣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若問梁朝朱領軍異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10](卷26《徐陵傳》,P333)陳朝初期,由于戰爭不斷,國家財政拮據,無法用錢財獎賞立功的將士,所以就升遷他們的官職,來代替錢絹的賞賜,這導致很多人都有了員外散騎常侍、諮議參軍等頭銜。徐陵認為這導致官職的升遷混亂,即應該賞賜錢財、不應升遷官職的人,而升遷了他們的官職;頭銜滿天飛,官職的數量膨脹,含金量大大降低。此處的“官階”“選序”含義相同,都指官職晉升的序列即官班,官職的遷轉由吏部(也稱選部)掌管也可佐證。
綜上所述,在魏晉南朝,官班制作為官職遷轉的主要依據,最明確區分官職的地位高低,因而官班作為官階不僅是制度性的規定,而且得到當時人的普遍認同。
二、秩 石
眾所周知,兩漢以秩石標識官階,官職的秩石多少就標志著其官階的高低。魏晉以來秩石作為傳統的官階仍被沿用。如同陳長琦所說:“魏晉以及南朝宋齊所沿襲的漢代官秩制度,實際上是官階制度。官員的秩別,就是官員官階的階別。”[17](P173)曹魏時官員的待遇和禮儀等規定全部使用的是秩石。[18]兩晉時官員的政治和經濟待遇以及禮儀等規定,仍然大量使用秩石作為標準,而且其范圍甚廣。西晉時不僅妃嬪的等級是按照秩石規定的,而且妃嬪的選拔條件也是依據官員秩石的高低。晉武帝規定,三夫人位視三公,九嬪位視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9](卷41《后妃傳》,P1269)。“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后宮……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9](卷31《武元楊皇后傳》,P953)西晉官員服三年喪分兩步實施,也是按照秩石規定的。第一階段是“泰始元年(265),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10](卷15《禮志二》,P391)。第二階段是泰始三年“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9](卷3《武帝紀》,P55)。結合上一條史料可知,此處的“二千石”指二千石及其以上。后來又再次重申這一詔令。即太康七年(286)十二月,“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9](卷3《武帝紀》,P77)。由上文所述可知,此處的“大臣”指二千石及其以上的官員。這一制度始于鄭默,他的事例是有力佐證。鄭默,“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9](卷44《鄭袤傳附子默傳》,P1252)。大鴻臚的秩石為中二千石,這進一步證明此處的“大臣”指二千石及其以上的官員。“(孫)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19](卷50《孫皓滕夫人傳》注引《江表傳》,P1203)此處的“二千石”也是二千石以上的意思,這更明確地說明,秩級二千石是大臣的下限和標準。皇帝駕崩后禁止地方官員到京師奔喪,也是依據秩石規定的。咸康八年(342)六月,晉成帝駕崩,康帝即位,“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不得輒離所局而來奔赴”[9](卷7《康帝紀》,P184)。東晉國子學和西晉太學的入學條件也都依據秩石。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建立國子學,“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10](卷14《禮志一》,P365);晉武帝泰始八年,對太學生進行整頓,詔令“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10](卷14《禮志一》,P356)。如上文所述,此處的“大臣”指二千石及其以上的官員,即西晉太學是選拔二千石及其以上官員的子弟,與東晉國子學的選拔條件相一致。授予官員爵位的標準也是依據秩石的高低。太熙元年(290)五月,葬晉武帝于峻陽陵,“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9](卷4《惠帝紀》,P89)。趙王司馬倫登基后,為了籠絡官員,“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9](卷59《趙王司馬倫傳》,P1602)。東晉使臣的選拔和勤王時征召官員赴臺也是依據秩石。東晉明帝時,前將軍溫嶠建議使臣的任用,“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9](卷67《溫嶠傳》,P1789);蘇峻叛軍攻陷京師,江州刺史“(溫)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9](卷67《溫嶠傳》,P1794)。東晉朝廷不可能選用官品二品的大臣充當使臣,因而上文中的“二品”指鄉品,而不是官品,這兩個事例都是以秩石為標準。持節都督刺史誅殺官員,以及政府對官員的懲治,也是依照秩石規定的。“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9](卷24《職官志》,P729)江州刺史應詹建議:“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9](卷70《應詹傳》,P1860)
晉朝大量的禮制體現在秩石的高低上。元會時百官朝拜的禮儀,按照秩石規定。“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10](卷14《禮志一》,P343-344)晉朝的輿服和印綬制度多依據秩石。“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仆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皂交路,皂帷裳”。[9](卷25《輿服志》,P762、P764)“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史,并冠一梁”[9](卷25《輿服志》,P767);“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簪珥”[9](卷25《輿服志》,P774);“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9](卷25《輿服志》,P775)。“公特進列卿代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13](卷62《禮二二》,P1740)“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千石者,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秩千石者,兩梁”。[10](卷18《禮志五》,P510、P514)這些事例說明,兩晉時官員權益和禮儀待遇的規定,大量使用秩石作為標準。
在南朝,官員的政治經濟權益和禮儀待遇等規定仍然多依據秩石。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二月“戊申,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10](卷3《武帝紀》,P56)。劉宋官員討論盜竊財物的量刑問題時,尚書右丞孔默之認為:“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10](卷42《王弘傳》,P1318)梁制:“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二千石已上非檻征者,并頌系之。”[16](卷25《刑法志》,P700)這兩條官員享有的特權,都將二千石作為下限,就是因為二千石是大臣的基本標準。蕭梁爵位的等級也參照秩石:“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16](卷26《百官志上》,P728)九卿的秩級為中二千石。南朝的冠服、車制、印綬等規定基本依據秩石。元嘉二十年(443),宋文帝將親耕籍田,規定“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10](卷14《禮志一》,P354)。南朝大臣夫人的服飾與晉朝類似,也是按照秩級規定的[13](卷62《禮二二》,P1737、P1740、P1741),此處不贅。宋制:“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13](卷65《禮二五》,P1829)這明確說明,直到南朝輿服制度基本沿襲漢朝的制度,基本依據秩石為標準。梁制:“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石,依卿尹佩劍。”[13](卷63《禮二三》,P1761)陳制:“諸縣署令秩千石者,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16](卷11《禮志六》,P224)陳朝的建康令為七品,五千戶已上縣令、相為八品,但二者都是千石[16](卷26《百官志上》,P745)。也就是說,它們的官品雖然不同,但秩石相同,因而冠服與印綬相一致。沈約在宋官品制的末尾注明:“凡新置不見此諸條者,隨秩位所視,蓋[晉江]右所定也。”[10](卷40《百官志下》,P1265)劉宋沿用西晉的制度,新設置的官職,其官位高低取決于它們的秩石。
魏晉南朝時的秩石與兩漢一樣仍舊屬于官階,除上文所述的大量證據外,還有以下四個證據:其一,魏晉南朝官員的俸祿“決定于其所任官職的秩石級別的高低”[20](P72)。其二,魏晉南朝官員的印綬也取決于所任官職的秩石[21]。其三,由于官職的俸祿和印綬取決于秩石,當時人有時以秩石來標志官位的高低。東晉末年,從事中郎謝瞻對相國劉裕說:“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10](卷56《謝瞻傳》,P1558)這是以秩石來標示官位高低的顯著事例。左司馬徐羨之對太尉劉裕說:“吾位至二品,官為二千石,志愿久充。”[10](卷43《徐羨之傳》,P1329)張森楷《校勘記》云:“案羨之時以鷹揚將軍、瑯邪內史,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轉太尉左司馬。據《百官志》,無一官在二品者,而鷹揚之號及內史并第五品,疑二品是五品之誤。”[10](卷43《校勘記一》,P1345)張森楷的這一推測雖然言之有據,但卻難以成立,因為此處的“二品”是指鄉品而不是官品,因此“二品”并不誤。與謝瞻類似,徐羨之不是以官品而是以秩石來衡量官位高低的,其原因就在于秩石在當時仍為官階。其四,皇帝的詔令通常稱秩石的等級為“等”,有時則稱之為“階”。東晉的諸葛恢,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9](卷77《諸葛恢傳》,P2042)此處的“位班”顯然指后文的“秩中二千石”。西晉武帝太康十年四月,太廟建成,遷神主于新廟,“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等”[9](卷3《武帝紀》,P79)。太廟建成是國家大事,為了慶祝這一事件,晉武帝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的官職保持不變,其官品一仍其舊,此處的“位”只能解釋為秩石,即文武百官的俸祿上調一個等級,作廟者則上調兩個等級。朝廷因為國家大慶普遍性的賜位是短期的,其時效是一個月還是幾個月,由于史料的缺失,我們還不清楚,估計僅限于當年。諸葛恢之類的個別官員所增之位則是長期的,這是二者的區別。因為喜慶或為了籠絡人心,皇帝經常通過上調俸祿的手段來賞賜官員。建武元年(494)十月,蕭鸞登基稱帝,“宿衛身普轉一階,其余文武,賜位二等”[11](卷6《明帝紀》,P85)。蕭鸞奪取海陵王蕭昭文的皇位后,首先要籠絡禁衛武官,因此他們的官職晉升一階,其余文武官員的官職保持不變,僅俸祿增加兩個等級。二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禁衛武官的“轉一階”優于其他官員的“賜位二等”,因為前者是長期性的,后者是暫時性的。
魏晉南朝沿用的漢代時的秩石,仍然屬于官階,因而官員的俸祿和印綬基本依據秩石,政治、經濟和禮制等待遇規定也多依據秩石,并且秩石有時也被稱為“等”或“階”。秩石是傳統的官階,官班是新生的官階。秩石雖然與官班并用,但其重要性亞于官班,因為不僅官職的遷轉依據官班,而且有時秩石并不能體現官職的權力大小。例如,九卿的祿秩雖然高居中二千石,但正如桓溫所說:“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22](卷203《職官一·總敘官》引《桓溫集》,P979下欄)又如,“西晉尚書臺已經基本上形成宰相機構,尚書臺長官已基本上相對于漢代三公,是國家宰相”[23](P167)。但尚書令,“自魏至晉、宋、齊,秩皆千石”[24](卷1《尚書都省》,P6)。這遠低于基本形同虛設的九卿。因此,只有在漢代,秩石才真實反映出官職的高低貴賤。由于社會變遷,在魏晉南朝官職的高低貴賤更充分體現在官班的高低上。
三、官 品
由于社會的發展變化,一項政治制度的性質時常會發生變遷。眾所周知,漢代的中樞機構尚書臺,由曹魏開始逐步變成了執行機關,中書省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決策機構;漢武帝時建立的州為監察區、刺史為監察官,到東漢末期,州演變為地方行政區,刺史演變為地方行政長官。與之類似,官品的性質也有一個從官才到官階的演變過程[25](P257-306)。由于官品制將官職分為九個等級,較之東漢秩石的十七個等級要簡明得多,因此從西晉開始,政府規定官員的政治經濟權益和禮儀待遇時使用了官品作為標準,官品開始向官階演變。
兩晉時官員權益和禮儀待遇有些是按照官品高低來規定的。其一,經濟權益。人們最熟知的是西晉官員占田、蔭族、蔭客的數量多少與官品高低直接相關。“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族。宗室、國賓、先賢之后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26](卷495《邦計部·田制》,P5922下欄)東晉也有按照官品高低蔭佃客和衣食客的制度,其數量較之西晉大幅度增加。“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命中武賁武騎,一人。”[16](卷24《食貨志》,P674)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權益并不僅限于在職官員。“宗室、國賓、先賢之后及士人子孫亦如之”,這明確說明沒有官職的士人也享有這些權益。也就是說,在九品官人法體制下,只要是士人,就可以按照門第的高低享有這些權益,并不僅限于官品。其二,政治權益。西晉國子生的入學條件是按照官品規定的。“元康三年(293)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11](卷9《禮志上》,P145)為皇后送葬的挽郎,按照官員的官品選拔。晉成帝咸康七年,杜皇后崩,“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10](卷15《禮志二》,P406)。釋奠禮后皇帝所會見的官員也按照官品劃定。晉孝武帝“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10](卷14《禮志一》,P367)。中央官員推薦郡太守的權力按照官品劃定。主簿孔寧子建議太尉劉裕,“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敘用”[10](卷63《王華傳附孔寧子傳》,P1677)。這次推薦郡太守的資格,地方官是刺史和太守,即五品以上,京官的要求則高于地方官,是四品以上,因為選拔的是太守,在職的刺史和太守更有發言權。其三,禮儀待遇。個別服制的規定依據官品。《晉令》:“六品[已]下,得服金釵以蔽髻”[22](卷718《服用部二·釵》,P3181下欄);“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采綺”[22](卷816《服用部三·綺》,P3628上欄);“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綃”[22](卷816《服用部三·綃》,P3630下欄)。“第六品已[下]不得服今縝綾錦,有私織者,錄付尚方。”[7](卷85《布帛部·綾》,P1460)“第七品以下始服金釵,第三品以上蔽結爵釵。”[27](卷136《服飾部五·釵》)車制有時也按照官品規定。《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道幰,朱里,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道幰,朱里。五品以上青道幰,碧里。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22](卷773《車部二》引《儀制令》,P3428下欄)“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后戶,仆射但有后戶無耳,并皂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后戶,漆轂輪。”[9](卷25《輿服志》,P763)
南朝的個別制度也是按照官品規定的,但數量較少,主要是治書侍御史彈劾官員的范圍、占山法、個別服制、三公轜車的規格等事例。宋制:“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上。”[10](卷40《百官志下》,P1251)尚書左丞羊希建議:“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10](卷54《羊玄保傳附兄子希傳》,P1537)被宋孝武帝接受。劉宋時期,“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以上、蔽結……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綾、錦、錦繡、七緣綺……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羅、紈、綺、榖,雜色真文”[10](卷18《禮志五》,P518)。“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褚)淵始也。”[11](卷23《褚淵傳》,P431)南朝較之兩晉,官品的使用數量大幅度減少。
學者通常根據上文所述西晉時按照官品占田、蔭族、蔭客以及國子生入學條件等事例,斷定魏晉南朝的官品為官階。這一觀點雖然有不少事實根據,但仍然難以成立。因為其一,官員的權益和禮儀待遇等規定,在曹魏使用的全部是秩石,沒有一例是官品[18];雖然從西晉開始使用了官品,但在兩晉南朝秩石的使用范圍和數量都遠遠多于官品。其二,在官品制中,同一部門的官長與其下屬處于同一官品,“如魏晉和南朝宋齊時期,尚書省的官長尚書令及其屬下尚書仆射、列曹尚書,在官品制下同列為官品三品,廷尉正、廷尉監、廷尉評同列為第六品”[17](P172)。其三,官階最核心的實質體現為官職晉升的次序,魏晉南朝時官員遷轉官職依據的是官班而不是官品。其四,魏晉南朝 “某一位官員的俸祿并不決定于其官品高低,而是決定于其所任官職秩石級別的高低”[20](P72)。其五,“最能表明官職高低與權力大小的是其所掌的印綬”,而“兩晉宋齊時期,印綬是與秩級相聯系的,而與官品則沒有關系”。[21]其六,官品有時并不能真實反映官職的高低貴賤,例如,在魏晉宋的官品制中,尚書令、尚書仆射、尚書、中書監令都為三品,但在官班制中,尚書令十六班,尚書仆射和中書監十五班,吏部尚書十四班,中書令和列曹尚書十三班,等級分明。因而官班制才最準確地體現官職的高低貴賤。其七,如前文所述,西晉吏部尚書劉頌制定的“九班之制”是一項官階制度,它和九品官制同樣是九個等級,如果九品官制也是官階制度,那么劉頌再制定“九班之制”就匪夷所思了,這就反證九品官制不是官階制。作為官階的官班和秩石,分別用于官職的遷轉、俸祿和印綬,而官品則沒有一項獨立的功能。因而當時官品的性質如同陳長琦所說,屬于官才而不是官階[17](P170)。兩晉南朝時政府的規定有時以官品作為標準,只是說明官品具有官階的某些色彩,或者說僅是萌芽階段的官階。
四、結語:魏晉南朝官班、秩石與官品的關系
在魏晉南朝的職官管理制度中,之所以同時存在官班、秩石與官品這三個體系,是因為三者的淵源不同、功能各異。秩石是由兩漢沿襲而來的傳統官階,因而承襲漢代的舊制,官員的俸祿和印綬與秩石相一致,官員的輿服等禮儀制度也多依據秩石。魏晉以來,門閥士族崛起,他們為了彰顯自己血統的高貴,不僅渴望頻繁遷轉官職,并對處于同一等級的官職,根據其俸祿的多寡和職務的閑劇區分優劣,因而“百官等級遂多”。官班制就是適應這一需求而產生的新官階,因而官員遷轉官職依據官班。魏晉南朝的官階制的確是雙軌制,但不是官品與秩石,而是官班與秩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一是秩石作為傳統的官階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很難遽然退出政治舞臺;二是官班長期以具體選例的形式存在,一直到蕭梁才形成簡明、系統的制度。官品制則是與九品官人法密切配合的制度,其制度構建的理念是:“某種官職如標明官品二品,就表示這種官職需要資品二品的人來擔任”;“某人如獲得資品二品,就表示有了作二品官的資格”。[17](P175)即官員的俸祿多少和印綬的高低取決于秩石的多寡,官員遷轉官職要遵循官班序列,官品則是官職所要求的官才,官員擔任某一官職的資格除自身資歷外還受制于擁有的鄉品等級。三者各司其職,相互配合。
在魏晉南朝的職官管理制度中,作為官階的官班與秩石并用的雙軌體制,以及官品制體現出來的某些官階色彩,體現了當時制度發展過渡性的時代特征。這種過渡性還體現在官品與秩石的配合使用上。晉制:“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綿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9](卷24《職官志》,P729)梁制:“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16](卷10《禮儀志五》,P193)“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于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秩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于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于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于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13](卷48《禮八》,P1341)賀循基本上以秩石來區分官職的高低,也使用了官品,并且上士和中士同時使用了官品和秩石,這是由于秩石的多寡與官品的高低不一致,為了準確起見,二者需要配合使用。
在魏晉南朝的職官管理制度中,秩石、官品與官班同時并用的狀況,是門閥士族社會的特殊產物,體現了政治制度的過渡性特征。但官班、秩石與官品并不一致,因而三者有時又相互沖突和矛盾。例如,陳朝的中書令、侍中、吏部尚書、御史中丞都是中二千石,都為三品,但它們的官班則分別是中書令十三班、侍中十二班、吏部尚書十四班、御史中丞十一班。又如,尚書左右丞為六百石,司徒左右長史為千石,都是四品,但尚書左丞為九班,尚書右丞為八班,司徒左長史為十二班,司徒右長史為十班。三者之間的相互抵牾,決定了三者合一的發展趨勢和最終結局。在北魏,官品正從十八級基本吸取了魏晉南朝官班的成分,與梁陳的十八班官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官班制被拋棄;秩石不再作為官階使用,官員遷轉官職基本依據官品,官員的俸祿多寡則完全與官品高低相一致,官品成為唯一的官階。北魏結束了魏晉南朝官階制的過渡性特征。
[1]閻步克.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黃惠賢.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四卷(魏晉南北朝)[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3]楊恩玉.官班制的性質、編制標準與作用考論[J].史學月刊,2012,(10).
[4]楊恩玉.蕭梁政治制度考論稿[M].北京:中華書局,2014.
[5]白鋼.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總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6](宋)章樵.古文苑[A].叢書集成初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唐)歐陽詢.藝文類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清)阮籍.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4.
[9](唐)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0](南朝梁)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1](南朝梁)(宋)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12](宋)李昉.文苑英華[M].北京:中華書局,1966.
[13](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4](唐)姚思廉.陳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15](唐)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6](唐)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7]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18]楊恩玉.曹魏官品制性質辨析[J].歷史教學(高校版),2017,(9).
[19](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0]黃惠賢,陳鋒.中國俸祿制度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21]張小穩.魏晉南朝時期的秩級[J].史學月刊,2004,(5).
[22](宋)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0.
[23]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4](唐)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
[25]陳長琦.官品的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26](宋)王欽若.冊府元龜[M].北京:中華書局,1960.
[27](唐)虞世南.北堂書鈔[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