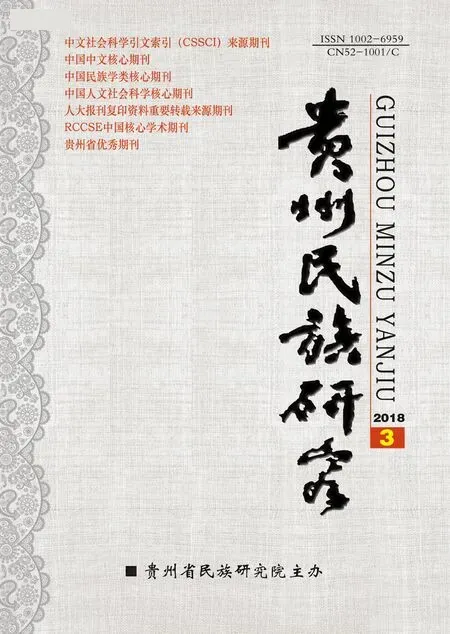商業模式下民族鄉村旅游的原生態文化濃縮
王 野 顏幫全
(三峽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4100)
一、商業模式沖擊下民族鄉村旅游的文化載體
(一)民族村寨古樸的傳統
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作為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兩駕馬車,支撐著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基本格局。傳統建筑作為內涵最為豐富的人文景觀始終是民族文化的綜合體。一方面民族建筑外在設計表露著民族審美文化,比如,南龍古寨旅游區布依族門樓的幾何設計和依山傍水的宜居,反映著布依族獨特的審美文化。另一方面,民族傳統建筑在旅游開發中逐漸成為特定民族符號,成為民族文化的名片。比如,以旅游著稱的楓香坡侗族風情寨中侗族特色建筑——風雨橋極為醒目。另外,少數民族傳統建筑除外在的設計外本身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比如,在增城畬族風情村標志建筑中都有《盤瓠王歌》等反映本民族圖騰文化的符號表達。總之,隨著商業模式的沖擊下民族原生態文化的變異,以民族建筑為代表的靜態文化成為傳遞民族原生態文化的鏡子。
(二)神秘多元的民族飲食體驗
飲食作為民族地區鄉村體驗式旅游的樞紐,承載著民族原生態文化的獨特因子。一方面飲食折射了民族群體社會生活的基本形態,以民族飲食為體驗式旅游開發切入點是民族鄉村旅游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飲食背后的習俗文化蘊意是民族旅游同文化銜接的催化劑。就民族文化的承載而言,一是飲食體驗直截了當地反映了飲食文化。比如,積石山東鄉族農家樂以東鄉油炸食品為主,在肉類飲食中以各式各樣的烹羊為主,崇尚平秋飲食文化(類似于AA制消費)。二是飲食體驗背后的忌諱、圖騰等多元民族文化的隱性承載。飲食文化中崇尚與忌諱是并行的,比如,東鄉族群眾秉承伊斯蘭教宗教文化,禁止吃豬肉和飲酒等,并在村寨風情旅游區均有提示。三是飲食體驗中餐桌習俗是對民族文化價值取向的體現,比如,鄂溫克自治旗鄉村旅游以全家體驗餐桌禮儀,早期鄂溫克族群眾主張“魚頭敬老”,即魚頭要給飯桌中長者以視孝心,體現著孝道文化。此外,飲食體驗中還間接體現著民族樸素生態文化等。
(三)傳統民族工藝的文化代言
民族工藝是民族旅游的專屬名片,民族工藝是民族原生態文化的活化石。首先,民族工藝是民族鄉村旅游總括,民族工藝對本民族地域文化進行定位。比如,肅南裕固族馬蹄寺旅游區以裕固族腰刀等為主的工藝設計,異曲同工地彰顯著游牧文化、藏傳佛教文化等,特別是石雕、轉經輪等大型直觀工藝更是將民族工藝的文化載體功能體現得淋漓盡致。其次,在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經濟效益的誘導下傳統民族工藝刻意承載著典型民族文化。比如,海南黎苗椰田古寨旅游區以銀器制作為主的工藝,除外在的商業文化和工匠文化外,祈福文化、審美文化等特色黎苗文化的蘊藏才是銀器工藝文化承載的本意。再者,民族工藝作為民族旅游的延續,對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宣傳也是旅游活動對民族文化的一種特定承載,乃至民族文化的社會認同[1]。
(四)極具民族元素的商業包裝
民族地區旅游產業借助民族元素進行自我包裝從而提高品牌效應,旅游產業對民族元素的包裝更多的是對民族文化符號的藝術設計與裝潢。比如,在張川回族風情園以伊斯蘭宗教文化為主的商品包裝五花八門,以清真寺元素符號為主的食品包裝、以清真文化為主的餐飲文化等。旅游行業開發對民族元素的商業包裝成為時代文化的同時也自始至終承載著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
二、基于民族鄉村體驗式旅游的文化特定表達
(一)極具指導價值的生態文化折射
民族鄉村旅游本身是邊疆自然奇景同浩瀚人文景觀的文化結合。特別是少數民族群眾依山傍水的傳統生活模式對大自然的依賴使得少數民族群眾對大自然有著獨特的情懷,主張敬畏自然的生態文化是諸多少數民族共同的信仰。比如,瑤族群眾在村寨旅游中以忌諱習俗禁止游客在河水中投擲垃圾。對于少數民族群眾身體力行的樸素生態文化對旅游開發者、游客等都具有極大的指導和教育意義。
(二)富含人文哲理的家庭文化統籌
富含人文哲理的家庭文化是民族村寨旅游最為常見的,在實際生活中喜聞樂見的文化形態。一方面民族地區家庭文化的獨特性使得開發者在旅游資源設計中平中出奇,使家庭文化貫穿整個民族鄉村旅游的始末。比如,鄂溫克族群眾的孝道文化貫穿至鄂溫克族鄉村旅游區的諸多環節,特別是在餐桌上,鄂溫克族以“魚頭敬老”的傳統習俗引導游客感悟典型民族孝道文化與餐飲文化[2]。另一方面,在海南黎苗古寨旅游區傳統家庭文化處處凸顯,特別是男耕女織的家庭文化和黎族母系式文化。此外,民族鄉村旅游中少數民族家庭文化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向集體輻射,使家庭文化同鄉約習俗相統一。比如,普米族寨子以家庭體驗為主的旅游設計旨在體現尊老愛幼、婆媳和睦等家庭文化習俗。
(三)樸素獨特的宗教祭祀文化密布
少數民族群眾普遍的宗教信仰和圖騰禁忌組成了民族群眾的信仰文化,民族地區鄉村旅游人文景觀和民族音樂舞蹈藝術的表演也基本上依托宗教祭祀文化。宗教信仰的生活化使得宗教文化依附于民族生活成為必然[3]。比如,張川回族風情園從建筑到文藝匯演基本上以伊斯蘭教文化為主;務川仡佬族村寨旅游景區能歌善舞的民族秉性和宗教信仰的精神寄托融為一體,使舞蹈藝術表演成為旅游文化的非物質表達,典型的“依飯舞”成為承載仡佬族旅游與文化銜接的引擎[4],“依飯舞”對宗教色彩的表露盡顯無遺。另外,部分民族鄉村旅游地區通過傳統節日體現祭祀文化,比如,毛南族群眾通過祭祀舞蹈“還愿舞”,俗稱肥套已演化為祈福等特定場合的特定文化表達。
此外,無獨有偶的民族地域文化凸顯的是民族鄉村體驗式旅游文化特定表達最為典型的形式之一。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是開展民族鄉村旅游、反映異域民族文化的焦點。民族地區鄉村旅游文化的承載和全新表達需要多元化的開發模式和復雜多樣的民族文化。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的聚焦包羅萬象[5],創新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的路徑是新時期深化民族鄉村旅游的工作重心。
三、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的路徑
(一)以市場為導向,注重民族文化的旅游開發
以市場為導向注重民族文化的旅游開發,是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的關鍵。在以體驗式互動型民族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是命運共同體,民族文化成為民族旅游資源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比如,西雙版納基諾族風情園在自然景觀開發的基礎上依托基諾族原始部落文化而成為著名的民族村寨旅游區[6]。以市場為導向注重民族文化的旅游開發,一是要以地方旅游市場的動態變化為導向,根據旅游市場的基本特征和民族文化本身的屬性開發民族旅游文化資源,實現民族文化資源旅游開發與文化創意的并舉。比如,臨夏東鄉族村寨旅游開發同國際美食節對接,在旅游文化資源的開發中針對散客開展平秋飲食文化主題活動,在改善旅游食宿基礎建設的同時推動了東鄉族特色飲食文化的傳播。二是要堅持市場規律,避免盲目開發造成的旅游資源重疊,特別是縣級民族自治地方同一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過度密集容易造成游客審美疲勞。三是要堅持旅游市場特定原則,注重民族旅游文化資源同自然景觀的關聯,同時注重民族鄉村旅游的基礎建設,為文化資源的開發奠定基礎[7]。比如,早期德昂族鄉村旅游只注重歷史景觀的保護與開發,忽略旅游資源的關聯,近年來隨著茶文化和熱帶自然景觀旅游改造,形成了以德昂族鄉村旅游為主的觀光旅游產業帶。
(二)以共享為目標,注重民族群眾的共同參與
以共享為目標注重民族群眾的共同參與是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的根本[8]。一方面民族地區原生態文化的呈現需要少數民族群眾的參與,特別是民族鄉村旅游滿足體驗式資源的開發都需要民族群眾參與其中。比如,海南黎苗古寨通過黎族群眾織錦等主體性參與模式創新民族鄉村發展旅游模式,以民族群眾為主導,還原民族原生態文化資源避免盲目臨摹造成體驗式旅游的本性失色。另一方面,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開發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建設相統一,少數民族群眾參與到旅游活動中,積極發揮自身特長,從而實現經濟利益的共享。比如,隴川縣雙坡山景頗生態園“天宮目瑙”文化的旅游開發,以刀舞表演為核心的文化資源的涉及必將以景頗族群眾為主體,在發展民族生態文化旅游的同時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9]。此外,就民族鄉村文化資源而言,以共享為目標注重民族群眾的共同參與是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
(三)以認同為基礎,注重民族優秀文化的弘揚
以認同為基礎注重民族優秀文化的弘揚是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的本質[10]。民族鄉村旅游中民族原生態文化資源的群體接納和認同是文化資源旅游設計與開發的前提,特別是符合時代價值觀、具有教育價值的民族原生態文化資源的旅游載體搭建與游客認同是民族鄉村旅游中傳統文化弘揚催化劑。以認同為基礎,注重民族優秀文化的弘揚。首先,要注重民族傳統文化時代洗禮。一方面要注重民族原生態文化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對接,使原生態民族文化成為主流價值觀的載體[11]。比如,哈尼族群眾在垂釣園中巧妙利用“禁止捕獵幼小魚仔”的樸素生態文化,將游樂同生態理念結合,成為整個生態示范區的亮點。另一方面,要注重民族傳統文化的革新,弘揚民族文化正能量。比如,撒拉族、土族等民族群眾在鄉村農家樂旅游開發中性別歧視等地域文化不斷滋生,在旅游開發中要堅決杜絕。其次,要注重民族原生態文化的理解與包容,使民族文化自信成為民族鄉村旅游文化資源開發的主旋律[12]。比如,早期藏族天葬文化,雖然難以理解,但是作為藏族群眾原生態文化的延續,理應在理解與包容的基礎上革新。再者,要對民族旅游文化進行必要的時代創新,避免民族傳統文化的誤導。
(四)以游客為主體,注重旅游與文化的相統一
以游客為主體注重旅游與文化的相統一是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基礎。民族原生態文化的濃縮除內部機制調整外,在旅游資源開發中游客參與到民族原生態文化的新知和感官表達是挖掘民族傳統文化精髓的有效途徑之一。民族原生態文化的旅游資源表達是以游客為視覺的文化提取[13]。因此,注重旅游同文化的相統一是民族原生態文化集萃的關鍵。以游客為主體,注重旅游與文化的相統一。一是要注重游客對民族旅游文化資源的感知與評價,通過游客感受評估民族文化資源的旅游設計,構筑旅游同文化的共同體。比如,達斡爾族等民族群眾通過游客反饋、游客投訴、游客咨詢等方式評估民族原生態旅游文化資源的設計價值[14]。二是在資源開發過程中注重民族文化的滲透,比如,東鄉族農家樂等鄉村旅游項目中處處涉及特色民族文化。三是以游客為主體注重民族傳統文化的體驗,比如,鄂西楓香坡侗寨以采摘茶為主的民族文化體驗,成為民族鄉村旅游的另類亮點。此外,以發展為動機注重民族旅游文化的整合作為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永恒主題,也是商業模式沖擊下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濃縮的有效途徑之一。
民族鄉村旅游中原生態文化的濃縮是應對商業模式沖擊下民族原生態文化失真、民族旅游實行雙向對策[15]。經濟利益驅動下民族原生態文化逐漸被時代潮流快餐文化所蠶食,以旅游路徑濃縮民族傳統文化是惠及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金鑰匙。就其價值而言,有助于豐富民族地區旅游資源發展的模式;有利于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有助于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全方位發展;有助于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習俗保護與傳承。總之,實現民族原生態文化的濃縮至少是當前民族地區深化旅游與繁榮文化最為迫切的需求。
參考文獻:
[1]余麗.關于民俗變遷的一點思考——以青海省互助縣土族為個案[J].科教文匯(下旬刊),2012,(1):66-67.
[2]韓曉梅.淺議民俗旅游對土族民間文化的影響及對策[J].中國土族,2011,(2):103-105.
[3]劉安全.旅游與民族地區社會文化變遷研究評述[J].貴州民族研究,2011,(1):89-93.
[4]梁自玉.湘西鳳凰縣民族文化變遷機制探析——以苗族為例[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2.
[5]潘順安.旅游開發引起民族文化變異的經濟學審視[J].貴州民族研究,2009,(6):33-37.
[6]費勝章.土族民俗文化與土鄉經濟發展互動機制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9,(4):56-61.
[7]倪靜.符號消費背景下旅游商品對地方文化的利用與開發——以安慶黃梅戲為例[J].榆林學院學報,2017,(1):7-9.
[8]邢啟敏.基于旅游凝視理論的少數民族地區文化保護與傳承[J].學術交流,2013,(4):115-117.
[9]吳曉山.民族文化旅游產品文化失真對消費者行為影響的實證檢驗[J].統計與決策,2012,(22):68-70.
[10]陽寧東.民族文化與旅游發展演進互動研究——以九寨溝旅游表演為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4):127-129.
[11]魏佳,付健,曹平.旅游企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以西部旅游景區為例[J].社會科學家,2012,(1):55-57.
[12]張振祥,蔣倩,龔雪.海南檳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區民俗旅游產品開發研究——基于旅游體驗[J].現代商貿工業, 2016,(14):81-82.
[13]方碩,段文軍.民族旅游文化自覺自信問題研究——以貴州六枝梭嘎長角苗文化為例[J].河北旅游職業學院學報,2014,(4):92-94.
[14]王律,杜龍.海南黎苗文化資源與保亭旅游業發展[J].新東方,2014,(6):43-46.
[15]陳心林.村落旅游的文化表述及其真實性——以鄂西楓香坡侗寨為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3,(11):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