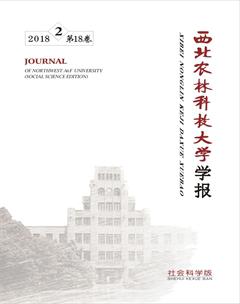當前農村不良社會風氣的態勢、成因及對策
摘 要:基于全國200多個村約4 000家農戶連續3年的調查,運用Spss統計分析,研究當前農村不良社會風氣的總體態勢,并深度剖析其形成的社會根源,在此基礎上提出系統性、針對性的對策建議。研究表明,當前農村婚喪嫁娶大操大辦、人情負債、孝道缺失、封建迷信等一系列不良社會風氣嚴重,其主要原因是國家治理取向偏失和鄉村長期缺乏內在治理要素培育,同時現代化轉型嚴重沖擊鄉村內在治理,導致農村處于“失魂”“失根”“失血”狀態。要破解當前農村不良風氣,必須加強農村文化治理,強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傳承和發展鄉村文明,激發農村內在文化動力,為鄉村社會注入新資源、新要素、新活力。
關鍵詞:轉型期;農村社會;不良風氣;文明鄉風
中圖分類號:F328;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8)02-0094-07
一、問題的提出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開展農村不良社會風氣專項治理,整治農村黃賭毒、非法宗教活動等突出問題”,“培育文明鄉風、優良家風、新鄉賢文化”。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提出“培育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適應的優良家風、文明鄉風和新鄉賢文化,提升農民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加強農村移風易俗工作,引導群眾抵制婚喪嫁娶大操大辦、人情債等陳規陋習”。連續兩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到整治社會風氣、培育文明鄉風,充分體現黨和政府對當前農村社會風氣問題的高度重視。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農村社會風氣問題進行了一定的調查和研究,不過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且側重于農村結婚彩禮、人情消費、老人贍養等單一問題的研究,缺乏全國性的大型調查和深度研究。那么,當前農村存在哪些不良風氣,造成不良風氣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又該如何培育文明鄉風,傳承鄉村文明?為回答上述問題,課題組依托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百村觀察”平臺,圍繞“鄉村不良社會風氣”這一問題,從2014年至2016年連續3年對全國31個省(區)的農村進行問卷調查。2014年暑假調查到265個村4 178家農戶的有效樣本,2015年暑假調查到267個村4 078家農戶的有效樣本,2016年暑假調查到261個村3 819家農戶的有效樣本,2016年12月調查到262個村4 245位農戶的有效樣本。依據調研數據,本文將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以期對當前農村不良社會風氣進行總體研判,并深度剖析其形成的社會根源,在此基礎上提出系統性、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二、當前農村不良社會風氣的總體態勢
(一)浪費攀比之風興盛
1.“人情漸變異,壓力猛如虎”。調查數據顯示,有人情消費的受訪農民2016年戶均人情消費為5 297.47元,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高達16.08%。在農民的日常生活開銷中,除飲食消費外,就屬人情消費最高。據調研統計,16.66%的受訪農戶每年人情支出超過1萬元,人際廣、生意大的家庭要好幾萬元,5.91%的受訪農戶人情支出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半,更有甚者要舉債隨禮。
隨著人口流動的不斷擴大,農村人情消費范圍也不斷延伸,消費媒介呈現貨幣化趨勢,消費主體的心理呈現“亞健康”狀態,農戶人情消費的負擔越來越重,人情壓力也越來越大[1]。調查中有農民戲稱:“人情不是債,頭頂鍋蓋來賣,沒錢的就是砸鍋賣鐵也得還人情”。調查數據顯示,人情往來過程中,63.52%的農戶表示“寧負債不欠情”;在沉重的人情消費負擔之下,66.63%的農戶贊同“人情猛于虎”這一說法;有51.68%的農戶坦言人情消費壓力非常大(見表1)。在農村,人們把人情看的比什么都重要,錢可欠,但人情不可欠。“你辦酒席時別人隨過禮,那別人辦酒席,你就必須等額或更高的隨禮,否則關系不好維持,而且還會被人戳脊梁骨”。頻繁高額的人情支出讓農民不堪重負。
2.結婚花費飆升,“因婚負債”現象普遍。數據顯示,農民的結婚花費持續增長,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結婚花費平均為152.85元,進入90年代農民的結婚花費飛速增至13 946.46元,突破1萬元大關。到了21世紀,農民彩禮花費增速愈加迅速,頭10年的均值為50 765.54元,2010年以來更是突破10萬元大關,達到114 013.38元。總體來看,農民的結婚花費均值呈現倍數增長的態勢,每個年代的增長率都在100%以上,尤其是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增長率更是達到了280%和264%(見表2)。
天價彩禮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戶娶不起媳婦,有些家庭因娶媳婦而致貧、返貧或債臺高筑。在4 033個有效樣本中,23.90%的受訪農戶表示“因婚負債”,戶均負債金額為22 192.89元,結婚花費給他們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壓力。彩禮一直存在于農村的現實生活中,并且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2]。在農村,“兒子娶媳婦,爹娘脫層皮”的現象普遍存在,農民直呼“娶不起”。甚至有的農民表示“過去養兒怕抽丁,如今養兒怕娶親,娶親拔了老樹根”“兒子結婚猶如過鬼門關,不死也得昏三天”。
3.“厚葬薄養”問題嚴重,“因喪負債”現象普遍存在。通過考察農村喪葬花費情況發現,農村喪葬的平均消費為18 016.99元,接近2萬元。其中,酒席消費最高,其次是棺木費用(見表3)。訪談中了解到,有的受訪家庭一次的白事花費高達75萬元,僅僅擺酒席的花費就高達10萬元。從實地調查中發現,一些地方崇尚“禮重則顯孝”,通過物質和金錢的投入,以此表達自己的孝心。湖北省江漢地區的一位老人,久病不愈,生前有4子3女,子女怕耽誤外出務工,將老人獨自留在家中活活餓死。老人去世以后,按當地最高規格請32位抬喪伕抬棺,并在當地浩浩蕩蕩的“拖街”拖街:指按當地的習俗在街上抬著棺材慢行,街兩邊的住戶放鞭炮為老人送行,去世老人的孝子或孝孫要向放鞭炮的住戶下跪磕頭,并給每家每戶發送一包香煙表示感謝,這一活動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為老人送行,耗費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以此顯示各自的孝心,這突出反映了“厚葬薄養”的問題。
在農村為了面子,厚葬老人的現象比比皆是,有些家庭甚至“打腫臉充胖子”,不惜借錢操辦,最終債臺高筑。調查的180個樣本顯示,6.54%的受訪家庭因喪負債,平均每戶負債8 779.66元。面對居高不下的“白色消費”,很多人坦言“負擔不起”,同時也有不少人感嘆“死不起”。在調查的2 753個有效樣本中,55.87%的農戶反映喪葬消費壓力較大,比重超過半數;37.41%的農戶表示壓力一般,只有6.72%的表示壓力較小。
(二)不孝之風日漸蔓延
1.老人與子女分開居住現象普遍。通過考察老年人居住情況,在4 175個有效樣本中,54.75%的老人與子女分開居住。可以看出,超過半數的老人屬于空巢老人,沒有和子女住在一起。而家庭居住情況對子女提供贍養的可能性有著顯著的影響[3]。實地調查中發現,農村中“子女住洋房,父母住破屋”的現象不在少數,一些子女嫌棄老人臟、亂、差,或是擔心照料責任人落在自己頭上,通過各種方式將老人“請出去”,此后對老人不管不顧。
2.子女不贍養、不孝順老人的問題突出。由表4可知,超過一成的受訪老人表示子女不贍養自己(占比14.51%)。接近一成的老人表示子女不孝順(占比9.01%)。當前子女不贍養、不孝順老人的問題比較突出,不孝之風在農村有所蔓延。
3.子女對老人的精神關愛缺乏。除了生活照料缺失外,子女與老人定期聯系也較少。在調查的2 277位空巢老人中,34.65%的老人反映子女會定期聯系自己,65.35%的老人表示子女只是不定期聯系自己。調查發現,當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的留守老人越來越多,仍有相當一部分的子女不定期聯系父母,這使得留守老人的精神關愛十分缺乏。
除此之外,當前子女看望父母的時間也較少。從子女看望父母的時間來看,在2 206位受訪的空巢老人中,55.89%的反映子女有空的時候才來看望,36.63%的表示“逢年過節”時子女才來看望,還有2.77%和1.22%的老人表示只有當自己“生病的時候”和“主動要求”時子女才來看望(見表5)。在農村,由于分家、年輕勞動力外出、孝文化斷裂等原因,“精神贍養”缺乏問題日趨嚴重[4],多數子女無法或者不愿定期看望父母,大都只有逢年過節才去看望老人。
(三)重男輕女之風猶存
1.農民生男孩意愿強烈。調查顯示,在生育政策只允許生一個孩子的情況下,49.12%的農戶表示希望生男孩,只有9.04%的表示希望生女孩,還有41.84%的表示生男生女無所謂(見表6)。可見,農民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較重,尤其是江西、福建、廣東等一些宗族觀念較強的地方,生男孩的意愿尤為強烈。從實地調查來看,二孩政策放開以后,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很多計劃著生二孩,希望求得一子。
2.傳宗接代觀念重。進一步考察農民偏好生男孩的原因,在1 907個有效樣本中,為了“傳宗接代”的農戶占比超過六成;17.83%的是為了養老,7.71%的是因為男孩是重要的勞動力;表示因為“繼承家業”“壯大家族”和“有面子”的比重分別為5.03%、2.94%和2.52%(見表7)。在許多農村地區,傳宗接代是農民偏好生男孩的主要原因,這種現象在華南地區的宗族村莊尤其普遍,有些沒有兒子的家庭會通過過繼的方式來實現傳宗接代的愿望。
(四)封建迷信之風抬頭
1.農民迷信觀念較重。改革開放以后,封建迷信活動在農村“死灰復燃”,而且持有迷信觀念的人不在少數。從調查數據來看,在4 027個有效樣本中,有12.79%的農民表示自己相信鬼神存在,23.89%農民表示對此半信半疑,即36.68%的農民相信鬼神存在之說,從中可以看出,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相信鬼神存在之說。
另一方面,在4 024個有效樣本中,有20.30%的農民相信“老人死后會繼續保佑自己的家人”,36.21%的農民表示對此半信半疑,兩者占比合計達到63.79%(見表8),可見,大多數農民都相信祖先保佑這一觀念。
2.農村封建迷信行為普遍。逢年過節或特殊日子,多數農民會祭拜祖先、土地神、財神爺,還有部分農民會進廟燒香、看風水等。通過分析發現,在4 078個有效樣本中,進廟燒香、看風水、占卜問卦的農戶不在少數,占比分別為41.88%、41.03%、31.68%(見表9)。由此可見,目前農村封建迷信行為普遍,有的家庭蓋房子要請陰陽先生看風水,結婚、生子、喪葬等要看黃道吉日,還有些人到廟里抽簽算運,占卜問卦等;甚至有些人通過拜土地爺、拜祖先等行為求醫治病、請神驅鬼。
表9 農民在逢年過節或特殊日子的行為選擇表中個案占比為響應數占樣本總數的比重。該題為多項選擇題,故個案占比和大于100%。
(五)黃賭毒之風日益滋長
通過借助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中國農村社會動態跟蹤系統”,對2002年至2017年網絡報道的“社會不良風氣”事件進行專題跟蹤調查。對初步數據源中的新聞事件類信息剔除重復后,共有363條“社會不良風氣”事件的信息納入農村社會動態跟蹤系統,由此形成了事件分析的數據源。
1.農村不良風氣中黃賭毒事件發生率較高。
當前農村黃賭毒現象泛濫,黃賭毒(包括黃色淫穢事件、賭博事件、涉毒事件)的發生率為46%,大操大辦(包括彩禮和人情消費事件)的發生率為25.62%,出軌、家暴、子女不孝、邪教問題、權錢問題的發生率分別為8.82%、7.99%、7.16%、3.86%、0.55%(見表10)。可見,農村黃賭毒事件在農村發生率較高。訪談中了解到,部分農村地區的村民迷戀于黃賭毒,甚至有些鄉鎮干部或黨員也染指其中。
2.東部涉黃現象嚴重,中部賭博活動較多,西部販毒事件頻發。根據“中國農村社會動態跟蹤系統”搜集的數據可知,農村中涉黃事件共有41件,其中東部地區發生28件,中部、西部地區分別發生了11件、2件,可見,東部地區發生比重最高,為68.29%(見表11)。實地調查中發現,在一些城鄉結合部的網吧、歌廳、影像廳等經常上演黃色、低俗內容;一些經濟活躍、市場開放的農村,辦理紅白喜事邀請的歌舞團為了博取大家的眼球,也會出現一些低俗、黃色的表演。
在農村不良社會風氣事件中,賭博事件共有50件,發生率為13.77%;其中,中部地區的發生率相對最高(見表11)。目前農村賭博的情況非常普遍,一些村莊不分男女老少、不論白天黑夜打牌賭博。人數越來越多,賭博金額越來越大,由過去的5毛、1元到現在的50元、100元,輸贏少則幾百,多則成千上萬。
統計數據顯示,在76起涉毒事件中,發生在西部地區的比重最高,為44.74%(見表11)。在實際生活中,廣西、貴州等邊境地區是涉毒事件的高發區域,同時在一些經濟條件較發達的地區,涉毒事件的情況也較多。有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將吸毒、販毒等惡習帶回農村,使毒品向農村滲透,甚至有的農村在紅白喜事時,農民還約在一起聚眾吸毒。
三、農村不良風氣形成的原因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當前農村浪費攀比現象普遍,子女不孝的風氣蔓延,重男輕女現象依然存在,封建迷信活動猖獗,黃賭毒之風日益滋長,這說明當前農村不良社會風氣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國家治理取向長期偏差,農村社會“失魂”
改革開放后,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對鄉村的治理也轉向了經濟發展。基層政府以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作為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在實際工作中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長期輕視或漠視農村社會風氣等文化建設工作。重物質文明建設,而輕精神文明建設,導致農村文化建設長期投入不足,文化陣地“空殼”問題嚴重。有些地方雖然對文化建設有一定的投入,但為了追求政績,往往只重視“硬件”投入,而忽視了文化建設的“軟件”投入和長期培育,尤其對鄉村內在的民風民俗、村規民約等很少涉及,從而導致農村文化建設成為“盲區”。由于文化建設的缺失,使得鄉村治理缺乏內在的文化紐帶,農村和農民普遍缺乏“精神食糧”,從而導致鄉村治理“失魂”。
(二)社會轉型沖擊鄉村文明臍帶,農村文化“失根”
城鎮化欲將傳統的鄉土社會“連根拔起”,為轉型期的農村社會注入了更多的現代因子,傳統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態被打破,農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利益格局、規則體系都發生了變化,大量人口處于“失根”“無根”的“漂浮”狀態,導致祖祖輩輩留傳下來的精神根基未能保留和傳承下去[5]。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和交換關系逐漸滲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生產、社會交往等各個方面,使得農民行為和動機對貨幣收入最大化追求更加強烈,“社會化小農”和“市場化小農”的特征越來越明顯[6]。又因國家未能及時在鄉村建立起新的價值觀念和體系,使得農民很難抵御外部負面觀點沖擊,受市場利益觀念影響越來越嚴重,從而導致“利益至上”“金錢至上”“消費主義”等觀念成為農民的行為準則,農民的日常行為日益功利化,人情往來也日趨利益化,從而導致農村人情關系的異化,引發鋪張浪費、大操大辦、天價彩禮等一系列不良風氣。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鄉村傳統文化不斷流失,傳統農村的倫理道德體系逐漸被消解,導致鄉村治理內在的柔性作用、自律性機制逐漸消失,鄉村秩序的內生基礎也逐步消解,鄉村賴以維系的文化紐帶逐漸失去作用,從而導致農村社會陷入“失根”狀態[7]。
(三)城鄉失衡擠壓鄉村內在文化,農村治理“失血”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這不僅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而且使其對鄉村文化的認同度降低,傳統的理論價值規范也日漸斷裂,農村的傳統文化隨著人口流動而“流失”和弱化[8]。對于外出農民而言,在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下,“生長在農村,生活在城里”的狀態,使其難以真正融入城市,同時由于種種原因又不愿意回到農村,這種“漂浮”狀態導致農民精神和價值觀念上的游離,農民返鄉后多參加賭博、六合彩、迷信等活動來消磨空閑時間,以此引發一系列不良風氣。另一方面,青壯年的外流,使得農村發展的中堅力量削弱,“386199”成為農村主要人口,使得文化活動和文化建設難以持久開展。同時,鄉村中年長者在鄉村文化秩序的權威不斷弱化,在家庭中的角色不斷邊緣化,難以有效規范村民的行為或習慣,這使得鄉村內在禮俗難以發揮作用。留守老人問題日益突出,也是因為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弱化,引發了農村的不孝之風。總體而言,在城鄉失衡背景下,鄉村傳統文化逐步消退,現代文化又尚未發展起來,使得農村文化生活貧乏,而沒有文化的浸潤,農村的治理處于“失根”“失血”的狀態。
四、破除農村不良社會風氣的對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培育文明道德風尚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輿論導向,堅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推動形成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社會風尚。”改善農村不良風氣必須從培育和加強農村內在文化基礎的角度出發,將國家治理的取向由“政權治理”“物質治理”轉向“以文治理”,通過強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傳承和發展鄉村文明,激發農村內在文化動力,以此為鄉村社會注入新資源、新要素、新活力,從而為鄉村社會“塑根”,通過文化的治理培育良好的公共秩序和道德規范,讓文明積極的風氣內化于每個農民心中。
(一)深化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提升文化服務
農村公共文化的建設是促進“以文治理”的基礎和前提。針對當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發展滯后的問題,需要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推進農村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為農民提供優質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不斷豐富農民文化生活。(1)以政府為主導,公共財政為支撐,強化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的職責,推進文化服務向基層傾斜。(2)引入市場機制,激發社會力量參與,推進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的工作,創新文化供給方式,提高文化服務的水平和供給效率。(3)供給過程中,避免“運動式、大水漫灌式”的供給方法,以民生問題為切入點,以農民滿意為文化服務的出發點,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針對不同農民群體的實際需求,將文化服務的供給方式、供給內容與農民日常生活相結合,實現服務的有效供給,不斷提升農村公共文化水平[9]。(4)深入推進“精準宣傳”,創新宣傳方式,豐富宣傳內容,融入地方文化,拉近公共文化與農民之間的距離,擴大宣傳效果,讓公共文化深入人心。
(二)深入推進移風易俗,樹立文明新風
移風易俗是“十三五”期間深化鄉村文明行動的核心內容,是新時期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破除農村社會的不良風氣和陳規陋習,需要深化開展移風易俗活動,促進移風易俗真正“進村入戶”,讓文明鄉風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可以鼓勵和支持農村基層成立紅白喜事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禁毒禁賭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為移風易俗搭建服務平臺;民主選舉理事會成員,勸導和監督農民節儉辦事。同時,充分利用村莊內閑置房屋、場地、器具等為農民節儉辦理紅白喜事提供方便。另一方面,開展新風討論活動,征求群眾意見和建議,制定移風易俗和文明新風的細則,將移風易俗納入村規民約和村民自治章程,通過制度化的規范來約束農民行為。同時,建立長效的獎懲機制,推進新規新風“進村落戶”。對于嚴格遵守文明新風規定的農戶,適當的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獎勵;對于大操大辦、鋪張浪費違反規定的村民酌情通報批評。
(三)傳承和弘揚鄉村文明,夯實文化根基
深入推進“文化治理”,需要充分挖掘和傳承農村優秀文化,注重主流文化、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創新。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文化整合功能,加強傳統文化場所如祠堂、茶樓、集市等的保護與利用,依托傳統文化資源建設農村文化禮堂,打造村莊文化“地標”,充分利用當地優良鄉風教化資源,組織民俗文化活動,塑造村民人文精神。并結合農村實際情況,積極培育“新鄉賢”,對于鄉村中社會威望高、品德好、能力強的人進行重點培養和發展,強化對鄉賢能人公共文化、法律知識等多方面的培訓,充分挖掘鄉賢傳統文化,吸引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發揮“新鄉賢”引領示范作用,以此優化鄉村治理資源,增強農村基層文化的自我發展能力。同時,村干部、鄉賢能人可以鼓勵和引導村民在村內組織開展優良家風、家訓、家規的宣傳活動,將優良家風融入到農民日常生活和青少年教育中,促使大家形成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時代新風尚融入鄉土文化,利用各具特色的鄉土傳統文化,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
(四)銜接村民自治,激發文化治理內動力
要促進公共文化和文明價值觀在鄉村發揮作用,需要與村民自治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激發農民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以此提升鄉村的內在治理能力。在文化服務和文化活動供給的過程中,積極探索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單元,根據農民的居住習慣、生活習慣等,依托自然村、村民小組等內生性單元,開展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活動。將農村文化服務與農民民主實踐結合起來,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引導和鼓勵地方探索多樣化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結合地方實際情況探索自治組織和活動,充分利用和挖掘村莊內在資源,發動農民參與文化服務和文化活動。同時,在公共文化建設過程中,賦予農民文化需求的表達權、決策權和監督評價權,不斷完善村民的參與機制,通過扶持和引導農民成立文化組織,以組織化促進農民參與。優化以村務公開、民主評議、民主理財為主要手段的民主監督制度,促進農村公共文化有效實施。
本文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委托的《農村社會建設和鄉村治理》研究課題的成果之一,報告原題為《當前農村社會不良社會風氣的態勢、成因及對策建議》。此報告由中國農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鄧大才教授主持,筆者執筆。在文章的寫作過程中,鄧大才教授給予有益指導,在此致以謝意。
參考文獻:
[1] 陳浩天.城鄉人口流動背景下農村地區人情消費的行為邏輯——基于河南省10個村334個農戶的實證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1(7):117-121.
[2] 納玉蘭.河湟農村高額“彩禮”探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5,26(1):67-70.
[3] 鄢盛明,陳皆明,楊善華.居住安排對子女贍養行為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01(1):130-208.
[4] 穆光宗.老齡人口的精神贍養問題[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4):124-129.
[5] 徐勇.“根”與“飄”:城鄉中國的失衡與均衡[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69(4):5-8.
[6] 鄧大才.農戶的市場約束與行為邏輯——社會化小農視角的考察[J].中州學刊,2012(2):45-50.
[7] 侯江華,魏淑娟.現代化進程中村莊傳統的流失——以上能村為個案[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7(3):119-122.
[8] 雷洪,趙曉歌.“城歸”現象:主體特征、形成機理與生成邏輯[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4(4):58-62.
[9] 陳浩天.民生服務:基層善治與鄉村資源整合的政治邏輯[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3):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