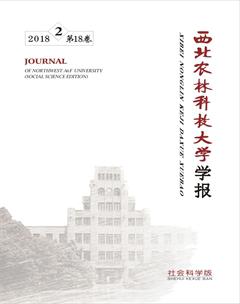經驗資本及林地規模對林農信貸的影響
摘 要:林農信貸可獲程度低下已成為制約南方集體林區林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基于福建林農調研數據,運用Double-Hurdle模型全面考察了經驗資本及林地規模對林農信貸獲得概率及獲得規模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林農獲得貸款難度仍然較大,樣本農戶中獲得林業貸款的僅為29%;經驗資本中,經商經歷可以顯著提高林農信貸獲得概率,而林業經歷和貸款經歷能夠顯著提高林農貸款獲得額度;林地規模不僅提高了林農貸款獲得概率,還提高了林農貸款獲得額度。因此,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深化階段,要積極引導林農合作經營,鼓勵農戶聯保貸款,加大金融機構支持力度,以提高林農信貸可獲性。
關鍵詞:經驗資本;林地規模;林農信貸;集體林改
中圖分類號:F326.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8)02-0131-08
引 言
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后續配套改革也在不斷推進。林業信貸作為配套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林業和林區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關于做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與林業發展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要積極開辦林業貸款業務,增加林業貸款覆蓋面。然而,目前我國林業信貸市場很不完善,農戶面臨著嚴重的信貸約束[1],絕大多數林農無法獲得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即使能申請到貸款,額度也十分有限[2-3],這導致林業經營無法得到長期資金支持,資金匱乏成為抑制農戶從事林業生產的主要瓶頸[4]。已有研究表明,貸款中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會造成信貸配給的發生[5],導致有信貸需求的農戶獲得貸款難度很大。經驗資本和土地規模可以通過信號傳遞對信貸可獲性產生影響。林業信貸中,經驗資本與林地規模會怎樣影響林農信貸可獲性?其對貸款獲得概率和獲得額度的影響有何不同?回答這些問題對于緩解林業資金約束、促進林業發展和提高林農收入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文獻對林農信貸的研究較多側重于林權抵押貸款。有研究表明,除了受農戶家庭特征、社會環境及貸款特征等因素的影響之外,林農林權抵押貸款參與意愿和需求還受到林地規模和林農外出打工經歷的顯著影響[1,6]。隨著林業貸款政策的實施,有學者發現林地面積越大,林農參與林權抵押貸款的可能性越高[7];由于小面積的林地抵押會增加貸款違約風險,因而金融機構傾向于林地面積大和資產雄厚的大客戶[8],這樣擁有較大規模林地的林農更有可能獲得林權抵押貸款[4]。
此外,梳理農戶農業貸款可獲性的文獻也可以發現,農業從業經驗和貸款經歷會顯著影響農戶參與信貸市場[9-10],而土地規模和土地評估價值被認為是影響農戶信貸可得性的重要因素[11-12],黃惠春的研究也表明,農戶經營規模對金融機構發放擔保貸款有顯著影響,而機構發放農地抵押貸款時主要考慮耕地面積較大且擁有貸款經驗的農戶[13]。
以上研究從不同視角分析了經驗資本、林地規模與農戶林業信貸的關系,但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文獻大多集中于分析林農林權抵押貸款需求、意愿和行為,較少分析林農信貸可獲性。二是現有研究較多地分析了土地規模對林農貸款可獲性的作用,但對經驗資本如何影響信貸可獲性涉及不多且不夠全面。三是既有文獻主要采用二元選擇模型分析林農貸款獲得情況,而對林農獲得具體貸款額度差異有待進一步探討。鑒于此,本文以集體林權改革試點地區福建省為例,基于林農調研數據,分步討論經驗資本及林地規模對林農信貸獲得概率與獲得額度的影響,進而反映集體林改背景下林業信貸政策實施效果及其需要完善的著力點。
一、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一)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目前林業信貸政策實施仍處于初級階段,現實中很多林農沒有獲得林業貸款,其貸款金額為0,出現受限因變量的問題,而運用Tobit模型分析會讓因變量所受到的制約影響其后續取值,使得其選擇和取值都由相同的參數決定,容易產生樣本選擇性偏差。鑒于此,Cragg放松了Tobit模型的假設條件,提出Double-Hurdle模型,將個體行為分為兩個不同決策階段,指出兩階段分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即決策選擇階段和數量選擇階段可以有不同的估計系數[14],其實質是一個Probit模型和一個斷尾回歸(Truncated)模型的組合,適合用于處理兩階段特征的數據。
林農貸款可獲性實際上是兩個階段的有機結合:第一階段是概率模型,即林農是否獲得正規金融機構林業貸款;第二階段是金額模型,即林農獲得貸款的額度。因而選用Double-Hurdle模型進行估計,第一部分構建Probit模型來處理林農是否獲得貸款的“0~1”值選擇型數據;如果林農獲得貸款,完成數據截斷工作,則第二部分用斷尾回歸模型來分析影響貸款額度的因素。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是經驗資本和林地規模,還選取了影響林農信貸可獲性的控制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戶主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是否有林權證、家庭人均收入、社會關系、貸款認知、貸款機構辦理業務積極性以及到鄉鎮距離9個變量。其中,社會關系分別測度了農戶和朋友、鄰居、同村村民、村領導、政府、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及林業部門7類人員和機構的關系情況,用LIKERT五分法表示,并通過因子分析計算得到社會關系總因子變量得分。此外,林農貸款可獲性受一些無法觀測的區域特征影響,需引入地區虛擬變量。
(二)研究假設
1. 經驗資本。經驗資本來源于人力資本理論,指的是人力資本中人的經歷和工作經驗,屬于人力資本的一部分。Schultz認為,人力資本主要體現為人的知識、技能、經歷及工作熟練程度[15],Mincer也在《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人力資本差異包括工作經驗的積累[16],本文選用林農經商經歷、林業經歷以及貸款經歷作為經驗資本的衡量指標。
經商經歷是林農所擁有的較為普遍的經驗資本。一方面,有經商經歷的林農見識更廣、思想更先進[1],具有較強的資金運轉能力,意味著其還款能力也較強[17];另一方面,經商林農具有廣泛的人脈網絡,在需要私人擔保的情況下,他們能夠提供可靠的擔保人,而且人脈網絡能實施社會制裁,使違約者受聲譽損失,降低違約的可能性[18],有利于增加林農貸款可獲性。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1-1:
H1-1:經商經歷可以提高林農貸款獲得概率,且有利于增加貸款額度。
林業經歷屬于林區農戶特有的經驗資本,是指林農從事護林員、林場場主、木材經紀人等林業相關職業的經歷。具備這種經驗資本的林農比較了解林業政策及林木市場狀況,有助于及時掌握政策走向;此外,有林業經歷的農戶比普通林農具有更強的林業經營能力,易取得金融機構的信賴和支持。由此,提出研究假設H1-2:
H1-2:林業經歷能夠提高林農貸款獲得概率,也有助于提升貸款額度。
貸款經歷是指林農在獲得林業貸款之前是否獲得過正規貸款。一方面,成功的貸款經歷會在金融機構留下信用記錄[19],該記錄可以較大程度的減少林農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機構將以往的信用記錄作為是否放貸的重要條件[13];另一方面,經歷過正規貸款的林農在再次貸款時可以相應減少金融機構的交易成本。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設H1-3:
H1-3:貸款經歷不僅可以增加林農貸款獲得概率,且能夠提高貸款額度。
2. 林地規模。林地規模是林農生產經營的資本和載體,而林地面積反映林農的林業生產經營規模[6]。大規模的林地面積不僅具有較高的土地評估值[20],還能與金融機構博弈,使機構偏向于規模林農,林農所經營的大規模林地可通過降低金融機構信貸風險來增強其放貸積極性[12,21]。林地規模是影響金融機構決策的重要因素[11,22]。由此,提出假設H2:
H2:林地規模越大,林農獲得貸款概率越大,獲得貸款金額越高。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性分析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自于課題組2016年8月對福建三明、南平和龍巖的實地調查。福建全省森林覆蓋率居全國第一,是典型的南方重點集體林區。2003年,福建被選為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省。三明、南平和龍巖地區由于森林覆蓋率較高(分別為76.8%、74.75%、77.9%)成為了重點林改地區。本文調查抽樣按照隨機分層原則,在每個地區抽取2~3個縣,如三明(沙縣、尤溪、永安)、南平(建甌、順昌)以及龍巖(漳平、永定);然后,依據各縣林業生產與經濟發展情況,在每個縣選取3個鄉鎮,每個鄉鎮選取2~4個行政村,在村莊內進行隨機抽樣。調查收集了樣本林農在新一輪集體林權改革后(2003-2015年)的林業貸款獲得情況及相關信息。由于林農的信貸需求是獲得貸款的前提條件,因而本文主要分析有貸款需求林農的信貸狀況。共獲取有效樣本204個,具體的樣本分布和容量見表1。
(二)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樣本中獲得林業貸款的林農僅有29%,林業貸款平均額度為17.02萬元,這反映出,重點林改地區獲得林業貸款的林農占比較低。經驗資本方面,有經商經歷和林業經歷的林農占比不到50%,而有貸款經歷的農戶占比則接近70%,總體來看林區大多數林農有一定的經驗資本;林地規模方面,林區森林資源豐富,林農平均擁有林地面積為404.01畝;戶主的平均年齡為49.67歲,文化程度中等,戶主是(或者曾是)村干部的接近一半,有林權證的林農占65%,2015年平均家庭人均收入為6.07萬元,林農的社會關系水平整體較高,且林農對林業貸款認知程度也比較高,而貸款機構辦理業務也是偏向積極的。主要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不同信貸狀況下林農特征比較分析
表3對比分析了不同信貸狀況的林農特征,并就其差異進行了獨立樣本t檢驗。可以看出,不同林業信貸狀況下的林農特征有很大差異,尤其是在經驗資本和林地規模上差異更為明顯。經驗資本中,獲得貸款的林農擁有經商經歷(72%)、林業經歷(60%)與貸款經歷(82%)的比例均大于無貸款林農(35%、33%、59%),均值差t檢驗結果表明,這三項經驗資本指標在兩類林農間的差異都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其與林農信貸狀況存在顯著關系。林地規模方面,獲得貸款林農平均林地面積為831畝,而無貸款林農平均林地面積僅為226畝,遠低于前者;兩類林農間差異也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林地規模與林農信貸狀況之間亦存在較為明顯的關系。此外,信貸不同的林農在林權證、人均收入、社會關系、貸款認知、機構辦業務積極性以及地區等變量中也表現出顯著差異。
(二)經驗資本、林地規模對農戶林業信貸可獲性影響分析
本文首先運用Stata14.0統計軟件,通過似然比檢驗(LR test)[23]對比了Tobit模型和Double-Hurdle模型,檢驗結果顯示:LRchi2(15)=224.88,P=0.000,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采用Double-Hurdle模型比Tobit模型更適合估算經驗資本及林地規模對林農信貸可獲性的影響。模型估計結果見表4。
1. 經驗資本變量。根據表4回歸結果可知,經驗資本3個指標對林農信貸獲得概率和獲得額度的影響程度有差別。首先,經商經歷在概率模型中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與預期一致,也就是說擁有經商經歷的林農更容易獲得林業貸款,原因是經商林農人脈廣,還款能力也強,可以降低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金融機構更傾向于向經商林農放貸。而金額模型中,經商經歷與貸款額度呈正相關關系,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多數經商林農自身有一定資金積累,其對林業貸款需求量不是太大,可能會選擇一些程序較為簡單的小額貸款,導致經商經歷沒有顯著影響到林農貸款獲得額度。因而,假設H1-1中“經商經歷可以提高林農貸款獲得概率”得到了驗證,而“經商經歷有利于增加貸款額度”未能得到驗證。
其次,林業經歷在概率模型中與貸款獲得概率呈正相關關系,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在于獲得林業貸款的林農只有60戶,而這些林農大多數為大戶,小戶即使擁有林業經歷也可能無法獲得林業貸款。而林業經歷在金額模型中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也就是說,林業經歷會提高林農貸款金額。擁有林業經歷的林農不僅可以獲取較為全面的林業貸款信息,而且其從業經驗也會增強林業經營能力,有利于提升這部分林農在金融機構的信用度,使其貸到的金額更大。因此,假設H1-2中“林業經歷能夠提高林農貸款獲得概率”未能得到驗證,而“林業經歷有助于提升貸款獲得額度”得到驗證。
最后,貸款經歷在概率模型中與貸款獲得概率呈正相關關系,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可能是獲得貸款的林農中大戶占比例較大,使得小戶的貸款經歷也無法顯著影響到林業貸款獲得率。而貸款經歷在金額模型中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原因在于貸過款的林農對貸款流程更加了解,而金融機構也會因林農之前留下的信用記錄而愿意為其發放金額更高的貸款。由此可見,假設H1-3中“貸款經歷有助于增加林農貸款獲得概率”未能得到驗證,而“貸款經歷可以提高林農貸款額度”得到了驗證。
2. 林地規模變量。表4回歸結果顯示,林地規模在概率模型和金額模型中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這說明,林農林地規模越大,能夠獲得林業貸款的概率越高。由表3可知,獲得貸款的林農只有60戶,僅占總樣本的29%,但其林地規模遠大于未獲得貸款的林農,這既與調查區域現實情況相符,也與很多學者研究結果相吻合[11,13,24]。此外,林地規模也會顯著提高林農獲得貸款金額,據調研了解,樣本地區林農林業貸款主要包括林業小額貸款、林業貼息貸款和林權抵押貸款,其中,林業小額貸款和貼息貸款金額較小,而林權抵押貸款金額相對較大,因為抵押面積越大,貸到金額越大。金融機構對抵押面積有要求,傾向于將額度較大的林權抵押貸款發放給大客戶。由此可知,林地規模對林農貸款獲得概率和獲得額度都具有明顯正向影響,假設H2得到了驗證。
3. 其他變量。控制變量方面,戶主文化程度對林農貸款獲得額度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戶主文化程度越低,其獲得林業貸款金額越大,這與范香梅等[25]、李韜等[26]的結論相似,其解釋是較高文化程度的林農可能會由于風險大、收益低而減少林業經營,進而會影響到林業貸款獲得額度。社會關系對林農貸款獲得概率具有正向影響,即林農社會關系水平越高,越可能得到林業貸款。貸款認知對貸款獲得概率的作用也是正向顯著的,但其對貸款獲得額度的影響是負向顯著的,原因在于:獲得貸款的林農普遍對林業小額貸款和貼息貸款比較了解,而對林權抵押貸款認知較少,但抵押貸款金額大,這就導致貸款認知對貸款獲得額度產生負向作用。金融機構業務辦理積極性也對貸款獲得概率有顯著正向作用。此外,林農信貸獲得概率與獲得額度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地區差異。
(三)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模型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隨機抽取原樣本的85%重新組成樣本量為173的新樣本,再次估計經驗資本及林地規模對林農信貸可獲性的影響效果,結果如表5所示。
表5中回歸結果與表4結果較為一致,說明本文實證分析結果比較穩健。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福建林農調研數據,實證分析了經驗資本、林地規模對林農貸款獲得概率與獲得額度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在當前集體林改環境下,面對周期長、投資大的林業生產,相當多具有信貸需求的林農并沒有得到貸款支持,林農獲得正規金融機構林業貸款的難度仍然較大;經驗資本中經商經歷會因其較強的還款能力增加了林農貸款獲得概率,而林業經歷和貸款經歷通過林業經營能力和信用記錄提高了林農信貸獲得額度;目前金融機構仍偏好于擁有較大林地規模的林農,林地規模不僅對林農貸款獲得概率有促進作用,而且會顯著提高林農貸款獲得額度。隨著林區農戶林業經營資金需求日益增加,經驗資本和林地規模作為一種內在作用機制,可以有效推動林農貸款可獲性。本文的政策啟示為:第一,積極引導林農合作經營,培育經驗資本豐富的合作帶頭人,充分發揮經驗資本作用,使其帶領合作林農進行林業貸款;第二,鼓勵林農進行聯保貸款,外延式的擴大林地規模,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惠及小農信貸需求,提高小農林業貸款可獲性,間接增加林農收入;第三,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林農生產經營的資金支持力度,實施優惠政策,放松貸款約束,在信貸風險的可控范圍之內盡量滿足林農生產的貸款需求。
參考文獻:
[1] 曾維忠, 蔡昕. 借貸需求視角下的農戶林權抵押貸款意愿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 2011(9):25-30.
[2] 安海燕,洪名勇.農戶參與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行為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4):83-90.
[3] 張莉,王禮力,嚴惠云.農戶收入滿意度視角下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需求影響因素研究——基于陜西省和甘肅省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 2017(10):123-129.
[4] Zhou L, Zhang Y Q, Dai G C, et al.Access to Microloans for Households With Forest Property Collateral in China [J].Small-scale Forestry, 2016(15):291-301.
[5]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393-410.
[6] 石道金, 許宇鵬, 高鑫. 農戶林權抵押貸款行為及影響因素分析——來自浙江麗水的樣本農戶數據[J].林業科學, 2011(8):159-167.
[7] 朱冬亮, 蔡惠花. 林權抵押政策實施中林農參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8省26縣的調查數據[J].林業經濟, 2013(10):10-16.
[8] 李莉, 黃和亮, 吳秀娟. 林權抵押貸款借貸雙方的行為分析——以福建省永安市為例[J].林業經濟問題, 2008(1):81-85.
[9] Ward L, Oladele O I.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Attitude Towards 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Northern Cape, South Africa [J].Life Science Journal, 2013, 10(1):2 997-3 001.
[10] 曹瓅, 羅劍朝. 農戶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響應及其影響因素——基于零膨脹負二項模型的微觀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 2015(12):31-48.
[11] Hussain A, Thapa G B. Smallholders’ Access to Agricultural Credit in Pakistan [J].Food Security, 2012, 4(1):73-85.
[12] 蘭慶高, 惠獻波, 于麗紅, 等. 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農村信貸員的調查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 2013(7):78-84.
[13] 黃惠春.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可得性分析——基于江蘇試點地區的經驗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 2014(3):48-57.
[14] Cragg J G. Some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 [J].Econometrica, 1971, 39(5):829-844.
[15] M Blaug.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J].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6(5):581-581.
[16] 雅各布·明塞爾. 人力資本研究[M].張鳳林, 譯.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1.
[17] Henning J I F, Jordaan H.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for Farm Credit Applications——A Delphi Study [J]. Sustainability, 2016, 77(8):1-5.
[18] 王修華, 譚開通. 社會網絡對農戶正規機構貸款可獲性的影響研究[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38(1):30-34.
[19] Diamond D W. Monitoring and Reputation: the Choice Between Bank Loans and Directly Placed Debt[J].Journal of Polital Economy, 1991, 99(4):689-721.
[20] 于麗紅, 陳晉麗, 蘭慶高. 農戶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融資需求意愿分析——基于遼寧省 385 個農戶的調查[J].農業經濟問題, 2014(3):25-31.
[21] Oboh V U, Ekpebu I D. Determinants of Formal Agricultural Credit Allocation to the Farm Sector by Arable Crop Farmers in Benue State, Nigeria [J].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1, 6(1):181-185.
[22] Khandker S.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Evide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Bangladesh [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5 (19):263-286.
[23] Greene W H. Econometric Analysis[M].7th ed. Boston: Prentice Hall, 2012:834-887.
[24] 李韜, 羅劍朝, 陳妍. 農戶正規融資獲貸筆數及影響分析——基于泊松門欄模型的微觀實證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 2014(5):42-49.
[25] 范香梅, 張曉云. 社會資本影響農戶貸款可得性的理論與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 2012(4):177-178.
[26] 李韜, 羅劍朝. 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行為響應——基于Poisson Hurdle模型的微觀經驗考察[J].管理世界, 2015(7):5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