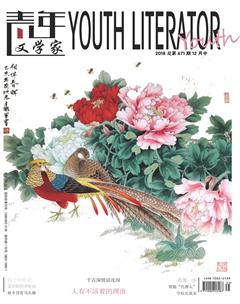試論森鷗外作品中的漢文化情懷
邱文熙
摘? 要:森鷗外(1862—1922)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與夏目漱石同被視為日本近代文學的開端,在日本學術界被喻為百門大都“梯貝斯[1]”。他從小就受到極好的漢文化教育,與漢文化有極深的淵源。下文欲從:①出世的政治理念;②含蓄內斂的人生哲理;③受唐朝影響的女性審美;④宿命論傾向四個方面探討他作品中的漢文化情懷。
關鍵詞:森鷗外;漢文化;情懷;漢詩文;女性審美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5--02
森鷗外在漢文學創作方面有極大成就——單留存下來的作品就有漢文(用中國的文言文所寫的作品)50多篇,計10余萬字;漢詩(用漢文創作的詩文)224首,共1500余行之多。由此可見,森鷗外與漢文化有極深的淵源。
一、漢文化中的出世理念在其作品中的體現
森鷗外從小就受到極好的漢文化教育,據他在《自紀材料》中記載,他6歲開始學《論語》,7歲學習《孟子》,8歲開始學習《四書五經》,深受儒家思想熏陶;10歲時讀了明初李呂棋的傳奇小說《剪燈余話》、清代陳球的長篇小說《燕山外史》、筆記小說集《情史》等中國小說,井熱衷于作漢詩、寫漢文;青年時期成為留德博士,歸國后作為軍醫隨軍征戰,期間常以漢詩抒懷,作品多收錄于《徂征日記》。
1894年10月,中日第一次在黃海交戰時,他作了《峽南早川君有詩見贈乃次韻卻寄》抒發壯志:“期我瘦骸埋異域,欽君孤劍謝騷壇。”說明作為軍人的一分子,他懷有十足的斗志和為國捐軀的信念。森鷗外還有憂國憂民的襟懷——在《次韻書感三首》[2]里,他化用杜甫《大麥行》,悲嘆道:“夫藏婦泣憶梁洋,滿目蕭條愁緒長”,表達了對日俄戰爭時期社會動亂、民生凋敝的感傷。
二、漢文化中含蓄內斂的人生哲理在他作品中的體現
同樣是在隨軍出征期間,當丁汝昌在威海戰敗、拒絕日本勸降而服毒自殺時,歐外為他作詩:
昨晚,在屋檐下,
那棵主人手植的梅花、
綻放了,
又迎來了今年的春天,
但他的主人卻看不見了。
花開在世間,
多么寂寞哀愁。
“梅”在漢文化里有著不屈不撓、巍然高潔等傲岸品格的意象,森歐外準確地用在這里以形容丁老的傲骨。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他受儒家文化影響而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情操,還能體會到森鷗外含蓄的人生哲理——作為高級軍官,不得不同書寫真善美的作家的良知作艱難斗爭,只得托志和寄情于漢詩。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目睹和經歷了戰爭的殘酷后,他在一首詞《擬寄內》[3]中寫道:“朔風侵戎幕,寒威徹敝禂。正談瀛海戰,忽動故園憂。”及“所希能起死,豈復覓封侯。”可以看到勛榮加身的他,對于流血不止的戰場已萌生倦意,“豈復覓封侯”或許正是他作為高級官吏在戰爭中無所適從的情感的委婉表達。
三、漢文化中的女性審美在其作品中的體現
盡管儒家崇尚中庸和內斂,但我們也不可忽視以盛唐雄肆宏放的文化氣氛、明清時期民眾思想初步解放為代表的我國文化顯著的階段特征,形成了唐朝俠女文化等女性覺醒思想。森鷗外或取材或直接引用這些形象,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了極具覺醒意識的女性主人公,強烈表現了他的感情傾向。
森鷗外的處女作《舞姬》(1890)講述主人公豐太郎到德國留學、偶然幫助并愛上落魄舞女愛麗絲、卻不得不拋棄她回國任官的故事。豐太郎曾試圖放下一切與愛麗絲同居,卻因經濟困難及社會輿論等壓力,選擇了拋棄愛麗絲回國從仕。為此愛麗斯精神失常,豐太郎內心也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創傷。這篇短篇小說取自森鷗外本人的經歷,但許多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都認為它與明朝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有淵源;學者德田武甚至認為,江戶后期著名小說家都賀庭鐘對馮夢龍原作的翻案之作《江口游女憤薄情沉珠玉》也對《舞姬》產生了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舞姬》發表后不久,石橋忍月以“氣取半之承”為筆名發表了批評《舞姬》的文章[4]說愛麗絲是一個“文盲癡呆,無見識、無志操的婦人”;森鷗外后以“相澤謙吉”為筆名作答反駁說:“愛麗絲似卓文君、楊家紅拂”——森鷗外以唐朝卓文君私奔、紅拂夜投李靖的故事為論據論證,表現出他對愛麗絲在戀愛中具有自主精神的贊美,我們也可從側面看出他受漢文化、或者說唐朝俠女文化影響極深。
創作后期,森鷗外因政治原因轉向歷史小說寫作,其中,發表于1916年的《魚玄機》更是直接以中國文學作品為素材,講述魚玄機的感情乃至整個人生的悲劇,描繪了一位千年前唐代女詩人的形象。之所以用“描繪”,是因為他在小說正文后列出了參照的中國文學典籍,我們可發現他的《魚玄機》不是簡單的我國傳說的疊加,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進行的再創作。從這篇小說中我們可看出森鷗外對魚玄機女性自由意識的贊許,影射了二十世紀初日本女性從蒙昧走向覺醒、并為追求自身幸福而不懈追求的全過程,反映了他的感情傾向。
他的另一部小說《雁》(1913)被稱作他的作品中“十分豐滿的現代小說佳品”。《雁》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取自他青年時代的見聞,以大學生岡田的朋友——“我”作為故事的見證人來追述小說的情節。小說講述明治年間貧苦少女阿玉淪為高利貸主的情婦;她渴望擺脫這種屈辱的境地、偷偷愛上一個每天從門前經過的大學生(岡田),但出于一個偶然的原因失去了表白的機會,終于沒能捕捉自己的幸福。從內容來看,學者孟慶樞指出[5]:開篇不久提到“我”去買《金瓶梅》的情節,包括在“我”之前岡田已花了6元錢買了此書——他認為,阿玉尋求自由戀愛是對屈辱的小妾生活的反抗,這一點正與《金瓶梅》有銜接點;另一處,文章第22節中先寫了“我們好像梁山泊豪杰出了店”,接著又寫岡田投石砸死大雁的情節,或許是《水滸傳》(120回本)第110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東京城獻俘”的投影,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述是很有道理的。從主題來看,阿玉極力抗爭婚姻被安排的命運,反映了明治初期婦女思想的覺醒。抗爭雖以失敗告終,但阿玉作為率先覺醒的女性,有理由得到同情與尊敬。
四、漢文化的宿命論思想在其作品中的體現
儒家主張尊天命、聽天命。孔子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們不難發現,森鷗外寫了數個故事來反映女性對命運的抗爭,卻都為她們安排了悲劇結局,正有宿命論的意味。
《舞姬》中愛麗絲帶著先進意識自我斗爭,終于不敵輿論和權勢、落得瘋癲;《雁》中,歐外把阿玉的不幸歸結為偶然性的惡作劇——文章結尾處描寫道:“岡田獨言自語:‘也是不幸的大雁啊。他想起了阿玉的命運。于是他們心里都蒙上了一層陰影。”用一只碰巧被飛石擊斃的雁來象征阿玉的命運,確是有極明顯的宿命論特點;《魚玄機》中魚玄機后期殺人的行為,既源于女性的嫉妒和憤恨,又是內心中壓抑已久的情感的宣泄,卻最終反映那個時代女性難以擺脫受壓迫之傳統的宿命。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對漢文化的崇尚貫穿了森鷗外的創作生涯、甚至是生命的始終;對漢文學乃至漢文化,他不是欣賞冰山一角,而是博覽群書、更甚之,化為己用;他吸收儒家文化的精華,把深厚的道德感融入自己的創作、積極入世、事主憂民,堪稱優秀學者的典范。
注釋:
[1]埃及中部的古代名城THEBES.
[2]1905《心之花》第九卷第四號.
[3]作于1894.12.2,收錄于《鷗外漢詩集》,光也編譯.
[4]1893.2,《國民之友》.
[5]森鷗外與中國文學[J].《日本學刊》,1995 (03).
參考文獻:
[1]“雙足”之學如長青之樹──評陳生保《森鷗外的漢詩》兼論鷗外漢詩[J]. 王曉平. 中國比較文學. 1995(01).
[2]森鷗外及其文學創作[J]. 葉琳.?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2(06).
[3]森鷗外與中國文學[J]. 孟慶樞. 日本學刊. 1995(03).
[4]森鷗外的漢文[J]. 陳生保. 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6(01).
[5]鷗外漢詩集. 光也編譯.
[6]鷗外全集第十九卷.(日)巖波書店發行.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