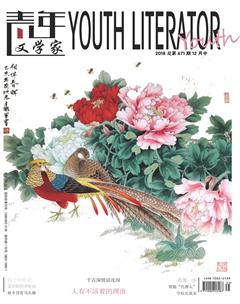論卡爾維諾小說的異化主題
李學召
摘? 要: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可以說是二戰之后世界文壇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之一了。他那令人贊嘆的小說創作技巧、充滿智慧和想象的寫作風格,他致力于窮盡小說藝術的無限可能性,以拓荒者的勇氣和智慧不斷開辟出新疆界被人們譽為“作家中的作家”。異化主題是卡爾維諾創作中極為關注的話題,而《意大利童話》中所展示的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意大利民族的歷史與現實,一定程度上也是整個人類的歷史與現實,其中對人類自我本質的喪失刻畫得入木三分。論文以卡爾維諾小說《意大利童話》為研究對象,從異化主題的成因入手,探討了作家小說的異化主題,進而對其異化主題進行了反思,在剖析卡爾維諾小說的異化主題的同時,揭示了作家獨特的詩學觀,以此展示了其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同時也對當下文學創作具有一定的現實啟示意義。
關鍵詞: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異化主題;生存境遇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5--02
伊塔洛·卡爾維諾是意大利當代最具獨創性和最別出心裁的作家,他以寓言式的寫作手法和童話般的語言為我們展示著他對世界的思考和認識,他的作品充滿智慧和人生哲理,但同時有帶有濃濃的超現實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氣息,因而有人評價他的小說為“人類智慧的文本”。《意大利童話》是卡爾維諾經過兩年的努力,經過大量的資料搜集和仔細整理后于1956年出版的一本童話集,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深遠。相較于《格林童話》,《意大利童話》雖然名氣不是太大,但其中對研究民俗學的幫助不容忽視,甚至有學者認為其成就遠在《格林童話》之上。
一、卡爾維諾小說異化主題的成因
縱觀卡爾維諾的創作歷程,異化現象成為他小說主題的原因簡單歸納有三個。一是其獨特人生經歷的影響。卡爾維諾的父母都從事和植物有關的工作,他自幼就學習到了很多關于大自然的知識,從小就對大自然有著莫名的親切感,另外,受父母親的影響他文理兼修,這造就了他更深刻的思維。他這種與眾不同的童年生活對卡爾維諾后來的文學創作影響深遠,他的作品始終富有寓言式童話般的色彩而同時又兼具哲理性。二戰時期,他和他的弟弟都參加了意大利當地的游擊隊,這對他來說是一段特別的經歷,他的第一部小說《通往蜘蛛巢的小徑》便是以此為題材;二戰后,他又經歷了意大利繁榮發展的黃金時期,可是戰爭給人心里帶來的創傷和摧殘卻沒有因社會的發展而消退,人們心理的異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卡爾維諾的關注,“我確信我是一個富有時代氣息的人。我們那個時代存在的問題體現在我寫的任何作品中。”[1]所以他在寫作過程中不斷探索和思考如何去解決人類現如今面臨的異化問題。
二是意大利的社會現狀促使卡爾維諾不斷思考現實。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正好是意大利甚至是世界格局動蕩不安的時代,意大利作為二戰的主要參戰國當然也不能幸免,戰爭帶給人們的創傷不可避免地成為創作的主題。除了戰爭,工業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也不斷擠壓人的生存空間,強烈的虛無感充斥著整個意大利。而戰后國家內部的不穩定使得大眾的心理也出現了問題,“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長期的不平等確保了長期的文化分化、政治動蕩和民族分製,沒有哪個階級、階層或者制度能就某一特定的興趣或者目標達成共識。政治常常在幾乎不太受歡迎的社團主義精英團體中,以敵對和陰謀的形式出現。”[2]
三是因為卡爾維諾詩學觀的影響。在他的詩學觀中,第一個要提的就是他關注對自我的探索和追尋這個終極哲學問題。其次,在卡爾維諾的詩學觀中,“輕逸”也是他極力推崇的,即以藝術之“輕”化解現實之“重”。卡爾維諾認為沉重的現實已經讓人感到痛苦,若文學作品中依然用非常悲傷或者壓抑的手法去再現沉重的現實,將會讓人難以接受,再加之他受“童話思維”的影響較深,因此他在文學創作中才大量運用童話班的語言和寓言式的寫作手法,用自己無窮的想象力讓讀者在輕松詼諧的環境中去感受現實世界的殘酷,這種反差的對比會讓人更加重視現實。這就是他的敘事技巧和文學風格,也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審美理想的映射,是他向我們展現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途徑。在搜集、整理、編寫《意大利童話》的過程中,他看到了童話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差別和聯系,許多優秀的民間故事渲染了一種幻境,但又沒有回避現實,這種表達是值得稱道的。
二、卡爾維諾小說異化主題的具現
異化 (alienation) 一詞源自希臘語,本義為分離、疏遠,現在一般指由主體創造出來的物反過來與主體對立,具體到人自身,就是指人被自己的創造物控制,人變得非人化了。在《意大利童話》中,非人化的現象比比皆是,而究其原因,大多為人心被物質操控,失去自我,價值觀被扭曲,變得孤獨空虛,完成異化的過程。這其中以嫉妒心理占大多數,因為嫉妒,人心就會失去自我,被欲望驅使,做出一些違反人倫甚至違反法律的事,等計劃落空,失去所有,才發現個體已經被異化。
孤獨是人類永遠繞不開的一個話題,是文學創作者想要竭力去展示的一個話題,也是卡爾維諾力圖表現的《意大利童話》主題之一,因為內心世界的孤獨,精神變得空虛,久而久之生命的形式便只是一副空蕩蕩的軀殼,靈魂被扭曲,人性被異化。《意大利童話》中所收集的孤獨故事,是整個人類孤獨的縮影。空有一身財富卻買不來幸福和歡樂,小喬萬尼最終死于孤獨;因同胞姐妹嫉妒慘遭殘害流落森林的善良女孩……這些擁有著親情卻被外在物質所蒙蔽而走向異化的人是孤獨空虛的,隔閡一旦產生,最終面臨的就是悲劇。與傳統童話“從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不同,卡爾維諾收集的故事大多沒有美麗的結局,孤獨的主人公最后往往還是在孤獨中終老。其次是表現在個體的自我異化方面。在意大利,二戰后短暫的繁榮讓人們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戰爭的傷痛逐漸被抹平,物質的刺激開始占據上風,金錢萬能的觀念越來越被人們接受,當金錢變得萬能,相對而言,人就開始變得無能,個體開始走向異化。《靠喝風活著的新娘》里塑造了一個比葛朗臺富有也比葛朗臺吝嗇的親王形象,他有富可敵國的財富卻因為不想養活老婆而一直未婚。當他聽說有個只靠喝風活著的女人時他就迎娶了這位姑娘,實則他是被仆人騙了。后來新娘趁他不在用金子裝修了房間,親王看到房子后便氣到在床從此沒有起來。吝嗇鬼的形象似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中,他們有著相似的性格和命運,但是在卡爾維諾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吝嗇鬼——他聽說一個女人只靠喝風活著時毫不猶豫地娶了她。我們可以看到從人人性的角度,這位富豪是希望能夠擁有一位妻子的,他也有追求愛情和幸福的欲望,但是因為對財富的變態追求是他竟然克制住了人性最本質的需求,這是一種多么令人驚訝的異化,相對于這些虛無縹緲而且沒有溫度的紙幣,難道人類特有的溫情和內心的充實不應該更是值得我們去擁有的嗎?物質財富的異化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能“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愛變成恨,把恨變成愛,把德行變成邪惡,把邪惡變成德行,把奴隸變成主人,把主人變成奴隸,把愚蠢變成明智,把明智變成愚蠢”[3]。他死后,新娘和他的仆人結了婚,他的財產也全部變成了新娘的嫁妝。有錢不是萬能的,中國有句俗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今天,我們不應該只是取之有道,更能應該視之有度,用之有法。
三、卡爾維諾小說異化主題的反思
薩特從匱乏這一點出發,認為人們因為物質匱乏而大力發展生產力、革新各種技術,所帶來的后果不只是物質的富足,更有人的異化。卡爾維諾繼承并發展了薩特的這一理論,深知工業化社會對人的影響和改變,他以夸張的筆法描畫出自我異化的狀態,希冀警示自我麻痹的現代人,直面自我生存的困境,探尋反異化的出路。正是在這一個層面上,卡爾維諾的小說彰顯了其獨特的啟示意義。
在《意大利童話》中,有很多篇章的結尾出現了一些和內容格格不入的句子或者段落,例如:在《蛇》這一篇故事當中,小女兒最終證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她的兩個姐姐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樣的結局如果在《格林童話》中應當是完美的結局,可是在《意大利童話》中卻有一段和內容看起來格格不入的獨白:“他們過著奢侈、冷酷的生活,我卻躲在門后挨餓,我回到客棧去吃飯,我的故事到此說完。”[4] 這種很突兀的獨白在作品中隨處可見,最開始看到時會使很多人不解,可是當我們細細去思考,才發現這里的“我”代表著處于主流社會之外的局外人形象,在作品中“我”只出現在結尾而且命運如此悲慘,而其實在現實中“我”的遭遇更令人同情和憐憫。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下,物質至上的原則無形中將社會分了等級,處于最低等階級的人是不被上層社會所接納的,甚至連最基本的同情都沒有。因此,對異化主題的關注也表達了卡爾維諾對這“局外人”群體的同情,對社會的不公的不滿,對人們現狀的擔憂,對物質利益的控訴。另外,卡爾維諾在1967年曾經說過:“現代文學的力量就在于它說出了社會和個人本來想說而又沒有意識到的一切,這就是文學所不斷提出的挑戰。我們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華,房子的墻上就越有鬼影,因為進步和理性的夢中往往摻雜著鬼影。”[5]由于卡爾維諾生長在二戰時期,對于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何況他還是一位對人類命運如此關心的作家。當戰后的無助和空虛逐漸被繁榮的經濟所代替,人類社會又出現走向異化的端倪,而當經濟泡沫破碎,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所表現出的又是一種脆弱和孤獨。社會的動蕩和心靈的疲憊加劇了人性的墮落,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過去的美好記憶又催促著人們急切的逃避灰暗的現實,而這時,一種美好而純真的世界——童話世界便悄然出現因此,我們可以從《意大利童話》一篇篇富有深意的故事中感受理想世界的美好,在童話故事中暫時忘掉現實世界的失意。
作為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卡爾維諾終生都在思考人類的發展前景。很多人身處這個被異化的世界,“理所當然”的生活而不自知,即便自知也懶得自救,但是仍有一些人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用自身的能力和與擔當喚醒著日漸麻木的群體,這就是像卡爾維諾一樣這類人的使命和責任。對于異化問題,他獨辟蹊徑,用寓言式的寫作和童話般的思維呈現給世人,除了批判,更重要的是重建,那種對異化的批判、對人類精神完整的呼喊、對個體自我意義的肯定、對社會集體的警示,都是閃爍著永恒的光輝,在今天依然值得我們銘記的。
參考文獻:
[1]HERBERT MITGANG. Italo Calvino,The novelist,dead at 61 [N]. The New York Times,1985-09-19.
[2]卡爾·博格斯: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危機[M].李俊、蔡海榕譯,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83.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昆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M].呂同六,張潔主編,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59.
[5]沈萼梅,劉錫榮. 意大利當代文學史[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