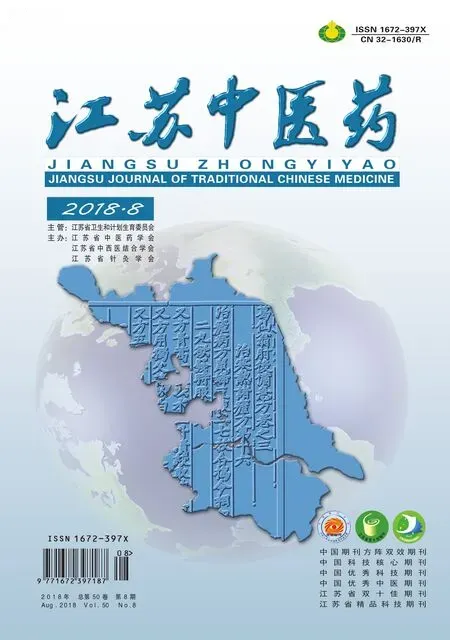從“形精氣味”談挽精逐濁法治療糖尿病腎病
趙雯雯
(成都中醫(yī)藥大學(xué)臨床醫(yī)學(xué)院,四川成都610075)指導(dǎo):岳仁宋
糖尿病腎病是糖尿病常見的慢性并發(fā)癥之一,是1型糖尿病的主要死因,在2型糖尿病中其嚴(yán)重性僅次于心腦血管疾病。其早中期癥狀多不明顯,晚期腎功能進行性下降,失代償期可見納差乏力、水腫、大量蛋白尿,甚至出現(xiàn)神識不清、惡心嘔吐、二便不通、心悸喘促等多系統(tǒng)損害。古代文獻中雖未見糖尿病腎病之名,但其記載卻散見于“消渴”“水腫”“尿濁”“虛勞”等疾病中。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內(nèi)經(jīng)》針對虛損疾病提出的治療原則,早在《金匱要略·血痹虛勞脈證病治第六》中就提到五臟虛損病因證治之法,言虛損應(yīng)該重視脾腎,蓋腎為先天之本,是真陰真陽所寄之處;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營衛(wèi)生化之源。當(dāng)虛勞病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往往以脾腎癥候表現(xiàn)較為明顯,故仲景以甘溫扶陽為重,創(chuàng)黃芪建中湯、八味腎氣丸一類,實乃對“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的深入理解。導(dǎo)師岳仁宋教授創(chuàng)“挽精逐濁法”論治代謝相關(guān)性疾病理論[1-2],提出糖尿病腎病的治療應(yīng)以“挽精逐濁”為法,且宜“陰陽平調(diào)固本”,并從“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出發(fā),擬參芪地黃湯加減治療糖尿病腎病,茲探討如下。
1 糖尿病腎病之病機
1.1 “精不足”乃糖尿病腎病發(fā)病之根 導(dǎo)師岳仁宋教授根據(jù)長期臨床經(jīng)驗提出消渴病根本病機為“脾弱胃強”,認(rèn)為稟賦不足、飲食不節(jié)、勞欲太過、情志失調(diào)等諸多病因?qū)е缕⑻撌н\,“脾弱”則氣血生化乏源,升清降濁功能失常,導(dǎo)致精微難成且失于布散;郁積于脾胃之精微在陽明氣盛之地化熱傷陰形成“胃強”而消耗人之津液(津傷),久病火熱之性更煎灼真陰(精傷)[3]。《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夫精者身之本也”。精是構(gòu)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物質(zhì)基礎(chǔ),糖尿病腎病發(fā)生于消渴病后期,其病機的發(fā)生發(fā)展常始于微而成于著,疾病日久先后天之本皆已受累,致“糖毒”久羈陰分,深入五臟六腑、骨髓經(jīng)隧,終致脾腎之精不足[4]。腎精妄泄、腎氣固攝無權(quán)導(dǎo)致水谷精微下注形成蛋白尿;病久陰損及陽失于溫煦,故小便清長、夜尿頻多;水液不能布散四旁,故見雙下肢水腫;百骸臟腑失于濡潤溫養(yǎng)故倦怠怕冷。因此糖尿病腎病以“精不足”為病機之本。
1.2 從“精不足”發(fā)展至“形不足” “形”是人體的一切有形之體,包括臟腑、經(jīng)絡(luò)、氣血等。劉曉玲等[5]對“形不足”的解釋主要有兩種觀點:即外在形體瘦弱不足之“形體不足”和衛(wèi)陽、陽氣衰微的“形氣不充”。腎中所藏精氣由先天父母之精相合而成,同時依賴于后天水谷精微的充養(yǎng),是構(gòu)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zhì)。今脾運失常,喪失“脾主肌肉”的生理功能,腎精不足、腎無所藏,從而形成“形體不足”的外在征象;腎陽為一身元陽之本,隨著病程進一步發(fā)展導(dǎo)致病情由陰及陽,進而容易表現(xiàn)出脾腎陽虛、氣衰血弱之證,終致怕風(fēng)、易感冒、倦怠乏力、納差少食、動則氣喘、精神萎靡等“形氣不充”之征象。
1.3 從“精不足”發(fā)展至“神不足” 經(jīng)云“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類證治裁》亦指出“腎之精華上升于腦,精能生氣,氣能生神,神定氣清”,腎精生髓充腦而成為神志活動產(chǎn)生的基礎(chǔ)。精氣神三位一體,統(tǒng)攝一切生命活動,精氣足才能使神的活動健全。若脾腎受損、腎精難充,元陰不足不能濡潤滋養(yǎng)五臟,元氣衰而五臟陽氣皆弱,則導(dǎo)致“神不足”。神以形為物質(zhì)基礎(chǔ),在癥狀上可見精不充形而出現(xiàn)形體消瘦、面黃肌弱等表現(xiàn),同時常因精不足影響五臟而出現(xiàn)神不守舍,或魂魄不藏,或意志不收等諸如害怕恐懼、失眠多夢、記憶力減退的臨床表現(xiàn)。
1.4 由精易濁——基于“精不足”衍生的他證 正所謂“非其位則邪”,脾失健運、腎失封藏,臟腑之精離經(jīng)變濁,精微物質(zhì)無以運化、蒸騰、固密,反成致病之邪阻于脈絡(luò)、郁于體內(nèi)而形成痰熱、濕濁、瘀血等,或疏泄太過,精微物質(zhì)外漏,而形成高血脂、高尿酸、糖尿、蛋白尿等,據(jù)此導(dǎo)師提出“離經(jīng)之精便是濁”理論。精微不足、濁邪膠著難祛,致氣機紊亂、清濁難分、變證叢生,免疫功能降低使病情稍有不慎則易反復(fù),終致水腫、癃閉、關(guān)格等。
2 挽精逐濁法治療糖尿病腎病
2.1 逐本溯源究其意——“氣”與“味”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內(nèi)經(jīng)》針對虛損疾病提出的治療原則。結(jié)合原文上下文意,可知其中“氣”與“味”當(dāng)指氣藥與味藥,《中醫(yī)名詞術(shù)語選釋》也提到“形不足指中焦虛弱而產(chǎn)生形體虛弱。須用溫氣藥補養(yǎng)中氣,則脾能健運,營養(yǎng)增加,使肌膚形體逐漸豐滿;精不足,指人體的精髓虧虛,應(yīng)補之以厚味,使精髓逐漸充實。厚味,指富于營養(yǎng)的動植物食品,也指厚味的藥物,如熟地、肉蓯蓉、鹿角膠等藥”,其中指出對于氣虛陽虛者當(dāng)以氣藥溫之,對于陰血虛精液虧者當(dāng)以味藥補之,據(jù)此,導(dǎo)師臨床多應(yīng)用“味厚氣薄”之參芪地黃湯(人參、黃芪、山藥、山茱萸、澤瀉、茯苓、丹皮、蟬蛻、土茯苓、萆薢、車前子、黃精、桑椹、枸杞等)加減用藥,以“挽精逐濁”為治療原則,陰陽平調(diào)、固益脾腎,治療糖尿病腎病。
2.2 挽以留精——“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精氣奪則虛”,宜“補之以味”。《素問·生氣通天論》提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今脾虛精微失去統(tǒng)攝,腎失封藏、精微失漏,應(yīng)始終抓住脾腎虛損之本質(zhì),治以補益脾腎、填精補髓。“精傷”絕非“津傷”,故應(yīng)選取添精補髓之法挽以留精,臨床上選用酸甘咸之“味藥”以滋養(yǎng)陰血、添精補髓治療陰精不足。可與淫羊藿、巴戟天、肉蓯蓉、鎖陽、杜仲等味咸質(zhì)滋、補而不燥之品聯(lián)用。“夫精血皆有形,以草木無情之物為補益,必不相應(yīng)”,故臨床多使用富含蛋白質(zhì)的地龍、僵蠶、蟬蛻等蟲類藥及鹿茸、龜膠、阿膠等血肉有情之品,以添補絕對或相對不足的營養(yǎng)物質(zhì)。另外也可以通過食療的方法滋養(yǎng)陰精,采用清補滋養(yǎng)法,選擇性質(zhì)平和或偏涼的食物,如龜、鱉、芝麻、蜂蜜、黑木耳等甘涼咸寒的清淡食物,以滋養(yǎng)陰精、生津養(yǎng)血[6]。
2.3 挽以取用——“形不足者溫之以氣” 通過選用溫?zé)釟夂瘛⒁鏆庵栔皻馑帯保谷砼K腑的陽氣得到充養(yǎng)繼而形體充實。《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指出“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zhuǎn),其氣乃散”,通過增強人體的氣化功能,使郁于經(jīng)隧中的精微物質(zhì)重新被人體挽取利用,從而實現(xiàn)挽以取用之意。譬如人參、黃芪健脾助運、益氣通陽,使中焦脾胃之氣、下焦腎之元氣振奮而表寒外散,寒飲內(nèi)蠲。
2.4 挽以防脫 此法多被稱為蛋白尿之“正治法”。蓋“滑者澀之”,使過多的精微物質(zhì)不至于大量從小便或其他渠道脫失。《醫(yī)學(xué)衷中參西錄》中提到“山萸肉味酸性溫,大能收斂元氣,振作精神,固澀滑脫。因得木氣最厚,收澀之中兼具條暢之性,故又通利九竅,流通血脈”,《沈氏尊生書·要藥分劑》云:“澀可去脫,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故可用龍牡、山萸肉等溫腎固精之品收斂固攝以達挽以防脫之功。
2.5 逐濁祛濁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dāng)其位則正”,精失封藏變?yōu)闈嵝啊㈦x經(jīng)之精失其常道轉(zhuǎn)變?yōu)樘禎狃鲅韧谂K腑經(jīng)脈,當(dāng)根據(jù)病理產(chǎn)物不同予以治水、治氣、治血、治痰之法,實現(xiàn)“邪去則正安”。臨床多用土茯苓除濕解毒、萆薢分清別濁、澤瀉利濕逐濁等。
3 參芪地黃湯的加減應(yīng)用
參芪地黃湯出自清代沈金鰲《沈氏尊生書·卷三·雜病源流犀燭·大腸病源流》,馬蒔謂“味不可以無氣,氣不可以無味”,故導(dǎo)師原方基礎(chǔ)上增加味厚氣薄之品,歸經(jīng)方面以肝、脾、腎為主,以益氣養(yǎng)陰之“味藥”為主,補中兼瀉。蓋味為陰,有質(zhì)而降,且味厚者多潤;稍以“氣藥”以達到氣薄避“壯火散氣”之失,且徐徐然蒸騰氣化,使得藥之厚味周身流轉(zhuǎn),滋養(yǎng)臟腑,化生為精,以達陰平陽秘之期。方中用黃芪補氣托毒,斂瘡生肌;人參甘溫益氣補虛、健脾助運以增黃芪之力;以黃精、桑椹、枸杞子替代熟地增強補養(yǎng)陰精之效,從而達到滋陰補腎、填精益髓的目的;山藥健脾滋腎,亦能固精;山茱萸補養(yǎng)肝腎,并能澀精;牡丹皮清泄相火,并制山茱萸之溫澀;茯苓淡滲脾濕,并助山藥之健運。在此基礎(chǔ)上,根據(jù)患者的具體表現(xiàn)可適當(dāng)配伍健脾、養(yǎng)肝、疏肝、活血、化痰之品等。
4 討論
盡管參芪地黃湯中氣藥味藥皆有使用,但是針對糖尿病腎病還是應(yīng)以味藥為主,因為精不足是產(chǎn)生形不足,乃至神不足的根本原因,導(dǎo)師強調(diào)糖尿病根本病機在于“脾弱胃強”。無論是飲食失節(jié),抑或情志失常,終會導(dǎo)致消渴病早期一派火熱熾盛之象,胃強則耗傷陰精太過,脾弱則后天之精生成不足,病久“飲一溲一,飲一溲二,則燥火劫其真陰。操立盡之術(shù)而勢成熇熇矣”。糖尿病腎病精損嚴(yán)重,而參芪地黃湯中大量味厚之品輔以氣薄之品實乃以偏糾偏,達到“陰陽平調(diào)”以固本。
正如高士宗強調(diào)“陰精不足而虛弱者,當(dāng)以陰分之味藥補之,陰味為能內(nèi)滋也”。我們未應(yīng)用補血養(yǎng)血之品的原因在于此時疾病已然發(fā)展深重,不但存在血的不足,還有津液、氣的虧耗,必須從源頭入手,補益先天之精與后天之精,只有在精充足的情況下,精化氣而氣血津液得充。故臨床上以選用添精增髓之“味藥”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