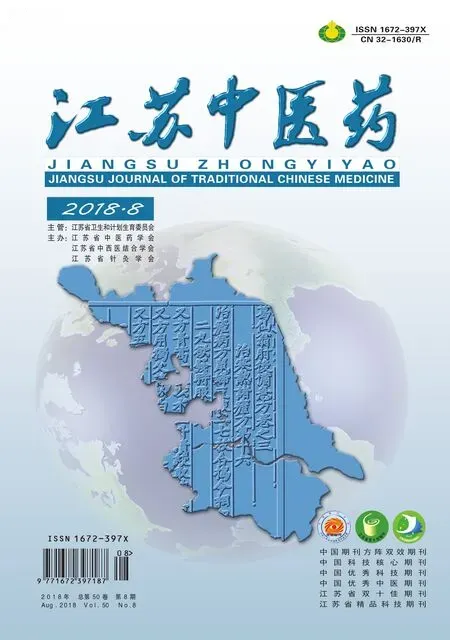喻文球論治尋常型白疕病經驗探析
熊河輝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無錫醫院,江蘇無錫214071)
白疕病是中醫皮膚科中常見的疾病,也稱之為“松皮癬”“干癬”等,以皮膚紅斑、厚層鱗屑為主要特征,相當于現代醫學的銀屑病,它是一種慢性、炎癥性、易復發的皮膚病。根據白疕病臨床特征,有尋常型、關節型、膿皰型、紅皮病型四種主要類型,其中尋常型白疕病是白疕病中最為常見的一種類型,約占99%以上。喻文球教授為全國第三、五批繼承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指導老師,從事中醫外科臨床、教學、科研工作近40年,對白疕病的治療有著豐富的經驗。關于白疕病,喻教授認為毒邪是致病的關鍵,血熱是病情發生發展的關鍵,是病機的核心,風、濕、瘀是發病的重要因素。筆者有幸跟隨喻教授,受益良多,現將其論治白疕病的經驗介紹如下。
1 病因病機認識
1.1 毒邪是致病的關鍵 所謂的毒邪是指蘊藏于普通食物、藥物、動物、植物及自然界六氣之中的一種特殊的致病因素,它發病急,來勢猛,呈進行性加重,且傳變迅速,易于惡化。同時它又是疾病過程中的病理產物,血熱內蘊,日久化毒;或血熱致瘀,瘀久化熱化毒,導致瘀毒互結。另外,毒邪致病多挾濕挾瘀,且病情頑固,反復發作,不易根治。從白疕病的發生、發展及轉歸來分析,其具備毒邪致病的特點。首先,白疕病多發病急驟,可突然泛發全身,呈進行性加重,并且傳變迅速,容易惡化(如紅皮病型白疕病);其次,本病多為素體陽熱之人因外感六淫之邪蘊結體內日久化火而成毒;或是五志過極、七情內傷、飲食失節,造成臟腑功能和氣血運行失常,以致氣滯、血瘀、濕阻,化熱成毒;第三,本病病勢纏綿,反復發作,不易根治。因此,毒邪是本病致病的關鍵。
1.2 血熱是病機的核心 白疕病常因內外合邪而發病,外因以風、濕、熱、毒多見,內因則常有素體血熱、情志內傷、飲食不節等,而內外各種致病因素均可導致血熱的形成。患者素體血熱;或七情內傷,氣機壅滯,郁久化火,以致心火亢盛,心主血脈,心火亢盛則熱伏營血而致血熱;或飲食失節,過食腥葷動風之物,以致脾胃失和,氣機不暢,郁久化熱,從而導致血熱;或素體陽熱偏盛,復外感風濕熱毒諸邪,搏于肌膚,郁久化熱入血則引起血熱。血熱內蘊,郁久化毒,以致血熱毒邪外壅肌膚而發為本病。血分有熱,熱毒內蘊,熏蒸肌膚,故發斑疹;熱盛生風化燥,故見斑疹色紅而白屑疊起;熱灼津液,血行瘀滯不暢,則見斑塊肥厚紫赤;若血熱內蘊,日久化毒,熱毒入營,損傷營血,則可致血燥;熱毒內蘊,血受熱煎熬則致血瘀。血瘀內停,瘀久化熱,又可加劇熱毒內蘊,形成不良循環,導致瘀熱互結;更有甚者血熱熾盛或外受毒熱刺激,以致郁火流竄,蒸灼皮膚,則可發生傳變而形成較嚴重的紅皮病型白疕,出現全身潮紅,形寒身熱,肌膚燥竭。因此,血熱是本病發生發展的關鍵,是病機的核心。
1.3 風、濕、瘀是發病的重要因素
1.3.1 風 《醫宗金鑒》曰:“此癥總因風濕熱邪,侵襲皮膚”,《普濟方》謂:“夫鮮……其病得之風濕客于腠理……故風多于濕則為干鮮”,認為本病的病因是以風邪為主,夾以濕熱。因此,白疕病的發病首先與風邪有關。風為百病之長,常與濕、熱、毒相兼為患。風濕之邪客于肌膚,則出現皮膚瘙癢,斑疹纏綿難愈;血分伏熱,風邪外客,風熱相搏,發于肌膚,則皮色潮紅,瘙癢起屑;血熱內蘊,熱盛生風化燥,抑或熱盛耗傷陰血生燥,則皮膚干燥疊起白屑。
1.3.2 濕 白疕病患者既可外感濕熱之邪,亦可因飲食不節或毒邪內蘊,敗傷脾胃,導致濕熱內生,濕熱邪毒蘊結,則使病情纏綿不愈。臨床上表現為舌質紅、苔黃膩,脈弦滑或濡滑。現代研究發現,銀屑病患者真皮組織病理表現為真皮乳頭延長、水腫。從中醫角度,我們認為這是微觀上的無形之“濕”。此外,白彥萍等[1]通過對尋常型銀屑病血熱證證候成因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濕邪是與銀屑病血熱證形成關系最為密切的因素之一。
1.3.3 瘀 血瘀是血熱病變發展過程中的病理產物,又是致病原因之一。各種內外因素導致血分有熱,血受熱則煎熬成塊,故血熱日久則可燔灼津血,使血液黏滯而運行不暢,因熱而致瘀,形成熱瘀互結。現代醫學研究發現,銀屑病發病與微循環障礙有密切關系,存在毛細血管扭曲,全血黏度增高,血管通透性明顯增高等變化。
因此,血熱毒盛是白疕病的主要病因病機,風、濕、瘀是其發病的重要因素。
2 涼血消疕湯為基本方
法隨證立,方從法出,血熱毒盛是白疕病的病因病機,并且有風、濕、瘀的作用。因此喻教授在遣方用藥時從這幾方面切入,在傳承中醫特色的基礎之上,總結多年臨床經驗,選用土茯苓、金銀花、菝葜、石膏、山梔、苦參、白花蛇舌草、白鮮皮、地錦草、黃芩、生地、青黛、丹參、郁金等十四味中藥組成涼血消疕湯。全方以清熱解毒涼血為主,兼有祛風除濕之功效。方中主要含有兩大組藥,一組解毒,一組涼血,解毒藥包括清熱以解毒,利濕以解毒,重用土茯苓、金銀花和菝葜為解毒主藥,三藥具有清熱解毒、祛風除濕散瘀之功,能解熱毒、風毒、濕毒和瘀毒,且藥性平和,具有解毒不傷正之功。毒邪又是疾病過程中的病理產物,血熱內蘊,郁久則化火化毒,故用苦寒之生石膏、山梔、苦參以加強清熱解毒之功效。《本草經疏》曰:“甘所以和毒,寒所以除熱,凡毒必熱必辛,得清寒之氣,甘苦之味,則諸毒自解,故為解毒清熱之上品。”另外白花蛇舌草、白鮮皮清熱燥濕,祛風解毒,增強方中解毒祛風之功效,以上解毒諸藥合用能有效清除機體外來和內生之毒邪,從根本上阻斷本病的致病之因。本病以熱為本,病在血分,故當治以涼血活血。方中以地錦草、黃芩、生地、青黛為涼血藥組,生地涼血滋陰,使清熱而不傷陰。方中還運用了丹參、郁金,取其活血祛瘀之功效,合以上諸藥可消除本病發病的根源,體現了葉天士在《溫病條辨》中說的:“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方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諸藥合用,共奏清熱利濕解毒、涼血活血之功。
3 善用蟲類藥物
喻教授認為,久病易成瘀,本病病情遷延,纏綿難愈,主要病因病機是血熱毒盛,血熱日久則可燔灼津血,使血液黏滯而運行不暢,因熱而致瘀,形成熱瘀互結,正如《素問·痹論》所提出的:“病久入深,營血之行澀,經絡時疏,故不通。”治療中若使用植物類活血藥物未能取得良好療效時,則重視并善用蟲類藥物如:僵蠶、地龍、全蝎、蜈蚣等血肉有情之品,此類藥物搜剔虛風賊邪活血通絡,通常可取得植物類活血藥物達不到的效果,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張錫純認為蜈蚣“走竄之力最速,內而臟腑,外而經絡,凡氣血凝聚之處皆能開之”。而且強調在使用蟲類藥物時,必須辨證準確,配伍合理,中病即止,不必盡劑。另外,蟲類藥物性多溫燥,故在配伍時宜用些滋陰潤燥藥以去性取用,盡其所長,提高臨床效果并盡量減少毒副作用的發生。
4 重視心理調適與飲食禁忌
對于白疕病,喻教授除了在病因病機、遣方用藥以及使用蟲類藥物方面有獨到的認識和見解,同時他還認為患者的心理調適與飲食禁忌在治療中也相當重要,我們要通過激勵的言行讓患者正確認識和面對白疕病,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接受治療,另外一定要告誡患者忌食辛辣葷腥發物以及戒除吸煙及過度飲酒等不良嗜好。
5 驗案舉隅
李某,男,40歲,工人。2012年7月18日初診。
主訴:軀干四肢紅斑鱗屑伴瘙癢反復3年余,加重半月。患者自訴3年余前雙側肘部及腰骶部出現紅斑或斑塊,厚層白色鱗屑,輕度瘙癢,至當地醫院就診,被診斷為銀屑病,給予銀屑膠囊及復方丙酸氯倍他索乳膏等藥物治療,病情明顯緩解。但近一年病情反復,且皮損面積較前明顯變大,延及四肢,反復多次使用中、西藥物治療(具體藥物不詳),療效不甚明顯。故特至喻教授處求治,刻診:軀干、四肢可見大小不一紅色或暗紅色斑片及斑塊,輕度腫脹,鱗屑,稍癢,部分已融合成片,少數斑塊上方鱗屑較厚,可見薄膜及點狀出血現象,精神欠佳,無關節腫痛,無明顯發熱,伴有口干,大便不爽,舌紅、苔薄黃膩,少量瘀斑,脈弦滑數。診斷:白疕病。證型:血熱毒蘊。治以清熱涼血活血,利濕解毒消斑。方予涼血消疕湯加減。處方:
土茯苓30g,銀花10g,菝葜15g,地錦草15g,黃芩10g,生地15g,山梔10g,石膏30g,苦參10g,白鮮皮10g,丹參15g,赤芍10g,青蒿10g,紫草15g,甘草5g。水煎服,日1劑,分2次服。
半月后二診:軀干四肢紅色斑片或斑塊,皮膚腫脹消失,基本無瘙癢,無新發皮疹,口干改善,二便可,舌紅、苔薄黃白膩、少量瘀斑,脈弦滑,原方去苦參,加用全蝎3g、蜈蚣2條,水煎服,日1劑。
再半月后三診:軀干四肢紅斑明顯減少,斑塊變薄,顏色變淡,無明顯口干,舌偏紅、苔薄白,未見明顯瘀斑,脈弦。處方:土茯苓15g,菝葜10g,槐花10g,地錦草15g,生地15g,丹參10g,赤芍10g,地龍10g,川芎10g,青蒿10g,甘草3g。水煎服,日1劑。
3周后四診:軀干四肢紅斑及斑塊已基本消退,僅遺留色素沉著或減退斑。囑患者繼續忌口并戒煙酒,預防感冒。1年后,電話告知未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