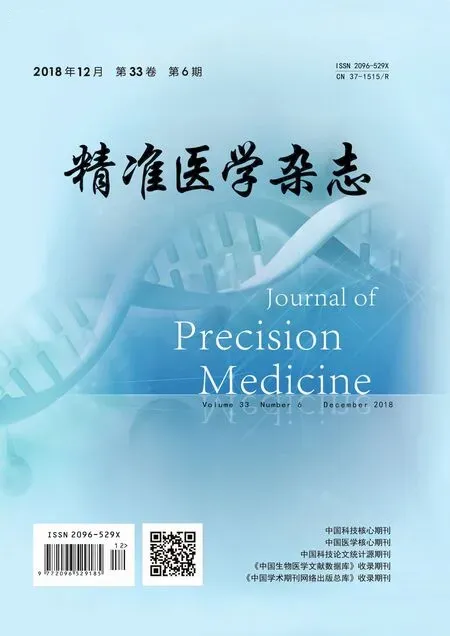原發性痛風和高尿酸血癥的精準分型及治療研究進展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山東省痛風病臨床醫學中心,山東省代謝性疾病重點實驗室,山東 青島 266003)
痛風是由尿酸或尿酸鹽結晶沉積引起的一組臨床綜合征,臨床表現為高尿酸血癥、反復發作的痛風性關節炎、痛風石沉積及痛風性腎病等[1]。高尿酸血癥是指在正常嘌呤飲食狀態下,非同日兩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高于420 μmol/L,即稱為高尿酸血癥[2]。高尿酸血癥是痛風發生發展最重要的生化基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飲食結構的改變,痛風和高尿酸血癥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近20年來美國痛風患病率達3.9%,而歐洲的痛風患病率為3.2%[3]。在我國尚缺乏較完整的與痛風相關的流行病學資料,但近年我國部分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顯示,中國痛風發病率逐年上升,山東沿海城市人群的痛風患病率達1.14%,而高尿酸血癥的患病率高達13.19%[4]。據估計,目前我國痛風患病人數已超過5 000萬人。痛風和高尿酸血癥已成為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謝性疾病,嚴重危害人們的身心健康。
目前,開展了許多關于痛風與高尿酸血癥遺傳背景的研究,發現了多個與原發性高尿酸血癥密切相關的易感基因,但痛風性關節炎相關的易感基因發現較少。最早通過對家系血尿酸水平分析,發現遺傳因素在高尿酸血癥中的作用占25%[5-7],而后通過對雙胞胎血尿酸水平分析,發現遺傳因素在高尿酸血癥中的作用約占0.73%[8]。此后多項大樣本家系研究證實[9-11],遺傳因素在高尿酸血癥發病過程中的作用占40%~50%。群體遺傳水平上,70多項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研究發現, PDZK1、GCKR、SLC22A、SLC2A9、ABCG2等28個基因多態性與血尿酸的水平相關,大多數為腎臟的尿酸轉運蛋白,其中僅SLC2A9基因位點即可解釋血尿酸3.7%的遺傳變異,可以作為篩選的生物學標志和精準治療的靶點[12-13]。由此可見,痛風和高尿酸血癥是非常適合進行精準分型和治療的疾病,開展原發性痛風和高尿酸血癥精準分型以及靶向治療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1 原發性痛風和高尿酸血癥的精準分型現狀
1.1 原發性高尿酸血癥的精準分型現狀
目前臨床根據尿酸排泄分數將高尿酸血癥分為尿酸生成增多型、尿酸排泄減少型和混合型三種類型,這是目前臨床判斷腎臟尿酸排泄能力的金標準。在排除其他疾病的基礎上,由于先天性嘌呤代謝紊亂和(或)尿酸排泄障礙所引起的稱為原發性高尿酸血癥;繼發于腎病或某些藥物所致尿酸排泄減少、骨髓增生性疾病及腫瘤化療所致尿酸生成增多等原因導致的稱為繼發性高尿酸血癥。該分型方法對高尿酸血癥的生活方式干預及藥物治療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但由于該方法需低嘌呤飲食5 d,收集24 h尿量等繁瑣過程,患者依從性差,難以在臨床廣泛使用。且目前的高尿酸血癥臨床分型較為粗略,不能充分反映高尿酸血癥的內在發病機制,因此不能作為高尿酸血癥的精準分型標準。
作為一種遺傳占主導的復雜疾病,高尿酸血癥發病涉及基因組、轉錄組、表觀基因組、蛋白組、免疫組和代謝組學等多個層面。目前,基因組學研究已發現了SLC2A9、ABCG2、SLC22A12等參與尿酸排泄的痛風易感基因[14-16];尿酸代謝途徑中HGPRT、XO、PRS、HGPRT等關鍵酶基因突變可導致尿酸合成增加,血尿酸水平升高[17]。全基因組關聯研究顯示,ABCG2和GLUT9與高尿酸血癥發生密切相關[18]。另外,研究證實,ABCG2和GLUT9參與尿酸在腸道的轉運,但其功能是否受腸道菌群影響、其功能異常是否影響腸道尿酸排泄以及ABCG2和GLUT9在腸道尿酸排泄過程中是否發揮關鍵作用,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綜上所述,全面考慮尿酸代謝、排泄等因素,通過多組學檢測技術尋找高尿酸血癥特異性分子標志物,制訂精準的分子分型體系是實現高尿酸血癥精準診療的關鍵。
1.2 原發性痛風的精準分型現狀
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復雜疾病是分子網絡疾病,其發生、發展及治療轉歸都是多個基因相互作用的結果[19]。近年來,針對腫瘤等疾病的多組學分子分型研究的成功,為復雜疾病的精準醫學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鑒[20-21]。痛風也是一種復雜疾病,其發病和預后涉及基因組、轉錄組、表觀基因組、蛋白組、免疫組及代謝組等多個層面。痛風易感基因和分子標志物的不斷發現及多組學技術的逐漸完善,使痛風早期預測、精準分型和預后評估成為可能。
目前,基因組學研究已經發現了cGKⅡ、IL-8、IL-12β及TGF-α等與炎癥發生相關的痛風易感基因[22-24]。筆者課題組前期在10 000余例大樣本痛風隊列中首次發現了調控痛風免疫信號通路的易感基因(BCAS3、RFX3、KCNQ1)[25]。通過表觀基因組和轉錄組學研究,已發現多個micro-RNA參與痛風發病的生物學過程[26-27]。其中miR-223調控痛風免疫信號通路關鍵因子NLRP3和NF-κB,miR-155下調免疫抑制因子SHIP1,促進痛風發生;而miR-146a抑制促炎因子IL-1β、TNFα,抑制痛風發生。這些研究盡管為開展痛風精準醫學研究提供了一些依據和支撐,但由于研究對象、手段和結果的局限性,尚不足以建立精準痛風分子分型體系。
蛋白組、免疫組以及代謝組學方面,VALIMAKI等[28]發現尿酸鹽晶體影響單核巨噬細胞危險相關蛋白、干擾素響應蛋白、免疫細胞因子的表達。JOU等[29]確認了多種尿酸性腎結石相關蛋白和高尿酸血癥相關差異蛋白。ALBRECHT等[30]發現與尿酸鹽相關的代謝產物包括核苷酸酶、氨基酸和類固醇。LIU等[31]發現基于肌酐、色氨酸、鳥苷和馬尿酸等生物標志物的數學模型可用于識別痛風,且其準確度優于單一尿酸指標。這些發現雖然為痛風多組學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了證據,但由于該方面研究較少,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有待于大樣本、多中心驗證,因此依據這些研究依然不能建立痛風的精準分子分型體系。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尚缺乏大規模痛風臨床樣本的基因組、轉錄組、表觀基因組、蛋白組、代謝組及免疫組學的系統研究,開展痛風的多組學及數據整合研究,對痛風進行早期預測、精準分型和預后評估勢在必行。
2 原發性高尿酸血癥及痛風的精準治療
2.1 原發性高尿酸血癥的精準治療
降尿酸治療是高尿酸血癥治療的關鍵。根據作用機制的不同,目前常用的降尿酸藥物可以分為三類:抑制尿酸合成藥物、促進尿酸排泄藥物和促進尿酸分解的尿酸酶類藥物。隨著對高尿酸血癥發病機理認識的不斷深入,目前出現了更為精準的靶向降尿酸藥物。按照作用機制可大致分為抑制尿酸合成的靶向藥物和促進尿酸排泄的靶向藥物。
2.1.1抑制尿酸合成的靶向藥物 抑制尿酸合成的靶向藥物主要作用于尿酸合成路線的關鍵酶,例如黃嘌呤氧化酶(XO)、嘌呤核苷磷酸化酶(PNP)、次黃嘌呤鳥嘌呤核糖轉移酶(HGPRT)、腺嘌呤磷酸核糖轉移酶(APRT)以及磷酸核糖焦磷酸合成酶(PRPPS)等等,從而抑制尿酸的合成。Ulodesine(BCX 4208)是一種PNP抑制劑,可作用于嘌呤代謝上游途徑,抑制次黃嘌呤核苷、黃嘌呤核苷、鳥嘌呤核苷轉化為次黃嘌呤、黃嘌呤和鳥嘌呤。臨床相關研究結果顯示,Ulodesine 80 mg單藥治療,血尿酸小于60、50、40 mg/L 的達標率分別為30%、21%和0;Ulodesine 240 mg單藥治療,血尿酸小于60、50、40 mg/L的達標率分別為77%、54%以及23%;Ulodesine 40、80、120 mg單藥治療,平均血尿酸下降幅度為27、33和44 mg/L[32]。
2.1.2促進尿酸排泄的靶向藥物 促進尿酸排泄的靶向藥物主要作用于GLUT9、ABCG2、URAT1、OAT等與尿酸排泄密切相關的靶點[18]。
葡萄糖轉運子GLUT9與果糖和葡萄糖重吸收有關,與尿酸的轉運也關系密切。女性中GLUT9遺傳變異可引起3.4%~8.8%血清尿酸濃度變化,男性中為0.5%~2.0%。GLUT9靶向藥物目前已有3種,是目前精準靶向治療的研究熱點。Tranilast是一種作用于GLUT9轉運體的藥物,在日本被批準用于治療哮喘及其他過敏性疾病,后被發現具有降尿酸作用。Ⅱ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分別應用Tranilast 300、600、900 mg/d治療1周,可使平均血尿酸水平降低11、32和33 mg/L[33]。
尿酸轉運子URAT1是腎近端小管S1段以及S3段尿酸從腎小管腔重吸收的關鍵離子通道。URAT1遺傳變異是導致尿尿酸排泄減少、血尿酸水平升高的關鍵因素。針對URAT1的靶向藥物迄今已有8種,也是目前精準靶向治療的研究熱點。雷西納德(Lesinurad)是一種URAT1抑制劑,目前已在美國和歐洲批準上市。RDEA3170是一種新型URAT1抑制劑,與其他促尿酸排泄藥物相比,該藥對URAT1的親和力高,降尿酸的作用更強[33]。Levotofisopam是一種用于治療各種壓力或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相關性疾病的苯二氮類藥物,被發現具有通過抑制URAT1從而達到促尿酸排泄作用。已開展的2個Ⅰ期臨床試驗發現,其具有快速降尿酸的作用,雖然其降尿酸機制尚不明確,但證實其具有增強尿酸排泄的能力[33]。
有機陰離子轉運體(OAT)家族蛋白是一類尿酸轉運蛋白,參與了腎臟近曲小管對尿酸鹽的轉運過程。其中,OAT1和OAT3位于基底外側膜,為尿酸分泌蛋白。OAT4是已發現的有機陰離子轉運體家族中為數不多的介導尿酸重吸收的蛋白,主要表達于腎小管上皮的刷狀緣側和基底外側上,通過轉運尿酸鹽與α-酮戊二酸或羥基離子完成重吸收的過程。UR-1102是一種新型的URAT1、OAT1和 OAT3抑制劑。動物實驗發現,UR-1102降尿酸的效能高于苯溴馬隆[34],但迄今其他關于UR-1102的進一步研究還未見報道。Arhalofenate是一種OAT4 抑制劑,Ⅱ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應用Arhalofenate 200、400、600 mg/d后,與安慰劑組相比,血尿酸的達標率(<60 mg/L)分別為48%、78%、83%,降尿酸效果明顯[32]。
ABCG2轉運蛋白主要表達在腎小管上皮細胞刷狀緣側,是一種尿酸分泌蛋白,約有10%的白種人痛風與該缺失突變相關。ABCG2基因有望作為別嘌呤醇用藥有效的篩查基因,也是潛在的高尿酸血癥的藥物作用靶點,但目前尚無針對ABCG2的靶向藥物[32]。
2.2 原發性痛風的精準治療
抗炎鎮痛治療是痛風急性期的常規治療,傳統抗炎鎮痛藥物的作用靶點較廣泛,因此導致起治療作用的同時,常常出現一定副作用,限制了他們的應用范圍。作為一類新型抗炎鎮痛藥物,生物制劑可以根據痛風的發病機制,針對炎癥通路中的特異靶點進行干預,從而達到治療痛風的目的。針對治療靶點的不同,可用于治療痛風的生物制劑有TNF-α阻斷劑、IL-1受體拮抗劑等。
2.2.1TNF-α阻斷劑 益賽普(Etanercept)是一種TNF-α阻斷劑,該藥在治療原發性痛風急性發作期患者中起效迅速、作用明顯。同時,用藥后不良反應發生率較之秋水仙堿相對更輕,常見的不良反應主要有注射部位瘙癢、疼痛等,部分嚴重者可能會出現皮疹、發熱以及咳嗽等癥狀,但發生類型較之秋水仙堿也相對更輕。TAUSCHE等[35]應用益賽普治療1例重度痛風發作患者,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2.2.2IL-1受體拮抗劑 阿那白滯素是一種IL-1受體拮抗劑,與IL-1α及IL-1β競爭性結合IL-1受體,阻止IL-1信號傳導;盡管沒有關于阿那白滯素治療急性痛風的安慰劑對照或隨機對照試驗,目前已有初步研究和臨床報道表明,阿那白滯素治療痛風急性期和亞急性期有效;根據目前的研究提示,使用阿那白滯素3~5 d可能改善痛風發作,然而治療劑量、間隔時間和療程仍需進一步探索[32]。
卡那單抗是IL-1β的單克隆抗體,其半衰期達23~26 d。兩項Ⅲ期臨床研究比較了一次注射卡那單抗150 mg和一次注射醋酸曲安奈德(TA)治療急性痛風發作的療效,研究發現卡那單抗150 mg比TA 40 mg可以更快緩解病人疼痛。2013年,卡那單抗成為唯一經歐盟批準用于治療頻繁痛風發作的IL-1抑制劑,適用于過去12個月中痛風發作≥3次,且NSAIDs和秋水仙堿藥物不耐受、存在禁忌或療效欠佳,并且不適合重復使用激素治療的患者。但由于卡那單抗治療可能伴隨感染風險增加、白細胞計數減少、肌酐清除率輕微下降和高甘油三酯血癥,考慮到風險/獲益比,FDA沒有批準卡那單抗用于痛風的治療[32]。
利納西普是可溶性誘騙受體,可以與IL-1β結合,從而阻止IL-1與細胞表面IL-1受體的結合。與傳統NSAIDs相比,利納西普治療痛風性關節炎并無優勢,但也不劣于NSAIDs,目前關于利納西普治療痛風性炎癥的進一步研究未見報道[32]。
3 小結與展望
精準醫學模式的提出集合了諸多現代醫學科技發展的知識與技術體系,體現了現代醫學理念“簡單到復雜,復雜到精準”的發展趨勢,也代表了臨床實踐發展的方向。痛風和高尿酸血癥的精準醫學涉及高尿酸血癥的精準分型、精準治療及痛風性關節炎的精準分型和精準治療。目前國內外學者已發現了多個與原發性高尿酸血癥密切相關的易感基因,開展原發性高尿酸血癥精準分型和靶向治療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但目前針對尿酸合成增加的靶向藥物較少,針對尿酸排泄減少的靶向藥物雖然較多,但針對尿酸排泄關鍵離子通道ABCG2的靶向藥物較少,仍需進一步研究。另外,目前國內外學者發現的痛風性關節炎的易感基因較少,開展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精準分型和精準治療的條件尚不成熟,有待于繼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