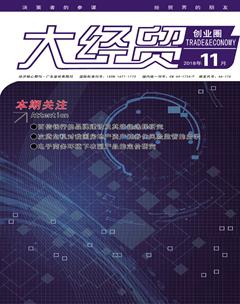淺析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機制的問題與完善路徑
【摘 要】 在我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大及地方各級人大,憲法賦予人大以立法權。這就要求所有立法必須以民為本、表民所愿,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而實現這一基本目標的必由之路,就是健全“人大主導立法”體制機制。本文從人大主導立法入手,著重分析當前我國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機制的問題,并針對現有困境提出建議性的完善路徑,希望有所裨益。
【關鍵詞】 地方人大 主導 立法機制 問題 路徑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可見,人大在立法的系統工程中發揮著“引領者”的作用。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有利于提高地方立法活動的科學性與民主性,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舉措。因此,分析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機制的問題與完善路徑,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與重大的法治意義。
一、地方人大主導立法的概念
“人大主導立法”就是指在我國立法過程中,應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決定并引導立法項目、立法節奏、立法進程、立法內容和基本價值取向。它是一項立法原則,同時也是立法體制和機制。地方人大主導立法,顧名思義,即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相較于其他地方主體,應居于優勢地位,并藉此對立法的方向、進程及結果發揮決定性作用。
二、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機制的問題
(一)地方立法權界限模糊。憲法、組織法與立法法確定了我國“統一兼分層”的立法體制。立法法第七十二條、七十三條、七十四條雖明文規定了我國地方人大的立法主體與立法權限,但該規定不僅在法律條文中難以分清,法律實踐中也難以界定其范圍。例如實踐中很難確定什么叫“根據需要”“認為需要”或“地方性事務”,這種模糊條款無疑為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規增加了難度,地方人大很難確定具體在哪個方面有權制定地方法規。此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環境日趨復雜,新興事物層出不窮,為應對多變環境而制定法規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受制于憲法性法律對地方人大權力的嚴格限制,地方人大很容易越權制定地方性法規。尤其是在稅收、金融等明確屬于法律絕對保留的領域,可能產生與國家立法權相沖突而歸于無效的結果。國家專屬立法權中的某些模糊用詞,如民事基本法律制度,看上去給地方立法留下空間,實踐中卻由于中央立法采取嚴格解釋反而限制了地方立法權限。
(二)地方立法“部門利益傾向”突出。出于立法需求,地方立法議案基本上由政府部門起草,他們往往從本部門利益出發,自己為自己立法,使法規草案帶有明顯的“部門利益傾向”。這種弊端致使法規在立法內容上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忽視社會、政治、生態效益;也為政府部門減輕、推卸自我責任提供有利條件,因而必須采取措施破除這一頑癥。“部門利益傾向”使得地方性法規的民主性與科學性大打折扣,某種程度上淪為了政府部門謀取己利的工具,因此要強化對政府立法的主動審查,夯實人大立法的主導作用。
(三)地方人大自身建設不足。地方人大自身立法能力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人大代表數量雖多,但專職化、專業化程度不夠,很難勝任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都是相對固定的短期會期制,無法提供充足的立法保障時間;加之,人大立法經費需要政府劃撥,立法經費得不到充足保障。這些因素大大削減了地方人大立法的質量與水平,必須從源頭上予以解決。
三、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機制的完善路徑
(一)健全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機制。堅持黨的立法領導是開展一切立法工作的必要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方立法實踐也同樣離不開。黨對立法機關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絕非直接干預、包辦代替,要明確黨委領導的事項、形式和程序,并嚴格執行,實現黨委領導立法的工作制度化、規范化。
(二)加強地方人大立法能力建設。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大代表制度,推進人大代表與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專職化、專業化,加強人大專委會、工委會建設,給予編制、經費保障,提升立法能力;建立人大組織內部人員立法能力定期培訓制度,增強其履職能力;加強立法工作隊伍建設,大力推進立法隊伍的正規化、專業化和職業化。
(三)健全參與機制。地方人大主導立法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因此需要拓寬公眾參與立法的渠道,建立多形式的多方參與機制。搭建多層次、多維度的參與平臺,建立健全專家庫制度,引入委托第三方參與立法、第三方立法評估等機制。拓展代表參與立法渠道,創新代表參與立法形式,邀請相關代表參與立法起草、論證、調研、審議等活動,認真聽取和吸收代表提出的意見建議。加強立法信息公開力度,重視公眾意見反饋結果,提高社會各方參與立法的熱情與活力。
四、結語
立法是一項浩大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地方立法亦是如此。地方人大主導立法機制的運行,是需要多領域、多部門的相互協調、配合,需要黨的領導、全國人大的指導、政府及其部門的配合、人大常委會的互通、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因此,堅持和落實“人大主導立法”原則,就要健全、完善乃至重塑作為其實現途徑的體制機制。使得地方立法權限在受到嚴格限制情形下,仍能充分發揮自身主動性,積極制定良法,保證法制統一。
【參考文獻】
[1] 劉平.立法原理、程序與技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0
[2] 阮榮樣.地方立法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9
[3] 桂宇石,柴瑤.關于我國地方立法的幾個問題[J].法學評論,2004.5
[4] 周旺生.關于地方立法的幾個理論問題[J].行政法學研究,1994.4.
[5] 封麗霞.健全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J].學習時報,2014.11
[6] 李高協.關于發揮人大立法主導作用的分析思考[J].人大研究,2013.2
作者簡介:趙亞龍(1994- ),男,漢族,新疆伊犁人,法學碩士,單位: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研究方向: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