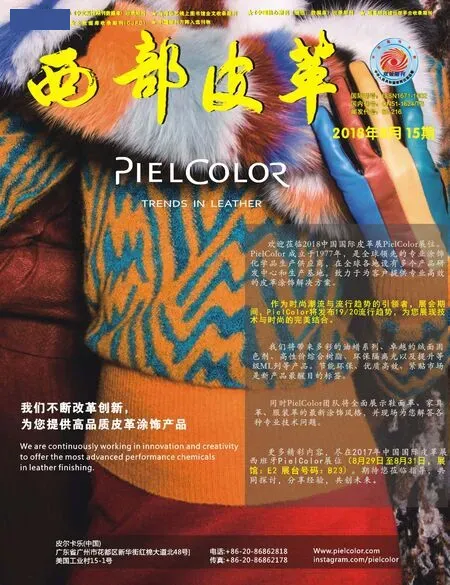城市與鄉村:二者的對立與互滲
于爽
我印象中的鄉村與城市,幾乎是呈兩極化的狀態存在著,同時,它也反映了當下的社會狀況存在著二重性。那就是既有落后的一面,又有美好的一面。今天的鄉村代表著一種落后,城市則代表著一種文明,而今大部分人愿意生活在城市。魯迅認為城市與鄉村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所以不能單純的把鄉村和城市看作落后與先進的象征。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在其《鄉村與城市》一書中描繪了英國鄉村與城市的景象,他的描繪或許對我們的當下是一種暗喻。
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對鄉村與城市的各種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主要辯駁了部分學者所堅持的“消逝的農村經濟”、“快樂的英格蘭”、“黃金時代”等緬懷舊日農村的錯誤觀念,并且威廉斯指出以上的觀點只是作者的想象,無論是從作家的作品,還是歷史事實,都呈現出了昔日的英國鄉村并不是我們理解的田園,而是充滿了苦難,然而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既不是充滿歡樂的故園,但它也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與此同時,城市雖然日益發達,但它也不完全象征著進步,因為在新的生產方式確立后同樣也產生了很多問題,在城市興盛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因此,雷蒙·威廉斯認為,城市無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我們把“鄉村”與“城市”放在中國歷史語境下觀看,中國近代“城市”的興起是與“鄉村”分不開的,五四以來城鄉關系形成了二元對立。近現代興起的許多新興城市,例如:上海,殖民者借此傾銷商品并且要運出原材料,因而這些近現代城市形成了一個特點:被壓迫、被抽血;而這些城市又從鄉村中抽血壓榨,城市與鄉村又變成了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長此以往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新中國成立后對城市進行了改造,勵志把消費型城市改造成生產型城市。上海這類城市最初形成之時并無反哺能力,富人與中國底層民眾的消費斷裂,并且通過榨取農民的剩余價值來實現工業化,而今天許多城市發展與當初的構想卻是背道而馳,如此就形成了一種畸形的城鄉關系。
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出現了描寫鄉村的題材,這些鄉土小說作家筆下的鄉村景象都是荒涼破敗的,民俗是粗魯野蠻的,農民是愚昧無知的,他們對于鄉村都秉持著批判的態度。而作家沈從文卻獨到的發現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矛盾沖突,沈從文對城市文明做出了有力的批判,他認為城市文明的發展是對鄉村的一種入侵,而鄉村生活是質樸的,鄉村人民是充滿其原始野性的,這就表現出了一種生命活力,而這種旺盛的生命活力并不需要城市的物質和消費來進行入侵,這是對鄉村的一種破壞,沈從文認為鄉村人民淳樸、善良,城市人表現得很文明,但內心卻是虛偽的,所以鄉村并不需要這種表面的“發展”。沈從文的鄉土小說著力于描寫鄉村的美,他頌揚湘西人身上的野蠻性,他描寫了湘西世界蠻荒的自然狀態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強力、元氣以及旺盛的情欲,讓讀者領略到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與強健。他的地方意識開始覺醒并得到強化。他要展現這種奇異世界,并在其中闡釋他理想中的人生境界,為民族靈魂的再造提供他獨特的方案。他的筆下不斷出現水手,寫他們身上的原始的生命強力,寫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他筆下的鄉村是一首田園牧歌。沈從文筆下的鄉村是現代性敘事的產物,他的寫作有著一定的政治性,正是認識到了現實的不美好,沈從文才寫出了這樣的鄉村,沈從文是站在城市空間里回想鄉村,他認為現代鄉村有一定的可取性,他比其他作家多了城市與鄉村的比較。
一座好的城市應該是怎樣的?我首先想到的是這一組詞:“民主”、“平等”、“共同生活”......王曉明在《弱勢者的空間》一文中說到:“城市的公共空間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弱勢者的空間”,這個空間的大小與好壞,可能是衡量城市生活的一個關鍵的標準。”在傳統的城市空間中,城市中的“弱勢者”往往象征著這個城市的陰暗面和諸多的不文明,他們往往被歧視,生存于城市中的小角落,他們向我們展現出了“弱勢者”的生存結構和生存空間,隨著近年來的城市化進程,這些“弱勢者”的生存空間卻變得更加狹小了。
事實上,在鄉村與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一直都存在并且不斷產生著各種問題,人們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卻是矛盾又復雜的,一方面,人們向往著大都市生活的繁華,物質社會的急速發展使很多人們喪失了初心,另一方面人們又羨慕鄉村生活的安逸,但又抗拒不了大都市的物質吸引。城市生活看上去很繁華,背后卻隱藏著深深的無力感;鄉村生活看上去很美好,背后卻缺少了可持續發展的可能;今天的中國社會急速發展,與此同時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對于新興事物的態度,到底是抵制還是迎合,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