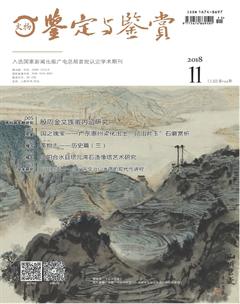關于義縣花爾樓出土青銅器的解讀
李海艷



摘 要:1979年遼寧省義縣花爾樓出土了5件商周時期窖藏青銅器。這組青銅器造型古樸、莊重,是錦州地區青銅窖藏的代表,對于研究商周時期東北地區的青銅文化和疆域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青銅器;青銅文化;北方草原文化; 孤竹國
1 青銅窖藏
1979年4月在錦州市義縣北邊的稍戶營子公社花爾樓大隊靠近醫巫閭山的西麓坡地上出土了一批共5件青銅容器。這些器物被發現時無其他物同出,屬窖藏。5件器物包括青銅鼎1件、青銅甗2件、青銅簋1件、青銅鈴俎1件,形制如下:
青銅鼎:通高32.8厘米,兩直耳稍外撇,三柱足,足高11厘米,頸部飾有饕餮紋(圖1)。
青銅甗:均為鬲、甑合鑄體,大小不一。大甗方唇、敞口,通高52.7厘米,索狀雙直耳稍向內傾,腹壁較直,腰緊束,內無箅,僅有置箅臺一圈,分襠柱足,頸部飾有3周凸弦紋,足部飾獸面紋(圖2);小甗通高44.8厘米,與大甗形制大體相同,耳無索狀,頸部飾一周饕餮紋,分檔柱足較矮(圖3)。
青銅簋:通高14厘米,侈口,斂頸,腹微鼓,高圈足,口沿外飾有蟬紋,頸部與圈足均飾夔紋,腹部飾有3組饕餮紋,通體等距離飾6道扉棱(圖4)。
青銅鈴俎:長33.5厘米,寬17.8厘米,高14.2厘米。上面作長方盤形,下為相對的倒“凹”字形板足,板足呈壼門狀,飾有精致的饕餮紋和乳釘紋,襯以云雷紋地。板足空當兩端各懸扁圓形小銅鈴1個,鈴上均有對稱扉子,一鈴為素面,一鈴飾有單層紋飾,其制作精巧,器形獨特,比較罕見(圖5,圖6)。
這批青銅器從形制和紋飾上看,鑄造年代應當在商末周初,其中簋可能制作于商中期,甗應屬西周初期。
青銅器是中國青銅文化的精髓,自產生之初就被賦予了那個時代的鮮明特征。中國的青銅文化起源于黃河、長江、珠江流域,距今約5000年,止于公元前5世紀,大體上相當于考古上的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時代,及文獻所記載的夏、商、西周、春秋時期,與中國的奴隸制國家的產生、發展和衰亡相伴。青銅器在長達15個世紀的發展進程中,也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高峰、轉折停滯、再高峰、衰退的過程。商周時期便是青銅器的鑄造和使用非常興盛時期。青銅器是指用紅銅、錫、鉛等合金鑄造的器物。青銅器有三個顯著的優點:一是熔點低,300攝氏度左右就能熔化和鑄造,省時省力;二是硬度高于純銅;三是加鉛的銅液減少氣泡,使其在模范里流淌順暢,更利于鑄造出銳利的鋒刃和精美細密的紋飾。商周時期無論是銅或錫,其礦藏在中原地區都是很匱乏的,青銅被世人認為是稀有貴重的東西,被稱為“吉金”,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夠擁有和隨便使用,只有國家統治階層才有資格擁有和使用,是貴族世家的標志,在廟堂中不可缺少。青銅器是古代帝王權力、地位與身份的象征,彰顯了古代帝王身份的尊貴,被稱為國家政權、等級制度的物化形式。
西周時期是我國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周王朝為了鞏固統治,加強了對諸侯的控制,從政治到文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史書上說的“周王制禮作樂”,就是指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禮樂制度其實就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秩序,鞏固王室政權的等級制度。這時,只有貴族有權使用的青銅器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普通的青銅生活用具演變為禮樂制度服務的器物,包括鼎、彝、鐘、簋、尊、爵、卣、豆等。這些禮器被統治階級在繁文縟節的儀式中使用,陳于廟堂,或用來祭天、祭祖、盥洗、宴饗賓朋、賞賜功臣、記功頌德,或用來死后隨葬等。
商代禮器的重酒體制自周初開始轉變為重食體制,盛行以鼎、簋、鬲、甗的食器組合。花爾樓出土的5件青銅器實物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鼎、簋、甗、俎在用途上屬飪食器,但隨著西周禮樂制度的強化,它們同時也具有禮器的屬性。鼎和簋是炊具,鼎用來烹煮,簋用來盛食物,相當于現在的大碗,后來鼎演變成為權力和等級的象征,是最重要的青銅禮器之一。《周禮》記載:“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鼎和簋奇偶數相配表示了嚴格的身份等級,使用者必須根據身份等級恪守法度,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亦是如此。甗是蒸飯器,由鬲和甑組成,相當于現在的蒸鍋。青銅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鑄造,但為數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為數已較多,特別是西周末、春秋初,甗是絕大多數殉葬禮器的必有之物。俎是專門盛載家畜的禮器,而且只許盛放“三牲六畜”,其他鳥獸之肉不允許擺放,祭祀儀式中與鼎、豆并用。《周禮·膳夫》載:“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禮記·燕義》說:“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俎的形狀為長方形案面,中部微凹。這種形狀設計一是為了盛放祭祀牲體時不滑落,二是防止牲體的血溢出來。古代祭祀是國家的大事,用俎的地方非常多,但因年代久遠,出土和傳世的青銅俎都極其稀少,或許是當時的俎多為木制不易保存。而義縣花兒樓出土的這件青銅鈴俎,獨具匠心,屬國內罕有。
2 北方青銅文化
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遼西錦州地區整個青銅時代的歷史基本以夏家店下層文化、魏營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代表,年代跨度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鑄造業已相當發達,種類、數量都遠遠超過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幾乎與中原地區同時步入了青銅時代,青銅制品已用于炊具、容器、生產工具、兵器、馬具、裝飾品等方面。這幾種文化受中原地區商文化的影響,又與之互相交融,有些青銅制品不僅兼有本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共同特點,而且在造型創意以及紋飾等方面或更勝中原一籌,創造出獨特的遼西錦州地區的青銅文明[1]。
這5件青銅器以典型的中原式青銅器為主,但也融合了一些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其中鈴俎器形和花紋都是典型的中原式風格,饕餮紋及雷紋在我國中原出土的同時期青銅器上非常多見,但板足襠內懸雙鈴且鈴體甚大,這是比較少見的。懸鈴銅器時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地域分布上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到目前為止出土的懸鈴銅器中,商代晚期的共有8件,主要出土于陜西中北部;西周早期共13件,主要出土于遼寧、江蘇、安徽、陜西和湖北地區;西周晚期共6件,主要出土于山西和湖北地區。器形有觚,簋,尊,豆,盤,簠,提梁方卣,方座桶形器,彝,罍,觶,俎形器等。從出土時間來看,懸鈴銅器最早出現于我國北方地區,后來隨著戰亂和民族遷徙,懸鈴器形傳入中原和江南地區。鈴是我國出現的最早的青銅樂器,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銅鈴是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出土的紅銅鈴形器[2]。考古發現的其他鈴有懸掛在車馬器上的車鈴、殉狗頸下的狗鈴、祭祀用的執鈴,還有系于兵器首端的鈴等。北方民族喜歡用鈴裝飾青銅器可能與他們游牧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懸鈴銅器是北方草原文化與商周青銅文化既相互融合,又互相影響的產物。懸鈴為北方民族所喜愛,在使用過程中能發出悅耳的聲響,尤其是在莊嚴肅穆的宗教祭祀儀式上,突然而至的鈴聲被視為祖先神靈對人們祭祀活動的一種回應,從而增添整個儀式的和諧氣氛和神秘感。所以懸鈴常被商周青銅禮器所吸收,這是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交融的一個例證。
3 孤竹國
窖藏是因為戰亂等突發的原因臨時開挖窖穴用來埋藏珍貴器物,以躲避災害。后來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因某種原因,器物的主人再也沒有機會將它們挖出來,于是它們就被深埋地下三千多年,成為今天我們解讀歷史的寶庫。那么我們在這里推測一下這幾件器物的來源。
這組青銅器的窖藏地點位于醫巫閭山西麓一處坡地上,南臨大凌河的支流。商朝時期王室的主要治理區域還是中原一帶,商初建都于亳,后盤庚遷都殷,因而商也被稱為殷商。商朝實行內外服的地方行政體制。“內服”指商王直接統治的區域,即王畿所在地,由君主直接派官員管理;“外服”是指諸侯國統治的區域,由各地諸侯管理,但外服諸侯與商王是一種君臣關系。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表明,錦州所屬的遼西地區曾屬商朝孤竹國。《史記集解》引應劭注云:孤竹在“遼西令支”。《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條:“令支下有孤竹城。”1973年和1974年在遼西朝陽喀左地區前后出土6批共69件商周青銅器,其中包括著名的父丁孤竹罍。已故唐蘭先生據此以文獻為佐證,李雪琴先生對該器銘文中的“孤竹”二字進行了深一層考證,二者都堅定地認為遼西是孤竹國所在之地。直至今日,在遼西朝陽縣南還有以“孤竹營子”命名的村莊,以此推斷錦州地區在商代屬孤竹古國的管轄范圍應當沒有問題。孤竹國是商王室所封的同姓諸侯國,國君墨胎氏。《史記·索隱》記載:“孤竹君,商湯所封。”孤竹國鼎盛時期的地域涵蓋了河北北部、遼東、遼西和內蒙古東部地區,是商王朝在北方的重要屬國。這一組器物用實物證明了商周時期的版圖已越過大凌河流域,到達了醫巫閭山。
商代中葉,孤竹國發展到了中期,孤竹國與商朝王室往來密切,中原的青銅文化涌進了遼西地區,這是中原文化集中傳入東北地區的開篇之作,中原文化的涌入對遼西青銅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遼西青銅文化。發現于遼西地區的銅器,大部分具有中原風格,有些學者們認為當時本地的青銅鑄造工藝水平還沒有達到與中原相同的高度,推測這批窖藏銅器是從中原帶過來用于祭祀的。還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批銅器是孤竹國匠人在中原青銅文化影響下,鑄造的具有地域特點的青銅工藝品,代表作有小波汰溝出土的圉簋、馬廠溝出土的鴨形尊和北洞出土的龍鳳罍等,造型生動別致,擁有濃厚的北方民族特色。商被周滅亡之后,孤竹成為周的異姓諸侯國,從此逐漸衰弱,成為分封國燕的附屬國。公元前664年,山戎出兵伐燕,燕向齊國求援,齊桓公為救燕出兵伐山戎。公元前660年,齊桓公又“北舉事于孤竹,離支(令支)”,孤竹國滅亡。國雖隕滅,但其創造的絢爛文化及伯夷、叔齊兩君子不食周粟的節操卻被后人傳頌,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影響。
花爾樓出土的這一組青銅器造型古樸莊重,紋飾簡單,由于鼎簋數量不成套數,器身又無銘文,它們不可能是君王的賞賜品,也不能是某個當地貴族的隨葬品。這一組器物很有可能是當地的工匠所鑄造,是用來祭祀或宴請賓客的普通禮器,由于當時不知道發生什么緊急情況(可能戰亂等原因),被它們的主人匆匆地埋在了地下,再無尋回的機會。
參考文獻
[1]王碩.遼寧地域文化通覽·錦州篇[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2]孫明.商周時期懸鈴青銅禮器研究[M]//魏堅.北方民族考古 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