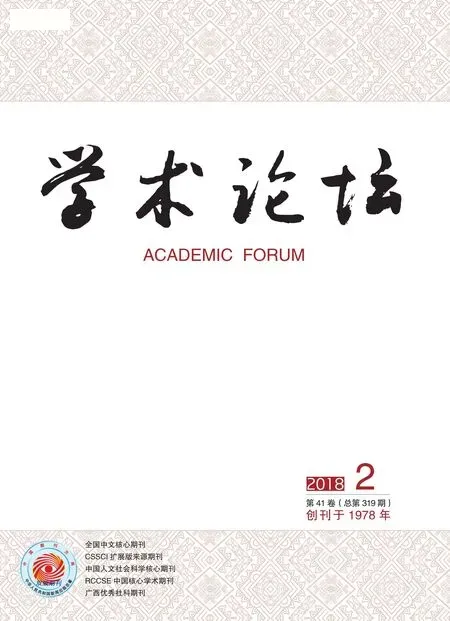論民法典編纂中我國婚姻協議的立法規制
李 俠
雖然我國現行《婚姻法》第十九條規定了婚姻協議,但該條存在諸多弊端和不足之處。例如,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不明,引發諸多學理爭議和法律適用困境;未完善婚姻協議對外效力制度,在強力保護交易安全的同時對當事人利益保護不足;保護弱勢配偶利益的公平原則概念付之闕如。值民法典編纂之際,本文旨在通過域外法的比較和考察,重點探討和分析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形式要件、對外效力和公平原則這幾方面內容,以期為我國婚姻協議立法完善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和思路。
一、婚姻協議的法律圖景
婚姻協議依訂立時間,可分為婚前協議、婚內協議和離婚協議三種基本類型。據現有資料考證,早期婚前協議的歷史起源可以遠溯至古代猶太人稱為“Ketubah”的婚書。現代婚前協議的前身則首次出現于16世紀英格蘭,當時英格蘭衡平法院和普通法法院均認定婚前協議有效[1]。在人類社會早期,婚姻本質主要是建構或擴大家族親屬同盟,而婚前協議則是夫妻雙方婚前訂立的,關于締結婚姻的財產交換等條件的約定。然而,除了名門貴族、富豪商賈以及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還有少數學者外,婚前協議很長時間以來被普通百姓棄如敝履[2],處于婚姻制度的邊際角色。隨著個體自由主義濫觴,家事領域的私主體自治傾向也越來越凸顯。諸多再婚者因為離婚經歷的影響,希圖通過婚前協議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和前婚子女利益。相較婚前協議和婚內協議在實踐中被采用的逐漸增加,離婚協議因離婚率的攀升而在三種婚姻協議中最經常被采用。由此可見,多重因素的疊加導致婚姻協議在現代社會婚姻財產法領域中占據的地位愈加重要。
二、婚姻協議域外法的考察和比較
各國婚姻家庭立法的歷史背景、發展階段與特點存在相當大差異[3],考察和比較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婚姻協議的立法和司法經驗的研究工作可能更富有貢獻和價值意義,“因為司法四分五裂之際,往往是學說大有可為之時”[4]。
(一)大陸法系國家
基于婚姻協議內容實定化的證明效果、強化交易安全等因素的考量,大陸法系國家的婚姻協議立法一般注重從以下幾方面作出規制。一是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在奧地利、比利時、法國等國,當事人既可從本國或國外的夫妻財產制中選擇其一,亦可自行創設夫妻財產制。在丹麥、意大利和瑞士等國,當事人僅能從本國法律提供的幾種夫妻財產制中選擇其一[5],以免“配偶間任其自由訂約,漫無標準,則人各異其制,而第三人與之交易,殊感困難,在社會上亦覺不便”[6]。二是婚姻協議的形式要件。在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瑞士,婚姻協議必須公證。在丹麥和芬蘭,書面婚姻協議必須注冊登記。三是婚姻協議的效力。在大陸法系大多數國家,婚姻協議一般具有效力,僅在合意無效或者包含有違公序良俗條款的情形下被認定無效[7]。
(二)普通法系國家
著名法律史學家Maine最為人所知的名言是,“迄今為止,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8]。然而,Maine關于身份轉向契約的論斷在大陸法系婚姻協議立法模式中體現得更為明顯。相較大陸法,普通法大體上抵制婚姻語境下契約自由的高歌猛進[9]。早期普通法在理論或制度上排斥、不肯承認涉及離婚財產清算事項的婚前協議有強制執行效力,其主要理由在于婚前協議變更法定離婚財產清算規則可能誘發離婚風險,有悖于贊成婚姻永續的公共政策。隨著普通法的演變發展,契約自由在家事法領域越來越呈現擴張傾向。1970年美國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判決的Posner v.Posner一案標志著美國開始肯認涉及離婚財產事項的婚前協議有效①Posner v.Posner,233 So.2d 381(Fla.1970).。然而,美國諸多州仍規定法官必須依據公平原則對婚前協議是否具有強制執行效力進行審查,以保護弱勢配偶免受重大婚姻財產利益損失。2010年英國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Radmacher v.Granatino一案中確立了認定婚前協議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標準②(2010)UKSC42.。由此可見,在諸多普通法系國家,法院審查婚前協議是否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標準比普通合同更加嚴格。
(三)兩大法系婚姻協議的法律規制存在差異性與共通性
前文對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婚姻協議立法模式所作的簡短闡述,或即使是任何浮光掠影的一瞥,都足以顯示出兩者的制度理念存在歧異。前者注重規制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和形式要件;后者考慮和討論的焦點卻是當事人雙方間關系所產生的合理附帶權利義務內容,以及如何在婚姻協議立法中體現這種權利義務。那么,究竟是何種原因造成兩者存在差異?龐德富有洞見地指出,大陸法賴以為憑的理論內核是意志,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法律制度關乎法律交易,普通法的核心要點卻不是意志,而是關系[10]。據此,兩大法系的婚姻協議立法模式受法系特征影響至深。但隨著現代社會呈現“私法公法化”或“身份法公法化”趨勢,兩大法系有關婚姻協議的法律規制也存在共通性。例如,婚姻協議的訂立需遵守形式或程序強制,以保障當事人知悉締約的法律后果;通過立法或司法判例的類型化保護弱勢配偶利益;將婚姻協議效力分為對內效力和對外效力,平衡當事人利益和交易安全。
三、我國民法典編纂中婚姻協議立法完善的探討
我國現行婚姻協議立法過于簡略和粗疏,無法充分發揮法律規范的確定性指引作用。本文擇其要端,擬圍繞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形式要件、對外效力和公平原則這四方面展開闡述,以期為我國婚姻協議的立法完善以及補苴罅漏提供有益思路。
(一)擴張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
當前我國學界和司法實踐皆對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問題施以極大關注和側重,其中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的定性既是司法實踐中婚姻協議糾紛爭議的焦點,也是婚姻協議立法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點。毋庸置疑,討論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需要明確的前置性問題是我國究竟采用何種約定財產制。
1.《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范含義的兩種解釋。我國學界和司法實踐對《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的規范意義或內涵存在兩種解釋。第一種觀點認為,該條采選擇式約定財產制,規定了分別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這三種夫妻財產約定模式[11];另一種觀點認為,該條采自由式約定財產制,規定的幾個選擇項囊括了一切可能性[12]。評析上述哪種觀點更具有合理性,關鍵在于厘清和甄別不同語境下婚姻協議的準確含義。狹義的婚姻協議,指選擇式約定財產制下的夫妻財產制協議,內容是當事人從法律規定的幾種夫妻財產制中選擇的某一種夫妻財產制,并非某項或某些特定財產約定。廣義的婚姻協議,指自由式約定財產制下的夫妻財產協議,內容既可以是一種夫妻財產制,也可以是某項或某些特定財產約定。換言之,當事人約定的“夫妻財產不必及于全部財產,對于一定之個人財產,亦為可能”[13]。最廣義的婚姻協議,內容可以涵括夫妻財產約定和其他約定事項。例如,在美國諸多州,婚前協議內容除可以是夫妻財產約定外,還可以是不違反公共政策或刑事法規的包括人身權利和義務在內的任何其他約定事項。由此可見,隨著約定內容涵攝范疇的遞進式擴張,夫妻財產制協議、夫妻財產協議與婚姻協議依次具有概念從屬關系,因而可以統合在婚姻協議這一概念之下。在選擇式約定財產制下,當事人選擇的任何一種夫妻財產制均是整體建構式閉合體系,約定內容被框架性限定。與之不同,我國《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幾個選擇項可以經排列組合構成復雜的混合型夫妻財產制,如婚前財產與部分婚后財產歸各自所有,部分婚后財產共同所有。就此而言,與其說該條采選擇式約定財產制,不如說采自由式約定財產制更妥適。
2.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的定性探討。在我國現行婚姻法與合同法等多部法律的整體法律效果下,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與夫妻贈與經常難以區分:其一,婚姻協議法定形式是書面形式,贈與以不要式為原則。但贈與房地產應當采書面形式,實踐中許多當事人對標的物并非房地產的贈與也選擇簽訂書面合同,由此造成婚姻協議與書面贈與的形式相同。其二,我國采自由式約定財產制,婚姻協議與書面贈與內容均可以是夫妻間財產無償讓與,于是兩者界限進一步模糊。那么,應當如何規制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與夫妻贈與之間的關系?我國學界和司法實踐采取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路徑是兩者統一適用合同法。《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六條采用該路徑,其理論依據是我國采選擇式約定財產制,一方所有財產約定為另一方所有不適用婚姻法第十九條[14]。若仔細推敲,以下幾方面尚存疑義:其一,基于贈與的無償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賦予贈與方任意撤銷權,保護贈與方利益。與之不同,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表面上具有無償性,但婚姻協議內容往往是夫妻雙方在討價還價、相互妥協基礎上談判和協商確定的結果,條款之間可能構成相互依存的對價關系,并不涉及一般意義上的保護贈與方利益問題,如“自結婚登記之日起甲的全部財產與乙共同所有,乙的房產A歸屬于甲所有”。若認定前款是婚姻協議,后款是夫妻贈與,在乙行使任意撤銷權的情形下,甲無償給予乙的財產份額將成為無法收回的沉沒成本,導致婚姻協議條款之間的對價關系失衡。其二,即使婚姻協議條款之間不構成明確對價關系,但夫妻雙方實施的包括締結婚姻協議在內的諸項行為可能構成婚姻語境下關系契約的具體履約內容,贈與條款的對價是隱性的,包括一方對另一方債務的承擔或情感補償等。不過,基于婚姻共同體內身份關系與財產關系緊密關聯的錯綜復雜的情狀,婚姻協議毋需以獲得對價為必要。其三,在《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缺乏清晰規范意義的背景下,字面解釋必須讓位于更趨實質性之考量。夫妻財產歸屬約定實質上涉及夫妻財產性質轉化,包括共同財產轉化為個人財產、個人財產轉化為共同財產、一方個人財產轉化為另一方個人財產,這三種轉化均具有一方無償給予另一方財產份額的性質,并無本質差異。若將前兩種轉化納入婚姻法第十九條適用范圍,而將第三種轉化排除在外,似乎有進一步斟酌的余地。
第二種路徑是兩者統一適用婚姻法,原因在于身份關系是劃分夫妻財產關系和一般民事主體間財產關系的標準,亦是適用婚姻法和合同法的分水嶺。有學者認為,該路徑有利于保護受贈方利益,但存在贈與方輕率允諾后遭受財產利益損失的剛性問題,因而建議由法官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平衡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15]。該觀點力圖在規則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取得適度平衡,但我國遵循大陸法系立法例,法官不輕易直接以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作為裁決依據,贈與方尋求法律救濟的請求可能得不到法官支持,因而面臨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高昂和消耗司法資源的不利因素。
第三種路徑是對兩者予以二元區分,但當前學界和司法實踐尚未就如何區分兩者達成共識。有學者認為,《婚姻法》第十九條采夫妻財產制協議概念,夫妻財產制協議與夫妻贈與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當事人選擇的具有繼續性特征的能夠直接產生物權變動效力的夫妻財產制,屬于附隨的身份行為;后者僅涉及某項特定財產權利歸屬,與夫妻身份關系并無緊密聯系,僅發生債的效力[16]。有學者認為,當事人就某項特定財產加以約定是我國夫妻財產約定常態,一直為立法和司法實踐所準許,應推定夫妻雙方訂立的內容不明確的房產變動協議為婚姻協議[17]。有學者認為,夫妻之間給予不動產約定的性質,應當探尋當事人的約定意圖,并結合婚姻法規定的夫妻財產制類型予以綜合判斷[18]。
在上述三種路徑中,前兩種是一元路徑,后一種是二元路徑。那么,哪種路徑更具有合理性?采自由式約定財產制的域外法或許可以為解決該問題提供有益思路。在法國,夫妻雙方可以通過婚姻協議進行財產贈與約定[19],但變更贈與條款須在約定財產制實施二年之后,夫妻雙方得為家庭利益,通過夫妻住所地法院認可的公證文書予以協議變更[20]。一般贈與不得任意撤銷[21],但夫妻在婚姻期間所進行的一切贈與卻始終得予撤銷[22]。夫妻贈與的撤銷,可依據贈與方實施的明確表明其有撤銷夫妻贈與之意圖的任何事實或行為而產生[23]。在美國諸多司法轄區,夫妻間財產無償讓與分為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兩種形式:采婚姻協議形式的,適用婚姻協議立法或合同法;未采婚姻協議形式但符合贈與要件的,是夫妻贈與。婚姻協議生效后不得任意解除,受贈方取得贈與財產的既得權或期待權;美國普通法將贈與定位為實踐合同,有利于保護贈與方利益。在一般贈與下,贈與財產權利轉移之后,受贈方通常終局性取得贈與財產。但美國佛羅里達等州規定,婚姻存續期間夫妻間贈與的財產是離婚時可被分割的婚姻財產,而非受贈方個人財產。
由上可知,在法國和美國諸多司法轄區,婚姻協議與夫妻贈與、一般贈與和夫妻贈與均存在差異,受贈方利益受保護的強度大致可以歸結為:婚姻協議高于夫妻贈與,一般贈與高于(或等于)夫妻贈與。于此情形下,雖然身份關系是劃分家事法與物權法、合同法等財產法的重要標準,可以作為討論劃分夫妻間財產無償讓與和一般贈與問題的契入點,卻難以為透視區分夫妻間財產無償讓與兩種方式(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的必要性和機理提供更深入解釋。換言之,身份關系并不是釋明家事法內部法律規范機理的惟一因素。即使依憑身份關系將婚姻協議與夫妻贈與均視為附隨的身份行為,但隨后又會出現邏輯上的“拐點”,即必須藉由身份關系之外的“次級依據”或“第二層次依據”(secondlevel reasons)對兩者予以進一步厘清和甄別。拉倫茨指出,在研究契約類型時必須留意隱藏其后的當事人間典型的利益和風險分配,依此才能凸顯契約規整的特征,并對其重要性予以適當評價[24]。本文的初步思路是,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是整體主義和單一主義方法論差異下的兩種不同權利配置和資源配置模式。在此意義上,法律經濟學視角下的利益衡量可以作為區分兩者的“次級依據”。
其一,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立法思路存在差異。基于婚姻語境下復雜、多面和微妙的身份關系與財產關系相互交織的事實,婚姻協議立法采整體主義方法論,以身份關系為軸心,充分擴張當事人在約定事項范圍方面的契約自由,準許當事人通過婚姻協議對夫妻財產的靜態歸屬、動態利用、債務負擔和子女撫養等多項法律關系進行“一攬子”約定。在此思路下,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以特定方式與其他條款結合成一種有意義的、彼此關聯的規整,或被內嵌為婚姻共同體內成員間整體行為結構的一個節點。與婚姻協議不同,夫妻贈與依循單一主義方法論,突出的是典型個別性契約中當事人利益的分離性和自立性,而非統一體的凝聚性和合作性。
其二,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立法思路差異建基于兩種不同權利配置和資源配置模式的分析框架。家庭經濟學理論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貝克爾創設的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家庭生產理論。該理論將家庭視為企業,家庭功能是整合家庭成員擁有的時間和各種商品等可用資源,生產出其所需的產品或商品[25]。另一種植根于交易成本經濟學[26],側重分析婚姻語境下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用。兩種家庭經濟學理論均認為,既然可被強制執行的契約權利對于企業或婚姻共同體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那么也可以通過設置契約權利保護措施來激勵當事人選擇進入婚姻共同體和決定將資源投入婚姻共同體。由于允諾的可強制履行在理論上可帶來低交易成本下的最優履行與最優信任,具有激勵人們相互交易與合作的效果,而這正是當事人雙方在最大化預期收益時所需要的,婚姻協議立法旨在建構一種與經濟效用理論密切相關、提供正式且強有力的違信懲戒機制,以及具有成本和預期收益確定性優勢的權利配置和資源配置模式,為當事人雙方通過婚姻協議自愿交換財產權,實現家庭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用最大化提供了可能。在此意義上,婚姻協議是整合一系列契約的基本利益結構單元,其包含的贈與條款是當事人雙方共同協定的家庭資源配置方式,而非贈與方“好意施惠”的贈與。相較婚姻協議,夫妻贈與強調贈與方的單方意志,受贈方能否終局性獲得贈與財產充滿不確定性、未知性和風險性。
其三,在佩雷爾曼看來,“法律在本質上是多元的。它認為諸多價值同時并存并且能夠根據具體情境對不相容的價值予以保護”[27]。因此,立法似乎并沒有追尋普遍性規范[28]。由于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在締約成本、利益承受和風險負擔規則等方面存在緊張對立關系,且契約固有不完備性,兩者中任何其一均無法窮盡和覆蓋各種履約相關狀況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亦無法圓滿解決紛繁蕪雜的社會現實需要,因而法律保持承認家事領域利益多元的謙抑態度,選擇為相互沖突的多重利益的同時并存提供法律制度供給,賦予當事人選擇權利配置和資源配置的開放式空間。科斯指出,人們按照交易成本選擇法律制度[29],當事人可以依據個人偏好或效用在婚姻協議與夫妻贈與這兩種法律制度之間作理性選擇。
綜上所述,雖然婚姻協議和夫妻贈與均可以是夫妻間財產無償讓與方式,但兩者的價值意蘊和利益衡量判然有別,互相不可替代。于此,將夫妻間財產無償讓與簡化為完全有利于贈與方或受贈方的兩種一元路徑呈現互為利弊的逆反構思,均因未體現利益分配的去中心化而欠妥。為契合家庭財產關系復雜多歧的情勢,我國宜采婚姻協議包含的贈與條款與夫妻贈與二元區分路徑,尊重當事人選擇法律制度的自主性。毋庸置疑,此路徑面臨著前述的一個難題: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婚姻協議與夫妻贈與的邊界不夠清晰。如何破解這個難題?從立法技術和立法成本看,形式強制或程序強制仍是規制重要契約關系或法律行為的一種事前最優方式,因而可行路徑是重構當事人締結婚姻協議的意思表示制度,即通過規定婚姻協議的訂立必須遵循嚴苛的形式強制或程序強制增加締約的時間成本和磋商成本,使當事人在充分知悉締約法律后果和意義的基礎上權衡利弊并作出理性選擇,以達致將當事人締結婚姻協議的意思表示與其他締約意圖相區隔的法律效果。換言之,這涉及婚姻協議的形式強制或程序強制的設置合理性問題。例如,基于同樣是當事人雙方共同生活的事實,《婚姻法》第八條以結婚登記作為區分法律婚姻與事實婚姻、非婚同居的形式要件。
3.《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的規范性重構。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是約定財產制理論系統的“骨架”問題,亦是婚姻協議含義的核心要素。《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既未采“何種情況得為”的詳盡列舉式和兜底條款相結合的立法例,亦未采“何種情況不得為”的否定式立法例,自由式約定財產制被確立而未能得到明確定義,存在立法疏漏,因而需要以“破釜重鑄”方式對該款予以規范性重構。在域外法中,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家事法典》第1612條全面、詳細規定了婚前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充分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契約自由①加利福尼亞州《家事法典》第1612條(a)款規定當事人雙方可以就下列所有事項訂立婚前協議:(1)各方就雙方或任何一方無論何時何地獲得的財產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2)就購買、出售、使用、轉讓、交易、拋棄、租賃、消耗、消費、動產轉讓、設立擔保權益、抵押、使承受負擔(或其他法律義務)、處分或以其他方式管理和控制財產所享有的權利;(3)以分居、婚姻關系解除、死亡或者任何其他事件發生或者不發生為條件的財產處分;(4)以遺囑、信托或其他方式履行婚前協議條款;(5)人壽保險單中死亡保險金的所有權和處分權;(6)選擇解釋婚前協議適用的法律;(7)包括人身權利和義務在內的任何其他事項,但不得違反公共政策或者刑事法規。該條(b)款禁止婚前協議對未成年子女撫養施諸不利益影響。由于我國婚姻法并未重視建構完善離婚扶養制度,這里有意忽略借鑒該條(c)款規定的離婚扶養條款。參見Cal.Fam.Code§1612.。由于該州與我國夫妻財產制存在類似之處,法定財產制采共同財產制,約定財產制采自由式,因而可為我國婚姻協議立法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確立婚姻協議的強制公證制度
大陸法系諸多國家強制性規定婚姻協議的訂立須經公證。緣何公證至關重要?富勒指出,契約法的形式強制是探求當事人真意的法律媒介和工具,具有證據、引導和警示三項功能:證據功能有助于防止欺詐;引導功能指通過形式主義將意思表示外部化,公開標示法律權利義務,增強訴訟裁決結果的可預測性;警示功能旨在起到確保行為人知悉和理解締約法律后果的“安全閥”作用[30]。法律有時規定意思表示僅在具備特定要件時才產生拘束力,這實際上賦予當事人一種“隱藏的”撤回權。在法律規定的要件尚未具備的情形下,當事人可以撤回其意思表示[31]。
在法律規定的各類形式要件中,書面形式具有證據功能,可作為保全意思表示內容的證據,減少或者縮短、簡化訴訟程序,那么為何大陸法系諸多國家奉行婚姻協議的公證要件主義呢?較之于書面形式,公證的警示和引導功能更強。正因如此,法國最高法院第一民事庭明確指出,離婚協議采公證文書形式是一項強制性規定,以確保有公證人對當事人雙方提出建議[32]。德國強制性規定婚姻協議的法定形式是公證證書形式[33],而不是書面形式或公證認證形式,旨在為當事人審慎權衡締約法律后果提供最高強度保護。我國《婚姻法》第十九條規定婚姻協議采書面形式,但書面形式在各類形式要件中警示功能最微弱。基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經公證的贈與不可任意撤銷,而夫妻財產歸屬約定涉及一方向另一方無償讓與財產份額的財產性質轉化,且婚姻協議不得任意撤銷,為使當事人充分知悉和理解締結婚姻協議的法律后果和意義,我國應當確立婚姻協議的強制公證制度,并將之與下文述及的程序強制相結合,以使兩者形成功能整合和有效銜接。
(三)完善婚姻協議的對外效力制度
婚姻協議關涉第三人利益保護和交易安全,因而婚姻協議效力分為對內效力和對外效力,前者指婚姻協議生效時在當事人雙方間產生法律拘束力,后者指婚姻協議產生對抗第三人效力。在諸多國家和司法轄區,婚姻協議產生對外效力的方式包括公示或“第三人明知”兩種。相較“第三人明知”需要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公示直接產生對抗第三人效力,更有利于保護當事人利益。德國規定,當事人以公證認證形式提請登記婚姻協議,區法院必須以為其公告而指定的報紙公布登記,任何人均可查閱婚姻協議登記簿[34]。在自由式約定財產制下,婚姻協議中的財產權利狀態可能高度復雜,公示規則越精細越有利于保護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在法國,若夫妻任何一方在結婚時是商人或婚后成為商人,婚姻協議的訂立以及變更必須進行公告[35]。法院判決認為,婚姻協議包含設置不動產共有條款的,亦應進行公告[36]。在美國有些共同財產制州,婚姻協議公示制度保護第三人利益和維護交易安全的強度甚高。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2332條規定:“婚姻協議或設立分別財產制的判決中的不動產權在該不動產所在行政區不動產轉讓契據記錄處被提請登記時,動產權在夫妻雙方居住地被提請登記時,對第三人產生對抗力。”②La.Civ.Code Ann.art.2332.
我國《婚姻法》第十九條未采公示對抗主義,僅規定以“第三人明知”作為婚姻協議產生對外效力的方式,極易導致當事人利益與維護交易安全之間關系的失衡。我國可以結合域外法經驗,從以下幾方面確立婚姻協議公示制度。一是我國行政機關介入的物權公示方式主要是登記,而登記存在暴露當事人財產狀況信息的弊處,為尊重當事人是否申請登記的本意,婚姻協議公示采任意登記主義順理成章。二是登記簿記載的物權歸屬和內容系權利推定而非事實推定,當婚姻協議登記簿與物權登記簿的記載內容不相一致時,前者優于后者的權利推定力。因此,若婚姻協議登記制度弱于物權登記制度維護交易安全的強度,難免減損或否定該制度價值。考慮到課加第三人查閱婚姻協議中每一事項的義務似乎很難可行且負荷過重,婚姻協議登記宜采區分登記主義,即婚姻協議的登記并非“畢其功于一役”,當事人必須對婚姻協議中的各財產事項各別地履踐登記之手續。值得注意的是,將婚姻協議中的期待權記載于登記簿實質上有擴張預告登記容量的法律效果,這意味著婚姻協議中可登記財產權的范圍和形態的多元化遠甚于現行物權法等法律規定的內容。因此,如何劃定婚姻協議中可登記財產權的范圍和類型值得探討。不過,即使婚姻協議登記制度有自成一體獨立性,也應與物權法等法律相結合。基于登記實益之目的,婚姻協議登記范圍應包括物權法上物權登記范圍內的不動產、特殊動產和財產性權利。這類財產或財產性權利通常價值較大,權益得失與權利人利害攸關。一般動產流轉頻繁且迅速,即使登記也難以準確反映動產權屬狀態,徒增第三人的信息查詢成本和社會成本,以“第三人明知”作為一般動產物權的對抗要件更妥適。三是為免于當事人企圖通過婚姻協議規避債務的欺詐,婚姻協議中的財產權未被及時登記且未被“第三人明知”,不得對抗第三人。由于婚姻協議無效、變更或撤銷等原因導致登記事項錯誤的,信賴錯誤登記的善意第三人權利不受影響。概言之,婚姻協議中未被第三人明知或應知的財產權不具有對抗第三人效力。
(四)設立婚姻協議的公平原則
有學者認為,我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立法要加強對婚姻家庭中弱者利益的特殊保護[37]。約定財產制表面上乃私域自治范疇,但實質上與國家利益和公共福祉緊密相關,涉及弱者利益保護范疇。我國婚姻協議立法應當如何體現公平原則的具體所指,而不是避而不談或含糊其辭。我國可以借鑒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立法及司法經驗,將婚姻協議的公平原則分為實質公平與程序公平兩方面。
1.實質公平。現代民法設立公平原則之目的,除兼顧締約當事人雙方利益外,也為“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顯示公平”規則設立判斷基準[38]。美國有些州為平衡當事人雙方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選擇忽略婚前協議的契約性質,依據重新審查原則對婚前協議內容是否符合實質公平進行審查。所謂重新審查原則,是指雖然婚前協議在訂立時為合法有效,但是法院必須在當事人雙方婚姻關系解除時對強制執行婚前協議所導致的結果是否公平合理予以重新審查,并且僅在結果公平合理的情形下才強制執行婚前協議。澳大利亞《2000年家庭法修正案》明確將情事變更原則作為法官審查婚姻協議是否符合實質公平的基準。該法案第90K條規定,若訂立婚姻協議后發生與雙方婚生子女扶養、福利和成長相關的重大情事變化,監護婚生子女的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請撤銷婚姻協議,否則該方或受其監護的子女將陷入生活困境。德國民法典并未確立婚姻協議的公平原則,司法實踐主要在判例基礎上對保護弱勢配偶利益的情形予以類型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在協議欠缺平等性的情況下,如婚前協議包含選擇分別財產制、排除扶養補償、互相放棄離婚扶養等對妻子特別不利的內容,或締約時女方已懷孕并因此處于不利地位,法院有義務根據一般民法規范對協議內容加以控制或變更[39]。
我國《婚姻法》第四十條規定旨在保障分別財產制下家事配偶的離婚經濟補償權,其理論依據實質是公平原則。基于公平原則是各項基本原則具體化和逐漸演變的重要依據,我國也可將重新審查原則、情事變更原則等作為判斷婚姻協議是否符合實質公平的基準。若法官對婚姻協議的實質公平進行審查后,確信強制執行婚姻協議將導致一方陷入實質性生活困難的窘境,可以酌情變更或撤銷婚姻協議。值得注意的是,公平判斷易受不穩定的“直覺主義”正義感影響,因而婚姻協議的實質公平審查端賴于法官的司法素養和專業能力。
2.程序公平。基于當事人雙方之間締約能力的不均衡和信息不對稱會削弱締約的自愿性和實質公平,婚姻協議的公平原則的構造力圖從后果性邏輯向程序性邏輯進行轉變,旨在通過程序公平機制(程序強制)警示當事人謹慎權衡締約的法律后果。雖然程序強制表面上是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和限制,但實質卻是維護和保障當事人擁有真正自治意義上的“自主性”。
一是訂立婚姻協議前應就婚姻協議事項獲取法律意見。美國諸多州規定,當事人各方在訂立婚前協議和婚內協議前應當或有機會咨詢律師。澳大利亞《2000年家庭法修正案》第90G條全面詳細規定了律師為婚姻協議當事人提供的法律意見書應當包含的內容。緣何獲取法律意見如此重要?由于當事人雙方存在真實或潛在利益沖突,審慎專業的法律意見可以使各方當事人知悉其“真實利益”的實現可能性及路徑,避免因法律知識匱乏和受有限理性束縛而無法全面理解締約的法律后果。考慮到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有的當事人可能不具備獲取法律意見的條件,我國可以設置婚姻協議的公證與當事人獲取法律意見相結合的彈性規則。具體而言,為達致程序繁簡分流和節約社會資源的效果,婚姻協議的公證分為公證認證與公證證書兩種形式。在當事人雙方向公證處提交經核認的法律意見書的情形下,婚姻協議得以公證認證形式訂立,公證人對婚姻協議僅作形式審查;在當事人雙方未向公證處提交經核認的法律意見書的情形下,婚姻協議必須以公證證書形式訂立,由公證人擬定婚姻協議內容或者對婚姻協議作實質審查。公證人應向當事人釋明締約的法律后果,并應盡量避免提供錯誤的法律意見,以免欠缺經驗的當事人遭受損害。
二是訂立婚姻協議前必須履行婚姻財產信息披露義務。由于婚姻財產信息的效用性與當事人利益相關度高,信息不對稱會產生影響當事人理性決策的負外部性,美國諸多司法轄區規定各方當事人在訂立婚前協議和婚內協議前必須履行婚姻財產信息披露義務,否則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澳大利亞《2000年家庭法修正案》第90K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欺詐手段(包括未披露重大事項)訂立婚姻協議的,法院可以判令撤銷或終止婚姻協議。類似立場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亦有所體現,以一個案例為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再審一離婚訴訟案件中認為,雖然涉案當事人雙方簽訂的婚前協議明確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歸各自所有,但是當事人一方因故意隱瞞婚前財產信息而造成另一方在訂立婚前協議時處于劣勢地位,因而法院依據照顧無過錯一方、撫養子女一方等原則,將婚姻存續期間前者以個人名義購買的一處房產判歸后者所有①見“門麗潔委托合同糾紛審判監督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5)高民抗提字第1188號。。該案重要意義在于法院積極主動承擔起“剩余立法權”的功能,將當事人應當履行婚前財產信息披露義務作為判決依據,起到以司法性立法方式暫補立法空白的作用,為相關立法完善提供了司法經驗的支撐。
四、結 語
綜上所述,隨著契約社會和法律契約化的歷史發展之使然,私主體自治日益凸顯其重要性。民法典編纂中我國婚姻協議的立法完善是順應“時運”所作的一種遲鈍、但無疑卻是積極的反應。我國應當在積極借鑒域外法的基礎上對《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予以規范性重構,擴張婚姻協議的約定事項范圍,但附帶而來的必然結果是立法應當摒棄形式平等理念,完善婚姻協議的形式強制和程序強制,保障締約合意是當事人雙方在權衡交易成本以及利益與風險利弊得失的基礎上所作的一種理性選擇。婚姻協議的實質公平旨在將社會保障思想引入婚姻協議立法,保護弱勢配偶利益。婚姻協議登記制度的設立可以彌補婚姻法未采婚姻協議公示對抗主義的立法漏洞,平衡當事人利益和維護交易安全。
[1]Judith Younger.Perspectives on Antenuptial Agreements[J].Rutgers Law Review,1988(4).
[2]Brian Bix.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Love:The Enforcement of Premarital Agreements and How We Think About Marriage[J].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1998(1).
[3]陳葦.外國婚姻家庭法比較研究[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6:5.
[4]賀劍.法教義學的巔峰——德國法律評注文化及其中國前景考察[J].中外法學,2017(2).
[5][7]Katharina Boele-Woelki, Jens M.Scherpe, Jo Miles.歐洲婚姻財產法的未來[M].樊麗君,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35-37;37-38.
[6]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新論[M].臺北:三民書局,1987:174.
[8]Sir Henry Sumner Maine.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06:165.
[9]Elizabeth R.Carter.Rethinking Premarital Agreements:A Collaborative Approach[J].New Mexico Law Review,2016(2).
[10]羅斯科·龐德.法理學[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212.
[11][14]中國人民共和國婚姻家庭法典[Z].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3,43.
[12]龍俊.夫妻共同財產的潛在共有[J].法學研究,2017(4).
[13]史尚寬.親屬法論[M].臺北:榮泰印書館,1980:307.
[15]裴樺.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沖突與協調[J].法學研究,2017(4).
[16]田韶華.夫妻間贈與的若干法律問題[J].法學,2014(2).
[17]許莉.夫妻房產約定的法律適用——基于我國約定夫妻財產制的考察[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5(1).
[18]冉克平.夫妻之間給予不動產約定的效力及其救濟——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 6 條[J].法學,2017(11).
[19][20][21][22][23][32][35][36]法國民法典[Z].羅結珍,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19,1123-1124,685,778,779,1165,1121,1126.
[24]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44-341.
[25]Gary S.Becker.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65-68.
[26]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J].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1988(1).
[27][28]Ch.Perelman.Justice,Law,and Argument:Essays on Moral and Legal Reasoning[M].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0:160,67.
[29]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Economics,1960(3).
[30]Lon L.Fuller.Consideration and Form[J].Columbia Law Review,1941(5).
[31]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M].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28.
[33][34]德國民法典[Z].陳衛佐,譯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451,475-476.
[37]夏吟蘭.民法分則婚姻家庭編立法研究[J].中國法學,2017(3).
[38]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7.
[39]迪特爾·施瓦布.德國家庭法[M].王葆蒔,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