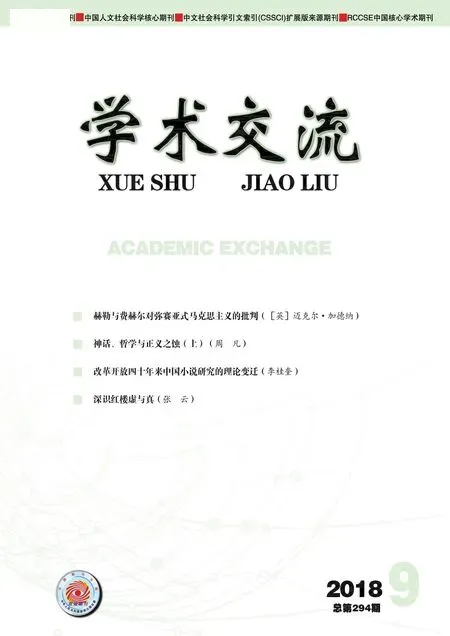論李大釗新聞倫理思想
徐新平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長沙 410081)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新聞事業的締造者,杰出的政論家和宣傳家。從1918年7月發表第一篇關于俄國十月革命的論文《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開始,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為陣地,積極介紹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李大釗在其報刊宣傳活動中還撰寫了多篇新聞學論文,如《晨鐘報》發刊詞,《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甲寅〉之新生命》《報與史》等。這些論文以及他撰寫的政論時評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在當前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熱潮中,我們要了解和探索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中國的源流變遷,就離不開對李大釗、陳獨秀等黨的創始人新聞倫理思想的研究。但是,在以往的研究文獻中,關于李大釗新聞倫理思想的論著很少,本文將就此進行簡略的論述。
一、記者要以促進國民精神解放為己任
李大釗的新聞宣傳活動與同時期的林白水等職業記者在動機目的上是有一定差異的。林白水等民營報人的新聞活動是以報道時事新聞、揭露社會丑惡為主要內容,而李大釗作為一個革命家、思想家和學者,他的新聞宣傳活動則以改造社會、振奮民眾精神為己任。還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期,李大釗在他主編的北洋政法學會《言治》月刊上就發表文章說,中國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國家依然處在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環顧神州,危機萬狀”[1],“吾人不幸,沉郁于專制阨運,”“嘆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耳!”[2]40-41面對國家危亡的局勢和社會黑暗的現狀,他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把扶持國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頭”[3]644。他說:“所望仁人君子,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奪政權之魄力,以從事于國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不勞爾輩先覺君子,拔劍擊柱,為吾民爭權于今日。”[2]43因此,他在十余年的時間里,所撰寫的政論時評都凸顯了一個主題:為振奮民眾精神服務。他相信:“三寸毛錐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阨運之中”[4]70。李大釗懷著對未來美好的愿望與憧憬,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利用報刊和文章“喚醒眾生于罪惡迷夢之中”[4]73。在其前期的代表作《民彝與政治》中,他提出了“民彝”這個獨特的概念。所謂民彝就是民眾不斷改善生存狀態的一種生存原理,又是民眾固有的衡量事理的價值標準。[7]以政治意識為例,我國民眾在民權自由方面,雖然“校先進國民為微弱,此種政治意識覺醒之范圍,亦校為狹小”,但是,“觀于革命之風云,篷勃飛騰之象,軒然方興而未有艾。則此民權自由之華,實已苞蕾于神州之陸。吾民宜固其秉彝之心田,冒萬難以排去其摧凌,而后以漸漬之工夫,熏陶昌大其光采,乃吾民唯一之天職,吾儕唯一之主張矣。”[6]158就是說,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封建專制壓迫下,雖然民主自由權利的思想意識比較薄弱,但是,這種思想意識的種子卻深藏于民眾的心底,從未消失。革命者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利用各種手段喚醒民眾這些潛在的本能的思想意識,促進其精神的解放。
1916年,“反袁斗爭”取得了勝利,但是,面對衰微的國勢和腐敗的政治,國人對民族前途悲觀失望,青年中厭世思想盛行。為了打破人們的悲觀情緒,振起人們的自信和勇氣,李大釗撰寫了《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青春》等文章,闡發了他獨具特色的宇宙觀和人生哲學。他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循自然法則的、機械的、漸次進化的大實在。宇宙萬象無時不在運動變化之中,其正反兩面的矛盾與斗爭不是無休止的循環往復,而是新陳代謝。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生的規律也是這樣,也有無盡的青春。人自覺“青春無盡”,這才是人生的基本精神。所謂有無青春,“非由年齡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個人而言,乃由社會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當益壯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頹喪者,乃在吾人詬病之倫矣。”[7]182李大釗的青春無盡的思想,代表的是一種昂揚奮發、樂觀進取的精神,他要求人的一生都要保持奮斗不止的青春活力與沖決羅網的創造能力。他指出,
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7]179
李大釗是一個富于理想、感情激越的人,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品格,對人生、對國家都充滿了樂觀的希望與美好的期待。他總是鼓勵人們要具備“奮興鼓舞的歷史觀與樂天努力的人生觀”[8],要“把扶持國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頭”[3]644。我們讀他的文章,總會感到一股樂觀邁進、奮發有為的力量在向外噴涌,絕不會有半點懶惰、任命、悲觀、灰心的氣象。例如,他在《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中提到,
中華民族現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在這一段道路上,實在亦有一種奇絕壯絕的景致,使我們經過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種壯美的趣味。但這種壯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夠感覺到的。[9]
他一方面,指出中國目前正處于艱難的境界,另一方面,鼓勵人們不要心灰氣短、萎靡頹唐,而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悲壯的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讀李大釗的文章,不得不讓人心魄震蕩,血沸神銷,一種昂揚奮發的精神油然而生。我們翻檢李大釗為幾種報刊所撰寫的發刊詞,就更加清楚地看到,他的報刊活動,一以貫之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國民精神以挽救民族、振奮國群。1916年,《晨鐘報》創刊時,他對外宣稱:《晨鐘》的使命就是“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7]182。1917年,他在《〈甲寅〉之新生命》中說,《甲寅》的唯一責任是“開導我國民使之進化”[10]。1919年,他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一文中強調,《少年中國》要用人道主義精神和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在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占據的沖動,變為創造的沖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11]由此可見,李大釗的新聞活動就是圍繞著改造國民素質、促進人們的精神改造和精神解放而展開的。他說:“我以為一切解放的基礎,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們的解放運動第一聲,就是‘精神解放’!”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他心中更加強化了民族自救、自強的夢想。他自覺以報刊為陣地,宣傳新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國民拋棄陳腐落后的觀念,樹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為再造青春中華而努力。他對新聞實踐和思想啟蒙宣傳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宣傳工作提供了直接的榜樣。
二、對言論自由的向往與追求
李大釗受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的影響,對“言論自由”充滿向往。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國。”[12]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左手持利刃、右手持金錢”,殘害異己,收買媒體,這樣一部中國的歷史,只有當權者的自由而沒有民眾自由的歷史。五四時期,北洋政府雖然在頒布的臨時約法中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但事實上這些權利被軍閥們恣意踐踏,言論出版自由成為一紙空文。
為此,李大釗、蔣孟麟等聯名在《晨報》上發表《爭自由宣言》,抨擊北洋政府壓制和剝奪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行為,強烈要求還權于民。他在《新生命誕孕之努力》一文中說:“《晨鐘》創刊,締造經營,竭盡綿薄,猶慮弗勝,此本報新生命誕孕之辛苦也。而本報不敢辭其辛苦,癉精瘁力以成之者,則亦本報欲得自由之努力矣。”[13]這顯示出他為爭自由而甘冒艱險的決心。李大釗言論自由思想主要有如下內容:
1.言論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李大釗指出,自由是上天賦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對個人而言,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人生也就失去了意義,“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于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14]8對國家來說,言論自由是國家政治發達的基礎。就如人的身體一樣,血脈暢通則生機勃勃,血脈阻塞則麻木不仁[15]。因此,他主張在憲法制定中強調保障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2.言論自由是法制保障的自由。李大釗指出,自由不是無政府主義,不是毫無約束,而是與“法制”“秩序”有著密切的關系。他說:“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16]他認為,自由與秩序,兩者是不能分離的,只有在法律保障條件下的自由才是真自由。“顧自由之保障,不僅系于法制之精神,而尤需乎輿論之價值。故凡立憲國民,對于思想言論自由之要求,固在得法制之保障”[6]169。從歷史上看,在專制制度之下,失去法律保障的自由,就是恃強凌弱、豪強橫行的自由,自由與專制不能并存。李大釗為人們了解和認識自由的條件與范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3.言論自由是允許各種意見發表,防止“眾同而禁一”現象發生。李大釗主張,在言論表達中要充分尊重公民自由權利,警惕“暴民政治”,防止“眾同而禁一”的現象出現。“眾同而禁一”的本質是以多數人意見壓制少數人意見,是多數人對持不同意見者的言論暴政。自由的言論不一定代表真理,報刊應同時反映對立雙方的意見,是非曲直只有在相互辯難中見分曉,健全的輿論才能夠形成。李大釗認為,
世間本來沒有“天經地義”與“異端邪說”這樣東西。就說是有,也要聽人去自由知識,自由信仰。就是錯知識了、錯信仰了所謂邪說異端,只要他的知識與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實,一則得了自信,二則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無知的排斥、自欺的順從遠好得多。[14]8-9
在政府層面,凡禁止思想、信仰、言論自由的做法都是一種罪惡;在社會層面,無論什么思想言論都應該讓他發表出來,才是正確的。李大釗主張,“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14]9因此,他“奉勸禁遏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借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14]9。
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社會各階層的自由進行了考察,認識到在階級社會里言論自由是有階級性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少數當權者和資本家才有言論自由,大多數民眾與自由是無緣的。俄國革命成功后,廣大民眾有了自由,少數壓迫階級的言論權被剝奪。因此,勞動人民要想獲得自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少數資本主義者之自由當然受束縛,不過對于大多數人的自由確是增加”[17]。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究竟是一種道德,還是一種權利?這是從晚清以來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例如,嚴復認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18]就是說,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梁啟超則認為,“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19]675“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19]679。梁啟超把自由看成是與奴隸性相反的獨立人格,包括行動自由與精神自由。他在《十種德性相反想成議》中,也是將“自由”看成是一種道德。
其實,在嚴復和梁啟超的文章中,自由有時被看成是政治權利,有時又被看成是一種道德觀念。在李大釗的文章里,也是這樣。例如,他在《自由與秩序》《憲法與思想自由》等論文中,都把憲法上規定的自由看作是國民生存的必須之要求,認為人的自由權利,包括身體自由、財產自由、書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等。這些自由顯然是指社會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
但是,李大釗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又把自由看成是一種道德。例如,他在《民彝與政治》中說:“歐西自由之說,雖經東漸,神州共和之幟,亦既飄然高樹。而社會言論武斷之力,且與其龐雜喧闐之度而俱增,而是非亂,而真偽淆,公理正義乃更無由白于天下,自由之精神,轉以言論自由愈湮沒而不彰。”[6]170在《立憲國民之修養》中說:“立憲國民之儀度,當以自由、博愛、平等為持身接物之信條。此等信條入人既深,則其氣質之慈祥愷悌、中正和平,必能相為感召,以成循禮守法之風習。”[20]這里所說的“自由之精神”和自由“為持身接物之信條”,顯然是一種道德。
其實,在中西方政治和哲學史上,自由從來就具有政治角度和倫理角度等多重含義,正如嚴復所說:“蓋政界自由,其義與倫學中個人自由不同。”[21]因此,自由既是一種政治權利,又是一種道德觀念,兩者既有區別又有內在的聯系。試想,一個民族或者個人壓根就沒有自由的精神與自由的信條,又怎么可能去勇敢地爭取政治法律和經濟上各種自由的權利呢?因此,我們在論述中國新聞倫理思想的過程中,不得不關注歷代報人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認識與主張。
三、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與職業素養
1922年2月,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李大釗在《晨報》上發表演說,這篇演說用唯物史觀從理論上闡釋了他對新聞事業的基本觀點,被認為是“我國第一篇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新聞現象的講話”[22]。在講話中他對“新聞事業”和“新聞”這兩個概念進行了詮釋。他說:“新聞事業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新聞是現在新的、活的社會情況的寫真。”基于以上認識,他提出了新聞記者的兩大責任:
其一,全面紀述全社會每天所發生的事實。他說,過去的歷史家只為帝王將相一家一姓作起居注,而社會是復雜的,具有多方面的關系,歷史應當注重社會上多方面的記載,不然就不是真實的歷史,新聞報道也應如此。他提醒記者要養成多方面的知識,學會全面地看問題,眼界要寬,要認識到社會復雜的、多方面的關系,從事物的聯系和變化中全面客觀地呈現社會生活的整體面貌。這一觀點在中國新聞思想史上還是首次提出,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在新聞業務中的體現。
其二,利用活的問題向國民輸入各種知識。他說:“新聞記者的責任,于紀述事實以外,還應該利用活的問題,輸入些知識。”[23]537就是說,記者傳播知識與教師傳授知識是不同的,應當聯系重大新聞事件靈活地向受眾灌輸些知識。例如,紀念達爾文的誕辰,就可以將達爾文的生平經歷和理論學說概要地介紹出來,讓讀者更多地了解生物進化的知識;如果報道地震的消息,就去采訪地質學家,通過專家講授有關地震知識,為民眾釋疑解惑。這樣,將死的材料隨著活的事實表現出來,理論知識也就成了活的、有趣的材料[23]538。他在《報與史》中也陳述了同樣的觀點,希望新聞記者“能把日日新發生的事件,用有系統、有趣味的筆法,描寫出來,以傳布于讀者,使人事發展、社會進化的現象,——呈露于讀者的眼前。”[24]李大釗的觀點對于記者如何將報道寫得生動活潑,將報紙辦得豐富多彩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同時,李大釗還認為,在分析社會現象、評論時事與指導國民方面,記者需要更高的修養和更多的努力,才能擔負起這個責任。他在《政論家與政治家》一文中提出,無論是政論家還是政治家,都要具備三種修養,即知識、誠篤和勇氣。他這篇文章雖然不是針對記者職業而言的,但是,從工作性質看,記者也屬于政論家之列,歷史上的許多知名記者如王韜、梁啟超等人,就是著名的政論家。因此,也可以看成是對記者的要求。從李大釗的有關論述中可知,關于記者的職業素養,李大釗著重提出了如下觀點:
第一,記者要有淵博深厚的知識。李大釗認為新聞事業是“活的社會事業”,記者“要想把這不斷的發生的、多方面的社會現象描寫出來,而加了批評或指導,非有相當的學問和知識不可。”[23]537“國家政治,叢雜萬端,而社會上之生活現象,尤為變動不居,靡所軌范,倘知識不足以濟其變,則凡一舉手一投足,皆有窮于應付之感,勉強為之,不鄰于魯莽滅裂,則歸于捍格難行而已。”[25]323就是說,記者的工作所面對的是不斷變化的、十分復雜的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如果沒有廣博的知識,就難以駕馭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更談不上對受眾加以批評和指導。
第二,記者要有誠篤的品德。李大釗說:“知識充矣,茍臨事接物之際,無誠篤之精神以貫注之,或權謀數術以試其詐,或虛與委蛇以從其惰,若而人者,雖能欺飾于一時,不能信孚于有眾;雖可敷衍于俄頃,不能貫徹乎初終,此亦政家之所忌也。”[25]323-324在這里,李大釗所說的“誠篤”,就是強調政論家態度要誠實,動機要純正。記者在辦報中也要恪守誠篤的品質,不能將辦報視為謀私射利的工具,對大眾不能有任何欺騙的手段,不然,就不能得到大眾的信任。新聞記者如果文過飾非,混淆黑白,欺騙受眾,就是一種罪惡,相反只有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全面記錄紛繁復雜的世界,及時反映流變不止的社會真相,才是自己應盡的職責。
第三,記者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李大釗認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于真理。”“茍其言之確合于真理,雖一時之社會不聽吾說,且至不容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囁嚅以迎附此社會;茍其言之確背乎真理,雖一時之社會歡迎吾說,而并重視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趨承此社會。”[26]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是需要勇氣的,“無百折不撓、獨立不倚之勇氣,以與艱難、誘惑相抗戰,則亦終歸于沮喪、墮落之途,不為境遇所征服而作艱難之俘虜,則為利害所迫誘而作勢力之囚奴耳。此又涉乎節操問題矣,而此修養又當儲備于平日,非可卒得于臨時。”[25]324
第四,記者要有團結合作的精神。無論是對《新青年》雜志同人,還是對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志會,李大釗都多次論述了團結合作的重要性,并對記者同志提出了團結一致干事業的期望與要求。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他更加強調記者的團結協作和集體觀念,強調要發揮集體的力量,以指導國民運動。在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志會上,他表達了對該會的希望:“胡先生說,不希望主張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發揮個性固然不錯。但是有了這個團體,總可以借此情誼,立在同一的、知識的水平線上,常有機會來交換各人不同的意見。遇有國民的運動發生時,我們總可以定一大目標,共同進行,以盡指導群眾,而為國民的宣傳的責任。”[23]539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們常常遇見這樣的現象:本來是同一個團隊的成員,有著共同的目標和利益,只是因為個性不同、意見不一而互不相讓,甚至反目成仇。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求同存異的胸懷與著眼大局的識見,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集體和個人利益都受到損害。李大釗的觀點對于人們正確處理團隊內部矛盾和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四、新聞記者要具備歷史研究者的修養
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說:“現代的報紙,其性質亦與史相近。有人說在某種意義,歷史可以說是過去的報章,報章可以說是現在的歷史。這話亦有些道理。作報的人要有文學的天才,亦要有史學的知識。這樣子做報,那作出的報章,才是未來史家的絕好材料。”[27]在《報與史》中,他從“史”字的原始意義入手,考察了報與史的密切關系。認為“史”的本義有掌司記事者之義,而且“作史的要義,與作報的要義,亦當有合”。他提出,“報是現在的史,史是過去的報”,“新聞記者的職分,亦與歷史研究者極相近似。”因此,“新聞記者要有歷史研究者的修養。”[24]
為什么說作報的要義與作史的要義相同呢?李大釗從三個方面考察了它們之間的關系。
首先,“察其變”。他說:“社會的進展不已,人事的變遷無常,治史者必須即其進展變易之象,而察其程跡,始能得人類社會之真象。”研究歷史就在于明白人類社會的變化,治史所以明變;新聞也是對變動不居的社會現象的記錄,也要用發展變化的眼光來認識世界,如此方能認識和反映社會的真相。其次,“搜其實”。李大釗說:“欲求人類進變之跡,茍于個個現實發生的事件,未得真確之證據,則難免馳空武斷之弊。”歷史研究以掌握真實確鑿的史料為基點,如果沒有掌握確切的歷史資料,研究就無法進行,也失去了意義。同樣,作為“現在的史”的新聞,也必須以新聞真實為基礎,沒有對事實全面的了解,任何記錄與分析都是沒有價值的。再次,“會其通”。“今日史學進步的程途,已達于不僅以考證精核片段的事實,即為畢史之能事了,必須認人事為互有連瑣,互有因果關系者,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實與事實之間,發見相互的影響與感應,而后得觀人事之會通。”[24]治史以尋求現象背后的歷史規律為目標,講究事實與事實之間縱橫的歷史聯系,并從諸多聯系的考察中探尋真相與規律。新聞以記錄事實真相、揭示新聞價值為目標,也要講究透過現象看本質,善于從事實的聯系與發展中記載新聞。李大釗還指出,歷史與新聞雖有許多共通之處,但兩者又有一定的差異。具體說,就是作史與辦報的時效性不同,作史可以慢一點,而報道必須快速及時,所以,記者在察變、會通兩方面比不上歷史研究者,這是工作性質造成的客觀存在。但是,新聞記者不能因此而放棄了歷史的責任與歷史研究者的修養。李大釗提出,
新聞記者要有歷史研究者的修養,要有歷史的知識,要具有與史學者一樣的冷靜的頭腦,透澈的觀察,用研究歷史的方法,鑒別取拾關于每日新生事實的種種材料,這樣子才可以作成一種好報紙,同時亦能為未來的史家預備些好史料。[24]
李大釗所說的關于記者要具備史學家的修養,主要內容是指豐富的知識、冷靜的頭腦、透澈的觀察,研究歷史的方法幾個方面。他認為,這幾個方面的修養與辦報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有具備這些修養,才能辦出好的報紙。我們知道,關于史家與記者的關系問題,并不是李大釗最先提出的,早在晚清時期國人辦報之初,何啟、胡禮垣、鄭觀應、梁啟超等人都提出過這樣的主張,并形成了記者要具有“史家精神”的共識。但在李大釗之前,誰也沒有寫過《報與史》的專論來探討這個問題。他們的看法都在零星的語錄中表達,缺乏完整性。李大釗對報與史、記者與史家關系問題的論述較前人更為充分與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