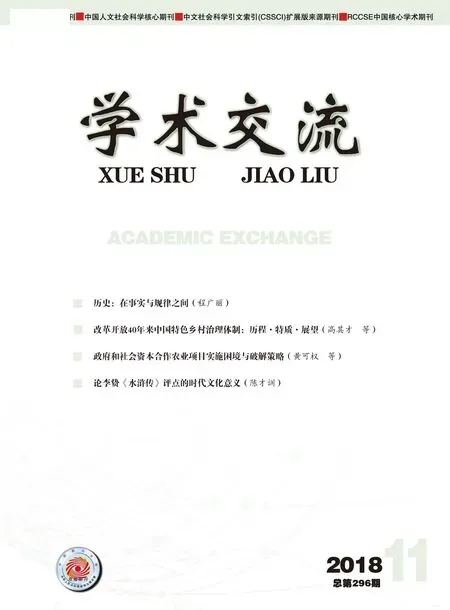“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文化意蘊
——兼談韓信形象的流變
關慶濤
(哈爾濱商業大學 基礎科學學院, 哈爾濱 150028)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說韓信棄楚投漢后,得蕭何力薦,劉邦拜其為破楚大將軍,韓信得以施展軍事才華,為劉邦建立不世功勛,因此成就王侯之業。后來呂后欲除韓信而無法,蕭何又助呂后除韓信。因為韓信成敗均與蕭何有關,故韓信祠堂楹聯有“成敗一知己,生死兩婦人”之語,這一“知己”即指蕭何,其思想意蘊與“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一致的。但史傳所載只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乃經歷漫長的流變,是伴隨著韓信形象的流變而逐漸形成的,其中的過程比較復雜,文化意蘊極其豐富。
一、 史傳所載蕭何與韓信故事
蕭何與劉邦同鄉,二人私交甚密,蕭何為沛主掾吏時,劉邦為泗上亭長,蕭何常幫助劉邦。劉邦沛縣起義后,蕭何等推劉邦為沛令,故蕭何深得劉邦信任,常隨左右。劉邦起兵進攻三秦,令蕭何守漢中,為高祖足食足兵,可見劉邦對蕭何的信任。韓信乃淮陰一落魄子弟,因其無行不得為吏,所以常為游俠。項梁起兵后,韓信投奔項梁,但并不受重用,故韓信棄楚投漢。韓信為治粟都尉后,始與蕭何接觸。通過接觸,蕭何發現韓信有帥才,對韓信格外欣賞,數次于劉邦處舉薦韓信,然劉邦終不用韓信,韓信負氣出奔。“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1]2611蕭何發現韓信有大將軍之才,韓信不得重用而棄漢,蕭何得知,追趕韓信,并薦之于高祖,封其為大將軍。韓信成才可謂主要得益于蕭何的賞識,故說“成也蕭何”是沒有問題的。
韓信之敗亡,原因極其復雜。韓信簒逆是根本原因,劉邦誅殺功臣是重要原因,蕭何助呂后除韓信并不是韓信敗亡的原因。韓信可謂軍事奇才,將兵多多益善,然政治才華比較平庸。下齊后,據勢要挾劉邦封其為假齊王;劉邦偽游云夢擒韓信后,削韓信兵權,封其為淮陰侯,韓信本應韜晦自保,然卻屢次于劉邦前炫耀兵威。凡此種種,皆是韓信自取敗亡。然韓信敗亡最根本原因在于劉邦恐韓信為亂。楚漢相爭的戰亂年代造就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他在戰場上屢獲戰功,無人能比。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韓信實力逐漸壯大,甚至超過了劉邦,名義上尊劉邦為王,受劉邦節制,但實質上是又一項羽,劉邦陰御之亦實屬必然,故韓信兩次被削兵權。但是劉邦無法根本抑制韓信,因為非韓信不足以抵項羽,伴隨著項羽逐漸敗亡,韓信也逐漸強大到劉邦無法掌控的程度。韓信經垓下之戰殺掉項羽,此時他已將兵二十萬,是又一個霸王,已然是漢家的心腹大患,故高祖偽游云夢,削其兵權,韓信因此怨曠,與陳豨謀反:“陳豨拜為巨鹿守,辭于淮陰侯。淮陰侯契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漢十年,陳豨果反。……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蕭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1]2628據史傳所載,劉邦陰御韓信確有其事,這主要緣于劉邦氣量狹小。由于劉邦削韓信兵權,韓信怨恨,因此反叛,若令韓信宴然而終,韓信未必會反漢。高祖出兵在外,韓信于中襲擊呂后和太子,將使國家重新陷入戰亂,于國于民均有百害無一利,蕭何助呂后除韓信符合國家利益,無疑是正確的,故蕭何除韓信實乃于國有功。
二、蕭何與韓信故事的歷史演變
蕭何與韓信的故事首先被太史公寫進《史記》,后世史傳,如《漢書》《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等史書對蕭何與韓信故事的記載,均本于《史記》,故事內容基本相同,但在表述形式上差別較大。這些差別促成了蕭何與韓信故事的流變。
《漢書》亦記載了蕭何薦韓信和蕭何助呂后除韓信之事,史實基本與《史記》相同。所不同者在于:在《史記》中,太史公為韓信單獨列傳,為《淮陰侯列傳》,以褒揚韓信在秦漢之際所立的功勛,而在《漢書》中,韓信則與彭越、黥布、盧綰、吳芮四人合傳,為《韓彭英盧吳傳第四》,以上四人有個共同特征,即均為叛漢之臣。在《史記》中,太史公詳細記載了韓信與陳豨謀反的過程,也就是說太史公承認韓信確實存在叛亂動機,但在卷末評語中卻對韓信贊賞有加。《漢書》秉持漢家正統觀,對韓信的評價則有失偏頗,全盤否定韓信助漢之功,卻無限放大了韓信叛亂之事。班固將韓信與四位叛臣合傳,在形式上自然就認定韓信為叛臣,且態度較太史公愈加鮮明。試比較太史公和班固對韓信的評價便一目了然: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敝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史記》)[1]2630
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自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漢書》)[2]
相比而言,太史公肯定韓信之功勛,對其叛漢多有同情,對其貧而有志格外贊賞,盡管對韓信叛漢持批判態度,但對劉邦逼迫韓信反漢亦持否定態度。而班固對韓信則無一美言,否定其德行,稱其善詐力,甚至認為其功勛非個人能力,乃時勢所致,對其貶低太甚,是不客觀的。二者相較,太史公的態度更加客觀,班固則持漢家正統觀,這明顯是在為劉邦辯護。
《漢紀》是首次將兩漢歷史以編年體形式寫就的史書,其中對蕭何舉薦韓信故事的記載與《史記》《漢書》大體相同,但對蕭何助呂后除韓信記載,則與《史記》《漢書》略有不同。其中增加了對韓信謀反原因的探索:“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韓信既廢,恐懼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于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3]《漢紀》提供了《史記》《漢書》所不具備的新材料,據此可見韓信謀反乃蓄謀已久,增加了韓信叛漢的罪惡。高祖親征陳豨后,韓信欲矯詔襲擊呂后和太子,蕭何據此設計擒捉韓信,解漢家江山于孤懸,可謂忠于漢室,全無“敗也蕭何”之意。《漢紀》成書于皇綱不振的歷史時期,是意主宣揚漢家正統觀念的著作,全書為漢家正統辯護,對王莽僭越凌主、擅行廢立的強臣持批判態度,對光武帝繼承漢家遺脈格外贊揚,因此韓信叛漢自然會受到批判。
《資治通鑒》在《漢紀》的基礎上記載蕭何與韓信故事,對于蕭何舉薦韓信的記載及蕭何除韓信的記載,與前史無異,但司馬光對韓信的評價則與前史差別較大: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于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闬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于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4]
司馬光首先對韓信的歷史功績予以肯定,認為漢家天下乃韓信之功;其次對韓信失職怏怏給予否定,正是因為韓信失職怏怏,遂陷悖逆,認為韓信被禍乃其咎由自取。與此同時,司馬光對于劉邦亦不乏批判,承認韓信本無反心,劉邦疑其心而偽游云夢擒韓信,這是導致韓信心懷怏怏的前提,因此司馬光也承認劉邦有負于韓信。可以說韓信叛漢,是劉邦逼迫而成。這是司馬遷、班固、荀悅均沒有表達過的觀點。司馬光對韓信的評價及劉邦過失的批評,是極為中肯的,比較客觀。
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于韓信死后引胡三省的評論:“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謀逆既露猶當宥其子孫。”[5]208胡三省認為韓信功過可以相抵,至少應囿其子嗣,因此對劉邦寡恩多有批評,認為韓信被夷三族,刑法過重,對韓信之死深表同情。朱熹對韓信之死同情更進一步,認為韓信并無罪過,罪在劉邦,其在《書法》中講: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何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于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5]208
朱熹認為韓信之死,罪不在韓信,而在劉邦,是劉邦負恩導致韓信之死。朱熹在《發明》中進一步闡發他的觀點: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怏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于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元其本心云爾。漢室之興,德信未孚于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叛者迭起,夫何恠耶?《綱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可以君天下者哉?下書梁王越夷三族亦然。[5]208
朱熹繼承司馬光的觀點,認為漢室有負于韓信,但與司馬光有本質的不同。司馬光認為韓信之禍乃咎由自取,主臣各有錯誤之處,而朱熹則對韓信充滿同情,對劉邦負恩持批判態度,認為韓信乃無罪被殺。朱熹此論過猶不及,與史實不符。史載韓信確實謀反,這毋庸置疑。但朱熹此論亦有合理成分,即韓信謀反乃劉邦逼迫,從偽游云夢開始,至削職為淮陰侯,韓信均是無罪被禍。韓信心懷怏怏是因為劉邦錯誤在先,此其一也;韓信有大功,無韓信則無漢家江山,即使韓信最后被迫謀反,但其罪未發,人主當原諒之,此其二也;司馬光所謂心懷怏怏乃不臣之舉,彭越、英布則無,結果亦被殺,故劉邦殺功臣乃蓄意為之,其意自明,此其三也。司馬光有為劉邦回護之意,朱熹則對劉邦徹底批判。
綜上所述,在正統史傳作品中,存在著這樣一個流變的過程,即韓信敗亡的原因,逐漸由韓信謀反被誅,轉變為劉邦負恩殺功臣,逐漸對韓信之死表達同情,對劉邦殺韓信則表示譴責。這種思想逐漸影響文學創作。宋元以后的戲曲小說中繼承了史傳作品對韓信的同情,與此同時,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出于為王者諱,遂將對劉邦的貶斥轉移到蕭何身上,故逐漸形成“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認識。
三、 蕭何與韓信故事的文學化
在正統史傳中,諸本作者對韓信逐漸同情,對劉邦殺韓信逐漸持否定態度,這種觀點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之中,進而影響到文學創作。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八》、陳善《捫虱新語》中遂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記載[注]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有如下記載:“黥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系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于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己為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207頁),蕭何之敗韓信,實乃紿信入未央宮而殺之。據時勢而言,蕭何助呂后殺韓信,挫敗韓信叛亂企圖,避免天下重歸戰火,這無疑是正確的。韓信被殺歸因于蕭何,實乃史傳同情韓信思想下移,特別是《資治通鑒綱目》的記載,進而影響小說戲曲創作。《資治通鑒綱目》是程朱理學主要觀點的代表作,被列入科舉考試的教材,對后世影響極大。朱熹乃南宋時人,縱觀南宋時期,外敵憑陵、漢民族意識高漲是時代主流,因此朱熹在《資治通鑒綱目》中特別強調漢家正統,格外高揚漢民族意識,一改《資治通鑒》中三國歷史以曹魏為紀年的寫法,而堅持三國歷史“帝蜀寇魏”論。 在這樣一種思潮的影響下,高祖劉邦必然被回護,而《資治通鑒綱目》對韓信被殺持同情態度,兩種傾向長期矛盾對立,韓信被殺的罪魁,逐漸轉嫁給了蕭何。
《前漢書平話續集》繼承了史傳同情韓信的情感基調,虛構出高祖親征陳豨前,密令呂后殺韓信的情節。[注]高祖親征陳豨前,對呂后言:“胸懷二憂也:外有陳豨之患,內有韓信之憂,內外困心。所以朕之煩惱,爾敢持內罪殺信乎”。呂后曰:“臣愿領陛下圣旨”。呂后殺韓信后,平話作者又發表一番評論:
大漢十年九月十一日,韓信歸世。其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長安無有一個不下淚,哀哉,哀哉,四方人民嗟嘆不息:“可惜枉壞了元帥”!人皆言蕭何共呂后定計。當日蕭何三箭,登壇拜將。今日成敗都是蕭何用機,人皆作念怨之。[6]
平話是民間文學的代表,洪邁所謂俚語正是出自民間。在平話中,平話作者對劉邦和呂后是極力否定的,對項羽和韓信等異姓三王被殺卻格外同情,所以平話作者虛構出劉邦命呂后殺韓信的情節,批判其兔死弓藏式的卑劣,也批判蕭何與呂后合謀殺害韓信,這有違史實,否定了蕭何殺韓信的歷史功績。
《三國志平話》前有《仲相斷陰間公事》一節,也對劉邦兔死狗烹給予強烈譴責。劉邦殺功臣不得人心,其負恩形象遭人痛恨。司馬貌斷獄故事深入人心,至《三言二拍》中,經馮夢龍加工增飾,形成《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故事,情節更加豐滿,劉邦負恩形象更加生動。值得注意的是,平話作者認為韓信之死,罪魁是劉邦,幫兇是蕭何和呂后,故有“人皆言蕭何共呂后定計”云云,此種思想乃直接繼承《資治通鑒綱目》而來。
元雜劇是宋元間民間文學的另一代表,其中的兩漢戲對蕭何殺韓信也格外關注。與平話作者相比,雜劇作者對蕭何殺韓信亦持批判態度,且程度更深,這是二者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在于,平話作者憎恨蕭何的同時,亦憎恨劉邦和呂后,而雜劇作者則極力為劉邦回護,更不提呂后之事,韓信敗亡實乃蕭何誣陷而死。在《隨和賺風魔蒯通雜劇》中,雜劇作者開篇即云:
小官在朝,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俺漢家有三個大功臣,第一是韓信……現今韓信封為齊王……爭奈韓信軍權太重,雄兵數十萬,戰將百余員。常言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那韓信元是小官舉薦的,他登壇拜將,五年之間,蹙項興劉,扶成大業。小官看來,此人不是等閑之輩,恁的一個楚霸王,尚然被他滅了,況今軍權在手,倘有歹心,可不覷漢朝天下,如同翻掌,這非是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作恁的反復勾當,但是小官舉薦之人,日后有事,必然要坐罪小官身上,以此小官晝夜尋思,則除是施些小計,奏過天子,先去了此人爪牙,然后翦除了此人,才使得我永無身后之患。[7]
顯而易見,雜劇作者既秉承了平話作者認定蕭何是韓信敗亡的重要罪魁的觀點,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藝術虛構,蕭何出于自保殺韓信,這與洪邁所持觀點相同,所不同者在于:一方面,雜劇作者同情韓信,因為韓信并未反叛,其被殺是因為蕭何進讒言;另一方面,劉邦并無殺韓信之心,不唯如此,韓信冤屈而死,劉邦還為韓信平反昭雪。在對待劉邦的態度上,平話與雜劇之所以會產生分歧,主要在于二者作者文化水平的差異。平話作者生活于社會底層,文化層次較低,故對劉邦殺戮功臣格外憤恨;韓信落難,蕭何未能施以援手亦格外憤恨,這些均源于下層市民最樸素的思想。而雜劇作者多為社會下層的士大夫,他們尊崇孔孟之道,在文學創作中注意為賢者諱,因此極力為劉邦回護。正是因為如此,在雜劇創作中就要回避劉邦殺韓信的情節,所以殺韓信之罪過便全部歸咎于蕭何,故“敗也蕭何”的文化意蘊已經生成。
明清時期,兩漢題材小說作者基本秉持了平話和雜劇作者對蕭何與韓信故事的評價,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豐富發展。在《兩漢開國中興傳志》中,在韓信被殺后,作者發表一篇評論:“韓信既死,天昏地慘,日月無光,自長安城中以至四外,官軍百姓知者,無不下淚,嘆息呂后蕭何合謀枉殺英雄良將。”[8]很顯然,此語來源于平話,《兩漢開國中興傳志》的作者對韓信持同情態度,認為韓信之死實乃呂后蕭何二人設謀殺害,這與《兩漢開國中興傳志》中保留高祖密囑呂后殺韓信的情節,彼此關合,這說明劉邦仍是殺韓信的罪魁,蕭何、呂后是重要幫兇。
在《全漢志傳》中,作者對蕭何與韓信的評價進一步流變,首先是《全漢志傳》刪除了高祖密令呂后殺韓信的情節,高祖親征陳豨,臨行前囑咐呂后曰:“朕領兵親征,又患韓信廢置,久懷異心,恐信兵中起,與豨為應,其勢可憂。煩御妻權國,早晚有□急,當以肖何計議,如畫策定計有陳平可謀。”[9]隨著兩漢題材小說的流變,小說作者逐漸為賢者諱,對劉邦殺韓信的事避而不談。如此一來,殺韓信的主謀便是呂后和蕭何。《西漢演義》亦繼承了這一思想,并進一步強化。在《全漢志傳》中,諸呂為亂是重要故事之一,故呂后亦為批判的對象,而《西漢演義》則停筆于惠帝即位,未演義諸呂為亂事,故呂后亦被美化。事實上,美化呂后,即回護劉邦,故袁于令在韓信被殺后評曰:“是日天地昏暗,日月晦明,愁云黑霧,一晝夜不散。長安滿城人盡皆嗟嘆,雖往來客商,無不悲愴。人言蕭何前日三薦登壇,何等重愛,今謝公著告變,亦當在呂后前陳說開國之功,可留他子孫,方是忠厚;反立謀擒信,及三族之時,卒無一言勸止,何其不仁甚耶。”[10]在袁于令看來,導致韓信敗亡的罪魁不是劉邦、呂后,而是蕭何,袁于令對蕭何未能為韓信開脫罪責甚為不滿,其態度與《資治通鑒》中胡三省所評內在精神一致,但不同的是,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胡三省均認為劉邦殺韓信有錯,而在小說中,則逐漸為劉邦開脫,認為韓信咎由自取,劉邦乃仁主。如此一來,除韓信的罪責就全部落到蕭何身上,故“敗也蕭何”越發名副其實。
四、 “敗也蕭何”文化探源
韓信于漢家可謂功勛卓著,導致其最終敗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劉邦建國后誅殺功臣,是韓信敗亡之根本所在。后世史傳和文學作品將韓信敗亡的原因逐漸歸罪于蕭何,其根本原因在于漢民族意識。
在我國歷史上,對中華民族影響最為深遠的王朝莫過于漢朝,故而中華民族的主體為漢族。伴隨著漢民族的產生[注]在20世紀50年代,國內外學者發起了關于漢民族產生時間問題的討論,主要觀點如下:1.形成于秦漢之際,以范文瀾為代表。2.形成于明代中后期,以楊則俊為代表。3.形成于清代,以康拉德為代表。4.形成于鴉片戰爭之后,以原蘇聯歷史學家格·葉菲莫夫為代表。詳見曹守亮《20世紀漢民族形成問題研究》和呂桃《漢民族形成于何時?——介紹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兩篇文章。隨著此問題研究的深入,至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越來越傾向形成于“秦漢之際”說,代表作有王雷《民族定義與漢民族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5期)、徐杰舜《漢民族形成三部曲》(《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吳廣平《漢民族形成新論》(《吉首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等。進入新世紀,仍有學者持此觀點,代表作為蔡瑞霞《試論漢民族的形成與民族史的撰述》(《中州學刊》,2002年第3期)等。,民族意識亦不斷形成,在此后的歷史長河中,民族意識對漢民族的影響異常深遠,尤其在少數民族入侵的御侮時期,漢民族意識可以最大限度地團結國內力量,抵御外來侵略。
盡管漢民族意識形成于漢武帝時期,但若論對于漢民族意識形成所起的作用,漢高祖劉邦要遠遠大于漢武帝。劉邦乃漢朝的開國之君,在秦末天下大亂時,劉邦從一泗上亭長,逐漸戰勝強敵,開辟兩漢四百二十余年的基業,功勛卓著,彪炳千秋。漢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系列治國策略,在其后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慢慢深入人心,得到人民大眾的普遍認同。最為重要者在于,兩漢時期百姓安居、國家興盛、天下太平時間多,戰亂時間少,百姓世受漢恩,所以感懷劉家威德。
此外,劉邦在打天下的過程中,具有仁政于民、折而不撓的意志品格,這不僅使其得到百姓的愛戴,最終擊敗項羽建立漢家王朝,也為漢朝執政者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后世光武、昭烈均繼承了劉邦仁民愛物、百折不撓的意志品格。與此同時,光武帝劉秀、昭烈帝劉備在中興漢室的過程中,均自稱漢家苗裔,以正統身份自居,以興復漢室自高,并最終實現了中興漢室的奮斗目標。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使漢家正統得以延續,劉備建立蜀漢政權,雖偏安一隅,也寄托了漢民族的希望。
后世每當國家政權旁落,希望中興時,便會高舉漢家大旗。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劉淵建立漢趙集團,五代十國時期劉知遠推翻后晉,建立后漢。劉淵與劉知遠均姓劉,與兩漢帝王同姓,這是其宣揚興復漢室的天然條件,但二者又有所不同。
魏晉南北朝時期,劉淵借助漢民族意識建立趙漢集團。劉淵與漢高祖劉邦確實有點血緣關系,西漢開國,劉邦無力征繳匈奴,并與之和親,匈奴冒頓也改稱漢姓。司馬氏與曹魏集團大戰之際,劉淵想利用二虎相爭之機,借助人心思漢的普遍心理,入主中原,他與眾將商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11]于是建立趙漢集團。正是基于此,劉淵被視作蜀漢的合理繼承者,劉淵建立的政權被視作再興蜀漢,劉淵的軍事行動被視作為劉禪復仇,后世三國題材中均持此觀點。《三國志平話》有意構建西漢、東漢、蜀漢、趙漢一脈相承的政治鏈條,以劉淵興漢做結。《三國志后傳》沿襲《三國志平話》的主旨思想,以劉淵作為蜀漢的繼承者,虛擬出劉淵帶領蜀漢后裔興復漢室的故事。
五代十國時期,劉知遠不滿石敬瑭出賣燕云十六州,繼而推翻石敬瑭建立的后晉,建立后漢政權,并“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祧”[12]。劉知遠與劉漢政權沒有血緣關系,但卻以高祖光武為祖宗,其意在于利用高漲的漢民族意識,助其一統天下。但后漢王朝僅立國四年,且厚斂于民。正是基于此,后世三國題材無劉知遠故事,但《殘唐五代史演義》中對劉知遠興漢給予正面評價。戲曲題材中也有《劉知遠白兔記》等名著流傳。
明末清初,歷史演義大盛,在“帝蜀寇魏”觀念與“擁劉反曹”思想影響下,《三國志通俗演義》率先出版。《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歷史演義的開山之作,同時也是巔峰之作,在當時社會產生深刻反響,其他題材的歷史演義如雨后春筍,兩漢題材歷史演義應時而生。兩漢與三國在歷史時序上前后相連,按照歷史發展時序講,三國故事有相當一部分是東漢故事。又因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表現的“擁劉”思想,本身就是劉漢王朝,所以兩漢題材歷史演義與《三國志通俗演義》密不可分,特別是在表現漢民族意識方面,兩漢題材歷史演義比《三國志通俗演義》更直接、更具體。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下,劉邦形象理應以正面形象出現。
因為高祖妄殺功臣的形象已深入平話和戲曲之中,而平話和戲曲又是兩漢題材歷史演義創作的素材,因此隨著兩漢題材歷史演義的不斷豐富發展,創作者文化素養的不斷提高,漢民族意識越來越強,為賢者諱的創作意識越來越濃,劉邦妄殺功臣的劣跡逐漸被凈化。韓信被殺,蕭何確實出力不少,特別是騙韓信入宮就擒,有賣友求榮之嫌。于是蕭何逐漸成為替主解憂的犧牲者,被釘在賣友的恥辱柱上。
五、結論
在韓信被殺這個問題上,韓信、劉邦、蕭何三者之間是聯動關系。韓信敗亡的根本原因在于韓信簒逆,劉邦誅殺功臣是韓信敗亡的重要原因,蕭何助呂后除韓信利國利民。南宋以前的史傳作者在客觀記錄韓信敗亡史實時,對韓信敗亡原因及歷史評價不斷發生變化,總體傾向是對韓信敗亡感到同情惋惜,對劉邦誅殺功臣持否定態度,故劉邦成為韓信敗亡的罪魁。南宋之后,受《資治通鑒綱目》影響,正統觀念加強,漢民族意識高漲,文學作品在史傳同情韓信敗亡、否定劉邦殺功臣的基礎上,對韓信敗亡故事進行大膽創作,總的傾向是為韓信脫罪、為賢者諱,蕭何則逐漸演化為韓信敗亡的罪魁。在漢民族意識高漲的歷史時期,劉邦作為兩漢開國之君,自然是諸家文學創作歌頌的典范,小說戲曲作者在韓信敗亡的問題上盡力為劉邦回護,對劉邦殺韓信避而不談,韓信敗亡的主要原因則逐漸演變為蕭何設謀擒韓信,并不肯在呂后前為韓信開脫,蕭何成為韓信敗亡的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