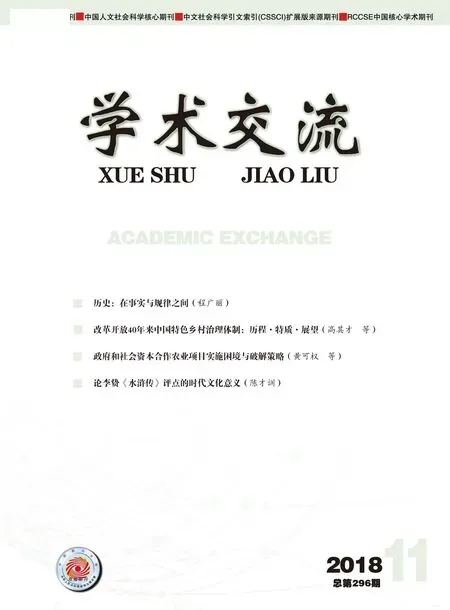自我異化中的心理學維度
——基于亞當·沙夫《作為社會現象的異化》的思考
謝宇格
(哈爾濱工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哈爾濱 150001)
一、馬克思異化理論發展的心理學批判與延展
馬克思異化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的理論資源自20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推動西方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新馬克思主義等流派的興起與發展。但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馬克思異化理論受到以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代表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政治家的批判,他們把異化理論的闡發作為一種修正主義的觀點來加以拒斥。正是在此背景下,波蘭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亞當·沙夫(Adam Schaff)作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站了出來,從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秉承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對馬克思異化理論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美蘇冷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對立的敏感時期,他與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弗洛姆(Erich Fromm)、卡倫·霍尼(Karen Horney)等具有心理學背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和合理借鑒,從心理學的維度重新審視、反思和批判了當時“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關于馬克思異化理論研究發展現實,并開辟了一條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異化理論研究發展的新思路,使馬克思異化理論的闡發得到了進一步深入全面的發展。
(一)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發展中的“教條主義”心理學維度的批判
20世紀50年代末,在面對馬克思異化理論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研究的式微,馬克思異化理論被視為“修正主義”的觀點,以及對這種理論的合理討論面臨被禁聲的危險的背景下,沙夫借用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和洛奇赤(Milton Rokeach)的封閉性心理理論(Closed Mind)對持上述態度的研究者給予了心理學維度上的批判與“診斷”,沙夫認為“(對馬克思異化理論持誤解、拒斥和厭惡態度的馬克思主義者——筆者注)個人堅持的信念和官方宣布的觀念之間的沖突,所堅持的信念和個人的實際行為之間的沖突,導致了認知的失調”。還有“一種可能性是與以前所堅持的信念發生沖突的信息和知識所形成的心理‘遮蔽’,具有導致認知失調的危險。于是一種‘封閉性心理’的人格出現了”[1]8-9。沙夫借用心理學的理論直接分析了這些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研究持消極態度的人的心理,并指出“當一個人在精神上完全閉塞,那么這是一種真正的病態”,是一種“特殊的病理狀態”,是一個“真正的信仰者”特殊的自我防衛。[1]16-17
在分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時,沙夫說:“不幸的是,心理學常常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阿克琉斯之踵(Achilles’hell)。”[1]17這些對馬克思異化理論持誤解和拒斥態度的人沒有意識到自己認知層面的“封閉”,而沙夫要做的就是指出這些人認知層面的失調和“封閉性心理”人格的形成,以及他們在“教條的思維”的心理基礎上所形成的“教條主義”意識形態。因此,沙夫借用心理學的理論批判了這些人的不合理思維,批判了這種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發展的教條主義意識形態,指明了馬克思異化理論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這也就是對“為什么要寫這本書”的最好的回答。[1]19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本身的心理學延展
沙夫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通過對馬克思原著的梳理和總結明晰了異化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真實存在,同時指出異化理論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不僅僅在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中,而且在成熟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也有所體現,異化理論是馬克思思想中自始至終、一脈相承的一條真實存在的理論鏈條。沙夫系統地梳理了馬克思異化理論對古希臘哲學、宗教學,以及對盧梭、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理論借鑒。與此同時,沙夫也梳理了馬克思本人著作中從《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神圣家族》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異化理論的具體文本表述和邏輯鏈條。最后,沙夫在梳理完馬克思異化的理論借鑒來源和馬克思本人著作中關于異化理論的闡發后指出:“異化理論將不再是異端或修正主義的謊言;它是馬克思的真跡,沒有它人們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除非[與費斯汀格(Festinger)的認知失調理論相一致]我們只從馬克思那里選取能夠被我們接受的部分加以理解。”[1]71沙夫以此來回應一些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異化理論的偏見。
而在沙夫進一步梳理馬克思異化理論文本和厘定異化相關概念并嘗試構建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的概念體系的過程中,沙夫在概念上對馬克思異化理論進行了類型學上的分析并指出:(a)異化和自我異化,(b)物化和(c)商品拜物教是異化理論主要的分析對象。其中,沙夫挖掘到了一個異化理論中還未被充分闡述并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理論資源——自我異化。沙夫敏銳地意識到,“一旦這種‘自我異化’涉及到人的自我時問題就會變得復雜”,他通過列舉“一個熱衷于藝術卻迫于生計淪為三流作家的人”和“一個可能受到極權主義體制威脅而貶低自己并且放棄理想的人”以及表述為“感到他的生命同他想象的自己之間的關系是相異的”來對自我異化的命題進行了獨特的詮釋。[1]80同時他也指出,回答這樣的問題“沒有必要以‘人的本質’或‘人類本性’”這樣的想象來切入,“這里更需要心理學的知識,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吹毛求疵’”[1]81。沙夫是東歐較早一批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相關研究的學者,這里他也批判性、反思性和建設性地指出:“盡管在以非馬克思主義為主的相關命題的著作中有一種趨勢將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等同于自我異化的趨勢,但卻很少有人提及這個問題或對自我異化進行深入分析。”[1]91沙夫認為,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弗洛姆在這方面是一個例外,他在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分析中,以及在為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節選英譯本所寫的導言中對馬克思關于人同他人以及自我異化概念進行了解釋。
這樣,沙夫通過思考關于自我異化問題背后的心理學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橫向廣度和縱向深度,開拓了研究異化理論的一個學術視野,豐富了馬克思異化理論的資源,同時也將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研究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從宏觀拉向了微觀,豐富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研究的視域。沙夫的這種思考與反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20世紀60年代初,沙夫在其早期著作《人的哲學》(1961)中就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個體維度,并將這一維度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核心維度之一。在其1965年發表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個體》中,沙夫邀請了具有心理學專業背景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作序。這足以證明沙夫已經逐漸開始意識到,人的問題是理解社會歷史問題的重要維度之一,因此通過心理學了解人的問題將極大地幫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更好地“改變”世界。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下,能夠最大程度地銜接個體問題與社會問題之間的研究域就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綜上可以看出,沙夫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系統闡發,其背后的意圖就是要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的哲學維度,建立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這也正是沙夫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研究者所持的基本立場。
二、社會層面的自我異化及其心理機制
沙夫在闡述自我異化的問題時首先錨定了兩個參照系,這一點十分重要,即當人感覺到“被異化了”是需要一個“參照系統”的,這兩個參照系是:(1)社會以及在給定的社會中以個人或集體形式出現的其他人;(2)人自己的“自我”(ego)。[1]163這兩個參照系一個是從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角度建立起來的,一個是從分析心理學角度建立起來的。其中,從社會學角度建立起的參照系統主要是借用了埃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關于失范(anomie)的定義,即個體在社會中感到“被異化”,主要體現在個體與社會、社會機構以及他人關系方面的異化。而從分析心理學角度建立起來的參照系統主要是指個體感受到與自我的疏離,進而感到“被異化”,主要體現在個體與“自我”、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行動相關的異化。而沙夫對上述兩個坐標系中個體的自我異化在心理學層面上的闡述都作了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上的批判性分析與討論。
(一)部分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對異化問題分析的短視
沙夫首先從在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美國社會心理學文獻入手,對從事相關經驗研究的理論家的主要觀點開始歸納和分析。沙夫列舉了梅爾文·西曼(Melvin Seeman)關于異化的五種含義:無力、無意義、無規則、孤立和自我疏遠[2]784,以及戴維茲(A·Davids)對異化的定義,即異化可以簡單地定義為綜合征,有下列相關的個人性情組成:以自我為中心、不信任、悲觀情緒、焦慮以及怨恨。[3]61沙夫對上述兩個關于的異化的定義作出了馬克思式的批判,他指出“拋開對這個問題的心理效用的分析,完全沒有異化的社會問題的分析。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種形式的概念是無用的。這兩個理論建議大體上說明了美國文學研究的理論弱點”[1]187。
沙夫在這里直接指出了部分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對異化問題理解的狹隘,西曼和戴維茲等人對異化的理解完全割裂了異化概念中個人問題與社會問題,這一點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立場上的研究者顯然是要給予批判的。西曼的短視之處在于他沒有把自我異化當作特定的生活領域和人的活動來加以分析,而戴維茲的短視之處在于他把異化當作人的個性心理特征的一種綜合征,根據這一個概念推出的異化在沙夫看來是屬于狹義的解釋范疇上的,而并不是全部異化現象的綜合。在社會層面研究自我異化的心理機制而又忽視人的生活領域(社會)在沙夫看來無疑是多數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異化問題的致命弱點。從這里可以看出,沙夫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與一般心理學家在學術立場和任務上具有本質的不同。一般心理學家們的學術立場通常是不涉及價值判斷問題的,而需要解決的任務往往也只要“解釋”問題即可;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立場是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的,這一取向貫穿其整個研究始終,而其要解決的任務也不僅僅是要“解釋”世界,其更重要的還要“改造”世界。因此,在同樣面對自我異化的問題研究時,作為哲學家的沙夫在學術立場上是人道主義取向的,而在解決問題的分析維度上也要明顯比一般的社會心理學家更加全面。
(二)社會層面自我異化問題合理的分析維度
然而在這里,沙夫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當時生活在美國的心理學家弗洛姆關于異化概念及其理論分析的推崇,他指出“弗洛姆的作品占據不同的地位,我們應當單獨研究他的思想”[1]184。就什么是異化的問題弗洛姆在其著作《健全的社會》中有明確的回答,即異化是一種體驗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人感到自己是一個陌生人。[4]120-121在其后期的作品《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中,弗洛姆更是把異化直接地表述為:從根本上講,異化就是作為與客體相分離的主體,消極地接受性地體驗世界和他自身。[5]56-57沙夫對弗洛姆將心理學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政治層面的嘗試性做法是表示贊同的,他評價道“這是一個值得稱贊的嘗試,討論政治層面而忽視任何心理分析是眾多學派思想的致命弱點,也包括馬克思主義”[1]190。
沙夫對弗洛姆利用分析心理學來研究異化問題的推崇不是沒有道理的。其一,此時的沙夫已經意識到完全從歷史和社會的維度去分析自我異化問題過于宏觀,因為自我異化問題畢竟與“自我”問題相粘連,而對自我相關問題進行分析的最好的理論工具就是分析心理學。這一點從沙夫把“自我”這個概念錨定在“ego”這個典型的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詞上就可以證明。其二,沙夫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其歷史社會宏觀視角分析問題的思維是他的長處和優勢,此外,沙夫始終堅信關于異化問題,包括自我異化問題的分析與研究是不可能缺少歷史社會視角的,因為異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問題,是一種作為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現象出現的問題。而在眾多西方心理學家中,弗洛姆成為了沙夫研究自我異化問題的最大借鑒者,這是因為弗洛姆對異化問題的解釋與分析參照了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個維度,而這里的社會學多是參考了馬克思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心理學則參考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學。
(三)對弗洛姆關于異化問題闡述的批判與揚棄
對弗洛姆的稱贊并沒有影響沙夫對其研究理論的批判,批判的關鍵點在于弗洛姆對異化概念的模糊。沙夫認為,“弗洛姆使用一個模糊的概念很好地揭示和分析了全部社會生活中的異化表現”[1]195。沙夫在對異化相關概念進行類型學分類時曾明確將馬克思異化理論中的異化分為異化和自我異化、物化、商品拜物教三類,在沙夫看來,弗洛姆模糊了這些概念之間的邊界,把異化等同于自我異化。[1]194沙夫認為,這樣的模糊缺乏概念上的嚴謹,也變相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關于異化問題的歷史社會學分析維度的地位。
沙夫主張在厘定異化與自我異化之間的明確界限的前提下,對個體自我異化問題進行社會的和心理的兩個維度的分析,而在社會層面分析自我異化的心理機制問題的又一個前提是如何處置“社會”這個變量。多數社會心理學研究者沒有意識到這個變量的重要性,而有些研究者則選擇了懸置這個變量,而像弗洛姆這樣的研究者選擇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大膽地引入這個變量并進行討論著實少有,這也是沙夫推崇弗洛姆關于異化問題分析的原因之一。
總之,沙夫雖然對弗洛姆關于異化問題中的一些表述提出質疑,但總的來說他們在分析當代人自我異化的問題上,具有很多一致性,而沙夫也承認他從弗洛姆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1]196在沙夫看來,社會層面中人的自我異化主要是指一種消極的和接受性的心理體驗,造成這種心理體驗背后的心理機制是人自我的主體性與環境客體(包括社會、機構、與他人的關系)相分離。筆者認為,在社會層面自我異化的心理可以簡單概括為由于個體自我主體性與社會及其關系的相異和疏離而產生的一種主觀體驗。造成這種主觀體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生物、心理、環境和社會制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本質原因之一是個體自我與社會及其關系之間的主體性爭奪的矛盾。
三、個體層面的自我異化及其心理機制
沙夫在論述社會層面個體自我異化的心理機制之后把分析的目標聚焦到了這些“孤獨者”身上,這些“孤獨者”的行為表現的發生雖然總是以社會條件為背景,但通常也是在特定的心理生理基礎上發展的。沙夫指出,“這些人的社會化,恢復參與到社會生活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這也是揚棄化斗爭的重要性的意義所在”[1]209。這里充分體現了沙夫在分析自我異化問題中對心理學基礎支撐的肯定以及其人道主義態度的完全展現。沙夫將個體層面的自我異化主要分為三種:與自我意識相關的異化、與自己生命相關的個人異化——生存空虛,以及與其行為相關的個人異化。
(一)與自我意識相關的異化
沙夫認為,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人在什么情況下會出現與“自我”相異化的體驗,他認為出現的途徑有三個:(1)在某些特定的心理疾病或精神分裂癥的病痛下人會出現失去自我認同感。(2)在一種更溫和的形勢下,即“當對比個人所具有的模式時,也就是與他想要成為什么,他想要在表面上看起來像什么進行對比時,我們能感受到‘自我’的異化”。(3)當個體投身于市場關系中,他可能會感到自己的特定特質、能力和行為是異化的,是商品或是物品。[1]210然而,異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沙夫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是個體從什么當中異化了?關于這個問題人們通常有兩種解答:一個是個體在人的本質(essence)和人性(human nature)中異化了;二是個體在社會內在化的人格的理想模式中異化了。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沙夫顯然認為第一個答案的討論屬于一個形而上的死胡同,因為他認為人性假設像宗教信仰一樣是無法核實的。沙夫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去理解這樣一個人格的理想模式,即每一個社會都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同時也擁有自己獨特的模式。在這個基礎上,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個性和性格特點,創造自己的行為模式。[1]213因此,在沙夫看來,“自我”就是個體通過社會和個人的人格模式之間的衡量來建構的。個體意識層面的自我異化就是指個體在多大程度上在自身和社會層面上與這個模式相異,異化的程度通過所接受的模型同真正的失態的偏離程度加以衡量。[1]214沙夫進一步追問這種與社會塑造人格模式有關的異化是否可能與喪失自我認同感意義上異化之間存在一種精神疾病有關的連接?其實,弗洛姆在其著作《健全的社會》中明確給出過精神健康的特點:有愛與創造力的能力;掙脫了同部族及土地的亂倫關系;人的身份感的基礎為體驗到自己是自己力量的主體和動因;能把握自身之內及之外的現實,即能夠發展客觀性和理性。[6]55-56而其中的第三點和第四點其實就是說的個體在非異化下的健康心理狀態。沙夫通過分析精神病學家及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維斯(Frederick A·Weiss)和卡倫·霍尼(Karen Horney)的著作后認為,自我異化的體驗與神經官能癥的體驗類似,進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弗洛姆的觀點,即“異化作為一種自身的疾病可被認為是現代人精神病理學的核心,甚至是在與精神病相比不那么極端的形勢中”[1]220。
(二)與自己生命相關的個人異化——生存空虛
沙夫在這里顯然是受到了美國臨床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Emil Frankl M.D)和弗洛姆的影響。沙夫不再從純粹的形而上哲學的角度去討論生存意義的問題轉而向心理學尋求合理的解釋途徑,但這種轉向是帶著馬克思主義式的轉向而非完全的轉向。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沙夫的歷史和社會思維視角已經從他的意識層滲入到了無意識層,無時無刻不在提示著自己不要忘了歷史維度、不要忘了社會維度。而弗蘭克爾和弗洛姆正是這種被沙夫認為“契合”的心理學家。弗蘭克爾和弗洛姆的立場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是通過剖析那些感到生活空虛和存在無意義的人的認知與行為來詮釋他們背后的心理機制。簡單來說,這種人酗酒、吸毒、濫交、耍流氓甚至犯罪,其目的是逃避空虛和存在無意義的生活,他們在面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生活帶來的消極心理體驗時本能地觸發了個體心理的逃避機制。關于心理逃避機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有著完整的論述,而弗洛姆從心理學的角度認為個體心理逃避機制的觸發源于孤立個體的不安全感,一旦個體沿著“消極自由”的道路進行退縮以此來消弭個體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鴻溝來克服孤獨,上述不良的行為就會產生,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外在原因就來源于社會或社會制度。[7]92-93針對這個外在因素,弗蘭克爾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增強意志以加強生命的意義,而弗洛姆在其《健全的社會》中更是直接將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社會制度的病態。在這一點上沙夫是不完全贊同的,他指出“與提出的揚棄異化操作相關的懷疑主義不適用‘生存空虛’理論本身。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我異化的最深刻的表現形式,即與人自己的生命相關的異化”[1]227。沙夫從實踐的角度主張,社會制度是導致個體生存空虛和無意義進而自我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現實生活中“人的活動”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辦法。
(三)與其行為相關的個人異化。
在借鑒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分析了與自我意識相異化,以及與自己生命相關的個人異化背后的心理機制及其形成的原因之后,沙夫又重新回到了馬克思主義解構性的批判與建構、歷史與實踐的思維中,從馬克思理論最基礎的勞動入手來闡述與行為相關的個體異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針對勞動異化問題曾寫道:“生命如果不是活動,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賴于他、不屬于他、轉過來反對他自身的活動。這是自我異化……”[8]54-55因此,勞動異化中的一個維度就是個體的自我異化。沙夫認為,創造性(creativity)和勞動(labor)之間的區別是判斷個體是否異化的行為表現形式。“人們自愿從事的活動是創造性,人們的行為是來自內部動機,滿足感使他感到快樂(消除了緊張的感覺,這種需求產生的感覺)。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人們為了獲得生存所需的手段,如由于身體或經濟需要,所從事的活動是勞動。”[1]228因此,沙夫在這里指出創造性活動是揚棄異化的人的活動。但問題在于決策者的決策標準往往與個體的意愿無關甚至相悖,并強迫個體——如果他想要生存的話——成為“市場”所要求的主體。沙夫認為,這不僅限制了創造者自身,并將其置于商品市場的影響之下。因此,對私有制的揚棄是克服個體勞動異化的關鍵。但在這里沙夫并沒有激進地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定沒有異化,而是更加清醒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不同并不在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異化現象,而是在于這樣的事實,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正是由于廢除了私有制——所以形成了揚棄異化的條件;而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克服異化現象。差別不在于是否存在異化,而在于是否存在揚棄異化的可能性”[1]234。
誠如上述,沙夫認為個體層面自我異化背后的心理原因是個體自我與通過社會內在化的人格的理想模式之間的相異和背離。個體層面的自我異化來源于個體自己的生命,當生活失去目標,生命失去意義,也就是在弗洛姆所稱的空虛感,弗蘭克爾所稱的生存空虛出現的時候,個體自我異化的主觀感受就會產生出來,而當認知具體作用到行為上就會進一步導致勞動力和工作的異化。沙夫認為討論空虛和無意義對人會產生什么樣的具體影響的問題是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命題,在這里沙夫更關注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怎么去克服自我異化。沙夫承認在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仍然存在自我異化,但現階段解決的焦點不是如何徹底克服自我異化而是如何使自我異化的克服成為可能,因此沙夫主張對私有制的揚棄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使個體的自我異化得到揚棄并使克服異化成為一種可能。
四、結語

沙夫無疑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中包含了深刻的人道主義,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以及宏觀地和歷史地、社會地分析問題的思維方式,但同時又不忘記俯下身去體察身在社會中的每個人的心理感受并試圖為他們找到一條能真正通往心靈解放的路。沙夫點亮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浩瀚海洋中關于人的燈塔并使它開始閃耀人道主義的光輝。然而燈塔雖閃亮并指引著方向,但在進發實踐的過程中沙夫發現這背后許多關于人的問題不能夠單單地從形而上的哲學層面和完全地從歷史社會層面來解決。如果說沙夫在其前期作品《人的哲學》(1961)和《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個體》(1965)中還主要在哲學和社會學視域中尋求解決人自身異化問題的方法的話,那么在《作為社會現象的異化》(1977)中沙夫或許開始更多地向心理學這樣的微觀視域的學科來尋求支撐以探索解決問題的出口,他已然意識到這個問題并著手涉及,當然,他的理論還存在許多問題。
沙夫一方面恪守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宏觀的歷史研究思維與研究邏輯,對完全從微觀層面切入研究異化問題的心理學者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作為一名心存人道主義信仰的研究者又深深體察到心理層面的分析對于解決異化問題是重要的且必要的。人是社會的人,但人也是自己的人。就在這種糾結和矛盾之間,沙夫想從制度層面去黏合這兩者之間的錯位,他的異化理論,尤其是關于自我異化的理論,以及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問題的理論闡述凸顯出了其本身的理論張力。雖然說沙夫在對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問題的嚴重程度的判斷有待商榷,在給出的關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克服個體異化的解決方案也帶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同時,他將異化視為一種一般的社會現象的看法存在著某種泛化的特點,但這并不影響他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和一位勇敢的理論探險家和實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