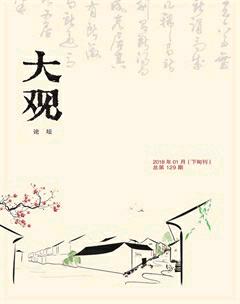杜尚的虛藝術(shù)
摘 要:我們應(yīng)該對美國做一個深入的但并不是很膚淺的了解,才能獲得杜尚為何成為大智者的背后原因,并將其與東方禪宗大師鈴木大拙的感悟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就能從中得到某種超越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啟發(fā),這種體會和感悟要比掌握藝術(shù)史的知識更重要的。
關(guān)鍵詞:杜尚;鈴木大拙;禪宗;純藝術(shù);非藝術(shù);權(quán)威
就美國80年代以前的現(xiàn)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總體情況而言,可以分為兩種趨勢既純藝術(shù)和非藝術(shù)。第一種純藝術(shù)指一種追求純粹的藝術(shù)形式而無需關(guān)注社會政治因素等的藝術(shù)流派,第二種是非藝術(shù),它與純藝術(shù)正好相反,它主張混淆藝術(shù)與非藝術(shù)的區(qū)別以及藝術(shù)與生活的區(qū)別,這對于把握這種時期的美國現(xiàn)代藝術(shù)發(fā)展脈絡(luò)是不會有什么差錯的。
但是第二種美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家混淆藝術(shù)與生活界限的時機的非藝術(shù)的來源是什么,那就是來源于東方禪宗,將禪宗介紹給西方的大師正是鈴木大拙,而他被譽為“世界的禪者”。(鈴木大拙(1870~1966),世界禪學(xué)權(quán)威,日本著名禪宗研究者與思想家。)
凱奇消化這禪宗思想,并影響到他的學(xué)生既勞生柏,勞生柏這種以生活為對象的革命性藝術(shù)的旗幟使藝術(shù)成為美國化,可見鈴木大拙的禪宗觀深刻影響到美國后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走向。
接下來談及杜尚“虛”藝術(shù)與消解藝術(shù)的“無用”藝術(shù),其和鈴木大拙禪宗思想上有何相似,而且擁有問題意識比學(xué)習(xí)美術(shù)史知識至少重要上百倍。
一、不相信藝術(shù)家有創(chuàng)造功能
馬塞爾·杜尚他是一位法國藝術(shù)家,20世紀實驗藝術(shù)的先鋒;是一位法國藝術(shù)家,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西方藝術(shù)有著重要的影響,是達達主義及超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創(chuàng)始人之一。
杜尚并不相信藝術(shù)家有“創(chuàng)造”功能,他認為藝術(shù)家與商人以及教師一樣,他們的工作就是“做”,“藝術(shù)”在梵文中指的是“做”。所以杜尚認為藝術(shù)家應(yīng)該是被稱為工匠的,只是,“藝術(shù)家”這名詞到了現(xiàn)代藝術(shù)以及后現(xiàn)代藝術(shù)時期時,才開始變成個體性名詞。在當代社會里,“藝術(shù)家”這名詞逐漸成為“名士之輩、知名人士”的意思,之后藝術(shù)家不再是那種專門生產(chǎn)類似商品的人。
同樣杜尚本身對藝術(shù)家這詞匯并沒有多少好感的,他與藝術(shù)家保持著不遠也不近的距離,因為杜尚他看到巴黎藝術(shù)是各自為政的,像立體派勃拉克和畢加索也是互相競爭并攻擊對方,這一點杜尚是極其厭惡,也是他正想回避的一點。
除了以上兩點原因外,還有更重要的是另外原因就是杜尚具有某種先知先覺,看穿了那龐大的現(xiàn)代及后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體悟到其中是與“人心”是脫不了干系的。
二、作品《泉》被拒的事件
杜尚之所以選擇了“現(xiàn)成品”純粹是為了消遣而已,對于杜尚為何要選擇現(xiàn)成品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它是可以避免個人的好惡趣味影響到它。杜尚一直提醒自己無需被美學(xué)形式或色彩或造型所框定。接下來說明杜尚《泉》被拒的原因。
這種現(xiàn)成品只是杜尚一個小小的陰謀:測試那后現(xiàn)代“新”藝術(shù)流派是否真的能夠接受“異”藝術(shù)——指其與最新建立起的藝術(shù)流派的觀念和思想完全迥然不同的帶有“異”因素的藝術(shù)作品。結(jié)果杜尚發(fā)現(xiàn)那所謂的打著“自由”精神的革新藝術(shù)流派,依然與傳統(tǒng)派同樣畫地為牢,不過是推翻舊廟宇,重建新廟宇而已。如同十字軍那樣為了奪回自己藝術(shù)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而已。有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藝術(shù)領(lǐng)域發(fā)生事件可以與政治事件作一個比較,兩者有相似之處。話說回來,《泉》正是超出“新”藝術(shù)流派的所限定的范圍,才會被評審團壓制著不讓展覽。當時杜尚也是其中評審團一員,但他不動聲色地觀察了所有發(fā)生的事情。
因此杜尚才會覺悟到,無論是傳統(tǒng)派,還是革新派,都是同樣樹立新權(quán)威,排除異己。
三、藝術(shù)家一生僅有四件精品
杜尚還發(fā)現(xiàn),再怎么被稱為“天才”藝術(shù)家,他那最優(yōu)秀的作品在他一生中不過是四五件而已,剩下大多數(shù)是湊數(shù)的劣品。像《亞威農(nóng)少女》和《大碗島上的星期天》確實是驚動了大眾。但是如果連畢加索畫下的廢品也要被贊賞的話,那也是有點小問題了。因此杜尚認為,藝術(shù)家畫上三四張杰作后總會有廢品,這原則用在所有的藝術(shù)家身上都不為過的。
杜尚曾經(jīng)接受采訪說到,他堅信“藝術(shù)家”只是作為一個媒介作用而已,這藝術(shù)家做出什么東西,然后某天有大眾的介入,他才會被承認,被后代承認。你是無法阻止其過程的,簡而言之,杜尚認為,這兩點構(gòu)成的產(chǎn)物,一頭是做出其東西,另一頭是看見此東西,杜尚給了兩者同樣的重要性。
杜尚想在此說明藝術(shù)家成名由來,以及觀眾的介入的重要性,和觀眾的介入對藝術(shù)家的塑造起到的很大作用。當然了,一般沒有藝術(shù)家愿意接受這樣的解釋。所以我們應(yīng)該靜下心來思考一下,何謂“藝術(shù)家”。
四、無心與無為的境界,我并不反感視網(wǎng)膜
有人誤解杜尚一直反對作品所帶有的“視網(wǎng)膜”成分,認為杜尚使用“現(xiàn)成品”是反對傳統(tǒng)那種“視網(wǎng)膜”作品。其實杜尚本身對“視網(wǎng)膜”作品并未有過什么反感,他說他喜歡超現(xiàn)實作品中的一種思想狀態(tài),對他而言,盡管超現(xiàn)實“視網(wǎng)膜”成分存在,但是總有出色的思想超越它們,杜尚認為強調(diào)觀念并不一定要指出很多觀念,杜尚無法接受的是作品里沒有任何的觀念在里頭,而是僅僅單純地訴諸視網(wǎng)膜的作品。
可見杜尚是不怎么反感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也并沒有刻意地去劃分藝術(shù)流派之界限。這種思想如同禪宗所言“無分別心”,從這件事可反映杜尚思想中存在一種“無為”“無心”的超高的東方獨有的境界。
五、一旦有了名稱就會受限制
杜尚推崇“姐妹方塊之和解”,此概念是他發(fā)明的一種消解藝術(shù)對立的系統(tǒng)。杜尚意思是,在舊的系統(tǒng)中防御的一方總是與新系統(tǒng)中防御一方有爭執(zhí)。杜尚說道:“我加上和解是因為我發(fā)現(xiàn)一個可以減少對立的系統(tǒng)。”
杜尚提出這理論的背后是因為,他所參與的超現(xiàn)實主義流派,其中成員之間因為某成員是否能夠堅持超現(xiàn)實主義風(fēng)格而產(chǎn)生了爭執(zhí)。事件是這樣子,成員之一基里柯開始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帶有濃厚的超現(xiàn)實主義風(fēng)格,后來他放棄此風(fēng)格并回到傳統(tǒng)風(fēng)格中去,導(dǎo)致普呂東等人大肆攻擊基里柯。杜尚基于“姐妹方塊之和解”的原則而為基里柯辯護,以此來消解與普呂東的矛盾。從這件事可見杜尚的思想境界有著東方禪宗那種大智慧。鈴木大拙曾言:任何事物,一旦擁有了名稱就會受限制,一有執(zhí)著,就會有局限,人生的格局就被限制了,沒有執(zhí)著,人生便有許多可能。endprint
正是因為普呂東他創(chuàng)立了超現(xiàn)實主義,有了所謂藝術(shù)上的新名稱后,就開始劃定藝術(shù)界限,然后普呂東處心積慮地拋棄傳統(tǒng)藝術(shù)手段,又不擇手段地去求取藝術(shù)革命。試問有誰能像杜尚那樣可以將“圓融無礙”的狀態(tài)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的,沒有人可以做到,包括藝術(shù)流派以及藝術(shù)家……
六、我并沒有看到多少新的東西
50年代之前歐洲產(chǎn)生了野獸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等各路流派,50年代出現(xiàn)的以美國為主的抽象表現(xiàn)主義、大色域等藝術(shù)流派,后者出現(xiàn)的藝術(shù)流派都追求純粹的形式,拋棄作品的宗教,政治以及社會在作品中的成分,他們極其推崇一位現(xiàn)代藝術(shù)最大的代言人柏林格林的理論主張。
到了70年代后,藝術(shù)開始脫離正派藝術(shù)之正軌,它們繼承杜尚之精神并衍生出波普藝術(shù)、環(huán)境藝術(shù)、行為藝術(shù)等。一個主義接著另一個主義,不斷地革命又革命,似乎是不斷向“新”方向前進。
我們來看一下杜尚對此會有怎么看法,杜尚說“看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已經(jīng)沒有多少新的東西了,波普藝術(shù)是挺新的,視幻藝術(shù)也挺新的,不過我覺得這種藝術(shù)已經(jīng)沒有多少前途了,當你做上二十遍后,恐怕它就會過時得非常快,單調(diào)又重復(fù)。只是我所做的與他們做得并沒有什么相似,因為現(xiàn)在他們的流行方式就是多做,盡可能的多做——為了多掙錢”。
這就是杜尚對現(xiàn)代藝術(shù)的態(tài)度,以“無為”態(tài)度來觀看那風(fēng)起云涌的藝術(shù)幫派。
七、曲解杜尚藝術(shù)思想的的美國人
美國人試圖理解杜尚,但是理解得不夠深刻,有時候還會曲解杜尚,將杜尚的反藝術(shù)行為當成反傳統(tǒng)的勇氣,其實杜尚醉翁之意不在酒。不管怎么說,美國人至少是杜尚精神的繼承者。
早在杜尚之前,美國人已經(jīng)建立起屬于自己的風(fēng)格流派,只是多年后,美國人對這種無限次地追求純藝術(shù)抽象風(fēng)格而感到厭倦。于是美國人利用杜尚思想開始踏上一條讓藝術(shù)成為非藝術(shù)的現(xiàn)成路,像波普藝術(shù)就是這時代下的產(chǎn)物。無所畏懼的美國人在60、70年代將這個藝術(shù)弄成改頭換面的新局面。這使得美國在世界藝術(shù)潮流中起到領(lǐng)頭羊的作用。西方后現(xiàn)代藝術(shù)正是從杜尚思想中衍生出來的。
盡管后現(xiàn)代時期出現(xiàn)的諸多藝術(shù)流派受惠于杜尚,但都沒有真正繼承杜尚那給我們所呈現(xiàn)的“無分別”狀態(tài)。杜尚給西方展現(xiàn)是“自由”的最高標準,使當今藝術(shù),什么都可以去做,卻無人可以去評價,結(jié)果造成藝術(shù)界的魚目混珠的局面。西方人誤解杜尚,甚至抱怨杜尚,認為杜尚是當代藝術(shù)罪魁禍首,他們要求建立新的標準。
其實倘若要說誰之過,錯在于我們,而不是杜尚,錯在我們這唯利是圖而無不心蕩神迷的人,將杜尚作為達到某種目的而采取的途徑,結(jié)果適得其反。
因為杜尚的境界太高了,他的深度無法被我們消化太多。西方嘗試走杜尚路,但多少在其中得失參半。
西方人所得是:現(xiàn)代藝術(shù)界已經(jīng)是“民主制度”——人人都是藝術(shù)家,都有發(fā)言權(quán)。西方人所失的是:大師是做不了了,但是新名堂換的太快,幾天一換,誰能受得了。更重要的是他們一邊欣賞杜尚的反標準,一邊用杜尚的反標準來評判當代藝術(shù)。倘若杜尚活到今日,指不定會拿起畫筆反一反這胡鬧的藝術(shù)也說不定。
八、結(jié)語
其實我們應(yīng)該在更廣泛的范圍內(nèi)去讀杜尚,不應(yīng)該將眼光局限在藝術(shù)這領(lǐng)域內(nèi),也更不應(yīng)該被藝術(shù)這新名堂限制了。像杜尚把他那最寶貴的思想如“自由”“無為”等給了我們,如同鈴木大拙中“沒有否定,也沒有肯定,只有簡單明了的事實”。
杜尚與鈴木大拙都認同“有就是無,無就是有”的思辨精神,這與杜尚曾經(jīng)說過的“拒絕與接受,其實是一回事”有異曲同工味道。所以我們會發(fā)現(xiàn)后現(xiàn)代藝術(shù)是一條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鎖鏈,若鎖鏈其中某一環(huán)單獨取下的話,藝術(shù)史成為無頭無尾的蛇,所以將杜尚和鈴木大拙這兩位關(guān)鍵人物連起來,并整體性考慮,就會非常清晰看見這條鎖鏈將會帶我們走向何處,這一點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
我們應(yīng)該對美國做一個深入的但并不是很膚淺的了解,才能獲得杜尚為何成為大智者的背后原因,并將其與東方禪宗大師鈴木大拙的感悟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就能從中得到某種超越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啟發(fā),這種體會和感悟要比掌握藝術(shù)史的知識更重要的。
參考文獻:
[1]王瑞蕓.杜尚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
[2]王瑞蕓.通過杜尚——藝術(shù)史論筆札[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
[3]鈴木大拙.禪與心理分析[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張艾心,天津美術(shù)學(xué)院2017級美術(shù)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自由藝術(shù)。
導(dǎo)師:鄧國源教授、王愛君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