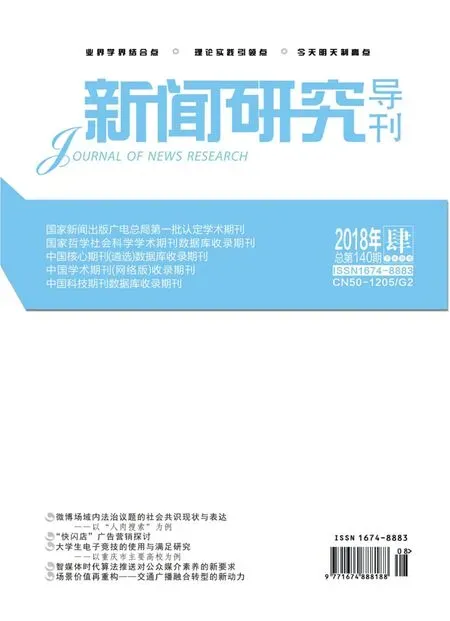淺析客觀性理念在早期媒體環境下的發展
王國洋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開篇緒論部分就美國新聞界經常受到“不夠客觀”的指責的問題展開討論,“作為商業性機構,為什么新聞業就理所當然應該客觀呢?從一戰期間極少考慮客觀性,到20世紀60年代業界普遍認為“客觀性是美國新聞業的象征”,期間經歷了美國報業的數次變革。作者以社會學為立足點,通過對美國新聞業的數次變革的剖析,為我們梳理了客觀性從無到有逐漸變化的清晰脈絡。
一、便士報——平等主義時代的美國新聞革命
便士報起源于1830年,伴隨著美國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出現并在之后得以迅速發展。在這個階段,客觀性成了新聞工作者始終遵循的理念。報紙的名稱也由“廣告報”轉為“先鋒報”“明星報”,被稱為美國新聞業的“商業革命”。
新聞成為報紙的中心,各家便士報極盡所能地搜集可稱之為“新聞”的事實并加以報道。19世紀30年代,城市商業精英和財政領袖的原有地位被為數更多的新興資本家占據。人才就業更加開放,越來越多的人成了投資者。便士報“獨立、廉價、大發行量、強調新聞、重視失效等這些讓同行既羨且恨的特征,與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密不可分”。但與此同時,便士報一切只向錢看的弊端也日益顯露:只要付出廣告費,人人都可以花錢雇傭公共報刊。在這一點上,便士報頗受詬病。
二、故事與信息——19世紀90年代的兩類新聞
在美國新聞工作逐步變成獨立職業之后,新聞工作者有了自己體制內的工作準則。郝斯特的《新聞報》和普利策的《世界報》的出現代表了當時“新新聞主義”(News Journalism)的興起。這種偏向娛樂的報道風格與奧斯克《紐約時報》追求事實的手法截然不同,作者將這分別稱之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在普利策的倡導下,報紙的業務運營及報紙與廣告客戶之間的關系得到了理性改進,并在19世紀80年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報紙的發行量成為廣告商衡量報紙的標準,廣告業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
普利策的“煽情主義”和“自我廣告”政策使報紙發行量劇增,但其背后還蘊含著復雜的經濟、政治等社會條件。1900年,美國的移民總數占總人口的46%,多數人不會英語或英語水平很低但有學習的欲望,加上受眾的“娛樂”欲望在這些報紙中得到了滿足,還有女權主義的崛起、消費文化的興起等社會條件,都使得這些報紙受到廣泛歡迎。然而19世紀90年代“信息新聞業”與“故事新聞業”之間的道德戰卻是階級沖突的一種遮掩。《時報》對準的是對自己的生活有較強掌控力的階層,較為理性; 《世界報》則以自己的風格營造出一種全新、奇異、不可預料的生活體驗,這種體驗對于“新近接受教育的群體、剛從鄉村進城的群體、工人階層和中產階級”而言較為貼切。因此簡單地判斷誰代表了客觀事實并不具備實際意義。
三、客觀性成為意識形態——戰后的新聞業
20世紀20年代,“記者們已經不再相信事實可以不證自明,不再堅持信息的功效,拋棄了進步主義時代中產階級引以為豪的中立性”,加上懷疑主義和質疑態度進入大眾教育的行列,理性受到懷疑,深刻影響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聞業。“現代公共關系之父”艾維·李(Ivy Lee)有句名言“世界根本不存在事實,一切只是詮釋”,可以生動地體現出“事實”在新聞中的沒落。
四、“批判文化”興起——20世紀60年代,新聞管理與調查性報道的對抗
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聞業兩代人之間圍繞“客觀性”產生的“對抗文化”,制造了一批更激進、更具懷疑精神的新聞受眾,不相信政府,年輕而反叛。當然,出現這類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民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則變得更加疏遠。政府與媒體的現代關系以1919年的巴黎和會為象征,政治議題的公開話成為首要問題,政府開始有意識、有組織地“管理新聞”。1961年,“偽事件”(pseudo event)概念出現,指形容事先設計好的,借以被記者報道和復制的事件。20世紀60年代此類偽事件在美國國內層出不窮,引起了新聞界的強烈不滿。伴隨著批判文化的興起,對政府更加嚴苛、政治上更加成熟的趨勢也慢慢出現在普通百姓中,新聞業的對抗性報道、調查性報道出現,廣播、電視等媒體形式通過開發新的新聞節目形式來適應社會文化的變化,在新聞業中迎接批判文化。
五、思考
對于美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以及民主化進程和文化的沖擊,客觀性理念始終貫徹其中。我國的新聞研究者和從業者也應當從中受到啟發:新聞事件源于社會,應更廣泛地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考察新聞事件,不能只是簡單地看待問題,應該努力提高新聞報道的水平和質量;當然,對于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也有很大的好處。
[1]張華.尋找新聞學研究的新路徑——《發掘新聞》的啟示[J].中國報業,2013(06):22-25.
[2]王樂.從《發掘新聞》觀照美國新聞業客觀性的由來[J].傳播與版權,2017(12):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