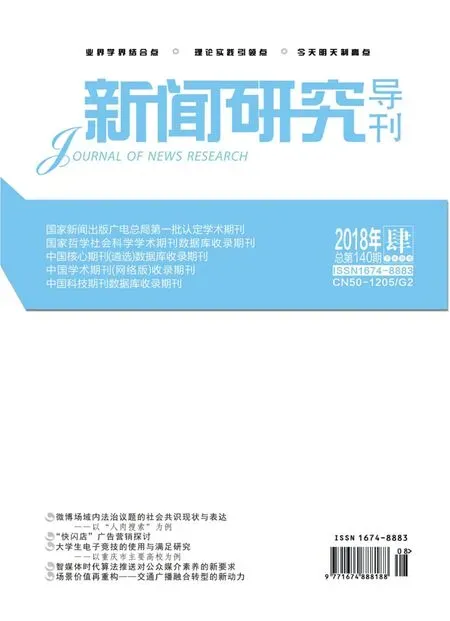智媒體時代算法推送對公眾媒介素養的新要求
金澤軍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89)
一、引言
2017年5月,AlphaGo以3∶0戰勝世界圍壇第一人柯潔。這次人機大戰似乎再次證明了在圍棋這一高智商競賽領域,人類已非機器對手,同時也讓人不禁思考:人工智能是否真會如霍金在2015時代精神會議上所預言的,在未來100年內取代人類。不管未來如何,人工智能正深刻影響著當今社會各個領域,媒體便是其中之一。學者彭蘭認為,人工智能與物聯網、AR/VR等種種新技術一起,正在把媒體帶到一個智能化時代。[1]
媒體的智能化主要體現在內容的生產和分發兩個方面。生產方面,以機器人寫作為典型。早在2006年,美國湯姆森公司就使用計算機程序完成金融新聞的撰寫。近些年,國內也陸續出現了騰訊的“dreamwriter”、今日頭條的“張小明”等機器人新聞寫作應用。而內容分發方面則體現在算法推送上,即基于用戶的興趣愛好、行為習慣等因素對信息進行個性化、精準化的分類呈現,國外以Facebook、Buzzfeed為代表,國內以今日頭條、一點資訊、天天快報等為代表。當今,算法推送正逐漸成為網絡新聞的主要分發方式,而上述平臺正日益掌握用戶的新聞接觸。
赫胥黎曾在《美麗新世界》中表達了一種憂慮,人們會漸漸愛上甚至崇拜那些壓迫他們的工業技術,從而喪失思考能力。換言之,毀掉我們的,也許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2]那么,智能化媒體時代,公眾應該如何應對只會“投其所好”的算法呢?如何在享受算法帶來的紅利的同時避免它的負面影響呢?筆者認為,除了依靠平臺、媒體人和政府的行動外,公眾自身也應該努力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
二、媒介素養的概念及發展
“媒介素養”一詞最早由英國學者李維斯在《文化和環境:批判意識的培養》一書中提出。1992年,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給出了以下定義: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在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3]
不過隨著媒介的變遷和發展,“媒介素養”這一概念也在不斷充實和完善。新的媒介環境對身處其中的人們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媒介素養”應運而生。2005年,美國新媒介聯合會在《全球性趨勢:21世紀素養峰會報告》中將“新媒介素養”定義為:由聽覺、視覺以及數字素養相互重疊共同構成的一套能力與技巧,包括對視覺、聽覺力量的理解能力,對這種力量的識別與使用能力,對數字媒介的控制與轉換能力,對數字內容的普遍性傳播能力,以及輕易對數字內容進行再加工的能力。這一定義不僅強調了公眾使用和解讀媒介的能力,還強調了其主觀能動性,即利用媒介進行表達和交流的能力。[4]
除了內涵的擴充,媒介素養適用的主體也在不斷擴大。它不再局限于公眾,學者陳力丹認為,媒介素養不僅是公眾對于媒介的認識和關于媒介的知識,還有傳媒工作者對自己職業的認識和一種職業精神。[5]學者彭蘭則將媒介素養主體擴展到政府。[6]不過,在智能化媒體時代,傳媒工作者與公眾的界限已模糊,受者也可以是傳者。并且,相對于職業的新聞工作者,公眾日益成為今日頭條這樣的智能化平臺的傳播主體之一。因此,在探討算法推送對公眾媒介素養的新要求時,公眾的傳者身份不容忽視。
三、智媒體時代的算法推送
(一)算法推送機制及傳播特點
目前,網絡數字新聞的分發渠道有三種:一是傳統媒體的客戶端,如人民日報、新京報、中國日報等;二是門戶網站的客戶端,如騰訊新聞、網易新聞、百度新聞等;三是如今日頭條、一點資訊這樣基于算法的個性化新聞推送客戶端。其中,前兩者都是人找信息,而后者則顛覆了這一傳統模式,讓信息主動找到對它感興趣的人。
算法推送的本質是信息和用戶的匹配。一方面,智能化推送平臺會從各方面收集用戶數據,如注冊、登錄、關注、點贊、收藏、評論、轉發等,從而生成用戶畫像,以了解用戶的性別、年齡、地理位置、閱讀偏好、行為習慣、社交關系等;另一方面,這些平臺會分析和聚合內容的主題、情感、語義等,然后再基于算法將信息與用戶進行匹配。
算法推送的特點在于個性化、場景化和社交化。首先,個性化的算法可以為用戶推送量身定制的內容。過去,信息分發是一對多,即海量信息同時呈現在用戶面前,用戶需要自己尋找感興趣的內容;而現在,算法推送實現了多對多,千人千面,沒有人會收到完全相同的新聞推送。其次,算法可以為適應用戶的場景化適配,即滿足用戶在不同時段、不同地理位置的新聞需求。例如,用戶在走路、運動時,通過可穿戴設備如智能手環,可以接收精短的突發新聞;而在等車、候機時,則可通過手機瀏覽一些有趣味性的內容。最后,算法推送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社交關系,資訊平臺和社交媒體日益融合,如一點資訊綁定微博、騰訊推出天天快報、知乎推出讀讀日報等。社交關系的綁定,可以幫助算法更好地推測用戶的興趣愛好,從而在內容推送上更懂用戶。
(二)算法推送的“反面”
雖然算法推送將用戶從海量信息選擇的疲憊中解放出來了,滿足了其個性化的需求,但似乎也正將人們置入其他困境中。
1.個性化的代價:隱私泄露。想要獲得個性化定制的新聞推送,就必須先泄露自己的信息,如性別、年齡、地理位置、閱讀興趣、社交關系等。只有在獲得這些信息的前提下,算法才能將用戶與信息精準匹配。然而,這一過程并非都是用戶主動選擇,人工智能技術在各行業領域的滲透,讓信息的采集變得更為隱蔽,如搜索引擎監視著我們的瀏覽習慣、社交媒體監視著我們的生活和社交網絡,淘寶類的購物平臺監視著我們的購物喜好……我們以個人信息換取這些媒介的服務,在互聯網上留下各種痕跡,算法技術則將這些痕跡整合,生成所謂的用戶自畫像,使我們活在赤裸相見的世界。此外,如果算法推送系統被黑客入侵,那么用戶的任何信息都有可能被非法使用。2012年,某電視節目做了這樣一個實驗:路人被邀請進入帳篷,他們只要安靜地坐在那里,帳篷內的通靈者就能說出他們的家庭地址、摩托車顏色甚至銀行卡密碼。正當他們驚訝時,帳篷內的一個白色幕布落下,里面坐著一群黑客,正在不停地搜索他們的社交賬號。可見,在這樣一個時代,個人隱私變得觸手可及,如果信息被非法采集,人們也許會因此受到傷害。
2.投其所好:欲罷不能。為什么瀏覽信息的我們根本停不下來?管理學的“瓜子理論”告訴我們如下規律:其一,無論人們喜歡與否,很容易拿起第一顆瓜子;其二,一旦吃了第一顆,就會吃第二顆、第三顆……停不下來;其三,在吃瓜子的過程中,人們可能會做一些別的事情,如去洗手間等,但回到座位上后,還會繼續吃瓜子,不需要他人提醒、督促;其四,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會一直吃下去,直到吃光為止。[7]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可以通過嗑瓜子在短期內獲得積極的反饋。而在算法推送中,“瓜子理論”更是被應用得淋漓盡致。首先,算法只推用戶感興趣的內容,因此他們更容易“拿起第一顆瓜子”;其次,算法根據場景推送內容,那么在不同時段和地理位置,用戶都可以瀏覽到自己想看的內容,從而獲得極大的滿足感,那么“嗑瓜子”會一直持續下去;最后,瓜子會被磕完,而算法推送的內容卻不會窮盡,何時結束這一過程完全取決于用戶自身,取決于用戶是否可以擺脫自己喜歡的東西。而現實是,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被算法推送的內容掏空時間,對其日漸成癮,沉溺其中,逐漸喪失自控力甚至自主意識。
3.只看你想看的:作繭自縛。在算法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只看我們想看的,而將那些自己不熟悉、不感興趣、不認同的信息直接過濾掉,從而陷入“信息繭房”。這一概念由美國學者桑斯坦提出,他認為,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8]其實,“信息繭房”并非這個時代獨有,在傳統媒體中,類似的現象表現為“選擇性接觸”,區別在于前者是用戶的自主選擇,而后者則是由算法和用戶共同決定的。當用戶長期只接觸一類信息時,結果可能就是“作繭自縛”,自己的觀點不斷得到強化,從而導致最終的視野狹隘和思想封閉,失去對社會的整體認知,日益遠離真相。類似的觀點還有“回聲室效應”:信息或想法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強。除此以外,如果所有人都將自己困在繭房,那么公共討論也將變得日益艱難。在桑斯坦看來,民主社會的健康發展得益于兩個條件:第一,人們的信息接觸是不期而遇的;第二,大部分公民應該擁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經驗,并且在討論中去分享這些經驗。[9]而在算法推送機制中,兩個條件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很容易導致群體極化現象。
4.點擊大于內容:價值迷失。在算法推送機制下,把關人從傳統的記者、編輯變成了機器,評判標準也變得單一化,變成了用戶點擊量。然而用戶興趣中不乏低級趣味,在這一標準下,點擊量遠高于內容質量,導致隱含負面價值取向的內容被大量推送,如標題黨新聞、黃色新聞、虛假新聞等,影響整個社會風氣的如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在這樣的環境中,未成年人最容易被影響。例如,前段時間的兒童邪典片流入中國,體現了算法把關極大的局限性。算法把關,主要還是靠對信息的語義理解,不能觸及語言背后的深義,也不能將其放置在整個社會大背景下去作深層次解讀,所以才會有兒童邪典片的猖獗。由此可見,算法把關看似客觀,卻反而容易造成新聞失衡、偏見和新聞價值的缺失,使真正重要的內容被忽視,公共利益讓位于個人興趣。
四、算法推送對公眾媒介素養的新要求
傳播學者喻國明曾說過:“從社會發展的邏輯上說,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猶如有機體的進化一樣,一旦發生便具有其發展的不可逆轉性。”[10]因此,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而要整合社會各層力量共同應對算法推送帶來的弊端。從個性化推送平臺出發,首先,平臺要優化內容質量來源,一方面給予專業新聞源更高權重,另一方面促進用戶原創內容質量的提升。其次,平臺需要不斷提高算法的智能化水平,不僅要提高用戶自畫像的精確度,更要通過機器學習幫助其識別和甄選優質內容。最后,要實現人機協作,充分發揮人的價值,彌補算法的缺陷。而在社會層面,嚴格的法律法規亟待制定,以保護用戶隱私,促進人工智能的良性發展。不過,公眾不能完全依賴平臺和社會的保護,而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從而更好地享受人工智能帶來的紅利。基于上文論述,筆者從媒介使用素養和信息消費素養兩個基本方面出發進行分析。
(一)媒介使用素養——自控、隱身
媒介使用素養,簡而言之,是媒介的基本使用能力,比如在傳統媒體時代,公眾需要識字才能閱讀報紙;而新媒體時代,則要求人們掌握網絡、手機的一系列操作,以獲取信息。不過智能化媒體時代,算法推送的發展對人們的媒介使用素養提出了兩個新的要求。
第一,使用媒介時的自控能力。算法推送基于用戶興趣,很容易讓人們對個性化推送平臺產生依賴、上癮,甚至沉溺其中。這不僅會占用他們的休閑時間,還會慢慢占據其工作、學習時間,影響公眾的自身發展和自主意識。因此,在面對這種黏性特別大的媒介時,公眾應有充分的認知,學會自控,通過時間管理、發展其他興趣愛好,將控制權收回到自己手上,合理、節制地使用媒介,而不是淪為媒介的奴隸。
第二,使用媒介時的“隱身能力”。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在智能化媒體時代,隱私已成為一種奢侈品,要保護個人隱私更是需要巨大的代價。不過,在《隱身術》(The Art of Invisibility)一書中,著名的黑客Kevin Mitnick為人們提供了一些可能性。他在書中描述了人們隱私可能泄露的情景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并給出了對應的解決方案,比如不輕易填寫個人的真實信息,關掉諸如閱讀、美顏等不相關的APP的定位服務,只連接可信賴的公共WiFi等等。[11]雖然要在這個時代隱身很難,但至少要掌握一些“隱身能力”,使個人隱私的保護程度最大化。
(二)信息消費素養——多元、開放及自我把關
在過去,海量復雜多元的信息要求公眾具備更多的選擇、判斷與辨識力。然而,在算法推送機制下,公眾面對的信息日益單一化,為其所想所聽,因此反而容易陷入“信息繭房”的狹隘境地中,并且在“回聲室效應”的影響下,日益強化固有的認知偏見,無法認知社會全貌。
在智能化媒體時代,用戶更需要培養多元開放的信息消費素養。換而言之,公眾要有社會參與意識,跳出“信息繭房”,多聽多看,有意識地接觸不同領域、不同媒體平臺的信息,關注公共事務,積極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避免思想僵化、極化。
除此以外,在消費算法推送的信息時,公眾還應具備對內容質量和價值的批判能力。由于算法推送智能化水平還不高,公眾要學會做自己的把關人,拒絕消費那些隱含負面價值的信息,讓壞內容無藏身之地。不僅如此,從信息生產素養出發,公眾作為內容生產者和傳播者,需要理性地、負責地進行傳播,避免傳播低俗、煽動性的內容,助力社會形成良好風氣。
[1]彭蘭.智媒化:未來媒體浪潮——新媒體發展趨勢報告(2016)[J].國際新聞界,2016,38(11):6-24.
[2]尼爾·波茲曼(美).童年的消逝[M].吳燕筵,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5.
[3]張玲.媒介素養教育——一個亟待研究與發展的領域[J].現代傳播,2004(04):101-102.
[4]A Global Imperative:The Report of the 21st Century Literacy Summit [DB/OL]. New Media Consortium(2005)www.nmc.org/publications/global-imperative . pdf,2013-03-22.
[5]陳力丹.關于媒介素養與新聞教育的網上對話[J].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02):12-17.
[6]彭蘭.社會化媒體時代的三種媒介素養及其關系[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2(03):52-60.
[7]瓜子理論帶來的管理啟示[J].人才資源開發,2006(03):99.
[8]畢競悅.通過網絡的協商民主——評桑斯坦的《網絡共和國》與《信息烏托邦》[J].清華法治論衡,2009(02):423-442.
[9]凱斯·R·桑斯坦(美).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畢競悅,譯.法律出版社,2008:8.
[10]喻國明.“機器新聞寫作”時代傳媒發展的新變局[J].中國報業,2015(23):22-23.
[11]Kevin Mitnick . The Art of Invisibility[M]. American:Little,Brown,and Company,2017:26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