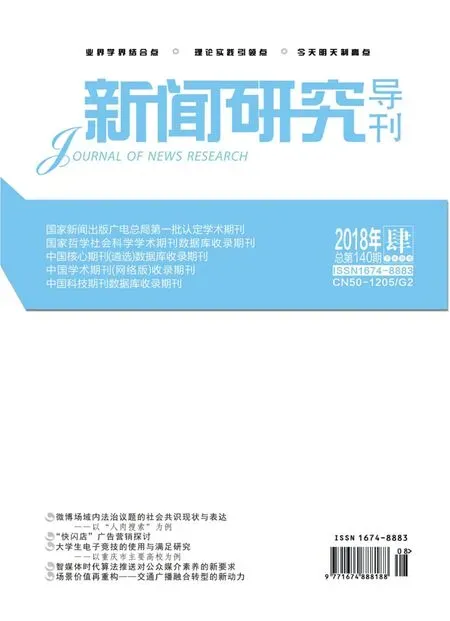“蘇報案”淺析
——新聞自由:不懈的追求
鄭天子
(渤海大學,遼寧 錦州 121000)
一、“蘇報案”的始末
“蘇報案”發(fā)生于清朝末年,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案件,在中國新聞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鴉片戰(zhàn)爭后,帝國主義的炮艦打破了中國長時間的封閉狀態(tài),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許多個沿海城市變成了通商口岸。上海城內也出現了租界,被人們稱作“國中之國”。外國人在租界除了帶來中國人從來沒有見過的商品和技術外,還帶來了中國從未形成的媒體——報紙。1896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個叫胡璋的人創(chuàng)辦了第一份報紙——《蘇報》。該報開始沒有什么特別,是一種格調低下的小報。該報幾經轉手落到陳帆的手上后,報紙經過改版,更貼近當時的政治生活,迅速成為一家極具影響力的報紙。列強的槍炮不斷襲擊著中國,在重重壓力之下,原本高傲自大的清朝政府開始反思自己,開始探索一條變革圖新的道路,于是朝廷開始興辦新學,希望能夠培養(yǎng)出一些掌握先進科技和管理方法的新型人才。對于一些新事物持鼓勵態(tài)度,報紙就是受益者之一。從此,上海灘辦報紙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內容也變得十分豐富,報紙的發(fā)行量也直線上升。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在早期活躍的報紙上發(fā)表講話成為一種潮流。當時的南洋公學,學生思想比較激進,學校越打壓,學生鬧得越兇,逐漸演變成學潮,《蘇報》抓住了這個社會熱點,開辦學界風潮欄目,連載這次學潮的發(fā)展和變化,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蘇報》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一些思想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開始在《蘇報》上發(fā)表文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都成為其撰稿者,《蘇報》很快成為抨擊清政府宣傳革命新思想的根據地。期初,清廷對這些言論大體上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但隨著革命思潮的涌動,人們的話語也越來越激烈,開始公開地站在革命的立場上。1903年5月初五,《蘇報》介紹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日本回來的革命者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也迅速走紅,公開呼吁革命最終引起了朝廷的驚恐。根據清廷的法律,對于這些大逆不道的言辭,應該把寫這些文章的人凌遲處死。但報紙在英租界里,清廷不敢前去逮捕,清政府和列強多次協商后,列強終于同意抓捕鄒榮和章太炎,警察趕到時,章太炎抱定必死的決心,安坐待斃,而鄒容本來已經逃脫,但聽到章太炎被逮捕,立刻投案自首。雖然列強同意清政府抓人,但是提出審查案件必須在租界之內進行,判罰后還要在租界里的監(jiān)獄來執(zhí)行。當然,列強也給了一點面子,同意由清政府主持審判,但審判的形式主要以西方國家普通法的共同形式,也就是說按當庭控辯的形式來進行,于是一個歷史性的場景出現了,清政府在外國法院指控他的臣民。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民平等對簿公堂,幾輪審判下來當事人之一的章太炎付出了3年牢獄的代價,只有二十幾歲的鄒容被判兩年監(jiān)禁但在獄中失去了年輕的生命。“蘇報案”作為在清末文字獄的典型代表,曾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轟動。在中國國土上第一次用法庭公開審理的辦法開庭,法官根據證據而非個人判斷來斷案。千百年來官本位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官老爺”說了算在中國民眾的心里打下了牢固的根基,“蘇報案”對中國民眾來說無疑帶來了進步的思想。從那以后皇權神圣的觀念在中國開始被摧毀。或許當時清政府有勇氣同意使用這種公開審理的方式,就是想讓民眾知道朝廷變法維新的決心。他們也在同步制定憲法,努力地還政于民,可惜這樣的決定來得太晚了。“蘇報案”是中國史無前例的案件,這個案件的審理使得當時的愛國人士和眾多媒體發(fā)現他們宣傳思想和引導輿論的新大陸,那便是租借地區(qū),從此租界地區(qū)就成了反清輿論發(fā)表的平臺,因為在租界內從事輿論宣傳可以回避政府的制裁。從此革命思想如星火燎原。“蘇報案”最終成為清王朝的喪鐘。
二、“蘇報案”的歷史意義
“蘇報案”是一個政治性案件,因其涉及新聞言論自由,在新聞史上也是地位非常。“蘇報案”曾在上海租界7次公開審理。昔日威嚴的清政府在法庭上控告手無寸鐵的文人,雙方在法庭上激烈爭辯。隨著章太炎和鄒容的不斷努力,法庭已成為他們宣傳革命思想的論壇,加之中外新聞傳媒的不斷報道,“蘇報案”讓那些不理解革命,不知道章太炎、鄒容和《蘇報》的人都知道了。讓清王朝感到事與愿違的是他們不但沒能壓制住革命的言辭,反而讓自己的絕對權力在租界地區(qū)失去了用武之地,更擴大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蘇報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事件。“蘇報案”的涉案人員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鄒容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章太炎遭受三載牢獄之災,而《蘇報》主編陳范因此而顛沛流離,家破人亡;但其成了革命思想在中國的一面旗幟。“蘇報案”雖然讓革命派喪失了一家報館,但卻向中國發(fā)出了振聾發(fā)聵的聲音,對清朝政府進行了猛烈的輿論攻擊,民主思想在中國迅速蔓延。清政府雖然鎮(zhèn)壓了這次事件,懲罰了鄒容、章太炎等人,但卻未能達到他們的預期目的,清政府的惡劣行為受到了輿論的譴責,中國再不是那個“官老爺”說了算的中國了。繼章太炎、鄒容之后,一大批思想進步的新聞人開始發(fā)表自己的言論,以后的上海租界民主思想言論更加猛烈,勢不可擋。正如孫中山先生對此案如是評論:“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于是民氣為之大壯。”
當歷史的車輪駛進21世紀,回顧100年前的“蘇報案”,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眼光衡量當時的事件,因為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也是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局限和時代背景注定了當時的報刊思想具有強烈的工具色彩。“蘇報案”在歷史上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清政府在朝廷中作為原告現身法庭,是對幾千年封建專制權威的嚴重打擊。其次,“蘇報案”推動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并擴大了其影響,讓人們逐漸看清了清朝政府的反動本質,中國的革命新思想隨之迅速發(fā)展。同時“蘇報案”也體現了言論自由在當時社會的缺失。“蘇報案”中對敢于發(fā)表言論的人的處理,也讓我們意識到自由總是相對的,絕對的新聞自由或許只存在于“理想王國”,在現實生活中并不能實現。但新聞言論自由是人類永不放棄的追求,“蘇報案”留給我們的是一個大膽發(fā)表自己言論的精神。拋開歷史的局限性,“蘇報案”仍在新聞史上獨放光彩。
三、新聞自由——人類文明的象征和人類共同的追求
新聞自由也隸屬于人權的范疇,其標志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也體現了民主的思想,更是人類永恒的追求。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新聞自由也是革命的追求和目標。在眾多資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人權法案》的通過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外,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也為新聞自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新聞自由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新聞自由,并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受到資產階級的控制。資產階級在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以后,它們逐漸把由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共同爭取來的新聞自由成果據為己有,所以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有濃厚的階級特征和局限性。新聞自由從一開始便具有濃厚的階級特點。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社會也在不斷地進步和變遷。當今世界各個國家都有自身獨特的國情、政治體制以及歷史環(huán)境,新聞自由也有不盡相同的內涵和意義。但是無論如何,新聞自由都是人類永無止境的追求。
[1]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史(上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8-15.
[2]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7: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