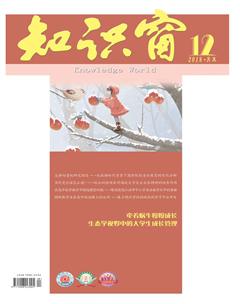書究竟應該怎么讀?
邢星
“對于教育來說,讓人知道知識的結構很重要”在馬未都眼中,知識是結構性的,有層次高低,“對于教育來說呢,讓人知道知識的結構很重要”。
“我覺得,人在讀書中最好的狀態是一個既冷靜、又能夠設身處地地深入一點兒的狀態。”馬未都說起自己當年讀《紅樓夢》的情景:“我當時對曹雪芹崇拜得五體投地,看書的時候就想,曹雪芹寫得有什么好。比如我去看他怎么描述這個賈寶玉,他說:‘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嗔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絳,系著一塊美玉。他一開始說臉色,‘鬢若刀裁,眉如墨畫說毛發,下面形容的都是五官,你看他最簡單的文學描寫這種羅列啊;他下面兩個動態描寫,我覺得一般人寫不出來,‘雖怒時而似笑,即嗔視而有情。曹雪芹這一段描寫都非常精煉,我當時就說,‘哦,他是這么寫,就明白了,這是我十幾歲的事兒。”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孩子讀書都太窄。”馬未都講起自己的讀書經歷,“我十幾歲、二十歲的時候,拿起來看著特別過癮的書是大部頭的醫學書,看解剖、看人體,就是喜歡。這些書跟專業無關,我可能終身都用不上,但是不代表它不會在某一個地方有潛在的好處。”
馬未都自學成才,但他同時強調:“現在很多成功的人沒有很好的學歷,這會讓人覺得好像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出不了這樣的人,他成功就是因為沖出教育的框架。但是你要知道,大部分人是不能獲得所謂‘成功人士意義上的成功的,而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基本能獲得一般意義上的成功,所以各有各的好處,各有各的壞處。我們認為啊,像清華、北大這樣的一類大學,畢業生成功率至少95%以上。”
因為仍將教育主要訴諸學校系統,馬未都對于學校教育的現狀也格外關注:“我喜歡對教育說話,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的教育確實有問題。”
“過去教育人是把德育融進知識里面去,比如《三字經》把中國簡史說一遍,《千字文》告訴你很多科學道理,同時也告訴你很多做人的準則。我們現在,知識是知識,道德是道德,分開教授,這就麻煩了。學生認為道德只在思想品德課上管用,這就是最壞的事。”馬未都越分析,眉頭皺得越緊,“我們今天的教育注重知識和技巧,但這個知識呢是不停地更新的,你也要不停地去學習。所以我覺得,教育主要是教學習的方法和做人的準則,這兩條恰恰是中國教育中最弱的。”
洞明皆學問,馬未都就是這樣一個要把事兒“看透”的人。“對,所以就特痛苦。”他比誰都明白。正是這份“明白”加上這份“痛苦”,在馬未都這兒轉化為一種社會擔當——“我是一個愿意做傳播的人,而且是一個有能力做傳播的人,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