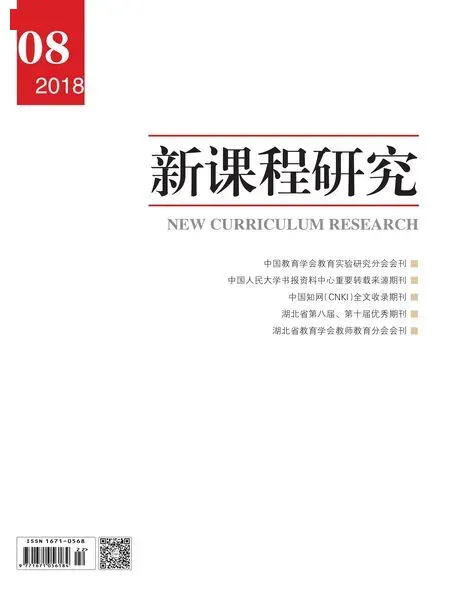程少堂語文教學理論與實踐探索研究
一、語文界的哥倫布
日本著名平面設計大師原研哉在《設計中的設計》一書中說:“一個真正的設計師,應該能夠豐富設計這一概念。”依照原研哉的觀點,我們可以這樣推斷,一個真正優秀的語文教師或者有影響的語文教學研究者,他應該不僅能把語文課教好,而且能夠豐富語文這一概念。程少堂這一生為語文而來,他創立的“語文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中國語文教學美學話語的一場革命,他豐富了語文這一概念。
1.2001年,語文味元年。回想一下,2001年以前中國的語文教師是怎樣教學的?是不是無外乎參考教輔資料之后再來設計教學?是不是無論如何花樣翻新,總也翻不出真正的新角度、新思想?那究竟為什么我們永遠也走不出設計的藩籬呢?
(1)語文味教學思想的誕生。2001年3月的一天上午,程少堂在深圳市羅湖區某中學聽課后,在評課中提出了一個他自己也沒見過的詞——語文味。這次評課后,程少堂馬上撰文《語文課要教學出語文味》,這是我國學術界正式提出“語文味”概念和理念,即把“語文味”初步概念化、研究化的第一篇文章。從此,中國語文界誕生了一個充滿美學味兒的新名詞——語文味。
(2)語文味教學思想誕生的必然性。語文味教學思想的提出是對當代語文教育思潮的辯證整合。語文味教學思想反映了語文教學的內在規律,與新課改語文教改思想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當今的語文教學存在著大量不屬于語文的東西,或把語文課教成其他學科知識的拼盤,或把語文課異化成其他學科的“保姆”,應試化、技術化使語文教學失去了自由、自我與自尊,機械化與模式化又使它喪失了本真與個性。一個本應是最藝術化最富有情趣的教學領域,而枯燥、乏味甚至沒有語文味的語文課卻比比皆是。要改造當今的語文教育,就必須純化語文課本、語文教學過程和語文教學方式方法。需要說明的是,語文味理論所主張的“純化語文教學”,不是有的人所主張的狹隘的“純化”。語文味教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密切關聯,是對中國古典美學中“滋味”范疇的創造性轉化。在審美理論中,所有藝術的最高境界都與詩有關系。而根據中國古典審美理論,詩的最高境界是“有味”即有“詩味”。語文教學既然是一門藝術,它的最高境界也應該是“有味”,那就是“語文味”。語文味正是一種基于漢語言文學特點故而極具中國本土特色的語文教學的美學追求。
(3)語文味的第一代表課。2002年4月,程少堂的大型公開課《用另一種眼光讀孫犁:從<荷花淀>看中國文化》轟動了中語界——這是發現語文新大陸的第一課。一線教師和業內著名學者,都不約而同用“巨大”來形容這堂《荷花淀》公開課的深遠影響。著名語文教育研究專家、上海師大王榮生教授更是把這堂課的教學實錄放在其主編的《走進課堂——高中語文新課程課例評析》一書的第一篇,并對這堂課給出了極高評價:“程少堂的《荷花淀》課例教學是別開生面的,給我們帶來的沖擊力量是巨大的,對教學改革的突破不但是一般的教學方式的變革,而是 ‘教學內容的創生’……教師是課程資源,學生也是課程資源,這一點在這一堂課中得到生動展示。”
程少堂的《荷花淀》作為語文味第一代表課,幾乎蘊含著語文味全部重要思想與理念的萌芽,由此可一窺語文味之堂奧。它一舉掙脫了傳統語文教學思想的鎖鏈,是印證語文味教學思想理論的一次大膽而成功的實踐,是語文新大陸的震撼發現,是中國語文教學美學新體系的奠基之作。
2.2007年,中國語文教育理論發展史不應忽視的年份。2007年4月,程少堂的公開課《在“反英雄”的時代呼喚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細讀》(以下簡稱《紀念碑》)再次驚艷中語界,《荷花淀》算是有了“接班人”,甚至有一線名師稱之為語文味的“巔峰之作”。
(1)語文味教學思想的研究理路。《荷花淀》的巨大成功大大激發了程少堂由此開始的“即器求道,道器合一”的求索之路。借鑒先哲,程少堂清醒地認識到,語文味教學思想要不斷向前發展就必須遵循“即器求道,道器合一”的研究理路。語文味理論即“道”,語文味實踐即“器”,理論離不開實踐,實踐是理論發展的基石。應該說《紀念碑》一課就是在這樣的學理背景下,在語文味思想理論不斷走向成熟時應運而生的。
(2)語文味教學模式雛形初現。對于語文味教學思想本身而言,經過“實踐——理論——再實踐——再理論——再實踐”這一螺旋往復式地不懈探索,《紀念碑》這堂課相較于五年前的《荷花淀》,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它將之前語文味教學中一些看似“無意識、無規則、無形態”的教學信息元與整體結構性要素明晰化了,它讓語文味教學思想的宏觀框架呈現出了清眉秀目,即:語言——文章——文學——文化。事實上,語文味“一語三文”教學模式的雛形在這堂課中已是清晰可尋。
3.2014年,《語文味教學法》誕生。從2007年到2014年,七年,意味著什么?語文味的這七年又如何?
(1)理論型的實踐家或實踐型的理論家。作為一名學者,程少堂的人生追求是“兩只翅膀的翱翔”,即要理論與實踐相濡并進,做理論型的實踐家或實踐型的理論家。程少堂的語文味教學理論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伴隨著實踐而來的。之后,他又通過大量的語文味教學實踐反復印證并指導著自己的理論,同時又不斷豐富發展著自己的思想理論,然后再把新的思想融入自己新一輪的實踐當中加以證明,隨之又再產生新的思想。理論與實踐的兩翼就是這樣在語文新大陸上空翩然鼓動,舞出一片旖旎風光。
(2)語文味教學法的誕生。在語文味教學思想發展到第二個七年之際,由程少堂主編、程少堂語文味工作室成員集體撰寫的《語文味教學法》誕生。該書是中國語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由一線中小學語文教師集體撰寫的語文教學法專著。它的出版無論是對于中國語文教育發展史來說,還是對突破當下的中國語文教學的困境來說,均具有積極的意義。作為語文味教學法的創立者,程少堂在他為《語文味教學法》所寫的序言中寫道:“目前已經有不少部語文教學法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僅僅在它們之中再加上一部。”是的,語文味教學法相對于已有的中國語文教學法,是貢獻,是發展,同時也是發現。
程少堂的語文味就是對語文概念的發現與豐富,也因此,我們稱程少堂為“語文界的哥倫布”。
二、構建一種革命性的中國語文教學美學新體系——以語文味和文人語文為核心
1.語文味。程少堂認為,所謂語文味,即在語文教學過程中,在主張語文教學要返璞歸真以臻美境的思想指導下,以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豐富學生的生存智慧和提升學生的人生境界為宗旨,以共生互學(互享)的師生關系和滲透師生的生命體驗為前提,主要通過情感激發、語言品味、意理闡發和幽默點染等手段,讓人體驗到的一種富有教學個性與文化氣息的,同時又生發思想之快樂與精神之解放的,令人陶醉的詩意美感與自由境界。
語文味這一內涵豐富的學術概念,如果通俗地表達就是在扎實的基礎上,把語文課上得有趣兒些、有味兒些、好玩兒些,也就是美些。
2.文人語文。借鑒中國近代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陳衡恪關于文人畫的定義,程少堂將文人語文的概念定義為:所謂文人語文,即由文人所教授,含有文人之趣味,在教學過程中不過多考究教學技術技巧,而于課之外能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的表現性(抒情性)語文教學。這一定義,首先強調執教者的文人身份和文人趣味,強調執教者主體精神的張揚。
在以語文味和文人語文為核心的中國語文教學美學新體系中,文人語文是語文味衍生出的陰概念,是語文味教學思想的進一步表述,它和語文味概念之間既互動、互補、互滲,也可以互釋。
3.語文味教學法。語文味教學法是語文味衍生出的陽概念,是語文味思想的顯性化表達,它在語文味定義基礎之上,針對教學實踐作了更為充分、清晰、生動的闡釋:語文味教學法是以語文味教學理論為指導思想,以教學過程中師生共生、共創、共享、共鳴、共融、共進為教學宗旨,以既要就語文教語文又要跳出語文教語文,使教學成為真、善、美、樂相統一的過程等為教學原則,以“一語三文”教學模式和其變式為主要教學方式,以語言、文章、文學、文化為教學內容要素和教學過程結構,以融合文本思想內容與師生生命體驗打造新的教學主題為教學重心,以營造教學審美意象與意境、建構教學藝術作品為教學追求,同時又充分具備語文教師和學生通過語文教學來抒情言志并實現價值推送之功能的一種“有溫度”的表現性教學法。
語文味教學法和以往的語文教學法有著本質的不同。首先,傳統教學法是再現性教學法,語文味教學法是表現性、抒情性教學法。其次,傳統語文教學法只教學課文主題,而語文味教學法強調在文本思想內容與師生生命體驗相熔鑄的基礎上,打造既來自于課文主題,又大于、高于課文主題的新的教學主題。再次,傳統或其他語文教學法大多規定的是“怎樣教”,即主要規定的是教學方法的程序,語文味教學法規定的是“教什么”,即是從教學內容角度對語文教學過程進行規范與制約。最后,傳統教學法基本上是對文本進行平面掃描,語文味教學法則要求對文本進行多層面(語言——文章——文學——文化)的立體式掃描,從而在保證語文教學層次性的同時,保證了語文教學內容的豐富性、立體性和深刻性。
程少堂認為,如果可以把語文味看作是“道”,那么由語文味之道就生出了“文人語文”和“語文味教學法”這一陰一陽兩個概念;再分別由“文人語文”這個陰概念生出教學境界、教學主題、體貼、真善美樂統一這四個關鍵詞,由“語文味教學法”這個陽概念生出“一語三文”教學模式、價值推送、語言把玩、幽默點染這四個關鍵詞,它們共同支撐起以語文味和文人語文為核心的中國語文教學美學新體系的大廈。
三、一種新的教學語言的智慧藝術呈現
程少堂的語文味教學最核心、最本質、最具價值影響力的思想就是表現性教學(或抒情性教學)。表現性教學是“有我之境”的教學,因而是語文教學中的“熱美學”。
1.“有我”的美學之境——滲透生命體驗。語文味教學法所強調的生命體驗,是指那些能夠激活人對生命的熱情,激發人對真、善、美的進一步追求,促使人的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之所愛、所恨,或所追求的人生價值,以及在這些追求、發揮與愛與恨過程中所產生的具有生命哲學高度的人生感悟。更簡單點說,所謂生命體驗,是指教學主體(師生)在追求和社會發展要求相一致的自我實現過程中,所產生的具有生命哲學高度的人生感悟。把這些人生感悟滲透進教學過程,變成教學資源和課程內容,就是所謂滲透生命體驗。
【例】人間惆悵客亦是“我”。程少堂的生命底色里有一種色調:憂郁。因此有老師評價他“富有詩人氣質”。其實,這種惆悵的憂郁氣質,與他人生經歷中的孤獨有關。
聽過程少堂講《錦瑟:中國詩歌美的“四個代表”》的老師一定不會忘記他與這位“人間惆悵客”之間人生經歷上的諸多契合,于是他在講李商隱的生平時,會讓人感到似乎就是在講他自己的內心經歷:他講義山父親去世,從此成了孤兒,便講自己父親去世,從此便感到自己成了孤兒;講令狐楚對義山大為憐愛,白居易對義山推崇備至,便隱隱感到他對知遇之恩的渴望、感激與珍惜;講義山的無路可走而終被玉成,便是他對義山或者說是對自己的孤獨感與成就感的咀嚼與回味;講義山“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忽覺他那一堂堂充滿語文味的課例又何嘗不是如此;講義山之無題詩的主題歷來爭議不斷,因此而成為中國詩人里“最獨特”的一個,便想到語文味的理論與實踐盡管也引發過一些爭議,但這卻絲毫不影響他的“獨持偏見,一意孤行”;講“770年杜甫死后墓志銘是元稹寫的,831年元稹死后墓志銘是白居易寫的,846年白居易死后墓志銘是李商隱寫的”,不禁想起他“提前為自己寫好的墓志銘”……
課行至此,屏幕上赫然投影出了一句話:“中國歷史,在知音與知音之間,回環相與地傳承,即使他們之間隔了湍湍沸沸的一個時代,卻不影響他們站在彼此的對岸,用靈魂大聲呼應。”詩、人、課如此這般的水乳交融,完美合一,此非“有我之境”不能至焉。教學的“有我”之境即是“詩”之境、“美”之境、“和”之境。
2.高雅的文化品位——打造教學主題。通過將課文主題和師生的生命體驗相結合相熔鑄,來打造既來自于課文主題,又大于、高于課文主題的新的教學主題,即形成整個語文課堂教學過程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內容,這是語文味教學法的核心思想與靈魂。
【例】打造英雄主題,創造英雄之作。程少堂可以被稱為語文味教學里程碑式的教學力作《在“反英雄”的時代呼喚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細讀》,其教學主題可謂一箭雙雕。
文本的說明對象是一尊外表冰冷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按照傳統教學,無非就是介紹說明對象、說明順序、說明方法,等等。這些機械的死知識,以機械對冰冷,怎能出新意?更遑論激起內心的熱血了。語文味教學完全不同。在執教者眼中,這尊紀念碑是有溫度的,只要你用情凝視它,就能激蕩出動人心魄的萬丈豪情。標題中的“英雄”與“反英雄”,兩相對比,頗具沖擊力,引起觀者和聽者的情感狂瀾。倘若執教者內心沒有驕傲的英雄情結,沒有不同的生命體驗,是斷不能從一篇說明文里自然挖掘出如此高遠、深刻、大氣的教學主題來的。執教者是借這座人民英雄紀念碑來抒發自己的英雄豪情,同時他也召喚、激發著每位聽者內心的英雄情結和不朽意識。
3.高邁的人文格調——實現價值推送。從語文味教學法的思想看,語文教學中的價值推送是使語文教學過程變成“有溫度”的教學的有效手段。
【例】嘉肴香飄千載,語文味風華絕代。程少堂運用語文味的頭腦和眼光,獨辟蹊徑,于《雖有嘉肴》這短短70字的小文里挖掘出令人擊節的內蘊主題“一段風華幾千年”。
程少堂從《雖有嘉肴》這段清新樸素的文字里,一方面抒發了自己剛健有為的人生價值追求,另一方面又將這種健康向上的價值觀順勢推送給學生,用儒家的君子之風感召著風華正茂的一代新人,整堂課格調高邁。
語文教學中的價值推送主要通過文化教學環節進行。通過價值推送,讓語文教學增強靈魂的沖擊與蕩滌的力度、強度,引導學生形成用文化眼光與科學價值觀深入觀察、思考、分析問題的意識與習慣,強化語文教學提升境界、增長智慧所需的應有的深度、厚度與張力。
總之,滲透生命體驗、打造教學主題、實現價值推送是語文味教學作為表現性教學的三大基本特征。這三大基本特征并非各自孤立、截然割裂,而是具有內在深層的關聯性和邏輯性,彼此相映生輝。比如,教學主題的生成一定滲透著生命體驗,價值推送又必然與教學主題高度一致。
4.在莊子的懷抱里繾綣纏綿——從“和”與“游”走向“至樂”。程少堂在長期實踐、研究中發現,語文味教學的“至樂”與莊子筆下的逍遙游之“至樂”一樣,均來自于“和”與“游”,即語文味定義中的“思想與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語文味教學用莊子式的幽默點染作引子,創造出使語文教學各要素之間彼此相“和”的教學環境與氛圍,從而使語文教學主體的心靈臻于“游”境——即教學主體達到個性與精神解放的最佳狀態,進入共享“至樂”的高峰體驗。
【例】把玩菜單,要素“和”,逍遙“游”。程少堂的又一另類課例《生活處處是語文——以 〈廣東地方風味菜單〉為例》把真、善、美、樂相統一表現得淋漓盡致。首先,通過學生高聲齊讀、方言朗讀(并用《國歌》變奏的方式指導學生揣摩情感的變化)、引用契訶夫的話指導誦讀這三種方式把玩菜單,掀起了整堂課的第一個高潮。為菜名杜撰故事的環節,則讓學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盡情遨游在思維的天空里,童真童趣一覽無余,愜意酣暢。教學中教師懂得放低自己,善于裝傻藏巧,真心尊重、體貼學生。整堂課師生一起把玩菜單,情感融洽,花火四射,教師、學生、文本等要素之間不分彼此,完全相“和”,課堂上幽默不斷,笑聲不斷,已然進入了至樂的“游”之境。
把玩,就是接近于游戲狀態的心靈審美運動。“把玩”“游戲”既是一種思想理念,也是審美的藝術境界,這是執教者對語文教學持有的生命狀態和精神高度。程少堂用自己的課堂踐行著他的語文味思想:課堂里只有多一點幽默,才能有“和”的氛圍,抵達逍遙之“游”境,教學主體才能共享“生發思想之快樂與精神之解放”之“至樂”。
程少堂的課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他順應語文內在規律,卻不受成規所縛,以逍遙姿態“游”語文;他的視野開闊,立意高遠,思維跳躍性、時空、跨越性較大,所以帶給我們的沖擊力是巨大的,其藝術魅力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