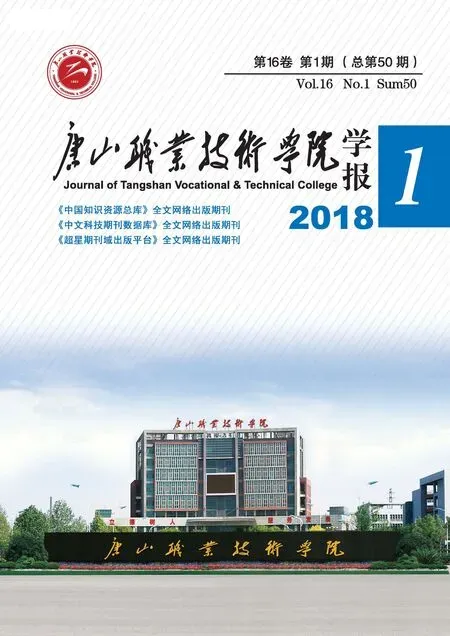“斷口”的隔絕與創傷
——評方方小說《琴斷口》
郭 茜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從古至今,愛情永遠是被藝術家所青睞的。從古代的《詩經》到現代的通俗小說,愛情似乎成為文學的恒定母題。寫愛情很好,寫好愛情卻很難。王安憶認為,“寫愛情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寫得不好就變成了風花雪月,因為愛情這樣的東西特別容易有假象,羅曼蒂克的假象,會失去生活的質感”[1]。然而作家方方就是憑借一篇愛情故事《琴斷口》一舉奪得了2010年魯迅文學獎的桂冠。她賦予文字以強大的力量,對生活產生燭照,折射出人在特定情境下的現實選擇。在長達三十年的寫作歷程中,方方始終秉持著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對生活致以嚴肅的觀照,并呈現生命某一方面的特質。她的作品總是脫胎于個人平凡的生活,但同時又對庸常的人生有所超越,從而傳達出作者對于生命人生深切的憂思。
一、情感的阻斷
“琴斷口”是一個地名,取義于俞伯牙和鐘子期的故事。古人俞伯牙在月下獨自撫琴時,兀地發現有人偷聽,其很是憤怒,一氣之下便把琴折斷了。琴雖斷了,卻也遇到了知音,琴可再覓,知音難尋,因此倒也不失為美事一樁。從《武昌城》到《烏泥湖年譜》,從《閑聊宦子榻》到《祖父在父親心中》,方方擅長在其小說中注入歷史敘事,這也一度成為方方的寫作特色之一。歷史與現實在作品中一同出現,淡化社會歷史和今昔現實的界限,使得二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從而能夠闡發其對生命觀照的特殊思考。
一夜之間,白水橋的悄然坍塌,一死兩傷的慘淡結局,改變了五個人的人生軌跡。第一個墜橋的是楊小北,因為雨衣的原因得救,爬上岸立刻去醫院療傷;第二個墜橋的是蔣漢,他把頭扎在摩托車車把上,當場昏迷,繼而沉入水底,錯失了最佳的搶救時機;第三個墜橋的是馬元凱,壞了的車門使他得救。摔斷了腿的馬元凱,并沒有立刻去醫院,而是爬上岸去攔車,以防止更多的人受傷甚至死亡。楊小北、蔣漢、馬元凱都圍繞與米加珍的愛情糾葛,戲劇性地陷入了這場情感的旋渦中。馬元凱年少時愛戀米加珍,但礙于兄弟情分,而放棄追求米加珍,三人是多年的好友;蔣漢與米加珍青梅竹馬一起長大,蔣漢平淡而踏實,對米加珍百般呵護、予取予求,兩人多年的愛情,彼此信任和依賴,被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會結為夫妻;風趣幽默的楊小北突然出現在琴斷口,米加珍和楊小北在朝夕相處中漸生情愫,米加珍下定決心準備與蔣漢分手。冬日里冰冷的早晨,楊小北約蔣漢面談想以男人的方式給這份愛情一個了斷。蔣漢的過橋是為了赴楊小北之約;馬元凱渡橋是為了去公司上班。橋悄無聲息地斷在了寒冷的冬日里的深夜,這一純偶然的意外事件將三個人扯入了現實選擇的精神困頓中。白水橋之“斷”,阻斷了米加珍與楊小北的婚姻,也阻斷了吳玉與馬元凱的愛情。楊小北墜橋后做出的行為選擇以及約蔣漢面談的事實,使得蔣漢的意外身亡給楊小北和米加珍的愛情籠罩了一層厚厚的陰影。盡管楊小北用愛情的結合以努力地排毒,可周圍的人總是用直白粗暴的言語把他們不斷拉入無法掙脫的世俗黑洞中。楊小北的邀約;蔣漢的善良,世俗的人言讓米加珍對蔣漢的死懷有強烈的負罪和愧疚意識,并使她在一連串的事件中去贖罪,直至失去了自己的親生骨肉。而在一系列事件的現實選擇中,楊小北可謂在愛情中節節敗退,從歌吟“愛情的力量太偉大”到感慨“愛很偉大,但愛情卻很脆弱”[2],楊小北從一個十足的愛情信徒變成了愛情落荒者。一座橋的意外坍塌最終使得兩顆熱烈而純粹的心漸行漸遠、分道揚鑣。如果說楊小北與米加珍的婚姻破裂是世俗力量推動的無奈之舉;那么吳玉和馬元凱的愛情則簡單而實際得多。馬元凱墜橋之后落下了殘疾,吳玉自知姿色良好,不愿與之共度一生,果斷干脆地離開了他。兩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本應該熱烈而明朗地享受著甜蜜的愛情,但不幸的是愛情隨著白水橋的倒塌也永遠地埋葬在冰冷的水底。白水橋之“斷”,阻斷的不僅僅是愛情也隔絕了馬元凱和蔣漢的聯系,兩人如同手足,馬元凱在得知蔣漢意外離去的現實時,在其驚愕的同時更多的是悔恨未曾下水救人,甚至把這種痛楚施加到米加珍夫婦身上。白水橋之“斷”,同時也疏離了米加珍和吳玉的閨蜜友情,米加珍的婚禮上,吳玉的酒后真言,不可不說是其心中芥蒂的一時外現。
縱觀整個事件的發展,斷了的白水橋成為改變人物命運的關鍵性因素。一對平凡普通的戀愛男女由于突發的意外事件引發的必然的人生別離。方方以其細膩的視角洞察了偶然事件所造成的情感的焦灼、人生的迷惘和命運的無常,冷靜地剖析了文本中人物的生存之困。
二、自我的救贖
蔣子丹曾經評價方方,“她有著一種近乎女巫的氣質,寫愛情,話死亡,玩游戲,說夢境,明明是現實主義,卻有著宿命般的殘酷和深刻”[3]。而這種殘酷與深刻最終都會指向言說的悲劇性。在方方一系列的作品中,無論是取材于市井還是取材于校園,抑或是實際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現實,都始終充溢著強烈的悲劇感。這股悲劇感甚至成為她建構小說的精神橋梁,《琴斷口》中亦是如此。這種堅硬強烈的悲劇意識使得琴斷口“就像一個巨大的隱喻,成為了當代中國人精神存在形態的一個拐點”[2]。在這個充滿巧合性的斷口處,眾多的人被拉入了煎熬的深淵。作者不悲不喜地站在斷口處打量著人物的掙扎,并向他們投去渴望他們自我救贖的悲憫眼光。在楊小北與米加珍心意相通時,曾有過這樣的對話“愛情的力量太強大,它天天在催我犯罪,我寧可成為一個罪人也要愛你”[2]。米加珍為他這句換感動著,她哽咽著說了一句“那我就陪你一塊犯罪”[2]。特定情境下,純潔美好的愛情在米加珍和楊小北口中成了犯罪,有罪自有贖。一語成讖,楊小北從愛情的結合到婚姻的離析,這整個過程便是他們自我救贖的歷程。
蔣漢如山茶花一般的溫暖使他贏得了米加珍的芳心,蔣漢與米加珍的愛情如潺潺流水、少許波折,緩緩向前。這份看似天經地義的愛情在瑣粹生活的消磨中轉化為了習慣與親情。帥氣睿智的楊小北使得米加珍的心搖擺不定。兩者之間,她既不舍蔣漢的溫柔卻也依戀楊小北的浪漫與詼諧。當米加珍終于確定了心靈的天平,這一關鍵性的斷口時,蔣漢意外死在了寒冷的白水橋下。米加珍從此活在了愧疚中,一則懷念蔣漢的好,二則認為楊小北的邀約和其墜橋后的離去對蔣漢的死負有間接性的責任。由此,米加珍開始了她的救贖之旅。在一次次的現實選擇中擊碎了楊小北對于婚姻生活的全部希望。“蔣漢的死,我們到底有責任”,米加珍放棄蜜月旅行去照顧蔣媽媽時如是說,楊小北無力挽留,責任是米加珍自我救贖的方式之一。而后,其主動提出搬家來回避觸景傷情之地,既是對自我的救贖也是對愛情的挽瀾。減輕了心中的重負,也給了愛情一個重新生長的機會。因此搬過去的第一個夜晚,他們如膠似漆般宛若新婚。后來,米加珍以減輕心中負疚的理由幫蔣漢競爭設計大賽,以替楊小北贖罪的說辭送別蔣漢母親,從而致使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米加珍在事件的發展中所作出了每一個選擇都是救贖自己救贖愛情,想要減輕自己的負罪感,卻又一次次的陷進去,不斷增加自己和楊小北的心理重負。同樣在這個偶然事件的后續發展中,救贖自我的不僅僅只有米加珍一個。意外的發生使得馬元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他執拗地認為自己是悲劇的源頭。因為他沉溺于愛情,無意間把米加珍推到了楊小北面前,導致了蔣米二人的分手以及在江漢落水后,他未能及時施救從而錯過了拯救蔣漢的最佳時機。面對著蔣家支離破碎的現狀,馬元凱也是懷著深重的負罪感參與到蔣家事務中,這其中不僅僅是馬蔣二人真摯感人的兄弟情,還參雜著馬元凱以代替蔣漢的方式來實現自我的救贖。與之相比,楊小北在整個事件中便顯得較為理性,其真切地認識到蔣漢的死只是一個偶然的意外事件。盡管楊小北想要“留下美麗,努力排毒”,可現實總是步步緊逼。外界的流言盡管可怕,但是米加珍才是擊碎他最后信心的決定性力量。米加珍把楊小北的悶悶不樂理解為落選的失意,曾經相愛的兩個人不再心靈相通,無話不談。米加珍的誤解吸掉了楊小北溺水之中的最后一口氧氣。楊小北清醒地認識到“生活不是光有愛就能過得下去”[2]。在這個感情的戰役中,楊小北承受不了如此重負,最終選擇了落荒而逃。深究楊小北的離開是與命運做抗爭失敗后的無力也是拯救其于困頓中掙扎的救贖之舉。
三、命運的困頓
命運是方方小說中一再出現的主題,作品中強烈的悲劇意識總是和困頓的命運觀密不可分。她總是極為醒覺地把握人性中特別是底層民眾的悲苦之境,甚至把它提升為對生命無常的感知。無論是二芝的困獸猶斗還是李寶莉的“萬箭穿心”抑或是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作者都力透紙背地刻畫出這種悲劇背后的無常性,從何傳達其對困頓命運的人文觀照。
琴斷口是古人遇知音之境域也是今天勞燕分飛之場地,不得不說這其中帶有很強的荒謬感與諷刺感。《琴斷口》中的悲劇就是一個偶然疊加的故事,偶然事件不斷放大從而推動情節發展,改變主人公的人生軌跡,其阻斷的無常性使文本充溢著很濃的宿命意味。梳理文本的時序,楊小北的出現是其兄與蔣漢叔叔在飯桌上隨口達成的協議,它并沒有充分的因果關系。楊小北就這樣突兀地出現在琴斷口。而馬元凱的無心之舉把楊米二人撮合到一起,這也是一個非理性的推動因素。甚至寂靜的雪夜,白水橋的坍塌如驚雷之響,卻沒有驚動任何一人,由此可見連外物的發展也充滿著神秘的無常性。白水橋的斷裂,一死兩傷的慘痛結局也是人的理性所無法把握的“巧合”。而就是這樣一個個非理性因素巧合的疊加,導致了悲劇的發生。正如方方所說:“生命中每一件事的發生,或許都去修正著一些人的人生軌跡。一個人的命運常常在這樣的修正中,被徹底改變”[4]。然而命運的困頓不僅僅體現在其阻斷的無常性,還體現為世俗暴力對個人命運的道德綁架。以楊小北與米家珍為例,楊小北的性格是理性因素占據主導,盡管他也曾經懷疑和困惑過,但他清楚地知道蔣漢的死是一個殘酷的偶然事件。他努力地掃除婚姻的霧霾卻一次次鎩羽而歸。在整個故事的發展中,米加珍一直被世俗蜚語所綁架,直至她在失去蔣漢之后再去失去楊小北,在愛情一無所有,拖入命運困頓的無底洞里。也許是蔣漢的敦厚與善良一直讓人念念不忘,也許是中國人固有插手他人家事的癖好。周圍的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楊小北與蔣漢的死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更有甚者將之定義為因果關系。“有你才有蔣漢的死”[2],“楊小北巴不得蔣漢死掉,這樣他才能把米加珍弄到手”[2]等等。世俗的言語無疑是米楊婚姻破滅的催化劑,米加珍在反抗世俗的戰役中迅速被繳了槍并成為了世俗的幫兇去加重楊小北身上的重負。楊小北作為一個理性樂觀的人,在世俗的言語中,不斷抗爭卻不斷失敗,最終落荒而逃。在文明理性的現代社會,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無法全權掌握自己的人生,無路可走的他只能被擁擠的人群推攘著前進,在周遭的環境中他不斷碰壁,在無常的人生里他無可奈何。困頓的命運讓一個萬念俱灰年輕人終結了愛情。在小說結尾,米加珍說:“其實是生活本身很可笑”[2],楊小北感慨道“是呀。我們不過是生活里的佐料罷了”[2]。這句話道出了個人與命運作搏斗的無力感,正如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里所感悟的那樣,人生是如此不可理喻的荒誕,可貴的是人能夠認識到其荒誕性,盡管無法抗拒荒謬,卻仍然蔑視荒謬的主體自由精神。
方方是一位對生命有著強烈寫作意識的作家。《琴斷口》用這樣一個關于愛情、生死、道德、命運的故事展列了普通男女在特定情境下的困惑與掙扎。作品中“外公”的話成為了一個巧妙的預言,預示了在遠和近不同的距離里,知音與敵人角色的轉變。琴斷口、碎琴山;人不見,家未圓。所遇到的他人也從來不是溫柔鄉。此地、此景、此人、此境,文本中縈繞著一股“方方式”的悲苦氣息,而作者像一個俯瞰的旁觀者。她不動聲色地講述著令人煎熬的故事,依然“冷靜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變幻無窮的最美麗的風景”[5]。然而,“生活是不介意這樣悲觀和失望的,它依然以它固有的方式繼續”。寫作如昔,悲苦如斯。從《風景》到《琴斷口》,悲苦成就了方方也限制了方方,使得其作品“憂傷悲苦有余,而解讀空間狹隘,美學意蘊不足”[6]。但是,我們仍然感激作者以其虔誠地寫作為我們展示了這靜默的“風景”,這是作家的責任,也亦是文學的使命。
[1] 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M].北京:人民文學大學出版社,2011(1).
[2] 方方.琴斷口[J].小說月報,2009(7).
[3] 方方.桃花燦爛序[M].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3).
[4] 方方.一個人和許多人[J].中篇小說選刊,2009(4).
[5] 方方.中篇小說[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1).
[6] 丁帆.中國新文學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