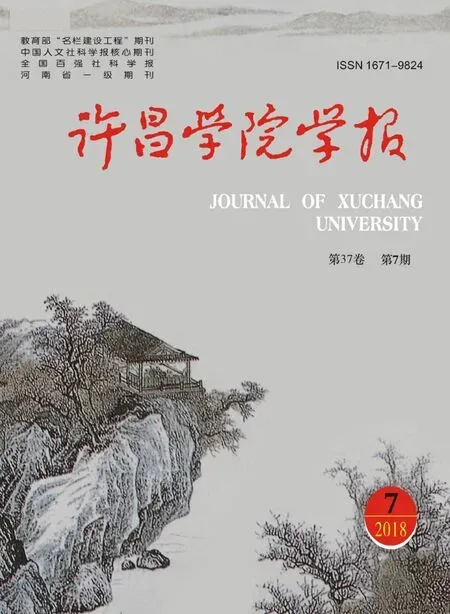司馬遷出使西南的時間、路線考
馬 寶 記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司馬遷在《史記》中兩次提到出使西南的事情:
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于河洛之間。[1]3295
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1]1415
巴郡,治江州(今重慶市西北),亦泛指今重慶及其附近地區。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邛指邛都,粵(亦作越)巂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省西昌市東南。笮指笮都,沈黎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漢源縣東北,后并入蜀郡。昆明,在今云南昆明西,后設為益州郡,郡治在今昆明市晉寧區東北。
《太史公自序》此段內容說得非常清楚,司馬遷出使時職官是郎中,出使原因是“奉使”“南略”,出使地是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出使之后回來立刻給武帝復命,復命時間是“天子始建漢家之封”之年,也就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相關的事件還有,其父司馬談因病留滯周南(洛陽),且病情危重。司馬遷回來后也即刻在河洛之間見到了彌留之際的父親。《河渠書》補充了司馬遷西南之行的內容:到了岷山,觀察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之離碓。
但是,因司馬遷沒有更加具體地記載奉使出使西南的時間、過程、任務、方法、結果等等諸多細節問題,以至于人們往往忽略了司馬遷的西南之行,僅僅以曾經奉使出征西南之語一筆帶過,而沒有真正認識到司馬遷此行的重大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司馬遷在鼎盛時期的武帝時代對西南地區民族融合、經濟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甚至也沒有理解到司馬遷這次出使的現實意義,這不能不說是司馬遷研究的巨大缺憾。
一、司馬遷出使西南的時間、行蹤考辨
1.遠赴西南的時間、到達的地點
元鼎五年(前112)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叛漢朝。秋,武帝派遣五路大軍平定南越王叛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仆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今云南、貴州境內北盤江及其下游流經廣西、廣東之紅水河、黔江、潯江和西江[2]763),咸會番禺(今廣東番禺)。”[3]187《漢書·西南夷傳》也記載了同樣內容:
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3]3841
元鼎六年冬十月,武帝東行到山西、河南,“行東,將幸緱氏(在今河南省偃師市東南),至左邑(今山西省聞喜縣)桐鄉(鄉名,在左邑縣),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今屬山西)。春,汲(今河南省衛輝市)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今屬河南)”[3]188。
在平定南越的五路大軍中,馳義侯遺為越人,歸降漢以后被封為馳義侯。在馳義侯遺的部隊中,有一支是且蘭軍,且蘭是夜郎部落成員之一,在今貴州省福泉市等地。這支且蘭部隊本應跟隨馳義侯開赴番禺平定南越,但是,且蘭君主擔心自己遠行之后,旁邊部落趁機虜獲自己部落的老弱人口,便不再跟隨馳義侯遠征,而是反將漢使者和犍為太守殺掉,反叛漢朝。且蘭平常就經常阻攔在滇道上,對漢朝來說,且蘭早就成為通向滇地的障礙。所以,實際上,且蘭反叛漢朝,所說擔心部落被侵略只是借口,從內心來說,他們并不想真心歸順漢王朝。
南越平定之時,馳義侯遺所率部隊尚未發兵。這時,還有一支漢朝部隊在西南,這支部隊由八校尉帶領,本來也是前往番禺平定南越的,但是,南越很快被滅,八校尉所部便停留在西南。
且蘭叛亂,武帝下令馳義侯、八校尉所部征討。《漢書·武帝紀》載:“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3]188就是在這個時候,司馬遷奉命前往,到達的目的地是馳義侯以及八校尉大軍駐扎地。
這里有個關鍵的地點,就是馳義侯及八校尉部所在位置,這個位置也是司馬遷的目的地。要判斷這個目的地的具體位置,可以參看以下幾條史料:
①《漢書·武帝紀》:“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3]187可知馳義侯所帶之兵力有“巴、蜀罪人”,還有夜郎兵,夜郎在牂柯江邊。
②《漢書·西南夷傳》:“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3]3841犍為郡在今四川宜賓西南,南距夜郎不遠。
③《漢書·西南夷傳》:“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3]3841這里是“引兵還”,即本來要去番禺,可是沒走多遠聽到了南越被打敗的消息,于是便率兵而回。回來的路上,把且蘭打敗了。說明他們所在的位置是在且蘭部落的南面或西南面。
第①②條是同事件的不同記載,可以理解為同一支部隊處在同一個位置。而巴、蜀在犍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賓西南)之北,夜郎在犍為之南,他們要沿牂柯江東下,因此,一個比較合理的理解是,這支部隊當時在牂柯江上游、夜郎附近。第③條關鍵詞是“還”,這支部隊本來是要和馳義侯的部隊會合,其中“巴蜀罪人”應該還是指馳義侯所率領的那一批人。既然不再前往番禺,這支部隊就要返回,返回途中順便消滅了且蘭的反叛力量,也就是說,他們當時應該在且蘭之南或西南,由南向北而“還”。且蘭的西南正是夜郎。所以,馳義侯和八校尉這兩支部隊當時會合的地點應該就在夜郎附近。這個地點也是司馬遷奉旨調動部隊要達到的目的地。
綜上,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也就是遠赴西南的時間是元鼎六年春,出發地點是汲縣新中鄉,到達地點是夜郎或其附近。因為司馬遷是傳達軍令,所以行走路線應取最近距離,姑設定從河南汲縣經長安、漢中,到達蜀郡、巴郡、夜郎。
2.各郡設置的時間及司馬遷行蹤
且蘭叛亂,八校尉部中郎將郭昌、衛廣在引兵回還的路上,消滅了且蘭,這樣,就在且蘭部落占據的地區設置了牂柯郡(治且蘭縣,今貴州凱里西北)。之后,又相繼設置了粵巂郡(治邛都)、沈黎郡(治笮都)、文山郡(治汶江縣,今四川茂縣北)和武都郡(治武都縣,今甘肅省西和縣南)。
根據《漢書·武帝紀》,武帝于元鼎六年冬十月,發兵征西羌,平之。然后:
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余善反,攻殺漢將吏。[3]189
由此處時間順序可知,武帝春天到汲縣新中鄉,秋天,東越王余善反。平定南越和西南夷,設置南越九郡和西南五郡都在這一時間之內,也就是在元鼎六年春天到秋天,其間,南越九郡設置在前,西南五郡設置在后。
司馬遷所云“南略邛、笮、昆明”,應該就是在這些郡設置的時候作為武帝的特派使者跟隨在部隊中的,其任務就是奉旨設立各郡[4]。據此,認為司馬遷出使西南是在設郡之后的觀點是錯誤的,如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當在置郡之后。”[5]250
關于各郡的設置,《史記·西南夷列傳》云:
南越破后,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莋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3]3842
最早設置的是牂柯郡,之后,又設越嶲郡,因越嶲郡在南部,離昆明較近,所以,司馬遷應該是在設置越嶲郡的時候到達昆明,考察昆明的情況。然后,又設置了沈黎郡、汶山郡和武都郡。
各郡設置的時間也是司馬遷在西南地區先后的行走路線。
3.司馬遷返回時間
各郡設置之后,司馬遷完成使命,開始返回。《河渠書》云“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當為司馬遷返回時所為。瞻:《說文》:“臨視也。”[6]72說明司馬遷是到達了離碓。到離碓的具體時間無可證文獻,姑置于此。
考察了離碓之后,司馬遷徑直返回長安,“還報命”,要給武帝匯報西南夷情況,并參加武帝次年即元封元年(前110)四月的封泰山大典。
司馬遷返回的具體時間沒有記載,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記載推斷出來。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周南代指洛陽。《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在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緱氏指緱氏縣,在今河南偃師市東南。武帝在緱氏下了一道詔令后,“行,遂東巡海上”。然后,“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從正月到四月,武帝從緱氏走到海上,又從海上折回泰山,可見,武帝一直在巡行。周南在緱氏之西,也就是說,司馬遷本欲返回長安面見武帝,但是,此時武帝已經向東出巡。司馬遷見到武帝時,武帝已經走到周南東面的緱氏,而父親因病留在周南。
司馬遷返回周南之后,是先見父親還是先見武帝復命,后世學者見仁見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蓋史公自西南還報命當在春間,時帝已東行,故自長安赴行在。其父談當亦護駕至緱氏、崇高(今河南省登封)間,或因病不得從,故留滯周南。適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間也。”[5]250祁慶富認為,按照當時禮儀,司馬遷應該先面見武帝“還報命”,之后才能去面見病危的父親:
“報命”在元封元年(前110)。這里有兩件事,一是“報命”,一是“見父”,二者孰先孰后?季鎮淮先生認為見父在先,報命在后。若果真如此,是違犯封建時代禮規的,因為諳熟君臣之禮的司馬遷不會身負君命未報先去見父。司馬談垂危之際仍念念不忘“事君”大于“事親”,他也不會容許其子這樣做。再從自序的行文看,“報命”亦在“見父”前。最大的可能是,司馬遷向武帝“報命”后,即去見父。[4]
張大可認為,司馬遷“在元封元年四月趕到河洛,受父遺命后上泰山參加封禪典禮”[7]80。
司馬遷返回的路線,根據他急于復命、參加四月封禪大典來看,應該是選取最近路線,如從離碓直接奔赴長安,然后到達周南、緱氏。
4.司馬遷在西南的停留時間
司馬遷從元鼎六年春(姑設為正月*郭宗全《司馬遷出使西南任務考》(《歷史教學》2009年第10期)認為,“武帝得呂嘉首級與下令征討西南夷同時,則司馬遷出發時間就為春正月”。可參。)出發,到元封元年四月之前返回洛陽。在西南停留前后共計約十六個月。其中,包含著往返路程。
據《續漢書·郡國志》載:“蜀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一百里。”[8]302“犍為郡,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8]307。“牂牁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七百里”[8]311。“越嶲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八百里”[8]315。如此遙遠的距離,按當時的交通情況,單程也得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另據《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東漢永平年間(58—75,上距司馬遷約200年),益州刺史朱輔上疏稱,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其中《遠夷懷德歌》有“百宿到洛”[9]2856,白狼就在西南夷,從白狼到洛陽,要一百天,這還是司馬遷之后二百年的事情。
即便按照這種速度,司馬遷單程也要三個月左右,考慮到司馬遷來往都是情況緊急,所以至少也要兩個月,往返需要四個月左右,這樣,他在西南停留的時間最多是十二個月,即元鼎六年三月到元封元年二月。
在這一年時間里,司馬遷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武帝宣諭漢王朝威德,招降納叛,安撫地方,設置各郡,也就是“征”“略”西南夷。
由此可見,司馬遷在漢王朝對西南地區建立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二、司馬遷出使西南的作用與意義
司馬遷西南之行,一般不太引人注意,大多理解為奉使游歷,而實際上,司馬遷此次西南之行意義卻重要得多,正如有學者所謂是“負有經略西南夷之任務”[10]。《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3]2863正是因為這次任務,司馬遷也成為和公孫弘等人一樣的“奉使方外”“英俊”。
司馬遷所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奉使”“征”“略”。所謂征,一般指軍隊出征,言以武力脅迫、奪取。在《史記》中,這種意義非常突出,用法也非常普遍。如“秦使章邯將而東征”,“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等都含有使用武力之意。當然,司馬遷以朝廷使節的身份出使西南,不可能帶有軍隊,所以,這里的“征”更多的是具有以武力恫嚇、威懾、鎮撫的意思,司馬遷是作為大漢王朝的使節來到西南的,他的背后,是強大的國家,他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宣示漢王朝的聲威,讓西南的少數民族臣服。所以,盡管沒有軍隊,司馬遷仍然使用“征”來表示自己出使西南的意圖。
所謂略,也有以武力攻取之意,但更強調占領、統治之意。《史記》中往往“略定”連用,可見其意義所在。如“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行略定秦地”,“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遂略定楚地”,“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余城”等。而司馬遷有時更是將“略定”與設郡、臣服放在一起:“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
由此可知,司馬遷是帶著武帝旨意來“征”“略”西南的,也就是說是宣旨討伐西南夷、建立地方政權,亦即要設置西南各郡,對西南地區行使行政管轄權。據此,通過《史記·西南夷列傳》和《漢書》《武帝紀》《西南夷傳》等所載征略西南、設置各郡的情況,司馬遷出使西南的重要意義主要有:
1.宣諭漢王朝威德,鎮撫邊疆地區民眾,維護國家統一。
在漢武盛世,武帝一直在謀求統治全國、經略天下的盛舉,除了征討尚未賓服的少數民族之外,對于各地企圖叛亂的少數民族,漢武帝毫不手軟,堅決予以平定。
司馬遷出使西南的這段時間,也是漢武帝奮力開疆拓土的重要時期。武帝即位之初,就以強硬手腕應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擾亂。建元三年(前138),“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3]158。六年(前135),“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3]160。之后,更強化戰爭手段,屢屢用戰爭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地區的安定與和平。元狩四年(前119),驅逐了匈奴;元鼎六年,平定了南越叛亂;接著就是司馬遷肩負著使命出使西南夷。所以,司馬遷這次西南之行,與以前一樣,都是武帝維護國家統一與安定的重要舉措。
2.建立行政機構,鞏固國家政權。
漢代中央集權制在行政建制方面的重要體現,就是郡縣制。郡縣制可以自上而下采取有效的政治統治,防止各地王侯尾大不掉,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司馬遷出使西南之前,西南地區已經設立了犍為郡、益州郡,司馬遷出使西南時,又設置了五郡,即牂牁郡、粵巂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后,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巂郡,莋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3]3842
西南郡縣的設立,為漢武帝實施對西南地區的牢固統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實施武帝經略大西南計劃的重要步驟。
漢武帝十分重視對西南地區的統治,一直不斷地采取各種措施維護西南地區的安定,司馬遷的出使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步。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六年,即委派唐蒙出使西南夷,“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余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1]2994。這是漢中央王朝首次以和平手段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實施統治,盡管僅僅是夜郎周圍的“小邑”,而且他們是因為貪圖財物才在名義上聽從漢朝的管理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畢竟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為以后在西南地區實施統治開了先例。緊接著,漢王朝在元光五年(前130)“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余縣,屬蜀”[1]2994。“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原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1]3046。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為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酋長歸降漢朝的目的多是為了錢財,加之距離中央王朝路途遙遠,所以他們總是降了反,反了降,反復不定。司馬遷出使西南夷,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司馬遷在一年時間內,不但完成了奉旨消滅反叛者且蘭的任務,更重要的是設置了西南五郡,大大提高了中央王朝對西南地區的有效控制。
總之,司馬遷出使西南,不但完成了漢武帝交付的重要政治任務,還詳細考察、記錄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分布區域、自然環境、豐富物產,記載了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與漢民族的交往等等,體現了司馬遷大一統的民族統一思想,極大地增強了中原文化與邊疆地區民族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