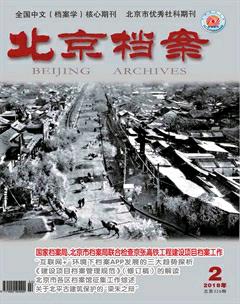日本京都大學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的經驗及啟示
鐘萬梅
摘要:本文介紹了日本京都大學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的相關情況,包括數字化設備超高解像度成像系統的主要技術和特點,數字圖像的開發情況及相關未來教育規劃。提出對我國檔案工作帶來的啟示:增強對檔案事業自信心,進行檔案資源深度開發,打開檔案數字化新思路,加強人才培養。
關鍵詞:日本文化遺產數字化啟示
數字化是檔案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它能使傳統的紙質、聲像、實物等檔案通過一定的手段轉換成數字信息,實現計算機處理和網絡傳播。數字化技術不僅影響了檔案領域,同時也影響了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由日本京都大學工程研究生院高級圖像技術實驗室開展的一系列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采用了目前全球先進的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對該項目所采用的技術及相關情況進行介紹,希望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一、京都大學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概況
文化遺產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具有較高文化、歷史、藝術或者科學價值,并以特定實物或者非實物的形態存在的人類創造物”[1]。文化遺產可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實物形態存在的是物質文化遺產,“通常被稱為‘文物”,如瓷器、古文獻、書畫、壁畫、古建筑等;以非實物形態存在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如表演藝術、社會風俗和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2]。本文所指的文化遺產為物質文化遺產,即“文物”。
京都大學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是指日本京都大學工程研究生院高級圖像技術實驗室(以下簡稱該實驗室)依托其研發的數字化設備及相關技術,在全球各地開展的對大型文化遺產進行數字化的一系列項目的統稱。該實驗室十余年來一直從事文化遺產安全數字化設備的研究與開發,其研發的成果——超高解像度成像系統,已被廣泛運用于保存中國、日本、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美國、澳大利亞和伊朗等國的重要世界文化遺產,技術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據介紹,目前有80多臺系統被歐洲、大洋洲、亞洲及非洲的文化遺產保護單位和博物館所使用,幫助這些單位對重要的文物進行數字化采集。數字化采集的對象有古寺廟、珍貴的雕像、巨幅畫作、古地毯等。
二、京都大學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
該實驗室主要通過其自主研發的超高解像度成像系統來開展文化遺產的數字采集工作(見圖1)。超高解像度成像系統有四項核心技術:(1)超高清三色掃描技術,有時與紅外輻射成像技術同時使用,常被用于掃描3米× 10米左右的物件。(2)超高清光感傳輸掃描技術,用于掃描歷史玻璃圖片和膠片。有些國家如日本、美國和菲律賓擁有150年前的玻璃底片,保存狀況不好,該技術可以對玻璃底片進行數字化掃描。(3)多譜線成像技術,具有8層以上的濾光器,可呈現與三色掃描儀相同的空間分辨率。通過不同濾光器捕捉到的光譜成像,能夠以約20微米(1200dpi)重建光譜反射率曲線。該技術可以用來掃描珍貴的古畫,并識別解析畫作的顏料信息(見圖2)。(4)偏光成像技術,可以用來掃描金、銀、銅等金屬文物,能克服反光帶來的不良效果,記錄金、銀和其他表面反光的金屬元素的細節。
超高解像度成像系統具有以下特點:(1)該系統具有顯微鏡級微小區域(5-80微米)檢測能力的高空間解像度,形成的圖像具有超高清的畫質。(2)具有高色彩保真度。能實現色差在1.0-1.5間的高解像度甚至是超高解像度,而商業相機的色差一般在5-9之間。(3)能采用最低的光照輻射,低于博物館展覽總曝光的5%,在掃描過程中避免光對文物的損害。(4)能適用于各種形狀、尺寸和表面特性如二維或三維,暗色或反光物體的掃描。(5)在掃描物體時不用接觸物體,避免損傷。(6)能夠產生解析信息,如光譜和色度信息。
可見,該實驗室研發的技術兼顧各類文物的特性,滿足不同文物的掃描需求,且對文物基本沒有損害,因此在原件保護、文物修復、文物鑒定和歷史研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原件保護。由于該系統擁有超高清的掃描技術,甚至能比肉眼識別出更細微的細節,其數字化副本有時可代替原件進行展覽。此外,很多文物因保管不善,或面臨衰變,對其進行數字化搶救,能保留其當時的面貌,保存人類珍貴的歷史記憶。(2)文物修復。對文物進行高清的掃描,便于文物修復人員識別細微之處,從而進行精準復原。例如對一副受損的古畫進行高清掃描,通過系統識別出的礦物顏料信息,修復員就可采用正確的顏料,進行精準地修復。(3)文物鑒定。該技術能夠解析文物的信息,可為文物鑒定提供依據。(4)歷史研究。高清的掃描及其產生的解析信息,能發現肉眼發現不了的信息,可以為歷史研究帶來新的有價值的信息。
當然,超高清的畫質也意味著需要更大的存儲空間,對圖像處理設備的配置要求更高,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
三、對文化遺產數字化圖像的開發利用
對文物進行掃描的直接成果是形成高清的數字圖像,這些圖像可以作為展現文物原貌的數字化副本進行歸檔保存,也可以用于展覽,這是數字化圖像的基本功能。但是該實驗室并沒有就此停步,他們認識到文物是人類社會實踐中直接形成的產物,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文化價值,因此倡導“藝術+科技”的理念,迎合公眾對歷史藝術的審美需求,與相關部門合作,對圖片進行深度開發,制作出各種廣受歡迎的文化產品,給靜止的文物賦予生動的內涵。例如把文物的數字化圖片做成動畫的教育片,既有教育意義又有經濟價值。該實驗室曾采用虛擬技術,讓觀眾參與歷史互動:“(展現在眼前的)是三維的敦煌洞窟,帶著三維眼鏡進入演示大廳后,立體的佛像呈現在眼前。最讓人震撼的是對于壁畫中的兩個舞蹈者點擊后,舞蹈者竟然從畫中走出,并跳了一段胡旋舞。據開發者介紹,這段胡旋舞是請兩位北京舞蹈學院的老師演出后做入這個三維演示中的。”[3]用該實驗室教授井手亞里的話說“一張圖片可以帶動很多產業”,雖然制作一張高清的圖像需要投入較高的成本,但是開發得當,一張高清的圖像也能帶來更高的價值和回報。endprint
四、教育布局
該實驗室提出了未來的教育規劃,即建立一個國際藝術和文化遺產數字化中心,該中心由四大模塊組成:數字博物館和數字展覽、高級成像技術教育研究院、知識產權管理、產品及商業推廣系列公司。四大模塊各有專攻,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其中高級成像技術教育研究院提供藝術科學和技術領域的碩士和博士課程,分為文化藝術、工程技術兩個方向。產品及商業推廣系列公司包括軟件開發公司、電影動畫制作公司、網絡傳播公司、文化娛樂商業公司、教育產品發展公司、知識產品管理公司等。可見,該實驗室立足于其獨有的技術優勢,發現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巨大市場,對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進行產業布局,其前景是非常可觀的。
五、啟示
文化遺產與檔案具有密切的聯系。在人類文明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產中,有些是以文物的形式保存下來的,有些是以文字記載(檔案)的形式保存下來的。無論是文物還是檔案,它們都需要人們進行良好地保護并適度開發利用。通過前文對京都大學全球大型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的介紹,筆者有感于三點:(1)創新的動力來自于內心的熱愛。該實驗室之所以能開發出如此適合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產品,筆者認為離不開開發者內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同與熱愛。井手強調,人類文化遺產有三大敵人——戰爭、貧窮和無知[4],并且堅信有太多的文化遺產需要通過數字化得以保護和傳播,鑒于此,才專注于適應文化遺產保護需求的技術開發。(2)注重資源的深度開發。文化遺產數字化,形成的產品是文化遺產的數字副本。如果不進行開發,就是躺在數據庫里的圖片。該實驗室創新思路,深度地挖掘了文化遺產的藝術價值,并迎合公眾的審美需求,開發出廣受歡迎的文化產品,取得社會和經濟的雙重效益。(3)打開思路,把事業做大。該實驗室提出的未來教育規劃,能基于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技術優勢,發現文博藝術領域的巨大市場,從教育、研究到提供產品開發服務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不能不說思路開闊。筆者認為,這對做好我國檔案工作帶來多方面的啟示。
(一)增強對檔案事業的自信心。京都大學實驗室之所以能開發出如此尖端的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其內在的動力來自于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熱愛,反觀在我們的檔案工作隊伍里,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檔案工作的態度消極,認為檔案工作很簡單、枯燥,沒有技術含量,不少人發出類似“一個中學生都可以干”、“培訓幾天就能上崗”的言論。有調查顯示,“87名(全樣本)檔案工作者對自己職業的認同程度一般,對檔案工作的前景期望不高,這種狀態不利于檔案工作的創新與發展。”[5]。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檔案工作的作用,建立對檔案事業的自信心和認同感,只有這樣,才能從內心深處激發檔案工作者的創造力,促進檔案事業的發展。
(二)進行檔案資源的深度開發。該實驗室充分地挖掘了文化遺產的藝術價值,開發出廣受歡迎的文化產品。檔案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直接形成的記錄,是可靠的信息,里面蘊含著豐富的經驗、知識和智慧,對于如何充分發揮檔案是“可靠的信息”這種核心價值,是值得檔案工作者思考的。
(三)檔案數字化的新思路。目前,我國檔案數字化工作也在積極開展,對于紙質檔案的數字化采集,基于成本控制的原因,普遍認為分辨率在100-300dpi之間即可,這對于普通的文件是足夠的。但是我國檔案館藏體系里有相當一部分的實物檔案和珍品檔案,這些檔案是檔案部門進行網上展覽的重點對象。對于這些檔案,不僅內容重要,其載體形式也很重要,對其進行數字化采集的傳統方式是相機拍攝。管先海認為,網上展覽普遍存在主題較單調、信息量較少、交互功能差、更新速度慢等問題。[6]“檔案展覽要想具備吸引觀眾、打動觀眾的魅力,必須有‘檔案味,必須考慮所用材料的質量和分量,必須有歷史的厚重感。”[7]對于這類實物檔案和珍品檔案,可以換一種采集思路,采用文博領域的三維、高清掃描,讓觀眾感受其清晰的紋理,真切地感受珍品檔案的歷史魅力。
(四)加強人才的培養。該實驗室提出的教育規劃中,把文化藝術和工程技術兩個方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培養既懂藝術又懂技術的人才。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給檔案工作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但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在信息時代,我們迫切需要培養既懂檔案又懂信息技術的“復合型人才”。對于如何科學地設置課程體系,實現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提供了一些借鑒。
注:本文的圖片和有關資料來源于日本京都大學工程研究生院高級圖像技術實驗室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講座,作者已經征得主講人井手亞里教授的同意。
參考文獻:
[1]王晨,王媛.文化遺產導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9
[2]同[1],9-13頁
[3]“東亞古文獻保存、修復和價值重現——現代技術的應用‘專題講座與工作坊”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http://libweb.zju.edu.cn/libweb/redir.php?catalog_id= 8580&object_id=206969。此例雖然不是來自于本次講座,但是可以讓人對文化遺產數字圖像的開發應用有個直觀認識。
[4] [7]掃描技術助古文獻保原貌,http://news. takungpao.com/paper/q/2015/0225/2926398.html
[5]張昱,朱代紅,全鈺平.檔案工作者職業認同現狀調查及分析[J].檔案與建設,2013.(5).
[6]管先海,孫洋洋,王鳳珍.1981年~2014年我國檔案展覽研究綜述[J].檔案管理,2015(4):6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