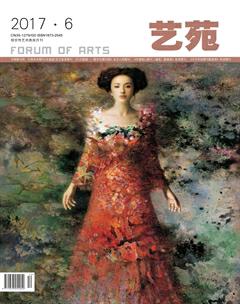都市照相館:早期西非攝影家的搖籃
崇秀全



【摘要】 本文擬從法國學者格里西爾斯的非洲攝影歷史研究和九屆巴馬科攝影節中整理出10名以照相館經營為主的西非攝影家,對他們的攝影生涯和拍攝活動做一個整體的盤點和介紹。進而,筆者深入3名攝影家的人像作品個案研究,從研究闡釋中管窺塵封在歷史影像中的殖民活動、西非社會及20世紀西非現代主義發展。
【關鍵詞】 現代主義;早期西非攝影;照相館;西非社會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攝影在西非(西部非洲)傳播初期,限于技術之困,在工業化水平較高的都市城鎮因地制宜地開設照相館,同時兼具民眾基礎和殖民初衷,亦能順應市場需求。因而,早期西非都市照相館的出現,可以從攝影技術、社會需要和殖民治理三個方面追根溯源:一、從技術方面,早期攝影受制于相機曝光時間較長、體積大且笨重不適宜攜帶、后期底片處理和照片沖洗印曬對場地和器材要求較為復雜等問題,設置照相館是解決此類問題的主要方法;二、從社會需要方面,在固定地點設置照相館,集招攬顧客、拍攝肖像、展示作品和后續服務為一體,順應民眾的消費心理和社會需求;三、從殖民治理方面,歐洲宗主國需要直觀殖民影像及想象非洲治理圖景,殖民者利用照相館這個隱性的聯系點,方便管理非洲民眾和維持社會秩序。因此早期非洲照相館就像歐洲殖民者帶來的種植經濟,在他們的培育和扶持下朝著歐洲需要的方向生長。然而,照相館經營與種植經濟一樣,也是一把雙刃劍,早期歐洲殖民者通過照相館教會非洲人攝影技術和經營技巧,非洲第一代攝影師逐漸成長起來,他們自設照相館,從而逐漸把歐洲人擠出西非攝影市場。近年來由于西非馬里巴馬科國際攝影節連續舉辦并持續發酵,引起國內攝影界的興趣,但相關攝影家的介紹尚未跟進,筆者擬從法國學者格里西爾斯(Guido Gryseels)的非洲攝影歷史研究[1]和已經連續舉辦九屆的非洲最大攝影節——巴馬科攝影節——中整理出10名以照相館經營為主的西非攝影家,對他們的攝影生涯和拍攝活動做一個整體的盤點和介紹,以作為觀展中的輔助參考。誠然,筆者還試圖進一步深入3個攝影家人像作品的個案研究,從研究闡釋中管窺塵封在歷史影像中的殖民活動、西非社會及20世紀西非現代主義發展。
一
順應殖民發展和攝影在西非的傳播路徑,第一代西非本土攝影家是在沿海國家開始出現的。據相關資料,最早的西非攝影家是多哥共和國的亞歷克斯·阿格巴格洛·阿哥拉特斯(Alex Agbaglo Acolatse,1880-1975)[1]30。他出身于開德茲英國及其后法國殖民統治時期頗受當地人敬重的名門望族,在20世紀初跟德國人在照相館研習攝影技術,后在洛美開設照相館。他的工作面很廣,涵蓋自黃金海岸至尼日利亞的整個沿海地區,連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成為他的顧客。考慮他的顯赫家庭出身及在宗教界的地位,多哥職業攝影師協會曾推選他為主席。阿哥拉特斯是西非最有資歷的攝影家,人們至今仍保留著他使用過的玻璃感光板。
塞內加爾民族史上第一位攝影師梅伊薩·蓋伊(Me?ssa Gaye,1892-1982)[1]34的個人照相館經營史與非洲第一座歐非風格的城市圣路易的城市發展史息息相關。首先,他在都市開設照相館。20世紀初,他就在圣路易市開辦了第一家達蓋爾攝影術工作室,無數商販、官員、軍人、冒險家以及攝影師都來過這個照相館,他們在這里留影的同時也留下了城市發展的印記。1945年,蓋伊配置了較為高級的祿萊相機在圣路易市的北區又開設了一家“熱帶相片”照相館,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熱帶相片”與馬提尼克人卡里斯坦開辦的工作室一起,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兩家照相館。其次,他走向城市街頭拍攝。蓋伊也帶著配有自制鎂光燈的木制暗箱,騎著自行車在圣路易來回穿梭,記錄下城市的歷史印痕。圣路易市在戰后成為時尚之都,人們周末來此合著爵士樂翩翩起舞,蓋伊忠實地記錄下這一切,現在這些城市生活快照的碎片集合成為圣路易城繁榮時尚的視覺見證。他還挖掘得更深,拍攝了名為“尤尼、尤尼”的圣路易市系列專題照片,“尤尼”意思是“此處或此在”,即用攝影專題保留著城市發展歷史中的“此時,此地”。第三,他教授西非人學習攝影。生于圣路易市的攝影家阿布德拉姆·薩卡利(Abderramane Sakaly,1926-1988)就是在隨父經商中向蓋伊學習攝影技術,后來成為職業攝影家的。1956年,他定居巴馬科,并在1960-1970年代開辦了一家“潮流照相館”。此外,薩卡利利用在文化活動中從事報道攝影,并為馬里博物館藏品拍照。
時至今日,所有圣路易市的攝影師們都將蓋伊視奉為先祖,因為他是圣路易市最早從事攝影的非洲人。誠然,如果從開設塞內加爾第一批照相館和記錄圣路易的城市歷史而言,給予他“先祖”的地位也不為過,但不為人所知的是,今天,我們把他的工作與另一位塞內加爾攝影師瑪瑪·卡薩特聚合起來,共同放置在非洲攝影的歷史坐標上觀察,他們的作用就更加具有革命性和里程碑的定位和意義。我也可以這樣說,他們的工作超越了簡單的攝影技術使用層面,將攝影轉變成為現代科技在西非的鏡像投射和城市發展的美學思考,即西非現代主義發展的表征。
與蓋伊同時躋身早期西非攝影歷史名人堂的塞內加爾攝影師瑪瑪·卡薩特(Mama Casset,1908-1992)[1]68從12歲起就在達喀爾向弗朗索瓦·奧斯卡·拉塔克學習攝影,在他讀完小學時被戴納甘雇傭去了法屬西非的攝影分行,跟法國人學習攝影。成年后,卡薩特去了法國空軍部隊服役,在此后漫長的軍旅生涯中為法國空軍創作了數量驚人的攝影作品。
卡薩特于二戰末期回國,在達喀爾老城區開辦了一家名為“非洲照片”工作室,照相館經營狀況良好,當地黑人同胞因為各種需要走進這間照相館,他/她們在帶走自己美好瞬間的同時也留下了法屬殖民時期的歷史縮影。卡薩特憑借十分時尚化和具有固定程式的肖像美學風靡一時:鏡頭前的黑人女性穿著艷麗,男性同胞樸素自然,很少背景和物件裝飾元素,常常固定采取傾斜式或對角線的人物姿勢,結合使用手勢、眼神、表情等身體語言,畫面緊湊,中距離和近景居多,人物常常2/3肖像占滿空間。當然,程式化有較高的識別度和風格特征,但也明顯存在著缺陷。著名非洲攝影策展人和批評家恩威佐曾就此評論說:“這樣的姿勢安排和短焦鏡頭的使用顯示了殖民地照片所缺少的坐著的被拍攝者和攝影師之間的相互關系。”[2]實際上,我們不難從照片中看出卡薩特的攝影器材和技術的粗陋。在欠發達的西非殖民國家,受限于變焦和長焦鏡頭的昂貴,攝影器材和道具短缺,而且并不富有的西非居民用在攝影上的開支是十分有限的。卡薩特簡單化地處理人像的姿勢,并把它們程式化,然后用短焦鏡頭捕捉某個不確定的表情和手勢,既節約了成本,也滿足了民眾攝影新生活的渴望。endprint
然而,卡薩特憑借攝影工作謀生之余,也發展著自身的愛好。他把這項工作投射在以妻子為模特的拍攝實驗中,持續不斷的拍攝妻子肖像工作足以令其躋身于西非歷史上著名藝術人像攝影家。也許是第二任妻子的年輕美麗激發了他的攝影熱情,也或是家人更加容易親近和方便拍攝,他嘗試用多種方式長期拍攝的妻子照片,并制作成明信片和海報類招貼畫,這些照片被制作后相當暢銷,成為許多商業裝裱畫畫家們臨摹的范本。今天,我們觀賞一幅卡薩特工作室出品的妻子肖像就像穿越過歷史時空,感受女主人身上芬芳的香水氣息一樣,一種甜蜜的憂傷或淡淡的哀愁被華美的服飾裹挾其中。因為,塞內加爾攝影史反映并建構著殖民化、后殖民化、現代化的復雜艱難的進程。這些過程在他們的攝影商業活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達喀爾作為一個文化地標的發展過程中被揭示出來。達喀爾作為法屬西非的首府被殖民者作為“非洲同化”進程中重要的站點加以推進,象征性地美譽為“非洲巴黎”。結果,達喀爾成為宗主國與西非地區聯系的大門,它既是法國的現代化和文明在非洲的中心,也是西非幾個世紀以來跨大西洋和撒哈拉沙漠與歐洲貿易的地區性中心。筆者將這些復雜的問題聚焦到卡薩特妻子肖像上,通過這些追求西方式的服飾文明、精致整潔的時尚婦女肖像,揭示出一些親法國行為和等級化文明的癥候。
20世紀80年代,卡薩特由于雙目失明而終止攝影。此后,他的照相館也在一場大火中被徹底燒毀,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打擊使他過度悲傷而離開人世。但值得慶幸的是,他的傳世作品多虧了攝影師布納·梅都納·薩耶的搶救和保護,才得以留存和延續。然而,達喀爾的人像攝影并沒有因為卡薩特的離世而停下腳步,80年代后,攝影師開始走出照相館來到顧客門前。業余攝影師也活躍起來,雖然那個時代家庭擁有相機的數量并不多,但照片放大技術的成熟,并借助彩色印刷技術廣布市鎮,業余攝影師用借來的定焦鏡頭巡回在達喀爾街頭,拍攝標準肖像,卡薩特等一代職業攝影家經營起來的照相館開始閑置下來。
二
比多哥共和國和塞內加爾稍晚,西非其他國家也有少數當地人開設照相館,這里列出5位都是所在國第一代開設照相館的攝影家。貝寧攝影師約瑟夫·莫伊斯·阿格波日路(Joseph Mo?se Agbojelou,1912-2000)在1935年法國應征入伍期間學習了攝影術的基本知識。作為柯達在貝寧的代理人,約瑟夫成為達奧美職業攝影師協會主席。在1960年左右,約瑟夫開辦了一間屬于他的照相館:“法蘭西照相”。拍攝范圍包括:婚禮、喪葬、守夜、圣餐、政治、文化、宗教慶典、社會新聞等。1994年,阿格波日路最終結束了他的攝影生涯。如今,貝寧將近50年的政治歷史和日常生活視覺筆記,沉睡在幾個大盒子里,還有待挖掘和研究。安托尼·弗里達斯(Antoine Freitas,1919-1990)的攝影技術從安哥拉的一位白人神父那里習得。1932年,弗里達斯定居首都金沙薩,1935年開始經營一家照相館,并抽空開始漫游剛果全境,上門拍照。我們可以在一張非同尋常的照片中看到:弗里達斯在開賽河邊聚集著的孩子和村民們中間擺弄著他的箱式照相機,對面是三個站在古典裝飾風格的彩色帷幕前的黑人婦女和她們的孩子正在擺著姿勢等待拍攝,一旁圍觀的當地居民好奇地打量著這一幕。在早期攝影被認為是魔法的剛果人面前,商業攝影增加一項工作是安撫他們見到自己照片的恐慌,因為剛果人認為攝影魔法攝取了他們的靈魂。象牙海岸多哥帕利美的攝影家科尼利厄斯·奧古斯特·阿扎格羅(Cornelius Augustt Azaglo,1924-2001),從18歲開始對攝影產生興趣并就此入門。然而他真正意義上成為一個攝影師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1995年,阿扎格羅在象牙海岸北部的科洛格定居,開設了北部的一家照相館并大獲成功。阿扎格羅還經常去鄉村的廣場,在土砌的墻前張起一塊簡單的背景布,在熾熱的陽光下給農民們拍攝肖像,也刻畫出農村生活的艱苦和記錄生存條件的惡劣。剛果攝影師(1)讓·德帕拉(Jean Depara,1928-1997)[1]144在1953年之前一直是個鞋匠(2)。50年代他用德國產亞鐸牌(Adox)的相機嘗試拍照,并且建立了“讓·德帕拉工作室”。1954年前后,他成為弗朗哥政府官方攝影師,作品曾受到弗朗哥的稱贊,還被邀請參加摩卡利亞的音樂晚會。白天,德帕拉經常去城里的酒吧,晚上,他背著照相機出入于舞廳,在這種環境里,德帕拉發展了首都最有代表性的夜生活攝影。剛果民主共和國攝影家盎姆瓦斯·恩蓋莫科(Ambroise Ngaimoko,1949-)[1]142為了躲避在安哥拉肆虐的獨立戰爭,12歲時就與家人一起來到了首府金沙薩,作為家庭唯一的男性和經濟支柱,他先在露天電影院謀生,因為叔叔馬可·恩多達經營兩家照相館而逐漸喜歡上攝影。恩蓋莫科于1971年設立了“3Z攝影工作室”,經營至1998年。
三
19世紀末期,攝影在西非,開始成為它的發明者——兩個最強大的殖民宗主國——法國和英國推銷異國文化和殖民治理的工具,那些生活在西非的歐洲攝影師借助明信片和新聞畫報向宗主國傳遞非洲的異國情調和殖民治理,從而持續刺激歐洲上層社會的浪漫想象和殖民熱情。到了20世紀初,那些曾經寄居在歐洲人開辦的照相館內的非洲攝影學徒也開始利用這一媒介來展現他們周遭的世界,他們獨立經營照相館,并逐漸走上街頭門前,從社會結構內部開展社會“寫真”藝術。“非洲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運用現代技術,公然反抗殖民者為了他們自己的文化表述而暗示的殖民邏輯。”[3]206非洲攝影研究者穆斯塔伐寫道。自學成才的馬里攝影師賽義杜·凱塔(Seydou Ke?ta,1921-2001)[4]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長達60年的攝影實踐,從開設照相館到走向街頭門前為顧客拍照,攝影這種現代主義的技術表征,現在成為非洲人記錄自己歷史和相互交流的工具,而不再是歐洲人的非洲他者文化想象。
20世紀30年代,少年凱塔初觸攝影。他的叔叔返鄉時隨身攜帶了一臺德國產的小型相機。因為父親和叔叔都是木工,常在一起工作,密切的親緣關系促成他拿到相機,拍下生平第一張照片,盡管他當時已經掌握木工技術,但還是被攝影深深吸引了,從此家庭成為他拍攝人像的第一個試驗場。當時,地處西非的馬里很少有人擁有自己的相機,所以攝影很容易轉化成為謀生的個體商業。[5]96據非洲學者安德烈·瑪格寧的研究,1948年,凱塔在馬里開設了第一家攝影工作室,經營商業人像。因為巴馬科是國際貿易中心,法國人的非洲殖民窗口,所以生活在這里的非洲人對攝影并不陌生,年輕黑人尤其喜歡攝影,他們常常走到凱塔的照相館里合影留念。同時,為了吸引顧客,提高影像品質,凱塔買了一臺5×7英寸的大畫幅相機,從1949年到1963年,一直使用這臺相機拍照,這也是為什么凱塔的照片經過半個多世紀后依然畫面清晰,影像質量和文獻價值較高的原因。endprint
20世紀50年代,出自西非照相館的人像的姿態、裝飾和用途等顯示了延續至今的西非人像攝影范式。“女人們穿著她們的奇異的服裝來到這里”,凱塔說,“于是,我為她們擺好姿勢,然后展示她們的服裝。最重要的是服裝必須在相片中展示出來。手、纖細的手指、珠寶……這些都非常重要。這是財富、優雅和美麗的象征。”[3]205凱塔將歐洲的服裝、鉛筆、香煙、塑料花、電話、珠寶、手表、收音機等現代工藝品作為顧客攝影的小道具。顧客從照相館墻壁上張貼的各種人像照片中展示的姿勢中進行選擇,有些富有的顧客自帶黃金珠寶類的名貴裝飾品,也可能會提前設計好發式造型。凱塔在拍攝時會跟她們協商拍攝姿勢,然后是選擇道具,再把鏡頭聚焦在頭、手和精心準備的發型和衣飾上。穆斯塔伐在《塞內加爾攝影簡史》中提到凱塔照片在當時的社會性使用:“照片洗印出來后,顧客通常會拿回家掛在房間內做裝飾,表明她精致閑適的生活,介紹和證明她豐富的社會關系。”[3]204他找到一種名為“Xoymet”的婚禮照片實際使用和流傳:“在婚禮夜晚,新娘被帶到她丈夫的家。丈夫的房間將臨時用那些從新娘鄰居或者親戚那兒借來的飾物和相片來裝扮。這就向這個新的家庭提供了某種有關她的社會關系的介紹。影像強調了當地對自我表達的關心,并隨著都市社會的發展和分層化提供了內部裝飾的新形式。”[3]205
室內照相館的主要工作地點在城市,照片的使用也是在市民的社交和親屬圈子內。然而,在巴馬科以外的偏遠集鎮和農村地區,盡管人們對攝影還心懷畏懼,一是怕攝影透視服裝,暴露人體;二是怕攝影偷走人的魂魄。但是,利用自然光攝影和走向街頭門前及農村地區是凱塔這代非洲攝影家的挑戰和夢想,他們用現場的底片逐漸說服了那些懼怕攝影的人,并就地取材利用窗簾、床單作為背景,利用住宅前面的院子和農村墻角的背陰處[5]96-98作為拍攝場地,游走村鎮10余年。在長期的村鎮游走攝影實踐中,凱塔從馬里戶外攝影因陋就簡中巧拾本土文化,演繹出了可以立即辨識的“凱塔式人像風格”[6]184,集結成馬里人的影像人類學,攝影的社會性使用也被大大拓展了。現在,這些被看成馬里人的影像志的國民肖像攝影,竟然得益于這么簡單的攝影夢。
20世紀80年代,首先,攝影技術飛速進步,鏡頭技術、快門速度提高和相機的小型化解放了照相館功能,戶外攝影和街頭快照更受歡迎。僅有少數富人或者儀式性照片還依賴照相館,攝影師們對室內造像或者端正的姿態已經沒有什么興趣,他們紛紛走出照相館來到居民門前或者走上街頭。其次,在家庭內部,尊貴的主人大量使用殖民地明信片的不同的主題將攝影帶入自家的院落、婦女們的臥室和社交圈,非洲人開始告別殖民武器——照相館,用都市生活快照完成自身文化情境的布展和再造。正如穆斯塔伐的評述:“通過這些新異的影像,非洲人把攝影納入他們自己的商業的、儀式的、自我設計的實踐,把全球的和本土的商品與影像流通聯系在一起。”[3]201
結 語
綜上,早期西非都市照相館的開設首先是受限于攝影技術粗陋的權宜之計,其次,也是城市化和商業化在西非發展的市場之需,最后,它們也是歐洲人他者文化的浪漫想象和方便殖民治理的社會性產物。然而,西非第一代本土攝影家們則借助照相館作為孵化器,在學徒制中從歐洲人手中學得攝影技術,接過攝影魔法、影像記錄和傳播的功能,開啟了20世紀非洲人的非洲攝影。
注釋:
(1)另外一種說法他是一位安哥拉人。
(2)參見網站http://www.artnet.fr/artistes/jean-depara/。
參考文獻:
[1]Guido Gryseels. LAfrique par elle-même,un siècle de photographie africaine[M]. Anne-Marie et al, Revue Noire, Paris,1998.
[2]Clare Bell,Okwui Enwezor,Danielle Tilkin and Octavio Zaya.In/Sight:African Photographers,1940 to the Present[M].The Solomon R.Guggenheim Foundation,New York,1996.
[3]胡迪塔·諾拉·穆斯塔伐.現代性的肖像:達喀爾大眾攝影中的時尚自我//吳瓊.上帝的眼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4]André Magnin.Seydou Ke?ta[M].Scalo Zurich-Berlin-New York,1997.
[5]安宜.塞義杜·凱塔:背陰處的美麗[J].攝影世界,2004(7).
[6](英)格里·巴杰.攝影的精神——攝影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M].朱攸若,譯.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