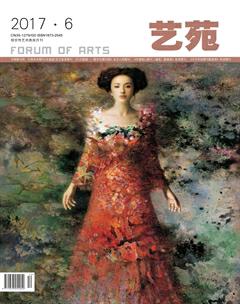意識“不在場”下的選擇自由
楊佳凝


【摘要】 本文以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大量的閃回鏡頭為切入點,探析比利·林恩意識的“不在場”、意識“不在場”的原因及“不在場”的深層意義。
【關鍵詞】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閃回鏡頭;不在場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李安的第20部電影作品,有人認為無論從寥寥174萬的北美票房成績還是從對于主體表現毫無助益的120幀技術使用來看,這部影片都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品;另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是,這是一部具有超時代意義的影片,其呈現的主題和應用的120幀呈像都已在電影史上烙下濃重一筆。筆者認同后者:影片對男主角比利·林恩大量“特寫-閃回”式的描繪方式制造出了一種人物意識“不在場”的效果,而這樣的“不在場”并非比利·林恩個體性的。
一、比利·林恩的“不在場”
電影中,誰占據了視點鏡頭誰就掌握了主要敘述權。按照敘述學理論,故事的完成同時需要敘述者和隱含敘述者,而二者的職能分界在于:敘述者越全知全能,隱含敘述者的權力越受限制,反之亦然。而全知全能包括如下一種或集中特點:知道故事的結局,有能力縱深到人物的心靈世界,而且/或者有能力不受時空的限制而任意移動判斷敘述者全知全能程度的方法,主要看敘述者的講述是否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說,我們是否只是受限于主要人物的行為和信息,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敘述者是否能夠在人物中間任意穿梭,以此判斷敘述者是否是“不受限制的”。[1]75《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敘述者是李安,隱含敘述者是比利·林恩。不難發現,敘述者的權力非常小,既不知道故事結局,也無法穿梭于人物之間。而比利·林恩作為這部影片的隱含敘述者,幾乎“全知全能”:他全程參與了整個故事,他不受時空限制地“穿梭往來”于過去和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必是林恩看到或經歷的。這種大大“擠榨”敘述者權力的自傳性表達借鑒于文學作品,在李安的電影中是首次出現。
然而,影片中大量“特寫-閃回”式的鏡頭組接方式又在暗示我們:林恩對于他參與的所有場景和故事,都不“在場”,如哈姆雷特感到“時代是顛倒混亂的”[2]34,林恩的意識同樣顛倒混亂。影片將敘事空間分為伊拉克戰場和美國城市兩處,因而閃回也僅存現于這兩處之間。
林恩和B班戰友被迎接回國,走在家鄉的街道上,林恩看著熱鬧紛擾的路人、小丑,眼前閃回伊拉克的街區:表面繁榮的市場、充滿敵意地盯著他們的當地人、賣毛片的少年;林恩在體育場觀看橄欖球表演,運動員呈拋物線狀丟出的橄欖球讓他眼前立時閃現與姐姐聊天時姐姐臉上的駭人傷疤;看著餐桌上大塊肥美的牛肉和墻上掛著的扭頭標本,閃回的是伊拉克的帳中:士兵們逼問當地人是否藏有武器,并在搜出一把護身手槍后殺死了一名男子;中場表演時眾人一臉忠誠地唱著國歌,林恩看著昂首歌唱著的菲珊,閃回的是與她做愛時她陶醉的表情和呻吟;班長鼓勵他的戰士:拿出打仗的勁頭準備中場表演,林恩眼中浮現的是伊拉克大仗前班長鼓勵每一個人的那一句:我愛你;而整個中場表演,更讓林恩的眼前閃回了人生最艱難一日的全部畫面:運動場的煙花和戰場的彈林、運動場的歡呼和戰場的槍炮聲、音樂家的歌聲和逼近面前的伊拉克士兵的嘶吼聲……畫面近乎重疊的一一呈現,他淚流滿面,如加繆所言,“始終是自己真情實況的受難者”[3]9,畫外音響起:我感覺,糟糕透了。
這些閃回或許存在內在邏輯,但它們指向同一個問題是:林恩從未融入任何一項活動。他的思想永遠是游離的,他的意識始終是獨立于活動本身的。換言之,比利·林恩始終“不在場”。通俗而言,在場是指“正在這里存在的東西,或者某物現在正在這里存在。這種當前存在是最堅實的,是我們可以直接感受和擁有的東西”[4],也可“被理解為直接性、完整的經歷,理解為真實可靠”[5]213。我們判定“不在場”的前提是認同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意識是存在的前提,以他的意識是否存在作為判斷他是否“在場”的標準。林恩的意識與他的肉體始終不同在,此時他是一個與德呂達所謂“不在場的在場者”[6]8恰好相反的,在場的不在場者。
林恩的不在場意味著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但他又如加繆筆下莫爾索一般“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3]8,因而他的“旁觀”就具有了悲憫意味。一方面,他是戰場的“局外人”:班長用近乎虐待的方式逼問他:你為什么要來?他的最終答案是“為了凱瑟琳”,凱瑟琳是他的姐姐,因車禍毀容,而后被未婚夫拋棄,喪失生活希望。林恩砸了姐姐未婚夫的車,為了銷除指控,只得答應父親去從軍。在炮火中,他同情無辜民眾,因殺人而寢食難安。而另一方面,當他以美國英雄的身份回國,受媒體熱捧、民眾擁躉,但他完全不享受這種烈火烹油的狀態,聽著人們表達對他的欽慕和贊美,他的表情非常疲憊,近乎不耐煩。他不是現實的一部分,現實視他為符號:他是反戰者眼中罪惡的輪子、擁戰者手中的英雄火把。
這種“局外人”的生命體驗在李安和李安的電影中并非孤例。這樣的“局外感”可歸因于長期的“流散”。復雜的生命經歷使得李安和李安電影常被作為“流散電影人”和“流散電影”來研究。“流散”的簡潔定義是:因不同原因而散居于一個以上地點的人群,他們雖散居各地,卻可能共同懷揣回歸故鄉的理想,他們無法完全同化于移居國,并可能與居住于不同地方的同一族群保持各種各樣的聯系,然而,如果對流散族群做進一步全面、完整的界定,那么就應當涵蓋社會形態、自我意識、文化生產等不同層面,至少應包含遷移、分布、定居、奮斗、網絡、回歸、傳承等七個方面的內容。[7]李安的復雜生命經歷和中美文化背景決定了他是一位流散導演,他的作品因而具有很強的流散特性,這樣的流散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流散于臺灣的大陸人、一方面是流散于美國的中國人,這使他不僅是臺灣的“局外人”,也是美國的“局外人”。林恩在這里同樣是流散者:一方面是流散于戰場的抗拒者,一方面是流散于現實世界的符號,因而他從未屬于任一個空間,哪怕他的意識游返于二者。endprint
二、比利·林恩“不在場”溯因
是什么導致了林恩的“不在場”。筆者以為原因有二,表層原因在于:林恩的“不在場”是因為他“有得選”。在參加戰爭之前,人們想到死亡,可能“無非把死亡當作一個文學事件或者時間對不完美的肉體施加的緩慢、默默的耗損。沒有想過死亡就是發生在某個戰場上的暴力爆炸,沒有想過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嚨里血流如噴”[8]72。因此在經歷過生死只差毫厘之后,士兵們理所當然會對戰場拒斥無比,但就像隊長質問的“你以為我們有得選嗎?”他們沒有選擇,榮譽感和責任感牢牢將他們束縛在戰場上,這是比監獄更甚的“規訓”。但林恩不同,一卷戰場上拼死營救的錄像帶“解放”了他,哪怕他不回戰場,也沒有人質疑他的責任感,國家更是將榮譽捧到了他的胸前,此時他獲得了做選擇的現實條件。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來自林恩不斷纏斗的內心。林恩不斷游返的意識與《喧嘩與騷動》中的班杰明(1)何其相似:他活在“現在”,但他的意識不斷地抽離,回到有姐姐照顧的“過去”,他說服自己相信“活在”過去,甚至用拒斥鐘表的方式逃避時間的耗損。李安使用這樣的相似表達,似在有意識地暗示我們:比利·林恩可能與白癡班杰明一樣“不正常”,但他并不是班杰明那樣病理性的精神病人,他是卡倫·霍妮(2)所謂的典型的“神經癥人格”:每個人的內心時刻處于各種矛盾沖突之中,而最主要的沖突就是我們都同時具有“親近人”“對抗人”“逃避人”的沖動,這些沖動若協調不好,就會使我們陷入各種各樣的焦慮和神經癥。[9]42溫吞的個性使得林恩無法與人正面交鋒(在姐姐受到傷害后,他選擇砸車而非打架的方式發泄憤怒),并不和睦的家庭使他很難與歇斯底里的母親、冷漠寡言的父親相處,而當時的美國由于“911事件”導致的異常緊張而又狂熱的社會氛圍也加劇了林恩內心的沖突感,沖突感積蓄為焦慮,他企圖保護自己以對抗基本焦慮。霍妮認為保護有四種方式:愛、順從、權力和退縮。[9]65林恩將這些方式一一嘗試,他試圖神圣化自己與菲珊的愛情,但被傷害;他試圖毫不懷疑班長的指令,但失敗;他可以接受好萊塢巨額的改編權邀約,但拒絕;他能夠選擇逃離戰場,但放棄。對抗焦慮的失敗嘗試引發了“神經癥”,他質疑自己與他人的關系、質疑自己與社會的關系,他不知道生活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不知道世界是有秩序合理的還是混亂無當的、不知道人心究竟是光明的駐地還是罪惡的淵藪。最終,他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參與活動,哪怕活動以他為中心。
三、比利·林恩“不在場”的意義
緊接著的第三個問題是:林恩的“不在場”有沒有意義?筆者認為意義有二:首先,他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世界和自己。意識的“不在場”直接導致距離感,林恩因此得以以一種旁觀者的立場看待世界,他站在觀眾席,看著“舞臺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同時扮演忠貞者與蕩婦、牧師與小丑、正義與刁惡、神性與魔性。如駱冬青所言:人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物——“此在”,被拋入了世界。于是,產生了陌生、荒謬與悲愴之感。以“局外人”的眼光來旁觀世界,必定痛心于一切意識形態的“幻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種種虛偽與幻想。[10]246
片中林恩糾結的主要問題是:留在險魅交織的現實世界,還是回到槍林彈雨的戰爭叢林。這種糾結持續存在于整部電影。“不在場”的第二個意義就在于,它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當人失去了行動的目的,他就會獲得選擇的自由。電影的開始,林恩和姐姐談話:“我必須回去。”“你為什么要回去?”“我承諾過。”“得了吧,我們都知道你為什么要上戰場。”“我必須回去。”“你敢回去我就自殺。”“我必須回去。”而在與菲珊墜入愛河后,林恩的決定動搖了:“我差點就帶著你逃跑了。”“逃跑?你是授銜的英雄啊,你要回戰場的。”“當然、沒錯,我說著玩兒的。”回與不回,如天平兩端,各有砝碼。回的一端是對現狀的疲憊、對菲珊虛偽面目的看清、對好萊塢奸商的厭惡;不回的一端是對戰爭的恐懼、對伊拉克枉死者的愧歉以及姐姐近乎歇斯底里的挽留。然而那些砝碼實際上是什么呢?戰場需要他,需要他“舍身為人”的精神激勵更多士兵身先士卒、化作權力輪子下的炮灰;姐姐渴望他留下,是想抓住自己失敗人生的一縷救命稻草;菲珊想占有他的每分每秒,是給自己虛榮的英雄夢的想象性滿足;好萊塢利誘他,不過是想利用他挑逗觀眾疲軟的“美國夢”的神經。人人各有所求,所求不過自己意淫中的喧囂夢幻的光怪陸離的狂歡、虛妄而已。因而當他看清這些“幻像”之時,就是這些砝碼失重于他之時,此時便無需平衡去留,因為無論來去,都是“也無風雨也無晴”。
李安的大多數電影中人物的行為模式都是“糾結-妥協”:在經歷了愛情還是親情的漫長糾結后,偉同選擇了向父母坦白同性戀的身份;在經歷了愛情還是責任的艱難糾結后,王佳芝選擇了“為虎作倀”,向易先生交代同伴所為;在經歷了愛情還是家庭的反復糾結后,杰克和艾尼斯選擇了一年只在斷背山見面一次。這些人物的選擇無論是非此即彼還是盡力兩全,但難度無異于壯士斷腕,若非掀起駭浪,便是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泥沼。
比利·林恩的選擇絕非一種“妥協”,而是非常的坦蕩而愉快,他坐在裝甲車中,微笑地望著每一位戰友,聽他們說“我愛你”,他的表情如釋重負,毫無作偽,仿佛解脫,這樣的解脫來自于選擇的正確嗎?如果留在家中他能獲得同樣的解脫嗎?筆者認為,毫無疑問,當然可以。我們在前文已經分析過了,回與不回,對他來說同樣充滿動力和阻力,因此他的解脫感并非來源于做出了回戰場的選擇,而是因為目的性喪失,因為無論去留都是無意義的,所以選擇是去是留就毫無分別了。看清了目的的無意義,接受了意義的荒謬,比利·林恩獲得了選擇的自由。此時他的選擇不是通往黑夜的漫長旅程,而是“那漫長的夜,輾轉而沉默的時刻”的終止。
注釋:
(1)《喧嘩與騷動》,美國作家福克納作品,被認為是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小說講述了南方沒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劇。其中班杰明是康普生的小兒子,三十三歲只有三歲小孩的智能。
(2)卡倫·霍妮,醫學博士,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中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社會心理學的最早的倡導者之一,她相信用社會心理學說明人格的發展比弗洛伊德性的概念更適當,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著有《精神分析新法》《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我們內心的沖突》和《神經癥與人的成長》等。
參考文獻:
[1](美)羅伯特·艾倫.重組話語頻道[M].牟嶺,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英)莎士比亞.哈姆萊特[M].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3](法)阿爾貝·加繆.局外人[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4]彭鋒.重回在場一一兼論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J].學術月刊,2006(12).
[5](德)艾利卡·費舍爾·李希特.行為表演美學——關于演出的理論[M].余匡復,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6]袁先來.德里達詩學與西方文化傳統[M].沈陽: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7]李明歡.Diaspora:定義、分化、聚合與重構[J].世界民族,2010(10).
[8](美)威廉斯.斯通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9](美)卡倫·霍尼.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M].馮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10]駱冬青.毒蛇[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