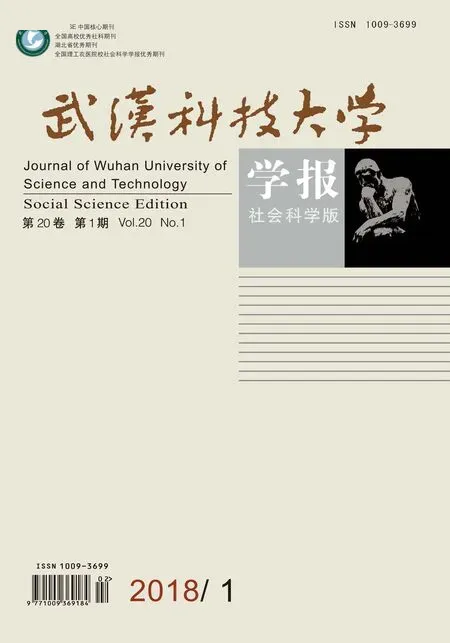儒家修、悟、證三境界說
——以顧憲成為主要考察點
李 可 心
(蘭州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中國哲學普遍重視道德問題,但道德二字與今天一般的意義不同。就儒家而言,孔子講“志於道,據於德 ”(《論語·述而》)。“道”是所志,是行動所應認識和遵從的基本原理或原則,“德”是所據,是對道的履行和成就。可以說,德無道不立,道無德不成。道德不是單純認識意義或單純行動意義上的問題,需要兼備認知和實踐兩方面的很多努力才能據有。修悟問題便是從對道德的追求中衍化出來,最終成為儒家學者討論道德實踐功夫的兩種基本形式。
一、由知行到修悟
修悟問題在魏晉佛教傳播時期已出現,但在儒家哲學中正式“出場”則很晚,大概到明代中后期才甚為顯耀。此前與修悟問題近似的是知行問題,知行問題屬本土哲學問題,淵源極久。因為知行與道德的實踐關聯密切,所以從一開始二者就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論語》里早就提出了所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和“困而學之”三種認知“道”的類型(《論語·季氏》),可見,對道的掌握開啟于對道的“知”,甚至,對于道在認知上的深入了解或洞見,就個體的生命意義來說,能夠起到根本性的改變作用,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但同時,《論語》又極為強調“行”的重要性,如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又如“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又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論語·子路》)等。此后在很長時間里,修悟問題一直未成為儒學的重要論題,即使在受到佛、禪影響比較大的兩宋理學中,也并未占有理論上的地位。在功夫論方面,宋代理學依然延續傳統的知行之論,并加以豐富的闡發。與此相應,格物致知、涵養用敬成為理學實踐的根本方法,并且貫穿整個宋明時期。以宋代心學而言,也不過強調發明本心和樹立主宰的重要性,與程朱理學在為學之方上,表現為“道問學”與“尊德性”兩種功夫入徑的差異。
關于修、悟,修的觀念在儒家經典里可謂俯拾皆是。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又如,子路問怎樣做一個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論語·憲問》),再如《大學》中“正心修身”“修身齊家”說尤為大家所熟知。悟的功夫則是一種比較具有宗教色彩的體驗,雖然不太為儒家所言說,但是在儒學中與“悟”相近的涵義不是沒有,如《論語·公冶長》中子貢云:“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又如《周易·系辭傳(上)》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由不知而知,由少知多,由一知全,這種短時間內發生的心智跳躍或義理通徹即為悟,可見,“知”本就包含悟的意義。《孟子·萬章下》中引述伊尹之言,提出“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覺”于是在儒家心性學說中具有了重要意義。孟子重視心之“思”的功能,認為“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這里的“思”不是一般的思維活動,而是對心性本然的認知或覺悟。“覺”和“思”,與后來所常講的悟的意義也約略相當。
修悟問題盡管蘊藏于我國傳統儒學的內部,但它直接出現并成為時代性的論題卻是在陽明學出現之后。陽明學以“良知”提宗,而良知學最本質的問題則是本體與功夫之間的分屬與通合關系。良知到底是屬于心的本體還是心體的作用;如果良知是本體,那么功夫從何而施;如果良知是心體已發的作用,那么功夫又當如何。這幾個問題成為明代陽明學聚訟的關鍵。而王陽明晚年所提倡的“四句教”,雖本意欲融合本體與功夫,使不落一偏,結果卻在其學生與后學當中加深了本體與功夫的對立。陽明區分利根之人與中下根人,認為“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而“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1]117。利根人的主要功夫就是悟,“其次”者“為善去惡”的功夫便是修。是從本體出發作頓的功夫,還是從發用著手作鈍的功夫,決定到為學的正確與否。所以,修、悟的優劣或關系究竟如何,便不得不成為緊迫的時代問題。由于“良知”的本性是自然、完全的靈明,“致良知”的要義在致良知的自然、本然之知,所以陽明后學往往偏重于強調良知的本體性而排斥功夫的人為性,以致言悟者多,修悟的正當關系被扭曲了。同時,這也在思想上和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對于陽明學的修正和批評自始不斷,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1550-1612)是比較卓越的有領袖地位的一個。在修悟觀上,他針對當世學風虛浮狀況,繼承學者如張元忭等比較平正的觀念,又吸收同時期講學者如鄒觀光、于孔兼等人有益的意見,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觀點。一方面他沒有拋棄陽明學中重悟的傳統,而是注意發掘傳統儒學中關于悟的資源,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忽視修的必要性,而是提高了修的地位。通過這兩方面的努力,他的修悟觀更加具有辯證、圓融的特性,豐富了修悟問題的內涵。顧憲成的修悟觀,帶有集成的性質,同時也充分體現了儒學本身不脫離身體實踐的特色,使儒學對修悟觀念的吸收和修悟矛盾的解決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修悟相即
修和悟都屬功夫,修、悟的對應也與本體、功夫的對應有關。一般認為注重本體的一路,其功夫主要為悟,而重功夫的一路則主要指修。純從本體出發者,主張對本體的“悟”或“知”,此乃陽明所謂“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這一派可以說是單以悟為功夫的,既悟之后,便無功夫(人為輔助性的功夫)。準確地說,悟其實還不是本體性的功夫,但經此一悟,便可轉入本體性的功夫。
據理而論,功夫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功夫,主要指人為的有目的性的功夫,旨在實現本體的完全;廣義的功夫,同時還包括本體性的功夫,這種功夫排斥人為的輔助性的活動,即陽明所說“本體上何處用得功”[1]119,本體的功夫實即本體的作用。一般所討論的本體和功夫,要以狹義的功夫居多,不少陽明后學所輕視的也是這種人為的目的性的功夫。
顧憲成反對玄談無根之學,講究一般意義的功夫,因此,他的著述和講學中對修給予特別的重視。但他也不是僅僅在救弊的意義上來看待功夫,他既講修,也反對不講悟,這一點正如他重視儒學之“實”,又反對專以“空”歸諸佛門,而大談儒學之“空”一樣。東林講學的參與者于孔兼(字元時,號景素)認為,“近世率好言悟,悟之一字出自禪門,吾儒所不道也”[2]393,把“悟”專門歸諸禪宗,排除在儒家功夫論之外。顧憲成不以為然,他舉經典為證,《周易·系辭上》有“神而明之”,《論語·述而》有“默而識之”,此皆言“悟”,“特未及直拈出悟字耳”。至于朱子,在解釋《孟子·盡心下》“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時,則曰:“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3]365又在解釋“先知先覺”時說:“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3]310顧憲成認為,這是朱子“明明道破”“悟”字之證。朱子雖平生不喜歡人張皇言悟,躐等虛矯,但其實也并不以“悟”為諱。因此,“悟”字“未可專歸諸禪門也,又不可以好言悟為世病”[2]393。
顧氏認為修和悟之間并不存在矛盾,相反,二者是相須為有不可或離的。他之強調修,也并不是遺脫了悟,或者認為悟不如修重要。在他看來,修和悟是辨證統一的,因此,他不但不反對世人“好言悟”,“據吾意,還病其好之未真耳”[2]393,其理由是:“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悟者與修相表里者也。”[2]393顧憲成提揭修字,與世俗言修而惡悟者不同,他并沒有執一廢一,而是把修和悟貫通在一起,在重修和重悟之間,不以一端自居。他說:
學不重悟則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為輕者也,何也?舍修無由悟也。學不重修則已,如重修,未有可以悟為輕者,何也?舍悟無由修也。[2]338
在修悟之間,單純的重修或重悟,不僅是片面的,而且是錯誤的。修和悟互為前提,必然要通過修方能悟,也必然要通過悟才能實現修,失去了彼此為前提,二者都將無法落實。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修悟雙提”呢?顧氏認為:“悟而不落于無謂之修,修而不落于有謂之悟。”[2]338依照上面這一詮釋,修悟在本質上就是一致的:悟即修,不落于無之悟便是修;修即悟,不落于有的修便是悟。修悟是對同一內容作出的不同衡量,二者是一體之兩面。顯然,修悟是融合在一起的,較之“修悟雙提”的說法,要更進一層。“雙提”有并重之意,或猶保留著修、悟之間的對立,而顧氏的說法,已經是合一之并重,修悟已經不存在對立。也正是如此,“即修即悟,無所不檢攝而非矜持;即悟即修,無所不超脫而非放曠”[2]130。那種認為修就必然意味著會過于矜持把捉,悟就必然會流于放縱超脫的看法,都是執一的、片面的,沒有理解修悟的辨證關系。
就朱子和陽明的教法來說,顧憲成認為,朱、王二子的教法與二人的性格有關。朱子平而精實,陽明高而闊大,所以朱子是“即修即悟”,而陽明則是“即悟即修”[2]294。朱子的“即修即悟”實指“由修入悟”,陽明的“即悟即修”實指“由悟入修”,這代表了修悟之間可能存在的兩條路向。顧憲成在《日新書院記》中,對兩種教法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闡發。他認為,兩種教法是“同而異”、“異而同”的關系,一種“善用實”,一種“善用虛”,二者都屬于儒家的圣人之學,最終的歸趣并無二致。并且這兩種教法的并存有其必要性。“同而異,一者有兩者,遞為操縱,其法可以使人入而鼓焉舞焉,欣然欲罷而不能。異而同,兩者有一者,密為融攝,其法可以使人入而安焉適焉,渾然默順而不知”[2]152。兩種教法既可以相互補充,使人人都能夠因之獲得相應的門徑,又可以相互救正,挽回彼此容易導致的流弊。
三、修悟之時序
修悟的關系,不應當只是渾然一體,空講所謂修中有悟、悟中有修,一味圓融,這其間還應強調一定的次序。《論語·公冶長》中記載,孔子問子貢其與顏回孰賢,子貢以“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答之。此中“一”“二”“十”不是簡單地表示數量的多少,“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地圓缺之辭”[2]318。陽明認為:“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1]32顧憲成進一步指明:“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2]318“了悟”指心地上的透徹,“影悟”即指聞見上的知解。此時孔子不直接說破“一以貫之”之旨,而必待于后,顧氏認為,“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恨不立地成圣,卻亦忙不得”,其間有個“時據”[2]319。這說明,悟應以一定的功夫積累為前提,如果功夫未作到相應的程度,悟是不適宜驟然講求的。
近似的還有另一個事例。孔子曾直接對曾子講:“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陽明認為:“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1]32并且,他還認為,“一貫”是根本,是體,“體未立,用安從生?”[1]32由此,陽明指出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所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3]72,解釋還不準確。顧憲成持不同看法。他認為,曾子平日潛心于忠恕,不能說“未得用功之要”,于孔子則“隨呼隨唯”,也不能說“未知體之一”[2]302-303。《四書章句集注》中說“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3]72,顧憲成認為這才是恰到好處的理解。孔子之所以直接點化曾子,正是因為曾子已經“真積力久”,功夫做到適宜的程度,將悟未悟,故下語來啟發他。功夫達到了,分寸適宜,便有致悟的必要。
由此二例可知,在顧憲成看來,言悟必有“時據”,這個“時據”具體就是指功夫的積累,亦即修。從修到悟之間,是不斷修的過程。這種觀點其實也是朱子的基本主張。朱子在《補格物致知傳》中說:“《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3]7這里的“豁然貫通”即“一以貫之”,意味著實現了“悟”的環節。朱子認為“豁然貫通”之境的實現,必以“用力之久”為基礎,而“用力之久”就自然會有“豁然貫通”之時,亦即他是主張以修致悟的。當然,朱子的功夫主要是廣泛的格物致知,運用上或偏在“知”或明事物之理一邊,而陽明學及顧憲成所言的功夫主要指內心體驗的修證。
我們還可以從顧憲成與友人討論程子《識仁說》中,更清晰完整地獲得他對修悟層次關系的說明。程顥言“識仁”,孔子言“為仁”,顧氏認為:“第‘為’以修言,‘識’以悟言。為則功夫便在眼前,行住坐臥,無一刻可違。悟則須是這功夫積累到久,忽然透岀。”[2]346這一意思與上所言相同。他同時認為,“及其得之又須密密保任,方有受用”[2]346,既悟之后也還要“密密保任”,悟后同樣不能丟棄功夫,不能就此“歇手”,還應不間斷地繼續做功夫。如此,“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悟境也。自一日之前至一日之后,卻只是一個修,更無別法”[2]346。悟之前和悟之后都需要功夫,也就是說,有悟前之修和悟后之修。悟前之修,因本體未透,所以是著力之修,須自強不息,“此在初入門便應著緊,無容些子含糊”[2]346。悟后之修,因已透徹本體,從本體發為功夫,一方面會自覺功夫“無可歇手處”[2]311,一方面又不必著意為功夫。然而此種“得力”“有非初入門可躐希者”[2]346。因而,顧憲成對程子《識仁說》作了兩點補充:至悟(識仁)之前,要“欲罷不能”,有所為而為;既悟(識仁)之后,要“欲從莫由”,無所為而為。
總的來說,“未悟則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2]393,“有修無悟,必落方所,非真修也;未修求悟,只掠光景,非真悟也”[2]346。悟必有修,修必求悟;悟前必修,悟后必修。悟前之修,修悟乃相須而非相即;悟后之修,修悟乃相須而可相即。如此,就修、悟的關系,我們在相即不離的基礎上,就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顧憲成雖然強調修悟的相即關系,肯定朱、王二子的教法有必要并行,其實,他的說法更突出的是修的在先性、修的累積性以及修的一貫性,而反對未修言悟,悟后便放手不修。因此,就基礎來說,他的修悟觀與他所認為的朱子之“由修入悟”更加符合。當然,如果說朱子的教法是“由修入悟”,陽明的教法是“由悟入修”,而顧憲成悟前“由修入悟”,悟后“由悟入修”,也可以說是朱、王教法的一種接合。
陽明學內部,比較平實的學者,對于本體和功夫、修與悟的關系,自一開始可以說是比較注意全面把握的,作了不少質難辨析的工作,其中,以陽明的同鄉張元忭最為突出。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1538-1588)“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四有教法”[4]323,實際上,由于王龍溪(名畿,字汝中,號龍溪,1498-1583)談本體而諱言功夫,因此他對龍溪之學進行了批判。當然,張陽和的批判并不僅僅針對龍溪,如他還明確批評羅汝芳的弟子楊起元,認為他也是“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為識得本體便是功夫”[4]326。張氏認為,這是當時陽明學傳播中存在的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仆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4]327
張氏與當時著名學者羅汝芳、許孚遠、周汝登等都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憂時、救時的心情十分迫切。就修、悟的關系,他說道:
悟與修安可偏廢哉!世固有悟而不修者,是徒騁虛見,窺影響焉耳,非真悟也;亦有修而不悟者,是徒守途轍,依名相焉耳,非真修也。故得悟而修,乃為真修,因修而悟,乃為真悟。古之圣賢所以乾乾惕若,無一息之懈者,悟與修并進也。[5]17
張氏的說法已經與顧憲成的某些表達基本相同了,可謂就是上文所述“修悟雙提”,他認為修、悟應當并重,兩樣應該結合在一起。但我們可以看出,張元忭的說法,較顧憲成在修、悟上的整體觀點還是少了曲折、細膩和圓融之處。
顧憲成三十多歲在吏部供職時,曾與張元忭有往來,他對張氏的評價很高,很希望他能夠為世所用,并且自謂“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2]314。張陽和對陽明學的流弊作了很有力的批評,他的修悟之說,不入“偏處”,在陽明學中很有特色,顧憲成的修悟之見很可能受到他的影響。
四、修、悟、證三境說
顧憲成的修悟說,并不以修悟二項為全義,他還有第三境,即證境。孔子有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論語·述而》)顧憲成認為:
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修也;誨人不倦,言證也。[2]283
他以悟、修、證三境對言,并不是偶爾一及。對《論語·為政》“十有五而志于學”章,顧憲成也作了如是分析,他說:
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2]347
在這里,顧氏很明確地認為,由修而悟,由悟而證,這是入道的正當次序。證境是最高的境界,悟境并非最高境界。就孔子的證境來說,主要是指孔子“耳順”和“從心所欲不逾矩”兩階段。
據常情看,“知天命”是神化上事,“耳順”、“從心”是自家身子上事,兩者較之,“知天命”似深,“耳順”、“從心”似淺。[2]348
一般認為,人生的意義主要是領悟最高的原理,或者說是悟道。人們通過不斷修行,一旦領悟到終極的原理,超越了自身的限制而得到心靈的解脫,就算是圓滿了,達到目的了。如此,“知天命”未嘗不可說已經達到了最高境界,但孔子不以“知天命”為止足,還要“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天命之知回歸到身心的順適。
顧憲成認為,“知天命”僅僅是對“天命”的一種感悟,或者是一種思想上的透徹,所以很可能只是停留在觀念中,還談不上真正的天人合一。“說個天命似涉渺茫,吾夫子定要一一自家身子上打透,方肯作準。蓋渺茫處可假,自家身子上不可假”[2]348。在他看來,“知天命”不僅只是知解上的知,更是身心上的實體(實際體得義),從知解到實體,還需要有一個過程。可見,他所謂的“證”,就是證上身來(“自家身子上打透”)。證已經是悟后的境界,不再是求悟,不再重知解,而是重實體,重行為與知解的自然合一,要“即形即天命”“即心即天命”[2]348。總之,到悟的境界,雖然涉乎凡圣之界,幾近生死之關,但尚屬玄虛,未為真得,只有達于證境,才可謂徹底著實。
顧憲成在分析程顥的《識仁說》時,又提出“化境”之說:
大都程子此篇,專要與人點出悟境,又要與人點岀化境。故說得如此直截,更不拈動第二義,防檢、窮索,盡與破除。若為求識仁者言,恐應自有說也。[2]382
顧憲成認為,程子的《識仁說》是承接著張載的《西銘》而來,所以起首便從很高的境界講起,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6]16-17。“識得此理”,即顧氏所說“要與人點出悟境”,而“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為“化境”。在化境之中,可以不必再強調功夫,而本體自然實現,“更不拈動第二義”,一切言筌、教條都用不著了。
證境強調身體的實行、實得,強調身心與天命天理的繼續磨合,而化境與證境相比,這些都已經完成了,體用合一已經實現,行為完全出于自然。因此,化境要比證境更高,是一種境界的完成狀態,或者說,化境是證境的證得狀態。證境之證,有二義:一是求證,二是證得。尚保留功夫的必要性的境界是求證之證境,不用提起功夫的境界為證得境界。這樣證境、化境未嘗不能夠統一,我們可以把化境歸入證境。
其實,顧憲成在修境、悟境基礎上又提出證境一說,十分容易理解。上文我們對他修、悟的層次關系已經明了,即修—悟—修,他認為有悟前之修,有悟后之修,修是不間斷的。對悟前之修來說,很顯然即為用力作功夫,要特別提撕,而且是以求悟為目的的,這可以說是一種純粹的修;對悟后之修來說,雖然用功,卻已經是解悟了本體后的用功,高度自覺,其功夫也不再指向本體之知,而是指向本體之合,這種求合本體的功夫,即可以說是證。如此,顧氏的修、悟觀念里不但有層次,而且不同的層次還有相應的不同意義。
顧憲成的友人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1551-1624,)也明確標舉修、悟、證三種功夫境地。鄒氏師從胡直(字正甫,號廬山),為陽明的三傳弟子。他在給老師遺稿所作的序文中,對修、悟的關系作了闡發:
學以悟為入門,以修為實際。悟而不修,是為虛見,修而不悟,是為罔修。先生已洞然圣學之大,而復與困學同功,茲所以全而歸也。[7]卷四
他認為老師“已洞然圣學之大”,即指能悟言,“而復與困學同功”,即指能修言。鄒氏也是強調修、悟的相須關系的,在他看來,只有既悟且修方才稱得上得圣門學問的全體。
鄒元標罷官居家,請于當道,建立仁文書院,為講學之所。他在所作《仁文會約語》中,標舉教法:一則曰“先悟”,一則曰“重修”,一則曰“貴證”[7]卷八。他認為,修和悟并不是兩回事:“悟者即悟其所謂修者也,以悟而證修,則不沮于他岐之惑;修者修其所謂悟者也,以修而證悟,則不涉于玄虛之弊,而實合內外之道,二之則不是矣。”[7]卷八對于證,他則說:“證者,證吾所謂悟而修者也”[7]卷八。他的證處于悟和修之間,所表示的是修和悟之間的一種約束關系,具體而言,證就是要以悟來證修,以修來證悟。證是對修、悟二者的檢驗和印合,亦即修要以悟為原則,悟要以修為歸宿,如是,修才不會誤入歧途,而悟也不會停留于玄虛。
鄒元標的修悟觀與顧憲成的差別很明顯,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功夫的起點不同。顧憲成強調要以修為起點,悟前有修,悟后有修,一以貫之;鄒元標則明確主張要“先悟”,把悟當作為學的“入門”,提倡“學必先悟”。其次,顧憲成所講的證是在悟后,與修和悟相比,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階段;而鄒氏的證并不特指獨立的功夫階段,而是對修、悟關系的一種雙向規定,悟中有證,修中也有證。再次,顧憲成的證是逐步深入的修,其具體內涵就是實體,這種實體包括人的身(形體)心全部,身心都要符合事理的規范,并不單以心言;而鄒氏之證完全是指心證,他說:“夫吾所謂悟而修者非他,即吾之心也,所謂修者非他,亦吾之心也。”[7]卷八相比之下,鄒元標是很鮮明的心學立場,而顧憲成與他的距離比較大。
五、躬行立教
對于顧憲成“證”之一境,尚有一義待發。顧氏在吏部時的同僚鄒觀光(字孚如),里居講學,建尚行書院,弟子請教憲成“尚行”之意,憲成認為,“鄒子之標尚行,正悟后語也”[2]139。這是因為,當人未悟之時,對于實行缺少動力,或誘之而行,或迫之而行,都屬于勉強為之,結果可能或作或輟。只有既悟之后,人才能從內心中生發動力,認識到行的必要和迫切而自覺去行,以行為尚。對于世間以悟為尚的人,顧憲成指出應當“歸而證之于行”[2]139,所自矜以為悟者一定要“一一實有之”方才無憾,方能最終躋于圣賢行列。如果沒有做到,那么,其自我矜許的悟境就不過是“揣摩億度而已”。“尚行”之說,既可以適用于“未悟者”,也可適用于“已悟者”。“未悟者尊而用之”,可以漸漸致悟,“已悟者尊而用之”,可以一一實有諸身,所謂“淪肌膚而浹骨髓”[2]140。
顧憲成最終提出:“然則悟于何始?因行而始。悟于何終?因行而終。”[2]140這與上文他所說“未悟則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用意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同樣還可以看到,顧氏強調悟后之行,依然是指“一一實有之”,這也是上文所說的“證”義。“證”和“行”的意義有所不同,“證”的意義比較含蓄,也容易發生歧義。“證”可以專指心證,如鄒元標所謂,而“行”就比較平實和明確,如果使用“躬行”一語就更加明確。顧憲成所謂證,我們上文以“實體”解之,實際就是“躬行”二字,行之于身,亦即體之于身(含心在內),而這里顧憲成所指的“行”確實就是“躬行”。
鄒觀光著《衡言》,其中發明躬行在當時的特別意義,他說:“今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堯舜,而議論愈精,世趨愈下。維世君子惟以躬行立教,斯救時第一義乎!”[2]139顧憲成對“躬行”二字佩服不已,謂先得同心,感慨極深,“為之徘徊三復,不能已已”[2]64。顧、鄒二子早年為官同處,都懷有很大的抱負,“生平之交,相期于徳義”[2]46,二人的情誼是比較長遠且深入的,因此,顧憲成在躬行觀念上,肯定受到了鄒觀光的影響。
顧憲成眼中的躬行并不是“專屬諸修”,尤其不是僅僅指“事為之檢飭,念慮之矜持”。他認為,這樣就“墮落方所而修弊”[2]396,這樣的修,必然會引起高明者的輕薄厭棄,轉而重悟,走向相反的極端。因此,他的躬行不是拘檢的,不是落方所的,偏指悟后之行,亦即“證”。
影響顧憲成躬行觀念的另一人物為共同講學的于孔兼。在戊申(1608)年春的南岳會講中,于景素告誡顧憲成:“兄主盟東林,只宜守定‘下學上達,躬行君子’八字。”憲成為之“點頭”[2]393。歸后,吳安節、于景素各作《春游記》一篇,于景素在文章中大抵發明“躬行”之義。二人之文,顧憲成讀后頗多感會而道:“私衷尤有味于‘躬行’一語。”[2]396此處他對躬行有新的體會。他認為,為學的“入門要指,入室微言”,“經孔孟發揮一番,已而又經周程諸大儒發揮一番,已而又經陽明諸先正發揮一番,業已說到九分九厘九毫,向上幾無復開口處,算來算去還是躬行難也”[2]396。照他的意思,為學的方法和道理,先圣先賢已經差不多說到頭了,指點得明白而周全了,后人沒有多少可以發揮的余地,所以可以不必再在上面糾纏不休,更實際而有意義的事就是照著去踏實地做。對于后人來說,躬行才是真正困難而具有考驗性的事。
這種觀點也早有淵源,明代早期的理學家薛瑄就曾說過:“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但須躬行耳。”[8]7229如又說:“將圣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4]117可見,薛瑄也是認為道理已明,不用再殫精竭慮去作重復無謂的發揮,并且他特別反對將學問僅停留于談說上,主張一定要切實躬行。這種學風,實際就代表了明代以后的思想動向。
容肇祖先生在他的《明代思想史》一書中,對這種變化已經揭示得比較清楚了。他認為明代初期的思想有承接宋元儒而來的“致知派”,這一派繼承了朱子格物致知的理念,學問規模廣博,義理精深,與朱子為同一血脈。從宋濂到方孝孺,沿襲了致知派的風格,然而這派此后逐漸衰落,朱子學中的“躬行派”(或稱“涵養派”)逐漸崛起。容肇祖先生認為,這一派與“致知派”的學者“大不同了,就是簡陋了,腐化了,依托于復性與躬行,而不事著作不做學問了”[9]13。
容先生固然道出了躬行派的特征,與朱子學的本來風格不同,但對于明代思想來說卻無疑是新的生機,也是明代思想的獨特靈魂。這一躬行特征逐漸流衍,發展成以注重自我和內心體驗為特征的心學大宗,完成了宋學到明學的蛻變,這是一次很重大的歷史性的思想動變。而朱子學的躬行派也自有流傳,主要為薛瑄所流傳的河東之學,其中以呂柟(字仲木,號涇野)為代表。
呂涇野認為,學“若徒取辯于口,而不躬行也無用”[10]123,不實行的學問,人于其自身終究缺少受用之處。因此,“學要講明做去”[10]123,“君子以朋友講習,不徒講之而又習之也,習即是行”[10]110。他的學問可以說不出程朱知行的范圍,知了去行,猶是程朱知行的本色,只是于躬行特別著力。黃宗羲謂:“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4]11
明代關學是以躬行著稱的。其實甘泉學派也是注重實際體認的。如湛甘泉的學問宗旨為“隨處體認天理”,“體認”便帶有很強的實踐意味。其再傳許孚遠,進而明確提出“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尚知解,而尚體驗”,“學者之學,重實修而已”[4]975。甘泉學派本不如陽明學之欲脫盡朱子的影響,而為朱子學和心學的一種折中。因此,我們還可以說這是朱子學中的“躬行派”,只是比明初儒者走得更深遠,是明代思想的主流之一。當然,明代的這些學派之間也都存在著交流。
因此,顧憲成之所以認可躬行,有著深厚的時代背景。有趣的是,明代自生的學術起于躬行,卻在躬行、體認中又迷失了,到了后期又重新號召躬行。
六、結語
哲學的要義無疑以尋求智慧為本,然而這種智慧不獨指向理論智慧,還自然乃至應當包含實踐智慧,中國哲學尤其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在儒學內部,知行問題自始就存在著,而且有著非常明確樸素的意識。一直到兩宋理學,知行問題也還作為一個重要的論題得到進一步的深化。然而,隨著宗教思想更廣泛的滲透,陽明良知學的出現和大發展,知行問題逐漸被修悟問題所掩蓋,對修悟關系的討論甚囂塵上。修悟問題成為關系儒學自身性格特質、為學方法等一些重要問題的基礎性問題,對修悟問題認識上的偏差,對其關系處理不夠妥善,往往會引發嚴重的流弊,貽害于世道人心。有識之士站在儒學本位的立場上,面對洶涌的時代思潮的惡化,積極作出不少化解危機的努力,顧憲成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顧憲成對修悟問題作了深入細致的考察疏導,也對前人時賢的相關思想給予了不少吸收,他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是比較完善的,帶有總結和集成性的。他提倡修悟相即,這種修悟相即不但是互補的,而且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不落于有的修即悟,不落于無的悟即修,有別于修悟雙提。但他的修悟相即說也不是混論調和的,而是在相應的時序當中來辯證地看待修悟關系。就一般的修悟關系而言,顧憲成又突出證境一環節,證境是悟境的延續和提高,是道理與身心的真正融合過程。證境的終極是化境,而證境的實現有賴于躬行。躬行強調親身實體,是儒家性格的真摯體現;它也并不專屬于修,而是一貫的自我修養功夫。對于反己實證、躬行實踐的追求,是明代儒學的根本特色。
宋代的理學開辟了一個崇高的理的世界,辨析理義,窮其精微,而明代的學者則又開辟了一個豐富的內心體驗的世界,這個世界既現實而又神秘。理學在宋代的晚期才成熟起來,而心學則在明代的晚期即露出了極大的幻相,因而,引起有識者向躬行的回歸。明代思想的起承轉合,已經到了合的地步,也預示著要走向尾聲了。
[1]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顧憲成.涇皋藏稿[M]∥無錫文庫第四輯影印.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 黃宗羲.明儒學案: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8.
[5] 張元忭.張陽和文選[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6] 程顥,程頤.二程集: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1.
[7] 鄒元標.愿學集[M].四庫全書本.
[8] 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9]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M].上海:中國書店,1941.
[10] 呂柟.涇野子內篇[M].北京:中華書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