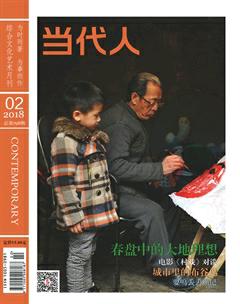春盤中的大地理想
安春華
2月4日,立春。初日曈曈,清寂了一個冬天的大地汩汩熱力悄悄漫上來,土坷垃底下的小草挺挺身子換上一件新綠的衣裳,路邊饅頭柳一串串柳眼也點亮了。人家的后園里,留冬的香蔥頂出可愛的羊角,菠菜潑撒了新肥,黃韭正嫩,青蒿正香。眼瞅著,青蔬撒歡兒瘋長,把人的胃、人的心都給招惹饞了。
是誰說,“食物里的鄉(xiāng)愁全是因為饞”。這一個饞字,也饞得有理呢。為了迎接春天的到來,早在唐朝就有了“咬春”的講究。唐《四時寶鏡》記載:“ 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菜盤。” 杜甫《立春》詩曰: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fā)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從詩中可見,安史之亂以前,長安洛陽一帶的立春日熱鬧而歡樂,而這份熱鬧和歡樂,竟是少不得春盤這個“道具”的。到了宋代,因了蘇東坡等一干酷愛美食的主兒,屬于春天的關(guān)鍵詞,更是無“盤”不歡了。“黃耆煮粥薦春盤”“蓼茸蒿筍試春盤”,在善于苦中作樂的老先生這里,不管黃耆蓼茸蒿筍,裝到盤子里就是菜,就是春天。
而南宋詩人方岳的詩《春盤》,則結(jié)結(jié)實實透露了古人在春天里到底吃的什么菜:
萊服根松縷冰玉,蔞蒿苗肥點寒綠。
霜鞭行茁軟於酥,雪樹生釘肥勝肉。
與吾同味蔊絲辣,知我長貧韭俎熟。
更蒸豘壓花層層,略糝鳧成金粟粟。
青紅饾饤映梅柳,紫翠招邀醉松竹。
擎將碧脆卷月明,嚼出宮商帶詩馥。
賜幡羞上老人頭,家園不負將軍腹。
人生行樂未渠央,物意趨新自相續(xù)。
五十三翁日落山,三百六旬車轉(zhuǎn)轂。
不妨細雨看梅花,且喜春風(fēng)到茅屋。
不過,除了“萊服”為蘿卜、蔞蒿為“蘆蒿”之外,對于別的林林總總的菜名或野菜名,詩人裁紅暈碧搞的這一大桌子豐盛菜肴,多數(shù)人只能看得一頭霧水。不管怎么說, “青紅”“紫翠”,鋪陳堆疊,分外妖嬈。
時空切換至當(dāng)下,設(shè)施菜、錯季菜,南菜北運,西菜東運,再加上漂洋過海的“洋”菜,餐桌上一年四季倚紅偎翠、春意盎然。春盤天天可以有,“咬春”天天相遇春。然而,與古人相比,我們的餐桌、我們的春盤似乎總是缺少一樣?xùn)|西。我們內(nèi)心的需索與大地的供養(yǎng)之間,總還是有那么一截落差。
我們要找什么,春盤里的安全、春盤里的健康、春盤里的豐饒、春盤里的詩意?
我們所找尋的,正是大地所努力的。在早春,在河北初暖的土地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擔(dān)當(dāng)大地理想,為新時代的春盤巧手裁紅、匠心暈碧。
李志彬:專種人們沒見過的菜
滄州青縣司馬莊村的李志彬,對普通蔬菜不 “感冒”,他愛培育各種“稀奇古怪”的菜。隆冬時節(jié),他除了接待冬季采摘的游客,還忙著張羅春節(jié)前高檔蔬菜禮品箱的備貨和運銷。
這些很少見的、價格很貴的菜,業(yè)內(nèi)稱為“特菜”。比如“冰菜”,是李志彬托人從非洲捎過來種子,在溫室培育成功的,它肥嫩的葉片背面溢出點點汁液,凝結(jié)在那里,如同掛滿了晶瑩剔透的露珠。“這種菜口味咸鮮,口感綿軟,涼拌或涮鍋吃都行,入口就化。”李志彬告訴筆者。這種冰菜,這里的售價達到了20元一斤。
進入李志彬農(nóng)業(yè)合作社的蔬菜大棚,仿佛就進入了一個特菜博物館:栗子味的南瓜、香蕉味的西葫蘆、日本的蘿卜、美國的蘆筍、漂亮如盆景的不包心的甘藍、狀如佛頭的“翡翠寶塔”菜花……粗略算來,葉菜達到一百多種,果菜也有四五十種。
回望十幾年的發(fā)展路,剛開始李志彬?qū)τ诜N什么菜,思路并不是特別明確。1998年,司馬莊村響應(yīng)上級號召,發(fā)展設(shè)施蔬菜,由村集體投資建設(shè)青縣司馬莊無公害蔬菜高科技示范園。由于采取“大鍋飯”的管理形式,園區(qū)連年虧損,2003年,為擺脫虧損局面,村委會決定園區(qū)對外承包,李志彬與其他5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包下了園區(qū)。之后,他去山東、遼寧,考察設(shè)施蔬菜生產(chǎn)及市場情況,思索擺脫虧損的對策。當(dāng)時,全國各地都掀起了設(shè)施蔬菜生產(chǎn)的熱潮,他發(fā)現(xiàn)各地盡管設(shè)施類型不同,但是種植的品種基本相同,基本以大眾菜為主,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腦海里誕生了:獨辟蹊徑,種特菜,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在他的主持下,合作社注冊了“大司馬”蔬菜商標,開始了特色蔬菜種植。
種菜難,種特菜更難,原因很簡單,沒人種過,沒有經(jīng)驗。面對技術(shù)難關(guān),李志彬一方面積極請教中國農(nóng)科院、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等農(nóng)業(yè)科研院所教授,一方面勤于觀察實踐。為掌握特菜生長規(guī)律,他干脆吃住在棚里,晝夜守在菜畦邊,夜間不知道起來多少次,打著手電筒觀察蔬菜生長情況。硬是憑著一腔創(chuàng)業(yè)的激情,掌握了各種特菜的種植技術(shù),特菜種植逐步走上了正軌。
現(xiàn)在,李志彬的合作社就是一個特菜“橋頭堡”。他不怕別人跟風(fēng)、模仿,因為合作社經(jīng)過多年努力,與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河北省農(nóng)林科學(xué)院、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guān)系,“他們有什么新品種就推過來,在我這兒試種。”合作社的土地,成為新種子落腳第一站。李志彬告訴筆者,十幾年來,合作社試種過的菜,僅黃瓜就有600多種了,“長出來之后,我們選擇那些口感好的,保留、推廣。”
與品種創(chuàng)新同步進行的是技術(shù)創(chuàng)新。無土栽培、節(jié)水滴灌、蜜蜂授粉、植物源農(nóng)藥……這里也是新技術(shù)新設(shè)備的試驗場。“給草莓授粉用小蜜蜂,給根莖類植物授粉用雄蜂,當(dāng)然我們也不排斥電動授粉器,關(guān)鍵是看效果。”李志彬?qū)Ω鞣N新東西都敞開懷抱接納、試驗。
在種出特菜以后,怎么賣出去,讓市場認可這些價格不菲的菜,又是擺在李志彬面前的一道題。為了促進銷售,合作社在園區(qū)建了自營飯店,烹調(diào)各種自產(chǎn)蔬菜,還推出了蔬菜宴。一桌子五顏六色的新鮮蔬果擺上來,每人面前一小碗醬,先蘸醬生吃,或品嘗涼拌,最后涮鍋。這種宴席別處沒有,游客嘗了哪種好,難免順手買回去一兩箱送給親友,由此,蔬菜禮品箱銷售也就帶動起來了。2016年合作社銷售特菜15萬箱,總收入達到4230萬元,實現(xiàn)利潤1200萬元。同時帶動起本村140余戶村民以及周邊三個鄉(xiāng)鎮(zhèn)60余個村1200余戶村民從事特菜種植,特菜種植面積已發(fā)展到1萬多畝。endprint
從2013年開始,合作社還做起了休閑旅游項目。這里緊鄰京杭大運河,運河邊上一塊幾百畝的天然濕地,與運河水地下暗通。種什么也種不了,以往就是一塊廢地,合作社將它清理疏浚,取名“運河湖”。大運河風(fēng)光及河邊波光粼粼的湖水,都為前來采摘的游客提供了新的觀光體驗。目前,合作社與天津宇航國際旅行社、北京華宇假日國際旅行社、周末去哪兒玩網(wǎng)絡(luò)媒體、滄州好地方旅行社、滄州市第二幼兒園等單位建立了長期合作關(guān)系,2016年游客接待量達到30萬人次。
下一步,李志彬想在北京開一家大的蔬果食品店,讓大城市的消費者能夠直接嘗到、買到青縣的菜,甚至也包括整個滄州的特產(chǎn)。
張沛君:大規(guī)模“馴化”野菜
現(xiàn)居石家莊、老家在辛集市的張沛君,這些年專注于“馴化”種植野菜。許多在我們童年記憶里純粹是用于“喂豬”的菜,都被他端上了餐桌,而且他會一臉嚴肅地告訴你:吃點野菜,對身體好。
走進張沛君的野菜公司,辦公室文員會給每一位來客捧上一杯熱乎乎的蒲公英茶。也不難喝,不苦,不澀,略有清香,這是我的第一感覺。“平時嗓子疼了,連著喝兩天這個水,不用拿藥也能好。”張沛君告訴我。
說起來張沛君是地道的文化人,河北省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會的常務(wù)副會長兼秘書長,《環(huán)渤海詩歌》總監(jiān)。他開廣告公司,在井陘仙臺山經(jīng)營賓館,閑暇時常約朋友上山玩。替他看著賓館的老母親,每每從山上挖些蒲公英,做成菜給大家吃,“沒有反映不好吃的。”
這啟發(fā)了張沛君,為何不搞野菜種植呢?作為60后的張沛君,小時候不是沒吃過野菜,麻生菜(馬齒莧)、曲曲菜、敗醬草、豬毛菜等,春天缺菜的時候,隨手從田間地頭薅幾把回去,做法只有涼拌,那時沒有肉味去燉它們,“只知道能吃,沒覺得好吃。”2005年,張沛君托母親從仙臺山采集了一斤蒲公英種子,撒在辛集姥姥家的蘋果地里,當(dāng)時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想賣野菜,如果賣不出去,曬干當(dāng)成藥材也浪費不了。
村里人是不理解的,因為農(nóng)村沒人吃野菜,都說這不是喂豬的嗎?第二年以后,村里人觀念漸漸轉(zhuǎn)變。何以見得?有人進園偷菜。張沛君把園子圍起來,同時暗暗笑了,“有人偷,說明有人認了。”
野菜并不好種,它在野地里時,只要溫濕度合適就瘋長,但是把它栽到大田或大棚里,它卻未必按人的意愿來。“比方說薺菜這東西,溫度超過20度就開花,然后就干死了。我第一次種了3畝,只包了一頓餃子,再去摘時,全開花了。沒辦法只好收獲了種子。”張沛君遇到困難就請教河北省農(nóng)林科學(xué)院的專家,經(jīng)過不斷學(xué)習(xí)探索,幾年下來,摸清了多種常見野菜的“脾性”,并實現(xiàn)了輪作,做到了不間斷產(chǎn)出。
為保證野菜的“綠色”“無公害”,張沛君不用除草劑,他雇人鋤草,一個工男的每天80元,女的每天60元;他以豬糞雞糞為肥,只在野菜長得快不行了時才用一點化肥;對付蟲子,他只用生物農(nóng)藥,還嘗試噴過辣椒水、漚煙葉水……做了各種試驗。
張沛君開著一家包子店、兩家餃子店,主打食材全部用自產(chǎn)野菜。“幾千年來,野菜之所以沒被培育成蔬菜走上餐桌,是因為它們多少都有點兒缺點,口感差。我會努力把它做得更好吃。”在張沛君的飯店里,廚師對各種野菜大展身手,筋道有嚼頭的干野菜搭配五花肉來燉,剛摘的鮮野菜涼拌、蘸醬或爆炒,干或鮮野菜剁碎做餡……同時店內(nèi)有包裝好的干鮮野菜供客人帶走。越來越多的客人在他的引導(dǎo)下,嘗試起野菜養(yǎng)生。
張沛君常給客人推薦的是四種野菜:馬齒莧、蒲公英、薺菜、養(yǎng)心菜。它們都屬于藥食兩用植物,都有明確的保健功效,比如降糖、抗癌、降三高等等。在糖尿病發(fā)病率很高的當(dāng)下,張沛君尤其注重了降糖野菜的種植。
2015年,張沛君和弟弟合伙注冊了野菜公司。這中間還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為野菜種植銷售沒有形成行業(yè),國家工商總局的名錄里沒有,當(dāng)?shù)毓ど滩块T提議按蔬菜或食品行業(yè)來注冊,張沛君沒有聽從,他堅持要叫“野菜公司”。后來,工商部門多次開會研究,終于特批了“野菜公司”。經(jīng)營范圍包括:野菜種植、銷售、深加工。
去年張沛君的野菜公司年營業(yè)額為150多萬元。由于種植成本高,廣告投入大,他的公司“目前仍處于前期投入階段”。下一步,他打算發(fā)展100家野菜包子(餃子)加盟店,并把野菜制成茶,比如蒲公英茶、養(yǎng)心茶、薄荷茶、紫蘇茶、秋葵茶、紅薯葉茶等,把全麥面粉加上馬齒莧粉做成降糖主食,把鮮野菜做成真空包裝小菜出售。
劉瑞平:建起蔬菜“育兒室”
邯鄲市曲周縣曲周鎮(zhèn)東牛屯村。劉瑞平對于早春大地迎來第一縷新綠,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感覺。因為在他的溫室里,一年四季都是綠的,時時刻刻都有種子萌芽。眼下,他正密切關(guān)注著溫室里茄子、黃瓜、西紅柿等蔬菜小苗的發(fā)育情況。作為一名專業(yè)育苗者,育苗合作社的老板,他可稱得上是點燃田野的綠色、染綠農(nóng)家菜園的人。每年,6500萬株小苗從他的工廠走出,走進周邊鄉(xiāng)鎮(zhèn),走進永年、肥鄉(xiāng)、廣平、雞澤、涉縣、臨漳,走到邢臺、石家莊、山東、河南、山西……又經(jīng)過不知多少農(nóng)民的雙手侍弄,最終長成一棵棵菜、一架架瓜,并走上無數(shù)人的餐桌。
傳統(tǒng)的蔬菜種植方式,農(nóng)戶從撒籽開始,全程管護,但劉瑞平將播種育苗這個環(huán)節(jié)單獨拿出來了。因為這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影響種菜收益的一個關(guān)鍵。
十幾年前,劉瑞平本是種業(yè)經(jīng)營公司的小老板,用俗話說就是賣種子的。2005年冬天,受天氣影響,當(dāng)?shù)剞r(nóng)民自己育的苗大部分沒有長成,到來年開春沒有種苗定植,農(nóng)民非常著急。看到農(nóng)民的急迫需求,劉瑞平通過朋友聯(lián)系到山東有穴盤茄苗,馬上趕赴山東考察。
當(dāng)時,農(nóng)民普遍采用“營養(yǎng)缽”育苗,相比于將籽直接撒在地里的土法種植,那一個個類似于小花盆的營養(yǎng)缽,更易聚肥聚水,是當(dāng)?shù)赜绲闹髁鳌K裕?dāng)劉瑞平從車上卸下一盤子一盤子的茄苗時,迎來的首先是村民訝異的目光。“這什么呀!”“苗這么小!”對于“穴盤苗”這種新事物,人們議論紛紛。
所謂穴盤,就是一個長55厘米、寬28厘米的長方形黑色塑料盒,里邊有幾十個大小均等的格子,一個小格育苗一棵。小格里放的不是土,而是進口草炭、蛭石、有機肥。將信將疑的菜農(nóng)們把這一盤盤苗子端回去,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它們的后發(fā)優(yōu)勢。穴盤苗雖然不如營養(yǎng)缽的大,但是定植后不傷根,不緩苗,長得快,而且坐果整齊,上市早,產(chǎn)量高。菜農(nóng)看到了穴盤苗的好處,劉瑞平看到了這里邊的商機。他決定自己建造育苗場。endprint
2006年夏天,劉瑞平的首批9個溫室大棚建起來了。和一般的大棚不同,他的大棚更像是工廠車間。里邊管管線線縱橫交錯,墻上掛滿了各種機器設(shè)備,鍋爐、熱風(fēng)機、自動播種機流水線、自走式噴灌車、進口施肥器、打藥車、補光燈……寒冬臘月,室外溫度低至零下10度,大棚里卻白天高達25度,夜晚也有15-18度,因為燒著鍋爐,吹著暖風(fēng)呢。控溫、控濕、控光線,自動播種、自動澆水,原來一個棚需要三個人來管理,現(xiàn)在一個人能管理三個棚。
本鄉(xiāng)本土就有專業(yè)育苗戶,很多菜農(nóng)就不再自己育苗了。菜農(nóng)規(guī)避育苗風(fēng)險,劉瑞平成為風(fēng)險的承擔(dān)者和成功的受益者。他崇尚道家文化,微信昵稱是“敬天愛人”,微信頭像是太極陰陽圖。但他并不認為,現(xiàn)代人就應(yīng)當(dāng)回到遠古,用原始方法種植。他更相信科學(xué)的力量。“現(xiàn)在養(yǎng)個孩子還講究科學(xué)育兒呢,養(yǎng)苗子也是一樣,思想要跟上,設(shè)施也要跟上。”劉瑞平引進套管嫁接、膜下暗灌、誘殺蟲板等新玩意兒,他相信,只要不違背自然規(guī)律,所有新的東西都值得肯定。
他不斷做培育各種新苗的試驗。他育的茄子苗抗病性強,育的甜瓜長得大、口感脆,育的“雙星蜜”哈密瓜中心含糖量達到百分之二十一。可能對于終端消費者來說,菜還是那些菜,瓜還是那種瓜,味還是那個味兒,但是只有劉瑞平知道,從撒下種子到走上餐桌,這背后有多少看不見的汗水與付出。
一路走來,如今,合作社的育苗工廠已達到占地230余畝的規(guī)模,有高標準日光溫室35棟,春秋大拱棚15個,簡易連棟溫室4000平米;培育的嫁接茄子、辣椒、甜椒、番茄、菜花、嫁接西瓜甜瓜、嫁接黃瓜等種類,一年可提供3-4茬,可滿足蔬菜周年生產(chǎn)的需要;合作社種苗年銷售收入1500萬元,實現(xiàn)利潤260萬元;擁有理事成員113人,會員1000余戶。合作社為會員提供種苗和技術(shù)服務(wù),使會員畝均增收300元左右,年終還有一定比例的分紅。同時帶動無公害蔬菜生產(chǎn)2萬畝,帶動農(nóng)戶10000戶,輻射帶動農(nóng)民增收2500萬元以上。
且喜春風(fēng)到農(nóng)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位在蔬菜種植方面領(lǐng)跑的人,背后都有強大的科研力量、鄉(xiāng)村政策在支持、在支撐。比如無土栽培技術(shù)在青縣的應(yīng)用,育苗基質(zhì)在曲周育苗基地的應(yīng)用,設(shè)施蔬菜綠色防控技術(shù)在固安的應(yīng)用等等,都離不開河北省農(nóng)林科學(xué)院專家們的努力。
春盤,像一個窗口,讓我們窺見,新時代的春天,科技的力量、創(chuàng)新的力量,正帶給鄉(xiāng)村以不同于以往的勃勃生氣。在蔬菜種植成氣候的村莊,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鄉(xiāng)多起來,有的村子甚至沒有人出去打工,忙著摘菜的季節(jié)還得雇人幫忙。蔬菜種植與采摘觀光相結(jié)合,又催生了鄉(xiāng)村旅游,促進了鄉(xiāng)村的凈化美化。
春盤,又像一個隱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對春盤里的需索和挑剔,催生著種植方式的改變和優(yōu)化,催生著鄉(xiāng)村經(jīng)濟模式的改變。春盤,連著“供給側(cè)”,連著鄉(xiāng)村振興,連著鄉(xiāng)村的小康和現(xiàn)代化。
在文末,且將《春盤》詩的最后一句略改,作為本文的結(jié)束:
不妨細雨看梅花,且喜春風(fēng)到農(nóng)家。
編輯:郭文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