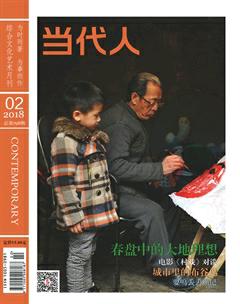人的世界
祝勇
自周代開始,那個人神混居的世界被一分為二——一個是天的世界,由神主宰;另一個是人的世界,由王主宰。人們從此不再在神話的世界里兜圈子,而是從玄幻世界回到了人間。這是人們打量自我的開始,從戰戰兢兢,放大為理直氣壯。
一
時間來到了戰國,一個大家都不打算好好說話的年代。那個時代的人,基本上都像吃了槍藥似的,為他們心中的真理、死理、面子,或者僅僅為一個女人,動不動就急赤白臉、以命相搏。那也是一個熱血的時代,是血的流速越來越快的時代——不僅在血管里流,在青銅刀的血槽里流,更在荒野大地上翻滾。那時的空氣中都回旋著血液的腥甜,像肥料一樣,滋養著人們的野心。
故宮博物院這件青銅壺,渾身上下,被四圈平行排列的三角云紋帶分成三個區:在前兩個區里,有人在采桑和射禮,有人在樂舞和射獵,春和景明,波瀾不興,一片生產勞動的和諧景象;但這些都只是鋪墊而已,第三區才是這組“壁畫”(壺壁上的畫)的主體和高潮——它位于壺的下腹部,界面最寬,可以容納大場面,所以,這上面的情節,也最驚心動魄。
它再現了戰國時代的一場戰役,而且,是一場水陸兩棲作戰。動用了戰船、云梯等各種先進的裝備,彼此打得狗血淋頭、肝腦涂地。
壺上沒有注明這場戰役的具體日期、戰場位置,我想那里應當離河不遠吧,不然怎么要兩棲協同呢?在中原大地,哪里沒有河呢?我們的文明,不就是被河流所孕育,并不斷塑造的嗎?
我也不知道誰在戰斗,只知道必然有一場戰役,隱在某一部歷史的秘冊里,隱在一層層的風雨背后。或許,就在這場戰役結束后,獲勝的一方凱旋在子夜,就想到了要鑄造一件青銅壺,來炫耀他們的勝利,捎帶著也紀念一下犧牲了的無名烈士——就像我們今天時常在昔日的戰場豎起一座紀念碑一樣。
只是那支取勝的部隊,沒能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是從勝利走向了塵土——他們就像他們的敵人一樣消失在時間中,即使歷史學家也打探不到他們的消息。在這世界上,只有時間是戰無不勝的,可以征服一切自大狂。但這件青銅器沒有被時間所消滅。人們把它從塵土里挖出來,送進故宮博物院,供人們瞻仰和研究。專家們為它起了一個很長、很專業的名字:
宴樂漁獵攻戰圖壺。
二
這件宴樂漁獵攻戰圖壺,對于藝術史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上面畫的不再是動物,而是人。
我們知道,在前面談到的那些青銅器中,只有動物才有存在感,后來植物也有了存在感,但人是沒有存在感的,人的存在感要通過動物和植物才能體現。但這件宴樂漁獵攻戰圖壺告訴人們,這種情況一去不復返了。
其實,人在青銅器上亮相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殷商到西周初年。安陽殷墟著名的婦好墓,出土過一對青銅鉞,被稱作至今發現最早的中國青銅鉞,其中一件上面就有虎撲人頭紋,那顆孤零零的人頭,居于兩虎之間,那兩只老虎張開大口,似乎馬上要分享它。故宮博物院收藏著一件西周后期的刖人鬲,這只鬲的平底方座上,開著兩扇門,門樞齊全,可以開閉,而守門者,是一位受過刖刑(把腳剁掉)的人。
只是,這些器物上的人,并不構成器物的主體,他們是弱者,是邊緣人,非死即殘。那是人自我貶低的結果——在他們看來,自己從來都不處在世界的中心。這個世界是由鬼怪神靈主導的,人得聽他們使喚。
那時的人們,經常被一些基本的問題所困擾,比如他們不知道鳥為什么會飛、山里為什么會有霧、人為什么會死。那個神出鬼沒、險象環生的世界,經常讓人感到無力和茫然。于是他們發明了青銅器,通過青銅紋飾超自然的魔力,去與上天神靈溝通,讓自己不再孤苦無援。
但這樣的情況不是一成不變的,由商入周,動物的神秘性就一點點消失了,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上幾乎再也找不出饕餮紋了。于是我們會想,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增加了,對神異力量的依賴減弱了。但是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值得提一下,就是周代建立以后,他們不能照搬商代的信仰系統了。商人尚鬼,他們的祖先,本身就是動物(神靈)變的,《詩經》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也是商代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所以商人祭祀時,鬼神和祖先往往是不分的,祭神就是祭祖,祭祖也是祭神。但是周人與商人不是一家,商人姓子,周人姓姬,假如商人與神是一個血統,那么周人就無法再與神攀上親戚了。于是,周人就把自己的祖先與神的世界分開了,祖先不再是有超自然能力的神靈,而是上天的兒子,他們統治天下,是因為他們的身上承載了“天命”。
于是,自周代開始,那個人神混居的世界被一分為二——一個是天的世界,由神主宰;另一個是人的世界,由王主宰。人們從此不再在神話的世界里兜圈子,而是從玄幻世界回到了人間。肉身的祖先成為信仰,有血緣溫度的人間秩序(禮制)開始確立。艾蘭(Sarah Allan)說,理解商——周轉變的關鍵,在于前者的“神話傳統”被后者的“歷史傳統”所取代。
這是人們打量自我的開始,從戰戰兢兢,放大為理直氣壯。
三
但是, 這個以周王為核心的人間秩序堅持了幾百年,就支離破碎了。
那是因為沒有了神鬼的震懾,禮法的緊箍咒也失靈了,人們心里的獸和魔,狂奔而出。
春秋戰國,是一場打了五百年的戰爭,比后來的一個朝代都長出許多。這場漫長的、看不到盡頭與希望的戰爭,把很多東西都打沒了,比如權力、財產、尊嚴、生命,還有道德底線——僅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就已“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孟子憤怒地說:“春秋無義戰。”
但戰爭這事,在很多人眼中,未必像孟子想得那樣嚴重。如之前所講到的,對于藝術史來說,中央控制力的減弱,反而帶來了紋飾、造型和工藝上的解放。至少,在那些游走在荒原上的、像蒼蠅一樣亂撞的游俠、猛士、縱橫家眼里,戰爭就無比可愛,因為在戰爭中,所有的規則都被打破了,人可以搶錢搶老婆,可以殺人不償命,當然自己的錢和老婆也隨時可能被搶,自己也隨時可能成為別人刀下之鬼。但大家都默認了,所以戰爭就成了一個大家都承認規則的大游戲,一場大Party。意義層面的事,是文士們的事,是歷史學家的事,對于當事人來說,舒坦就是意義。
前文說過,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氣質,同樣,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命。有些事情,既然沒有能力去解決,就莫如抱著一副放松的、幽默的、娛樂的態度去面對,打碎了瓶瓶罐罐,自然有人出來收拾。這個世界,從來都是有人管打,有人管收。
我想,在戰國時代,一定有人發現了戰爭的娛樂性質。這世上最大的娛樂,莫過于對戰爭的觀看。其實今天的人們也是如此,一點也沒有進步。我們被戰爭大片號召進影院,明擺著是沖著銀幕上的血腥慘烈去的,越是刀光四濺,越是血肉橫飛,觀眾就越High。現實中的戰爭也是如此,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利比亞的時候,世界上不少電視臺都在直播,這個時候,就是收視率一路躥紅的時候。相反,我從來沒見過直播和平的,比如直播我們吃飯、睡覺、上班、如廁。人們可以說,這是為了反對戰爭,引以為鑒,但我相信大部分人是看熱鬧的。他們臉上洋溢著正義感,卻把快感深深地埋在心里,打死也不說。
四
我們不妨把這件宴樂漁獵攻戰圖壺,當作那個年代里的“現場直播”(青銅器,不過是當時的屏幕而已),而用來紀念一場勝利的所謂“紀念碑性”,其實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于是,在戰國,在歷史上最深黑的夜里,有一群人趕在死亡來臨之前,用一只宴樂漁獵攻戰圖壺,記下了那一場拼死的廝殺,然后,把臉隱在黑暗里,孤芳自賞。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看法,即:在這個時代,缺乏宗教意義的裝飾充斥于器物之上;復雜精巧的設計將一件堅實的銅器轉化為一個“蜂房”般的構件。同時,器物也成為了描繪宴飲、競射以及攻殺等畫像的媒介。
他還說,古老的紀念碑性的各個重要的方面——紀念性的銘文、象征性的裝飾,以及外形——就這樣被一一拋棄,這種反方向的發展最終導致青銅禮器的衰亡。
編輯:耿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