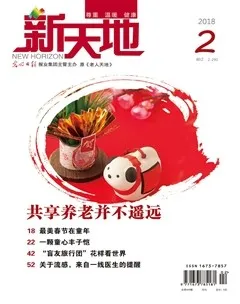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侯云德
李想
“雙鬢添白發(fā),我心情切切,愿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yè)。”這是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shù)獎獲得者侯云德的一首明志詩。當下,他最關(guān)心的是即將于2020年結(jié)項的傳染病重大專項,那時,他就91歲。
像偵探,緝拿病毒元兇
一輩子與病毒打交道,作為我國分子病毒學和基因工程藥物的開拓者,侯云德說:“認識世界的目的應(yīng)當是要改變世界,學習病毒學、研究病毒學,目的應(yīng)當是預(yù)防和控制病毒,為人類作出更加切身的貢獻。”
時光回溯到1958年,29歲的侯云德是蘇聯(lián)醫(yī)學科學院伊凡諾夫斯基病毒學研究所的一名留學生。他在導(dǎo)師戈爾布諾娃教授的指導(dǎo)下,研究副流感病毒。當時,研究所里發(fā)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動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死光了,而且原因不明。查找“真兇”的任務(wù)落在了侯云德身上。導(dǎo)致小白鼠死亡的病原微生物是細菌還是病毒?如果是病毒,會是哪個?
通過層層抽絲剝繭,侯云德將仙臺病毒列為重點懷疑對象。幸運的是,后來他成功從細胞里分離出了仙臺病毒。不止于此,通過深入研究,他還首次證明仙臺病毒對人有致病性,發(fā)現(xiàn)了仙臺病毒可使單層細胞發(fā)生融合的現(xiàn)象,并闡明了機理。
仙臺病毒是乙型副流感病毒的一種,最早在日本仙臺一實驗室里被分離出來,故而得名。1958年,日本學者岡田發(fā)現(xiàn)仙臺病毒具有觸發(fā)動物細胞融合的效應(yīng)。幾乎在同一時期,侯云德在1961年有了同樣的發(fā)現(xiàn),并闡明了機理。從蘇聯(lián)學成歸來后,侯云德開始著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學的研究。所謂病原學,是指研究疾病形成的原因。在緝拿致病元兇的路上,侯云德很快便有所斬獲。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在國內(nèi)首次分離出Ⅰ、Ⅱ、Ⅳ型三種副流感病毒,首先發(fā)現(xiàn)了Ⅰ型副流感病毒存在著廣泛的變異性。
做名醫(yī),研發(fā)國產(chǎn)干擾素
即使在“文革”期間,面臨重重困難,侯云德也竭盡所能地堅持科研工作。他帶領(lǐng)吳淑華等同事,對包括黃芪在內(nèi)的幾十種中藥展開研究,分析它們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古方“玉屏風散”通常用來治療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藥是黃芪。這便是侯云德鎖定黃芪的起源。大量試驗表明,黃芪對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顯的防治作用。隨著研究的深入,黃芪的作用機理也逐漸浮出水面:它可以誘生干擾素,促進干擾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輕微抑制仙臺病毒等復(fù)制的作用。在闡明黃芪抗病毒感染機理的同時,侯云德敏銳地意識到,人體自身的干擾素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抗病毒藥物。
干擾素是正常人體細胞分泌的一類低分子蛋白質(zhì),具有抗病毒、抑制細胞增殖、調(diào)節(jié)免疫及抗腫瘤作用。侯云德決定選擇這種物質(zhì)作為治療病毒病的突破口,開始研發(fā)的戰(zhàn)略性轉(zhuǎn)移。一開始,侯云德選擇用人臍血白細胞誘生制備干擾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長激素釋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國宣告成功。侯云德大膽設(shè)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辦法,讓細菌來大量生產(chǎn)干擾素。
1979年,基因工程對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而言聞所未聞,更遑論生物技術(shù)。利用基因工程制備干擾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細胞,但去哪兒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棄,他多方聯(lián)系,反復(fù)嘗試,最終在北京郊區(qū)的飼養(yǎng)場找到了一種非洲鯽魚,它的卵母細胞成為理想的替代品。當年,侯云德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國際干擾素會議上宣讀了這個制備干擾素的土辦法,由于操作簡便,立即受到了國際專家的高度評價。
1982年,53歲的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中國人抗病毒反應(yīng)優(yōu)勢的人α1b 型干擾素基因,并成功研發(fā)出國際上獨創(chuàng)的國家 I 類新藥產(chǎn)品重組 α1b 型干擾素。臨床證明,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細胞性白血病等有明顯的療效,且與國外同類產(chǎn)品相比副反應(yīng)小得多。
似將軍,狙擊在傳染病戰(zhàn)場
回顧我國傳染病防治領(lǐng)域的重大事件,2003年發(fā)生的SARS事件是繞不開的話題。事實上,也正是“SARS之痛”推動了我國重大傳染病防控體系的變革。自2008年擔任“傳染病防治”重大專項技術(shù)總師以來,侯云德領(lǐng)導(dǎo)專家組設(shè)計了我國應(yīng)對重大突發(fā)疫情的總體科技規(guī)劃,并進行了任務(wù)部署。
每當重大疫情來臨時,侯云德扮演的都是守在“火山口”上的角色,他要準確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應(yīng)對方案。
2009年,全球突發(fā)甲流疫情。在衛(wèi)生部的一間會議室里,圍繞甲流疫苗接種一劑還是兩劑,專家們在激烈地討論著。根據(jù)文獻和初步研究結(jié)果,侯云德憑借多年積累“一錘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劑接種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衛(wèi)組織推薦的兩劑接種策略。
一劑次接種有效的判斷不是憑空得出的。在疫苗臨床試驗中,數(shù)據(jù)顯示老年人群對此次的甲流病毒有一定的免疫記憶,一劑便可激活較強的保護性抗體,同時在一般人群中一劑次疫苗可產(chǎn)生有效的保護性抗體。侯云德說,在應(yīng)對流感疫情時,除了要評估疫苗一劑次免疫保護效果外,還要充分考慮阻斷病毒傳播所需要的人群接種率,并結(jié)合疫苗的生產(chǎn)和接種能力進行綜合判斷,否則免疫策略也難以實行。
在一系列科學決策的指引下,中國在87天內(nèi)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個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規(guī)模暴發(fā)前上市使用,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成功干預(yù)大規(guī)模流感疫情。
在侯云德的主導(dǎo)下,經(jīng)過近10年的科技攻關(guān),目前我國已建立覆蓋到省市級的應(yīng)對新發(fā)突發(fā)傳染病的綜合防控實驗室網(wǎng)絡(luò)體系,可以在72小時內(nèi)鑒定約300余種已知病原并對未知病原進行檢測和篩查。
侯云德的學生說:“侯老師能夠作出方向性的判斷,靠的不是拍腦門,而是長期以來扎實的積累。”他每天7點就開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飯。據(jù)說,這是年輕時養(yǎng)成的習慣,因為要抓緊一切時間做實驗。每天都會關(guān)注國內(nèi)外病毒學的最新動態(tài),并且親自翻譯、撰寫,送給相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dǎo)和同事參閱。
盡管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效益數(shù)以億計,但侯云德對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車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們問他想換輛什么車。侯先生說,帶轱轆的就行。生病住院,也從來不跟組織提任何要求。有時輸完液晚上8點了,還要自己回家做飯吃。”武桂珍說,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國的防病事業(yè)。在他身上,深深映刻著老一輩科學家的家國情懷。
“……吐盡腹中絲,愿作春蠶卒;只為他人暖,非為自安息。”在侯云德寫的這首名為《決心》的詩中,老科學家的初心可見一斑。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病毒世界,利用所學鑄就重大傳染病防控之盾,寫下一段段人生傳奇。
(責編:孫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