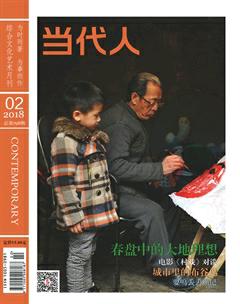耍嗚丟丟瑣記
安德路
東后街多出了一個門樓子,藍布圍起,靠墻山支立,上方有個小舞臺,一聲鑼響,就見有布偶人“嗚丟丟、咿咿呀呀”地開始表演。看客不少,男女老幼,都仰脖子湊熱鬧。我發小嘎巴耶說,這是“耍嗚丟丟”的。
嗄巴耶小名奎子,比我大六七歲,頭發自來卷,一身粗糙硬皮,總給人洗不凈的感覺。嘎巴耶是外號,形象貼切,朗朗上口,還帶些洋氣,不知道誰給起的,民間真是不乏高人。
嗄巴耶拽著我貓腰溜到布門樓底下,悄悄掀開一道縫兒往里瞧,隱隱有兩只腳在動,正要看仔細些,一個長著兔唇的人過來,沉著臉示意我們走開。
嗄巴耶說,里邊地底下埋鐵管兒,串線,是機關,就能讓小人兒動。我說,你怎么知道?嗄巴耶不無得意地一撇嘴,我就是知道,我爹給耍嗚丟丟的當過幫手。
耍嗚丟丟,上世紀五十年代常見于北京街巷,藝人找好場地,支起道具,布好機關,有人負責開鑼收錢,有人隱入布帷子里,操控偶人表演,“武松打虎”“豬八戒背媳婦”等節目,都是百姓喜聞樂見的故事。這個行當與皮影戲、木偶劇、拉洋片同屬民間藝術。耍嗚丟丟的起源及歷史無從考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與其他民間藝術一樣古老。而今,耍嗚丟丟絕跡江湖五十余年了,六十歲以下的人已知之甚少。
人性素來好奇貪玩,在物質、精神生活均匱乏的年代,一支嗩吶就能驅散大雜院許久的沉悶,三兩個布偶人就能牽動幾條胡同麻木的神經。城外,居住在矮舊平房區的市民,五行八作,出賣勞動力的居多,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沉悶的生活像街上往來的馬車,單調乏味,亦步亦趨,偶有婚喪嫁娶的人間悲喜劇,人們的衣著和情緒會罩上一層不同的亮色,尤其是那些愣蔥似的孩子們吃了蜜蜂屎似的,追逐啟蒙心智的娛樂,如鐵屑遇到磁石。
東后街沒了一個老頭兒,八十多歲了,說是老喜喪,得慶賀,熱鬧三天。頭天請和尚念經超度,接著是嗩吶班子獻藝,大小嗩吶齊鳴,吹嗩吶的人,口鼻演奏,擠眉弄眼,活潑滑稽,逗得大伙兒笑逐顏開,不亦樂乎。翌日,請的是耍嗚丟丟的,來的人更多了。
想不到還有這么個玩意兒,極大滿足了童真年代孩子的好奇心。五十多年前的歡樂,平淡簡單,卻讓懵懂的心充滿了欣喜。
通常,一聲鑼響,藝人的徒弟或助手會拿個托盤器皿走到每個人面前收錢,小孩子給得少,一分二分,毛兒八七的,大人給得多些。
我六歲,借人家辦喪事的光,見識了耍嗚丟丟的,同時,對死亡也有了新的認識,原來死了人,也是可以慶賀的;不過,有講兒,喪者須人丁興旺,壽終正寢。死亡讓人恐懼,卻化悲為喜,不乏智慧!那幕帷子舞臺上挑簾左右進出的小人兒,牢牢地吸引著眾人的目光,藝人的手牽動布偶,也牽動著觀眾的心,歡樂讓人忘記死亡的恐怖。
一對老夫婦,男人上山去打柴,女人出來相送,可沒料到,男人半路遇虎,人虎相搏。鑼鼓點配樂,喘息聲、喊叫聲,緊張激烈。耍偶人手腳嗓并用,很是投入。簇擁著的觀眾,都被吸引,時而安靜,時而唏噓,大眼兒瞪小眼兒地跟著入戲。
男人被老虎吃了。老虎也消失了。接著女人出場,左顧右盼,顯得很焦慮。女人進屋,出來時頭上多了頭巾,大伙兒明白女人去山上尋男人了,為她擔心。鑼鼓點伴著女人疾走,忽然,女人找到一把柴刀,接著又看見了老虎,女人明白了,男人被老虎吃了。女人與老虎搏斗,一來一往,柴刀掉了,氣喘吁吁,打不過老虎,女人絕望地捶胸頓足號啕大哭,邊哭邊喊:“我滴老頭子——”觀眾情緒被感染了,都在替女人悲傷,有人眼圈紅了,有人握緊了拳頭。
“我滴老頭子——”耍偶人捏著的嗓音像口哨,模仿著女人悲切的呼喚。把老頭子的“子”念作“栽”。“我滴老頭子(栽)。”正當女人一聲連一聲地哭老頭子(栽)的當口,只見老虎走過來,大家都緊張起來,要吃女人了!不曾料到,老虎走到女人面前,張開大嘴,哇,把男人吐了出來,女人一怔,看見發懵的老頭兒,驚喜萬分,撲了上去,相擁而泣——圓滿結局,眾人都松了口氣。
“我顛兒了。”嗄巴耶說。“跑什么?抖機靈,小子,人家不再要錢了,死人那家兒都給了。”一老大媽笑著說。
“嘁,誰跑啊?我回家圈鴿子去,別讓貓叼走一只。”
嗄巴耶養了兩只鴿子,別看家里破破爛爛不利索,可鴿子養得挺水靈,羽毛上帶著層白霜。嗄巴耶非常喜歡那對兒叫“墨環兒”的鴿子,通體雪白,脖兒上有一圈黑色的羽毛,環狀。前不久,有一只裹到黑四的鴿群里。嗄巴耶去要,黑四不給,說和他過死的(行話,過活的就還回去)。嗄巴耶他媽怕兩家打起來,噘著大嘴去喊他:“奎子,不要了,咱家多得是,大批批的。”
黑四媽一看這陣勢,娘兒倆都來了,老街舊鄰的,不能傷了和氣,生生摁住黑四把鴿子還了。黑四家鴿子多,點子、銅之烏、鐵之烏、鐵膀兒,黑翼翅、愣兒……一大盤兒,二三十只,見天在胡同上空盤旋。
隔天,嗄巴耶又來找我,說還上東后街看耍嗚丟丟的去,他手里多了一根金箍碌棒。
到了街角,空空蕩蕩的,人出殯了。哪兒還有耍嗚丟丟的。二人很是失落。少頃,嗄巴耶說,咱倆玩武松打虎。我先當武松,你當老虎,完了,我當老虎,你當武松。武松我沒當成,腦門兒上多了一個大包。嗄巴耶嚇壞了,一通說好聽的,說千萬不能說是他打的,我奶奶他惹不起,沒結沒完,他媽非打折他腿不可。他讓我保密,說趴出小鴿子,給我一只。
“一對兒。”“行,一對兒就一對兒。”
我額頭上包挺大,紅光閃閃,家人嚇了一跳,可無論怎么追問,我都說是撞墻上了。奶奶說,走道兒怎么不長眼睛。包好了,鴿子毛也沒見到一根。
市井生活不也像耍嗚丟丟的在上演嗎?隨著時代發展,一些營生悄然不見了,走街串巷的民間雜耍也早已沒了生存的市場。曾以此謀生的藝人不知所終,帶走了代代相傳的古老故事。
胡同逐漸消失了,與之并存的文化也隨之消亡,留下的唯有破碎的記憶和傷感。
嘎巴耶的老爹后來以拾荒為業,這白胡子的老頭兒很另類,借拾荒撿回很多俗稱“姜石頭子兒”的石頭,閑來端詳把玩,不僅碼了一窗臺,小屋滿地都是。老頭兒興致高時,會招手叫過來一些小孩兒,笑瞇瞇地拿起奇形怪狀的石頭說,看,這個像不像“猴子孫悟空”,這個像不像“彌勒佛”,秀完,輕輕地放回原處。孩子走了,老頭兒依然微笑著欣賞自己的寶貝。老頭兒沒了后,前腳送走老頭兒,后腳嘎巴耶拉起老頭兒的拾荒車,喘著粗氣叨咕:“沒事往家弄這破爛兒干嘛?”
人的審美情趣與學識無關。米蘭·昆德拉的《慢》中有句話:“樂趣不論平凡還是不平凡,都屬于感受到它的人。”
嗄巴耶說,收拾他爹的東西,找到幾個布偶人,霉了,扔了。
他爹死時六十九,不算喜喪。沒有耍嗚丟丟的。
編輯:耿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