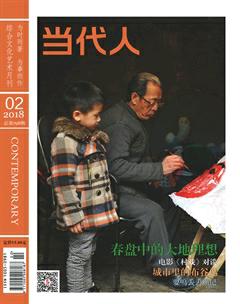在碧云寺
孔淑茵
赴京開會,尋暇去了香山碧云寺。
行至山門,迎面便見乾隆皇帝的御筆。藍底金字的匾額,赫赫然上書“碧云寺”三字,字體流潤飄逸,見大家氣象。山門卻與想象中有些不同,不見恢宏逼人的氣勢,頗素樸,更像皇家園林的內寺。
碧云寺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元朝。公元1331年,元朝開國元勛耶律楚材的后人耶律阿吉舍宅為寺,在此建了一座碧云庵。之后,明清兩代又不斷修葺擴建,山石流水,古木碑亭,殿塔飛檐,木雕彩畫……這座古剎規模越來越大,名字也由當初的碧云庵改成了碧云寺。
現在,我正慢慢走近這些前塵風物,袖里乾坤,且行且觀之。
羅漢堂
來碧云寺, 一定要去羅漢堂走一走。
當年,乾隆皇帝駐蹕香山靜宜園時,因念及這座古剎有待于護持,曾命人對其進行過一番修葺。羅漢堂就是在那個時候趁機新建的。經典的十字樓形,漂亮的建筑外觀,內斂的巨大空間,都甚為可觀可嘆。而此羅漢堂的十字形建筑理念,則與另一座羅漢堂——杭州凈慈寺的羅漢堂相仿。南宋詩人楊萬里曾經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說的就是這座凈慈寺了。“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詩詞不老,常讀常新,但凈慈寺的羅漢堂卻早已湮沒于光陰流水。而當年凈慈寺的住持永明禪師,則搖身成為眾羅漢之一,此刻正安靜地站在碧云寺的羅漢堂里,不問世事的散淡模樣。
羅漢堂又稱五百羅漢堂,然精確來講,堂內卻有508尊雕像。蓋除卻按隊形排列井然的五百羅漢外,還有端坐于正中的三圣佛、守護于十字甬道四端的四大天王,還有一位就是無奈蹲在屋梁上的濟公活佛了。羅漢們全部都是木胎雕塑,外面包著金箔,寶相華麗莊嚴。大多數羅漢身上的金色歷經時間的打磨業已暗淡無光,個別一些金色依然較鮮艷的,概是后來修繕的結果。徜徉羅漢群中,被它們鬼斧神工的藝術魅力所震撼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有人說這些雕像是佛教雕塑藝術的集錦,應該一點也不為過。它們或低眉垂目,或笑意盈盈,或安詳望遠……每一尊羅漢神情各異,體態不同,或老或少,或美或丑,或俗或雅,舉手投足皆率達于心。也許只有到這里,才能更好地理解何為相由心生,明明看起來丑丑的一尊羅漢竟能給人如此溫暖祥和的力量。
撇開宗教與雕塑藝術,現在來講幾個故事。這些來自不同地域、性別不同、出身與經歷各異而最終同修成正果的達觀真理者,正是因了這些故事而愈加眉目清晰,一副走下神壇貼近人間煙火的鮮活樣子。有意思的是,五百羅漢中竟然有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爺的身影。他們為自己塑了金身,搖身一變成了暗夜多羅漢(康熙)和直福德羅漢(乾隆),不聲不響在眾羅漢中占了兩個位置。看來這兩位處萬乘之尊者,大概覺得做了人間天子尚且不夠,仔細思量就有些意味深長了。我個人比較偏愛第171尊羅漢,那個纏了小腳、雙手經年累月在石頭上磨著鐵杵的女人。據說當年就是她點化了李白,才有了“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千古名句,鼓勵了世代的人。還有第33尊的阿那律尊者,這尊外國佛早年時因懶惰貪睡而經常受到佛的斥責,后來卻不知何故幡然改過,竟開了天眼,也算是一番天大的造化。還有就是因為救助民女而耽擱了排位時間,不得不委委屈屈長年棲身于屋梁上的濟公和尚……就這樣一尊一尊地數羅漢,會突然發現自己看到的可能不只是羅漢。
在羅漢群中走走停停,我大多不知道它們各自代表著什么,它們背后曾經發生過哪些驚心動魄或者靜水流深的故事,何時何地因了怎樣的觸動而領悟了哪般深奧的佛理。我僅憑著感覺去體味其中的氛圍,領悟那萬千姿態背后的真義,卻也不失為一種緣法。一堆木頭竟然就這樣有了生命,古今中外,承載厚重。而這些被神化了的形象,明明就在身邊,卻又好像遙不可及。整座屋子滿滿當當又空空蕩蕩,大千萬象,更映照出自己的渺小。
兩種樹的隱喻
游碧云寺,僅賞樹似乎就可以令人感覺不虛此行了。
那就去賞樹。碧云寺里歷來是不缺少樹木的,因為它本身就堪稱一座經典園林。寺內草木科目屬種繁多,以松柏為主。樹木們大多蔥郁蒼勁,樹形或古或奇,或怪或美,或昂然直秀或虬枝崢嶸,各具機巧,氣韻悠然。花和葉的色彩也極豐富,隨著四季赤橙黃綠錯落變換,葉尤其如此。當所有這些特性匯集一起,就將靈性、佛性、高雅、靜謐一并推向極致,樹也因此具有了樹木之外的隱喻,儼然淡出紅塵的方外姿態。更何況其中許多樹木還有不凡的出身,追溯起來各有一番來龍去脈。
三代樹,這個名字本身就足以讓人延伸出豐富的想象。樹身上有牌兒,牌兒上有介紹云:三百余年,生于枯根間,初為槐,歷百年而枯,在根中復生一柏,又歷百年而枯,更生一銀杏,今已參天。就這樣一個百年又一個百年地復生復滅,復滅復生,時間遼遠而深沉,生命強大,機緣巧合,令人敬畏。更有詩云:“一樹三生獨得天,知名知事不知年。問君誰與伴晨夕,只有山腰汩汩泉。”詩是出塵的詩,輕淡又雋永,時間擺出了紅塵道場,供我們去仔細參悟。
中山堂前植有娑羅樹。樹齡談不上多古老,至少相對于北京其他寺院動輒植于明清時期的娑羅樹而言,這棵植于民國時期的樹實屬小輩份。這是一棵讓我想象紛紛卻難以下筆的樹。即便看過了樹上掛著的牌子,瀏覽了網上的相關信息,我依舊猶豫不決。無知總是讓人氣餒無力,讓人游移不定。這究竟是娑羅樹還是七葉樹?亦或娑羅樹又名七葉樹?我著實有些糊涂。娑羅樹也好七葉樹也罷,歸根結底是佛教圣樹。由一棵樹想象開去,可以看盡許多模棱兩可。同樣由這棵樹想象開去,印度、佛祖、七葉窟、佛祖講經說法之處,簡單的詞匯可以漫散成悠遠完整的故事。故事里有葉大如輪,有香甘如蜜,有果大如瓶,有人于樹下出生,于樹下悟道,最后又涅槃于樹下。不知不覺就是一個輪回。
一個孤孑的側影
現在要談到孫中山紀念堂了。在這樣一個佛氣氤氳的所在,突然看到這么一個主體,會讓人瞬間生出混搭之感,可仔細端詳卻也不顯得特別突兀。
據載孫中山先生當年病逝于北京,暫時停棺于碧云寺金剛寶座塔的石券門內,四年后才被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而石券門內現在封存的是孫先生的衣冠冢。孫中山紀念堂內設有他的半身雕像,還可以看到他各個時期的一些照片以及著作樣本等史料史跡,而他逝后蘇聯贈送的一口玻璃蓋鋼棺也赫然擺放其中。一個人的一輩子,就這樣壓縮在一座屋內,像幾個著重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斯人已逝,多少心事托付于時光。endprint
而我被其中一張照片吸引了。宋慶齡女士身著黑色旗袍,側身坐在孫中山先生的棺槨前,為他守靈。孤獨,哀傷,濃得似乎從照片中溢出來,全世界仿佛于那瞬間荒涼了。
許多東西從光陰中緩緩流淌,時而滄桑時而清涼。但照片里那個孤孑的側影在那兒靜靜坐著,所有的感慨就失了聲。
通向高處的臺階
碧云寺的一進進院落是順著山勢層層向高處疊起的。院落與院落之間既相互呼應又自成一體,內斂卻也不自閉。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用腳步丈量著一級級的臺階,還有院落在更高處等著我。有一位作家曾寫及自己的一次徒步遠行。他說他在漫天的風雪中孤身行走于太行山的荒涼山道,邁左腳時他會念“阿彌”,邁右腳時是“陀佛”。阿彌陀佛,是他的溫暖,也是他信念的堅守。我沒有念阿彌陀佛,但沿著一階一階的臺階行向高處時,我屈膝弓步,生出的是近乎于朝拜般的心境。
碧云寺的制高點是最后面的金剛寶座塔。遠遠望去,寶塔掩身在一片松柏蒼翠之間,莊重典雅又不失巍峨大氣。金剛寶座塔由塔基、寶座和塔身三部分構建而成。塔基是磚石結構,塔身則由一色的漢白玉砌成,被精心打磨過的石面上,雕琢著形態各異的佛像,每一處雕工都堪稱精湛,即使外行之人也可以立刻看出它們的美。
順著塔基處的入口標志進入一券洞,才發現券門內的石階竟出乎意料的狹窄且陡立,通道內雖不是黑不可視物,卻也讓膽小之人心生惶恐。幸虧石階不長,幾個盤旋之后已到了寶座頂上。陽光和山風頓時迎過來,一切又通通透透的美好。
就是此時,我看到了那些塔。五座十三層密檐方塔,一座屋形方塔還有一座圓形的喇嘛塔,正在那兒靜靜聳立著。它們沐著午后暖陽,干凈純粹得讓人心疼心動,一種不可方物的美。不必去了解它們身上繁復的雕刻,甚至無需考量十三層在佛教里是不是有什么特別的寓意,我就這么直接被它們打動了心神。建筑是會說話的,誠然。
等我終于從這激動的情緒中稍作平復,才有時間環顧遠眺。香山如黛,林木翠玉,遠城近郭盡收眼底,頗有點兒“一覽眾山小”的氣勢。但這樣的形容畢竟有失貼切,于是想找出一個絕妙好詞來對應眼前的風物與感受,怎奈搜腸刮肚而不可得。
回來后看到一句前人描繪此情此景的句子“蕩蕩開朗,有大人威嚴”,簡直絕妙之極。而另一首“金風獵獵吹遠松,輕霞朵朵生殘峰,西山一經三百寺,唯有碧云稱纖儂”就多了一些塵味和歷史感。
不得不離開了。
重新站在山門處,回望,一石一木皆肅穆悠然,靜守歲月物我兩忘。香山公園里卻正是人來人往,陽光暖洋洋的,風也似乎止了。
編輯:耿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