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譯毛詩的歲月
☉許淵沖
1959年農歷除夕,我在北京歐美同學會的舞會上見到了照君。她1948年十四歲參軍,參加過淮海戰役,見到過毛澤東主席。毛主席一聽到她的名字就說:“昭君是要出塞的呀。”果然,她在香山外國語學院學習之后,轉入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畢業后分到塞外擔任教學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母親家過年,我們在晚會上認識了,談起香山外國語學院的領導和教師,她也認識很多。我們還談到德萊頓和羅曼·羅蘭的作品,《哥拉·布勒尼翁》是一本不容易理解的小說,她卻能夠欣賞。我想,如果我們結合,就可以同搞中、英、美、法、俄五國文學,那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學事業嗎?幾個月后,我們結婚了。回憶起來,當時我還寫了一首小詩:
舊夢依稀憶逝川,古都三十二年前。
舞裙卷起千重浪,華燈高懸不夜天。
得遂平生凌霄志,快馬黃昏自加鞭。
喜看琳瑯滿目書,莫教珠璣化云煙。
但那時她在塞外,我在北京,兩地分居,不免常有相思之情,我寫過幾首小詩:
永定河畔楊柳青,千絲萬縷訴真情。
煩請云影帶塞外,流水不干情不盡。
每逢佳節倍思親,況值新婚二月整。
鴛床幾曾溫鴛夢?孤燈空自照孤影。
新月入窗君入夢,入夢模糊入窗明。
明月有缺亦有圓,情人有分必有合。
愿將情思化動力,助君苦戰東洋河。
麥浪金波賽龍舟,兒女英雄顯身手。
高扎麥束堆粽子,遙舉銀杯賀豐收。

1959年2月12日與夫人照君合影
從詩看來,參加土改勞動對我的思想改造還是起了作用的。調英語系后,學院搞“大躍進”,說突出政治,就可以提高業務,外語水平就可躍進。我根據自己的經驗,沒有突出政治,只是背熟了三十篇短文,英語成績就提高了,所以就提出少而精的學習方法。英語系主任朱樹飏(大學同班)、教研室主任林同奇(大學同學林同端即南茜的弟弟)、副主任胡斐佩當時都對我進行了批評,說我和黨唱對臺戲,反對“大躍進”,是單純業務觀點。香山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后來出了一個院士、一個部長,遷到新北京后出了一個將軍,可見突出政治的作用。其時正要對我展開批判,不料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也提出教學要少而精。于是領導就說:戰略上要大躍進,戰術上可以少而精,免了一場批判。
我覺得毛主席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觀點很有道理,不但可以用于外語教學,還可以用于翻譯。剛好那時《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詞六首》,寫紅軍如何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取得了勝利。我想翻譯毛詩,也要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在戰術上重視困難。翻譯如果只是譯字詞,那就是沒有看到翻譯的難點,一定要翻譯字詞所表達的意,這就不那么容易了。下面就舉《清平樂·蔣桂戰爭》及兩種譯文為例,說明如下:
風云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譯文一)Sudden veer of wind and rain
Showering misery through the land,
The warlords are clashing anew,
Yet another Golden Millet Dream.

1997年許淵沖先生之子許明(左一)自美國回國探親,與父母在北京大學家中合影。
Red banners leap over the Ting River
Straight to Langyan and Shanghang.
We have reclaimed part of the golden bowl
And land is being shared out with a will.
(譯文二)A sudden burst of wind and rain,
The warlords fight again.
Sowing on earth but grief and pain,
They dream of reigning but in vain.
O'er River Ting our red flags leap,
To Longyan and Shanghang we sweep.
A part of golden globe in hand,
we,re busy sharing out the land.
“風云突變”中的“變”字,第一種譯文譯成veer,是突然轉變方向的意思,就是說軍閥已經開戰了,只是轉變方向而已。但是下面一句說“軍閥重開戰”,說明軍閥已經停戰,現在重新開戰,不是轉變的問題,還是譯成burst好些。而clash指沖突,不一定是戰爭,不如明確為fight好。“一枕黃粱”直譯為“金黃的小米夢”,讀者可能不知所云,不如意譯為夢想統治,但又不夠形象,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了。“直下”譯成sweep(橫掃)更形象化,而且押韻。“金甌”譯成bowl(碗)遠不如globe(地球)。這是就“意美”而言。如以“音美”而論,原詞和第二種譯文都押了韻。再說“形美”。原詞每句字數分別是4、5、7、6,6、6、6、6;第一種譯文音節數是7、9、8、9,9、7、10、10,不如第二種8、6、8、8,8、8、8、8。
之所以說了這些,是因為我的詩詞英譯、法譯就這樣開始了。此時,北京已經提出了“備戰備荒”的口號。為了備戰,外國語院校要從北京疏散到外地去,我們學院去了張家口。到張家口后,我的孩子許明出生了,《詩書人生》對此有記載,這里只抄錄當時寫的一首小詩:
愛兒墜地兩月半,愛睜圓眼愛看拳。
愛踢小腿愛戲水,爹媽愛看看不完。
1965年秋,我下放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即清理階級隊伍、經濟賬目,等等,我又寫了一首《晨曲》:
電線織成五線譜,晨星曉月作音符。
雄雞高吹黎明號,老牛慢敲田園鼓。
流水合奏今日樂,小橋低訴當年苦。
農村“四清”慶豐收,蒼松枯柳同起舞。
“四清”本來是以王光美為樣板的,不料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王光美被打倒,我這個歌頌“四清”的知識分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8月16日夜進行批斗,系主任朱樹飏和我們十個人戴了高帽,掛了罪狀牌,在大操場挨打挨罵,一夜不許回家。照君在張家口師范學院參加運動。那時許明在幼兒園,我參加“四清”回來時,幼兒園給他戴紅花來歡迎我;我挨批挨斗時,他掛了小“牛鬼蛇神”的牌子,坐在樓門口等我,沒有飯吃,就坐在門口睡著了。回想這段往事,不能怪他長大去美國以后,再也不肯回來工作了。
其實,我們受罪還不算大。我們院長是長征老干部,卻因為“執行資產階級教學路線,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自殺身亡了。在批斗領導的時候,我們也要頭戴高帽、掛罪狀牌,低頭彎腰,兩膝半分彎,陪著挨斗。在烈日下,非常難熬。我忽然想起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就默默背誦起來:“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立刻忘了烈日驕陽,仿佛見到了“惟余莽莽”“頓失滔滔”似的。“莽莽”“滔滔”這些疊詞怎樣翻譯好呢?反復推敲之后,想出了兩句譯文:
The boundless land is clad in white
(無邊無際的大地一片銀白)
The endless waves are lost to sight
(無窮無盡的波濤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覺得炎熱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于是再往下背誦,背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就譯成:
But alas!Qin Huang and Han Wu
In culture not well bred,(缺少文化修養)
And Tang Zong and Song Zu,
In letters not wide read.(沒有閱讀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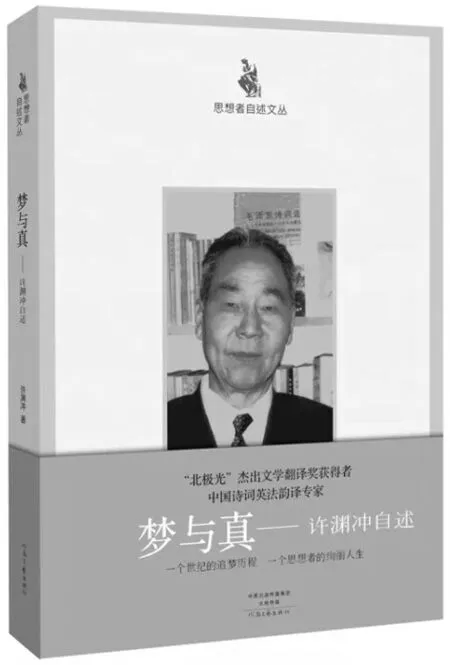
譯到這里,批斗會也完了,于是我暗自得意地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