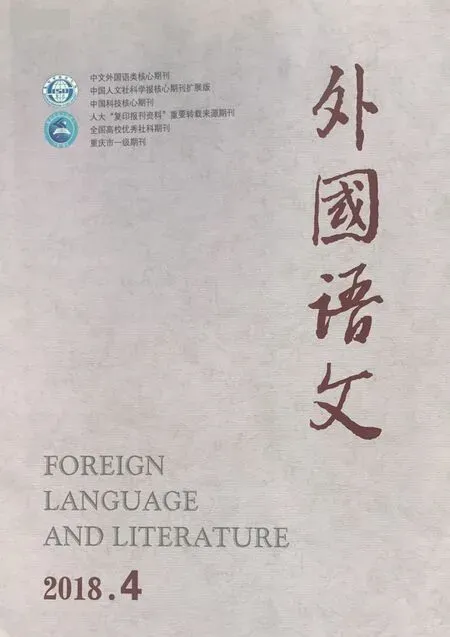結構對話語的反拔
——《荒謬斯坦》敘述者的不可靠性研究
孔 偉
(吉林財經大學 外語教研部,吉林 長春 130117/北京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北京 100089)
文本的含義與敘事相關,含義的生成往往體現在敘述者對某些事情的堅持或否定上。然而,“敘述者有時使自己成為一個戲劇化的人物”(Booth,1961:212),他的話語是不可靠的。《荒謬斯坦》①(Absurdistan,2006)是俄裔美國猶太小說家加里·施泰恩加特②(Gary Shteyngart,1972—)的第二部小說,講述的是俄國③富豪的獨子米沙·鮑里索維奇·溫伯格(Misha Borisovich Vainberg)迂回返美的故事。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和情節的參與者,米沙·溫伯格訴說了他對俄國的厭棄、對堅持猶太性的質疑和對美國生活的向往。但是,從文本結構上看,敘述者將諸多無厘頭的情節,根據主人公俄國、猶太、美國三重雜糅身份分門別類地編排,建構起三重疊套的敘事結構,即嵌套回環結構、復調結構和破碎性結構。這些并列且互為的結構,間接地傳遞出主人公對俄國的擔憂、對猶太性的堅守以及對美國不切實際的奢望與想象。結構擠壓敘述者表述內容的真實性,顛覆其話語的可靠性,形成結構對話語的反拔。
1嵌套回環結構:對移民敘事的反轉
所謂故事,即“連續的事件”(申丹 等,2005:174)。在敘事文本中,故事事件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再現,故事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敘事內容與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從內容上看,《荒謬斯坦》屬于移民敘事,情節始于列寧格勒④,主人公在歷經種種世事之后,結局定格在其奔向通往紐約的路上。米沙竭力重返美國的故事貫穿整個文本始終,是最主要的情節。而從結構上看,在這個主要事件里,又層層嵌入了多個小故事,如米沙曲線返美,誤入荒謬斯坦;在被困荒謬斯坦時,又獲悉當地兩個民族之間的淵源與糾葛等。文本前一半情節層層向內深入,推進敘事進程;后一半又與前文遙相呼應,向外一層一層補遺,最終回到敘事原點,形成大回環結構。這種層層嵌入的文本結構,在形式上逐漸累積自身的涵義,構成對內容的擠壓,以此揭示故事的真實意圖。此外,正文前后分別加以序言和尾聲,將米沙返美的故事再次包裹起來。序言以“這本書講的是愛的故事”(Shteyngart,2006:vii)*為方便起見,小說引文僅視需要標注原文頁碼。譯文參考吳昱譯《荒謬斯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部分譯法有刪改;關于作者譯名,本文采用美國通行讀音,譯為加里·施泰恩加特。開篇,尾聲再述主人公對美國女友的愛慕,二者共同承擔起最外層“玫瑰敘事”的作用。俄國人棄俄赴美的移民敘事,由此,轉變為俄國青年的愛情童話。嵌套回環結構的應用,最大限度地將故事限制在大西洋以東——美國本土之外,使主人公割舍不斷的俄國身份表達得淋漓盡致。
嵌套回環結構,也稱“俄羅斯套娃*“套娃”是俄羅斯頗具民族特色的玩具,它通過中空且大小不一的木質玩偶層層嵌套組成。套娃每層圖案可以相同,也可不同。”結構。這種結構將故事主題與俄羅斯民族性最為直接地聯系在一起。小說的結構如此安排,遠非單純創作技法上的別具匠心,而是要揭示敘述者的真實態度。《荒謬斯坦》采用第一人稱敘述形式,敘述者與主人公均以“我”的形式出現。作為“故事中的我”,米沙被塑造成一個體型笨重、奇胖無比、呆頭呆腦的形象。他對當下的俄國十分厭棄:“什么沙皇之城,北方的威尼斯,俄羅斯的文化之都……都見鬼去吧”,“圣列寧斯堡已經淪落成一副變幻莫測的第三世界模樣”,“那些新古典建筑都陷入了糞水橫流的運河里”(3)。然而,作為“講故事的我”,米沙深邃且洞見。他把諸多離奇的經歷嵌套起來,讓結構的意義躍然紙上,消解人物話語的內涵。人物米沙要建一個兒童慈善組織叫“米沙的孩子們”*這里指俄國的孩子們,而不是主人公“米沙”的孩子們。米沙在俄語中是小熊的意思,是俄羅斯的吉祥物,此處代指俄羅斯。,而他本人連它能做什么也沒說清楚,結果也什么都未建成。而敘述者搭建的嵌套結構,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大小不一的套娃意象,彌補了話語的失敗。處于隱含位置的文本結構,反而彰顯了俄國文化在主人公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記。
本質上,所有的故事都訴諸人們的好奇心,引發讀者追問“接下來發生了什么”。《荒謬斯坦》的結構不僅顛覆了移民敘事的線性結構,還通過嵌套回環的形式將最具內涵的情節置于文本的核心位置,故事的主題借助這種特殊的安排得以顯現。查特曼曾說,“陳述需依賴于特殊的表述媒介”(Chatman,1978:31)。這里的特殊媒介即結構的隱喻性,其功能與張力在此可見一斑。在文本的核心位置,米沙講述了兩個民族——塞翁族和斯瓦尼族之間的糾葛。他們原本一家,由于俄、美兩個超級大國先后介入使之最終分道揚鑣。塞翁人成為“愿意和西方交好的城里人”,而斯瓦尼人則保留了牧羊和“祈求救贖”的傳統(191-193)。俄、美兩國共有的狂妄和救世使命意識,加速了弱小民族的分化,他們對其他民族的干涉,制造了其內部的對立。故事主題被層層包裹起來,而一旦內核被觸及,其批判效果不言而喻。
有關俄、美兩國的敘事在文本中常交替出現、同時在場,故事在漸入結局時,被猛然拉回敘事原點,用最外層的回環結構把移民者無法回避的祖國、父子、鄉愁等復雜的文化聯結和盤托出,增強文本的感染力。在第41章結尾處,當米沙打算帶著塞翁姑娘娜娜逃離荒謬斯坦時,文本執意透過其父之口,揭示謎團:“你還不明白么?……你爸殺了個俄克拉荷馬人就是為了讓你回不成紐約。”(312)此時,文本章節所剩無幾,讀者也早已忘記第1章提及的米沙父親與美國商人之間的恩怨,而故事執意在此舊事重提,與開篇遙相呼應,將米沙復雜的身份用世仇與生命的代價牢牢鎖定在俄國一側。
此外,作為故事敘述者的米沙不斷闖入文本,反復提醒讀者“自己”與劇中人米沙的區別:“容我先向讀者簡單描述一下那個住宅區的景象”(50);“那么,告訴我,講述這些陳年往事的意義何在?”,“事情是這樣的”(233)。這種元小說敘事的手法將“故事的形式作為素材,(再造)其他的故事形式并凌駕之上”(Gass,1970:25)。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通過間離的方式,暴露劇中人話語本質上的不可靠。敘述者強迫讀者從故事中跳出,重新審視情節的發展,增強對人物話語的警惕性。形式即意識形態。故事表面上講述的是米沙重返美國的軼事,而實際上,文本一再展示米沙無法剪斷的俄國情結。敘事結構顛覆了人物話語,最終將文本真正含義呈現在讀者面前。
2復調結構:重現古老的猶太移民敘事
在討論猶太性問題時,復調結構的應用重現了猶太民族古老的歷史與文化。Howe曾認為,猶太移民敘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猶太移民經歷,“所以它必將面臨創作資源枯竭、記憶匱乏的尷尬局面”(Howe,1977:16)。然而,《荒謬斯坦》不但再現了猶太人綿延不斷的文化史,還追問21世紀是否要堅持猶太性的問題,頗具時代意義。故事引入多個角色,與米沙展開對話,說話人各自秉持自己的觀點且不妥協,形成有關猶太性存留與否的復調聲音。這些聲音此起彼伏,從多個方面、不同角度記錄了猶太人的割禮、大屠殺的記憶、猶太民族流散的經歷等。文本因此呈現出漣漪蕩漾的層次感,形成復調結構。米沙自始至終參與這種結構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他所說的要做一個“世俗化的猶太人”的論調,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對猶太性甚至宗教的堅持。
作為俄國猶太青年,米沙猶太身份的起點是歷經蘇聯無神論“改造”后的“新”猶太人,本身已不具備太多的猶太性。這也是他所持立場的現實基礎。米沙強調他崇拜斯賓諾莎、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這些人被外族同化,卻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他鄙視那些“在哭墻那兒見到的留著大胡子前后搖擺的猶太人”(251)。所以,米沙所說的猶太性至多是“一種民族性或‘國家性’,而不是一種教義”(Wanner,2008:679)。然而,多個聲音在此基礎上引發振蕩,米沙的形象從一個高呼同化與世俗化的俄國青年,轉變為一個竭力展現猶太性的當代猶太人。
首先,最虔敬的哈西德派*猶太教中一個派別,意為虔敬者。教徒的在場,激起了猶太教儀式感的波瀾。米沙要努力成為一個美國人,但他卻“受制于父親,父親讓他擁抱猶太教并確認自己的身份既不從屬于美國也不從屬于俄國”(Hamilton,2017:38)。米沙遵照父命施行了猶太割禮。而這種與上帝立約、確定猶太身份的行為,是信奉猶太教最典型的表現之一。米沙的猶太性因這種簡單的儀式而確立。在割禮過程中,他與哈西德教徒仍然立場相悖,但已然開始扮演引導教徒言說猶太歷史的角色:
“你們想拯救囚徒……瞧瞧我!我就是囚徒!是你們的囚徒!”
“所以你即將被拯救了!”
……
“亞伯拉罕親手給自己施行‘布里斯’*布里斯:bris,指猶太教的割禮。時都九十九歲了。”
“可他是圣經里的英雄啊。”
“你也是啊!從現在起,你的希伯來名字叫摩沙,意思就是摩西。”
“我的名字叫米沙。那是我美麗的母親給我取的俄文名字。”
“可你就像摩西一樣,因為你幫助帶領蘇聯猶太人走出了埃及。”(22-23)
米沙言語的不可靠性體現在其功能上。正是他不斷地反駁,才使得摩西、亞伯拉罕以來的猶太隱喻再次呈現。對話的結果使他秉持的“去猶太性”的論調蕩然無存,反而給人留下強烈的歷史感與民族性。復調結構顛覆了米沙話語的可靠性。又比如,在他與柳芭的對話中,其話語也是不可靠的。柳芭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當父親被人暗殺后,柳芭希望能皈依猶太教。米沙一再阻撓,但他的長篇大論非但沒有說服她放棄皈依,反而讓其覺得米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信仰猶太人的上帝:
“幫我皈依猶太教吧”。
“變成猶太教徒可不是個好主意”。“不管你是怎么看待猶太教的,說到底它不過是一個典籍化了令人焦慮的體系。它是用來制約膽小而邪惡的世人的。對所有相關人員來講,它都是一個失敗的主張,所有相關人員包括猶太人、猶太人的朋友、到頭來甚至猶太人的敵人,都是如此”。
“……要是咱倆能向同一個上帝祈禱該多好啊……”
“柳芭,你得明白上帝是不存在的”。
“上帝當然存在啦”。
“不,不存在。實際上,我們的靈魂里留給上帝的是一個消極的空間,我們最糟糕的感情就待在那兒,比方說我們的嫉妒、怒火、暴力和怨恨的根源等等。如果你真的對猶太教感興趣的話,柳芭,你應該仔細地讀一下《舊約》。你應該特別注意猶太教上帝的行為,以及他對一切民主和多元文化事務的極端鄙視。我覺得《舊約》的字里行間都十分有力地印證了我的觀點”(88-89)。
作為受述者,柳芭是信息的接受方。信息接收的失敗,源于米沙的話語正是對猶太教深刻理解的表現。米沙宣稱自己“是一個徹底世俗化的猶太人,不管是民族主義還是宗教都和我無緣”(viii)。而二人的對話顛覆了他對教義的一無所知,相反增強了柳芭皈依猶太教的愿望。柳芭最終成長為一個立場明確的對話主體,其言語內在自由度也因此得以提升,這正是米沙“教導”的結果。“過去由作者完成的事現在由主人公(自己)來完成”(巴赫金,1998:64)。米沙承擔了講述猶太教義的任務,讓原本只是因喪夫而尋求歸屬感的柳芭皈依猶太教的愿望更加堅定了。
除對儀式、教義的揭示,米沙還參與了猶太民族記憶的重建。當他誤入荒謬斯坦后,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路邊的攝影師、酒店的經理、納納布拉高夫先生等。這些人在說話前大都重復同一句內容:“猶太人民在我們的土地上有著漫長與和平的歷史。他們是我們的兄弟,他們的敵人是我們的敵人……我媽就是你媽,我的老婆就是你的姐妹,你永遠都可以在我的井里討到水喝。”(114)這段詞語貧乏、令人費解的話是當地人談話的開場白。作為一個整體性符號,它包含明確的能指,但所指讓人困惑。當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引述時,所指發生偏向,形成了關于“我媽就是你媽”的復調聲音。結構內部再次振蕩,話語內涵漸漸清晰。語義重疊的部分構成了含義的內核,也就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此刻要傳遞的重要信息——猶太人背井離鄉,流散并獲助的歷史。攝影師假借“咱媽生病”騙取救濟,米沙愿意慷慨解囊,映射了猶太人對流散地人民的反哺;米沙不懼危險搭救柏悅酒店經理的母親,源于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山里的猶太人自巴比倫流放時期,便和荒謬斯坦人同飲一井水,追溯了猶太人遭迫害而后被救助的歷史;甚至那些重復此話卻毫無實際意義的人,也是在以某種方式記錄著猶太人的經歷。這段話真實含義的揭示,恰是源自這些人以不同方式的重復。這種重復“事實上是一種思維的建構,在每一次重現過程中,消除了自身所有的特殊性,保留了同類事物之間共有的部分”(Genette,1980:113)。
最后,復調結構的建構,還體現在某些細節上。米沙與荒謬斯坦族人的對話還記錄了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歷史淵源、猶太民族慘遭大屠殺的厄運、猶太人被同化等現實問題。米沙說,“以色列*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第一個猶太人國家以色列。不是我的國家”,“紐約才是”(251)。這看似是他對以色列國的不屑,實際上是在號召世界范圍內的猶太人當以民族性為紐帶建立超越國別的更廣泛的聯結。至此,當主人公作為倡導“猶太人當世俗化”的代言人的使命終結,文本在各種聲音的激蕩中傳達了新的內涵。米沙完結了對猶太民族的種種追述,作為不可靠敘述者的角色也隨之終結。他的形象從一個徹頭徹尾的世俗化的猶太人,轉變為一個竭力保存猶太性的當代猶太人。
3破碎性結構:虛幻的美國想象
《荒謬斯坦》虛構了一個“真實的”世界,即若隱若現的美國。故事以主人公被困圣彼得堡開篇,以其逃出荒謬斯坦結尾。自始至終,米沙都沒有以一個純粹的、當下的形式,真正出現在美國的土地上。有關美國的記述,都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現出來。美國時而出現在回憶里,時而出現在憧憬中,或者以零星的人或事昭示自身的存在感。美國無處不在,而美國又從來就沒有“真實地”存在過。這種碎化的形式造成了歷史、現實、想象之間的交錯莫變。主人公誤把記憶和憧憬當作現實,屢次表達對美國生活的熱切期待。然而,真實卻遠非他設想的那樣完滿。破碎性結構制造了時空的錯位,拉開了人物與對象之間的距離,使米沙漸漸明白大西洋彼岸的遙不可及。
空間意象的建構是主人公追逐美國夢的基礎。列菲弗爾認為“空間是(建構的)產物”(Lefebvre,1991:26)。這表明,除物理要素之外,空間還可以以文化的形式存在。《荒謬斯坦》的全部故事都發生在大西洋以東,從地理上看,與美國并無直接聯系。而敘述者以點狀的人和物,搭建了一個近似的美國社會,時刻提醒自己赴美的初衷。無論在圣彼得堡,還是荒謬斯坦,米沙周圍隨處都散落著一個個與美國相關的東西:美國橄欖球運動員做的香煙廣告、姑娘們穿的萊卡*美國杜邦公司全資子公司英威達的商品名(Lycra),此處代指氨綸紗等面料的時尚服飾。、卡爾文·克萊恩*美國設計師Calvin Klein從1968年開始創建自己的公司,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Calvin Klein品牌迄今為止仍被認為是時尚的代表。牛仔褲、麥當勞、21世紀百貨商店*美國著名的連鎖百貨公司。、美國使館等。這些零零碎碎的日用品、服裝和建筑無不印證著美國的在場,然而真實的美國卻終不得入。其實,這種關聯性是敘述者的呈現與人物視角合謀的結果。主人公對事物有選擇性的聚焦,使其有如在之感,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他無法入境美國而帶來的心理缺憾。
客觀事物建構了物理空間,米沙身邊的人為空間提供了人文信息。主人公與女友羅艾娜初識于紐約,后來,他們在圣彼得堡匆匆相處過兩個星期。之后,便天各一方,以電子郵件保持間歇性的聯系。郵件涵蓋了二人在大西洋兩岸各自的經歷,包括羅艾娜移情別戀,后來又被拋棄的事。從郵件中米沙得知女友愛上別人,并懷上他的孩子,這本是對其赴美最大的阻力,但他在閱讀這些郵件時,摻雜了大量的初心,羅艾娜的不忠并沒有撼動其赴美的決心。米沙在“重建故事世界時,一定將交流的目的性納入推斷”(Herman,2009:38)。最終,他與人生的重大挫敗取得心理上的和解,踏上重返紐約之路。這符合米沙對自己身份的定義,“一個被殘忍地裝載外國軀殼里的美國人”(187),但也說明,美國絕非想象中的天堂,一個相貌“異樣”的人要成為美國人,必定要經歷非凡的內心考驗。
時間的扭曲也是破碎性結構的重要表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文本穿插了許多米沙曾經生活的過往,這些經歷以先于或遲于故事時間的形式呈現出來,如他在紐約讀書,在曼哈頓生活等。米沙的經歷宣示了其跨國主義身份,但也為其被拒絕入境增添了悲劇性色彩;其次,主人公對美國的想象闖入當下情節,干擾敘事進程的連續性,如第17章在米沙參觀斯瓦尼城的美景時,他“張開想象的翅膀……徑直向西北方向飛去,一直飛到曼哈頓的南端”(135),布朗克斯區、柏樹山、羅艾娜、豪威爾斯等一股腦地出現在他的意識流中。前后并不直接相關的話題因敘述者的想象,或隔離、或接續起來,碎化的形式推進或延緩了情節的發展。這種有意識的間離,制造了破碎性的敘事結構,使主人公與北美大陸以非當下的形式匯合,含蓄地表明米沙所期待的美國只不過是他一廂情愿,有選擇的記憶或想象而已。“我們僅僅看到我們觀看的東西,觀看是一種行為選擇”(Berger,1972:8)。米沙所展示的美國,無論是看到的或是想象中的,都是一種主觀有選擇性的聚焦罷了。一言以蔽,米沙從未放棄奔向美國,但他與美國之間的距離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全文的結尾定格在其奔向紐約的途中,而這條路更像一條移民者很難走完的征程。即使米沙厭棄俄國、拋棄猶太性,卻也實難觸及真正的美國。
4 結語
《荒謬斯坦》無論在題材或是敘事文類上都體現了21世紀初美國猶太小說創作的新趨勢。這部作品最大的創新性在于跳出美國與猶太的二元對立,讓俄國成為雜糅身份的第三極。這不僅增加了身份的復雜性,還追溯了美國猶太人的來源與祖籍國問題。像主人公米沙一樣,俄裔美國猶太人是21世紀許多猶太作家歡呼的身份特征。然而,俄裔美國猶太人也時常徘徊、躊躇。他們常被迫活在對過去或未來的想象之中,無法享受當下。作者施泰恩加特一代的作家打破了美、蘇對峙遺留的陰影,拋棄20世紀猶太小說中對俄國避而不談或一貫的批判態度,將俄國文化與俄國具體歷史時期的政策區分開,實現對移民者復雜情緒的深切觀照。此外,這部作品引入不可靠敘述者,將形式對內容的顛覆作為主要的敘事手段,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敘事技巧。總之,《荒謬斯坦》是一曲多元文化的交響樂,終將成為一部頗具時代價值的重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