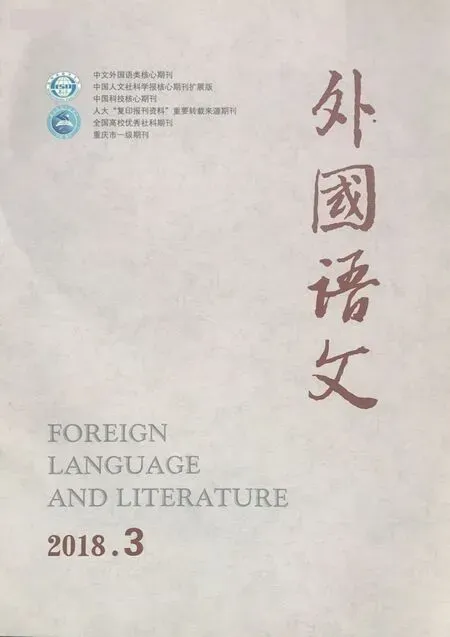論文化概念格式塔的實質
彭玉海
(黑龍江大學 俄羅斯語言文學系與文化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0 引言
文化概念(cultural concept)使人類復雜的精神生活成為現實,并使之有了豐富的人文色彩和社會文化意義,而概念背后的格式塔蘊涵、聯想內容在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概念格式塔反映人對事物的態度和對現實的切分方式,并從思想深處透射出人是如何認識、定位和對待世界與自身的,一定意義上代表著特定文化語境和語言世界圖景下人的文化思維方式,因此格式塔分析十分有益于走入人的心靈世界,解析人同世界和周遭的關系,能夠傳遞出與人的情感、思想、觀念等精神層面有關的多元民族文化信息。格式塔的特殊性在于它以語言的某種結構形式、話語方式真實記錄人的文化潛意識活動和思想內容,隱藏于文化主體思想深處的精神、意志、文化認識通過形象化的聯想方式呈現并固著于概念心理完形,使其成為民族認知、民族演進中的一個個文化事實得以沿承和不斷豐富,相應文化概念格式塔“物的蘊涵”和“意識映射”成為民族心智和文化認知現實的寫照,可以形象而真切地反映、揭示文化概念的社會價值、意義和特定民族的社會精神實質。某種意義上講,格式塔既是一種思維形式,也是一種文化機制,正是透過格式塔中這些直覺性、潛意識并兼以一定主觀性的心理投射和文化想象內容,能夠了解、把握一個民族的文化本真和文化精髓。本文一方面從文化認知立場出發,對文化概念格式塔內涵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從文化統覺與神入性、范疇錯置性質、次邏輯性質、“人化”性質、多維立體性及特殊的語言文化性等方面對文化概念格式塔實質進行闡釋和解讀,以增進對文化概念格式塔獨特性的認識和理解,促進更為積極、有效地運用其分析、考察俄羅斯民族文化概念,從文化概念格式塔角度推動俄羅斯文化研究。
1 文化概念格式塔
“文化概念深層上與特定民族之中人的意識是聯系在一起的。”( 彭玉海 等,2016:19)文化概念格式塔(gestalt of cultural concept)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的認知事實、生活感悟的真實記載和反映,所謂“認知即事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文化概念格式塔的“認知事實認定”來識解一個民族對人對事的思想態度,審察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精神修養,挖掘出人在認知對象化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文化意識,因此,隱含于各類文化文本中的概念格式塔在“傳承文化、延續民族同一性,建構民族價值觀的文化記憶”(朱達秋,2014a:122)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文化概念格式塔文化聯想內容既同人的生活經驗、情感意志等有直接聯系,又與人的認知水平、文化預置與知識背景等因素密切相關,它們都以“物的蘊涵”(object connotation)(Успенский, 1997: 151)形式呈現文化主體內心深處精神性、價值性的體悟,在民族文化思想體現和價值延承之中獨樹一幟。
文化概念往往以包含民族歷史文化積淀、民族文化記憶與認知、人生的體味與生命的理解等內容的抽象名詞為載體。當文化主體(“民族人”)在使用某一“抽象名詞-文化概念語詞”時,潛意識中會自然聯想、想象到,或者在心理上會自然地把它接受、認定、理解和體會為他經驗中的相應對象事物,該聯想物或意識蘊涵物即為文化概念格式塔*格式塔(gestalt)本身是一個基于感知和心理輸入形成的認知意識建構即主觀的心理構造物,它代表意象化的心理完形,強調經驗和行為的整體性,是針對某事態關系、屬性的完整意象代碼。。“文化概念格式塔指文化概念語詞的聯想形象或‘物的聯想’,它蘊涵著物化的文化想象和意識內容,后者是民族生活經驗和文化感知、領悟的凝結。”(彭玉海,2014:23)文化概念格式塔代表一種心理形象和文化認知意象,是圍繞人形成并展開的各種文化、社會關系在語言特殊文化語詞中的意識化沉淀和認知表證,它有一種文化心象的代入感,好比一個人穿上另一個人的鞋,走進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感知和體察他的所思所想、分享他的情緒意識與精神傾向。人的語言思維是命題式、完形化的心智行為,這在概念格式塔的文化認知功能中有同樣的反映。所不同的是,人們基于文化概念對現實的認識、表達往往不是直接、顯在的,而是間接、隱晦的,需要認知心理聯想和文化語義意識的支持,背后有一個事物中介的轉接過程,進而將它想象、理解為另一事物、尋找其物的文化蘊涵時,需要充分調動人的文化參與意識,而這本身是一個積極的文化行為過程。因此,文化概念格式塔具有動態延擴和多向位、輻射狀的文化釋出方式和文化表現內容,可視為是一個民族特殊的“文化記憶形象”(朱達秋,2014b:10),比如,俄羅斯文化中的“友誼是鮮花”(А. В. Кривошеев)、“友誼是太陽”(В. Соловьев)、“友誼是空氣”(Т. Шохина)等表達,映現出文化概念“дружба”(友誼)在俄羅斯民族認知中被記取、激活為“鮮花”“太陽”“空氣”等文化(事物)形象,而這里的“鮮花”“太陽”“空氣”即為“дружба”這一概念(語詞)的文化蘊意信息和格式塔內容(簡稱“文化概念格式塔”)。
文化概念格式塔折射出文化對象物同人的心理知覺(事物)之間的一種自然的想象性聯系,它是人在特定意識狀態下對文化概念事物的直覺知識的反映和記載。概念格式塔既有稱名、指涉性內容,也有述謂化、限定性的描寫特征,即各種語言意象、文化記憶、精神體驗等人文感知內容,相應文化概念形象產生于兩種事物、現象的某種交集或共時(意識)呈現。格式塔本身重在表現事實內容的完形性,即一個事物的聯想框架、思想整體性,格式塔的聯想信息來自于人內心深處對概念事物對象的理解與認知、意念和態度,這些認識和思想感受映襯出的文化概念到底是什么、相當于什么、類比于什么,體現出人的心智意識、文化意識和文化底蘊。這樣,格式塔內容就是文化概念對象在人的意識中被概念化出來的事物形象、“詞語的隱性形象”(趙愛國,2007:11),而正是格式塔所聯想的事物、概念同物的深層聯系為概念名詞的各種表層形式搭配提供了依據。從“Вкушая минуту радости, он знал, что ее надо выкупить страданием”(享受快樂時光的同時,他明白這快樂是用痛苦換得的)(А. Гончаров.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這一上下文可以看出,“快樂”(радость)作為人可能的狀態填充著時間,快樂是商品,而痛苦是對它的償付,是錢的等價物(Чернейко, 1997: 327)。由這些有關于“快樂”概念的文化語義聯想即格式塔內容可解讀并領略到俄羅斯人對概念“快樂”的體會和感受[包括它同概念“страдание”(痛苦)的潛意識對比],同時能夠識察出抽象語詞“радость”的上下文組配關系深層次緣由。總之,通過概念格式塔可以表現出文化主體對現實事物的主觀認識與領悟,形成概念詞的文化語義,因此,文化概念語詞的格式塔可稱之為“語言文化信息單位的語義格式塔”(彭文釗,2004:34),是文化概念在語言現實和思維想象中的一種基本運作屬性的體現。
2 文化概念格式塔實質的詮釋
首先,文化概念格式塔具有文化統覺性(cultural apperception)。概念格式塔來自于人的意識深處,基于人的文化感知積累、文化意識、價值經驗和他對人性道義的理解與領悟,深層次上是民族意識、民族意象的一種形象而又實在的釋放形式和文化心理連通管道,它給人以具象而又有某種難以捉摸的感覺,具有深刻而獨特的文化統覺實質,并且這一統覺性往往關聯于或具體表現為文化概念格式塔的“神入性”(empathy)。文化概念格式塔是概念詞進入文化整體、進入人的語言思維的基本操作單元,本質上是一種心理抽象物,是一種具有“移覺性”(synaesthesia)和“神入性”的認知心理抽象實體,這一點既是概念格式塔的典型實質,也可以說是概念格式塔的基本特征,它在理解和認識概念格式塔的過程中價值度極高,但往往被學者們忽視。
概念格式塔中,當文化主體基于文化智識、歷史文化經驗、社會傳統乃至生活觀念、審美情趣等因素,由文化概念(語詞)油然聯想到其精神貯存中所對應的文化對象物時,會產生一種自然而實在的文化心理聯覺感和精神—心靈默契性,形成文化概念事物的“神入性”,好比一個人感同身受地去體驗他人知覺狀態的這一心理過程之中所經歷、伴隨的“共情性”,其間所表現出來的心智—情志特性賦予了概念格式塔以文化想象的“心象默認值”。該“神入性”有一種文化上的集體“無意識性”(unconsciousness),包含“部分或完全的無意識過程”(郭本禹,2017:89),它以文化現實中人的“心靈自由”為基石(孫俊才 等,2016:107-108),集中反映出概念格式塔在文化聯覺方式上的自然、迅疾性以及聯覺內容上的(下意識)明確“標的性”。在概念格式塔的“神入性”作用下,人的思緒好像經歷了短暫剝離和瞬間的復位、遷延,并且潛意識中會伴有隨之而來的某種文化意象和意境,后者便是文化概念所對應的文化對象事物、文化概念在人心目中的文化投影,說得確切些是二者的心理意象混合體*Чернейко(1997)、Успенский(1997)等所稱的(文化)概念抽象名詞的“神話性”(“神話學”意義特性)實質上相當于此,以下將其統一理解、處理為“神入”。。神入性同心理學、神經學、智能學、認知學等均有關系,篇幅所限,以下只討論同文化語義、文化認知心理有關的層面,通過格式塔內容(運作)中的心智轉換和心智表現特點、主客觀互動與默契性、主觀意念與文化潛意識的共在性及其對事物文化蘊含的能動作用和引導性、統合性等來對此加以闡釋。
在概念格式塔“物”的蘊涵、投射過程中,經由心理抽象轉換得來的文化意象物已非物質實在上的原有事物,而是一個心智移覺實體。這正如“現實本身是不同質的,既有物質、身體上的實體,也有同物質實體同樣實在的觀念實體”(Чернейко, 1997: 5),此時兩種實體之間存在由文化意識前定著的心、物相生性或心物隨附、相通性,并且表現出意向性認知的特點,而“意向性的認知是一種虛擬存在”(王紅孝 等,2016:42),其中文化者的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達成某種心象契合和心念上的統一,心物聯想的“物我同懷性”促成并實現概念事物遷移的認知擬象化過程,這確乎在文化認知的根源上顯示出概念格式塔的“移覺性”“神入性”特質,表明格式塔內容是由下意識中的心靈融合、精神同化等意念化狀態所支配著的,它在人的頭腦中的出現是文化潛意識、文化自覺的體現。從概念格式塔的心智規定和語義意向上講,這里所謂“物”的蘊涵和投射所對應的實際是情志對象的化身,是已然“獲得精神含義的物質事物”(Степанов, 2004: 75),格式塔內容相應是借由原型事物生發出來的一種抽象形象和意涵,其間摻進了人的心智—意念內容。一方面文化概念格式塔是積淀并深藏于人內心的文化領悟的物化反映,顯示出人對文化概念“直觀化描寫的努力”(Раушенбах, 1990: 169),與此同時,從心理機制上講,該格式塔卻又是抽象的,是理性把握和能動創想的結晶,這是具體事物在人的心智中所構想出來的比照性(文化)事物,實質上是意識加工和心理換算的結果,進而其“物”的蓄隱中透溢出人的“文化自覺及主體意識”(朱振武 等,2015:64),例如,“Надежда озарила душу”(希望照亮了心靈),“Судъба/Жизнь улыбается ему”(命運/生活向他微笑)。這里文化概念“надежда”(希望), “судъба/жизнь”(命運/生活)的格式塔“物”的蘊涵——“太陽,陽光”(солнце)與“(有情感的)人”(человек)表象看上是具體的,而一旦其參與到心理聯想過程、成為文化思維操作的對象,所得出的則是一種心理回映物和心理感知意象,即心智抽象上的類比物。換一個角度,從概念格式塔的物的蘊涵、延伸機制上看,中間其實經歷了兩個步驟:一是從對作為意象投射參照對象的聯想輪廓的確定上看,所涉對象物往往是物質、具體的;二是從其投射過程、結果來看,介由心智跟進、加工而成的蘊涵物卻是被概念化、心象化甚至(文化)符號化的抽象物。這樣,原有事物同文化概念對象物之間實際存在一種互動關系:文化概念有了感知形象的物化投射和涵指,原有具象物又被文化概念事物和格式塔復建過程所抽象、同化,由此整合出新的文化擬象。“文化概念分析是通過話語分析和無法直接觀察到的現象同現實中可感知事物之間的對應性來確立文化載體對詞位所示情景的價值態度”(Лассан, 2002: 15),而格式塔方式在二者之間搭建起橋梁,借助抽象的意象轉移與認知移覺,可以對這種價值關系的文化深層內容加以識察和表征,凸顯出文化概念同蘊涵物之間的文化關聯性以及對概念對象的文化認知。
事實上,從認知上定位和理解,文化概念格式塔已然蘊含、規定著心智抽象的主觀意念作用因素,反映出“神入性”中自我意識統一性對文化對象意識的特殊制約性以及主觀意識對文化聯想潛意識性的作用態勢。正如劉娟(2007:7)所說:“認知語言學研究視角下的концепт(概念、文化概念——引注)……總是將事物與心理抽象物作比較,而這個心理抽象事物就是原型,它是某類事物理想化的表征。認知語言學框架下的концепт強調基于身體的經驗與想象,具有明顯的主觀色彩。”通過概念的認知運作,格式塔能夠將不在場的事物形象、畫面帶到當前文化概念、文化事物的心理擬象和構建中,可以通過前者表現、理解后者,成為民族心智和文化意義構造的重要一環。而由此復建的概念事物圖景實際屬于主觀抽象的心理構建物。格式塔能夠反映出文化概念對象同外在現實事物之間的特殊認知聯系,同時格式塔內容也是該文化概念在人的內心世界的投影,它能夠透過概念化的現實事物聯想,完成文化主體意識中的認知創建行為,其抽象心理屬性表現為概念對象、概念詞同其蘊涵物之間的深層認知和文化統覺聯系,背后類比關系的確立依賴于認知心象的特點、認知取意的運作以及文化經驗上的“厚積薄發”式輸出。而這同文化概念的產生背后的心智抽象(過程實質)一脈相承,“概念產生于形象,但它能逐步抽象化,由知覺形象演變為思維形象”(Маслова, 2006: 53)。例如,在“вкушать/вкусить счастье, славы”(嘗到幸福,享受榮光)之中,通過對文化概念事物“счастье”(幸福)、“славы”(榮耀,榮光)的類似于甜美食物的感性認知形象聯想,反映出人對“счастье”“славы”甘之如飴的思想化形象體會這一格式塔內容,此時文化主體會下意識地帶著蘊涵物的形象來體驗“счастье”“славы”,其認知心理抽象屬性和意念形象特征十分突出。當然,換一個角度,這也體現了概念格式塔的文化認知中,主觀意念與文化潛意識的特殊共在性、交織性,這一共現關系對文化對象事物的蘊含產生了引導性、統合性的能動作用。
從文化概念詞方面講,文化概念格式塔的心理抽象特性同抽象名詞即“概念稱名詞”的語義本原是聯系在一起的(Карасик, 2002: 30),這在文化語義層面上透射出文化概念所寓托的抽象名詞的“神入性”。“抽象名詞具有神入性,這同具有經驗現實支持的一切神入一樣。這首先指的是文化概念名詞(存在名詞,人類中心論名詞,直覺名詞)。”(Чернейко, 1997: 358)而從概念抽象語詞同其“物”的蘊涵詞(蘊涵物)之間的共軛(對合)關系上看,文化概念格式塔的聯想物、聯想場事實上也是“抽象”與“具體”進行移覺的交集點或連通域,隱含著二者間的一種“勾連、對接”交互作用程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概念格式塔是抽象與具體的異質實質的深層關聯結果”(Чернейко, 1997: 337)。抽象名詞一旦融入文化概念,它就代表著一種具有觀念性質和思想屬性的內容,這些同個人和社會群體思想認識、價值主張等有關的內容實質上也顯示出文化想象的特殊“靈感”和意識潛入性,所凝結的也正是人的心智抽象成果。舉例來說,在“Мы оказались раздавлены обрушившейся на нас свободой”(我們似乎被猝然而至的自由壓垮了)這一上下文中,抽象概念語詞“свобода”(自由)傳遞出的概念格式塔為“自由是突發事件”(свобода-катастрофа),顯然這是被人的主觀(神入)概念化的結果,是對文化概念抽象語詞“свобода”的觀念表達,文化主體借助“свобода”所隱含的形象聯想物形成了對現實感知的一種意識、心理回應。在“цена свободы”(自由的代價)、“крайности свободы”[極端化的自由(觀)]、“свобода безысходности”(毫無出路/進退維谷的自由)、“вчерашний раб, уставший от свободы”(為了爭得自由而疲憊不堪的往日的奴隸)當中,上下文所蘊蓄的該語詞概念格式塔分別是“Свобода-товар”(自由是商品)、“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世界觀)、“ тупик”(死胡同)、“ труд”(體力勞動).反映出說話人對“свобода”概念(語詞)所蘊含的社會關系的否定態度(Чернейко, 1997: 327)。而在“дышать воздухом свободы”(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中可以推導出的概念格式塔內容為“自由是空氣”,體現出“自由”(свобода)之于人的特殊重要性。這些都以人的經驗認識、生活體驗、心靈感悟等認知內容為基礎,同神入的意念跨域、概念想象的游移串接相關。由此可見,文化概念的抽象名詞實體彰顯出格式塔的文化抽象性和穿透力,這是一種文化認知的心理運作抽象單位實體,含納于其中的認知熟覺、認知統覺能力為它的共情性文化處理和創建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次,文化概念格式塔具有范疇錯置實質。所謂范疇錯置是指格式塔中作為文化對象事物的概念本體同其組配體之間的邏輯沖突和語義矛盾性,即“以不搭配為搭配、使不搭配成為搭配”。此時,概念語詞的抽象實質同其組配語詞的物理實體特征(物理行為、物理性能)形成范疇語義特征層面的對立和沖突(Зализняк Анна, 2000: 88)。這依據文化概念詞所處的上下文話語條件分兩種情形:一是概念詞處于動詞隱喻述謂構造、命題構造中;二是概念詞處于各種靜詞性組合中(包括形容詞+名詞,名詞+名詞等限定關系)。此時文化概念格式塔正是以表層上的范疇語義沖突映托概念詞的文化、語義聯想內容,傳遞出文化主體對該概念事物、對象的認識和態度等文化認知信息。這是文化概念格式塔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一個方面,因為它是通過表面上的沖突來表現文化概念,同時反映出概念事物的特有屬性,即:在人的文化意識中建立、形成的對概念對象的感受和體會,看似矛盾的字面意義關系實際是在深層次上實現概念詞同相關語詞的語義協同。例如,Она питается любовью/надеждой(她內心充滿愛/懷有希望),通過動詞“питаться”(吃,食,以……為生)同概念詞“любовь/надежда”(愛/希望)之間的語義范疇錯置,體現出“愛”和“希望”比似于“食物”必需品的重要作用和精神價值,反映出人對它們的價值判斷和文化體悟,也是人的生活經驗和文化積淀的意識化折射。同樣,“Меня питае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我以藝術創作為生)之中,通過“питает”(供養,喂養)同“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藝術創作)之間的表面沖突,反映出在人的意識和心智中概念對象“藝術創作”所具有的“精神食糧”這一文化屬性。漢語句子“情感世界的點點滴滴讓他真正明白了‘苦澀的溫柔、殘酷的溫柔’的含義”之中,概念語詞“溫柔”同“苦澀”“殘酷”的范疇錯置從物理知覺和心理體認上刻畫出情感的矛盾和苦楚這一文化形象,情緒表釋中的人文感著實而真切。句子“最后一位選手的表現終于讓我們看到了一絲驚喜”,通過表具體物量的“一絲”同抽象概念詞“驚喜”的表層矛盾限定搭配,表現出文化者對“驚喜”所產生的深刻心理體味和至為珍視的情結,體現出在人的心目中它的來之不易和對它急切期盼的心理,這些都是語言載體對“驚喜”的一種細致的認知心理體察,記載著“驚喜”這一概念的特有文化信息內容。而這同人的思維邏輯層次的細化和深入、延展有關,深層次上又牽涉到格式塔的另一個實質,即次邏輯問題。
再次,文化概念格式塔具有次邏輯性質。“格式塔反映概念的次邏輯部分——關于抽象名詞所包含實質的知覺知識”(Чернейко, 1997: 309),即相對于主邏輯、核心層邏輯語義的次層次邏輯、次級邏輯。如果說主邏輯代表概念詞的基本語義,是概念分析中的語詞意義核心(概念詞詞義)、概念(понятие)上的內容,對應于語詞字面上的理性意義、客觀意義,因而是尋找格式塔的參照、依據或切入口,那么次邏輯則是文化概念格式塔的直覺知識邏輯關聯性、非一般邏輯聯系或超常相關性,反映格式塔內容的下意識聯想方法實質,是概念詞的非理性化想象、“人本中心”(эгоцентризм)內容的生發依據和原則。從文化想象的策略和對象上講,次邏輯信息也是格式塔內容的基本構成,“對個體意識所無法完整掌握的現象進行的完整觀察是有必要次邏輯化的”(Чернейко, 1997: 357)。具體而言,格式塔次邏輯的核心點是非常規性、不真實、非現實性、非理性等主觀特性,它反映人文化思維、文化創想中的跳躍性、靈動性,即想象性、創造性這一實質,正因于此,次邏輯內容相應也構成格式塔抽象的“神入”聯想的主體部分,這包括“所有表現于概念詞組合性能中的語用成分……也包含反映人對世界的情感—評價性感知內容的非邏輯的、非理性的聯系”(Чернейко, 1997: 323),這些內容能夠從深層次上反映出文化概念的人類中心特性和社會本質,具有很強的社會認知和個體認識文化意義、價值,進而文化概念格式塔以其特有屬性構成“語言意識的非理性的次邏輯基礎”(Чернейко, 1997: 326)。建立和分析文化概念詞的次邏輯關系是概念格式塔分析的重要環節。
最后,文化概念格式塔具有交流性、對話性這一“人化”(humanization)實質,而這由概念格式塔的文化對象性活動這一語義意識交流方式所決定。正如“抽象名詞是對話性的,因為沒有也不可能有適用于所有人的心智世界片段的統一理解”(Чернейко, 1997: 356),它隱含著許多與人的理解能力、知識背景、情致特征等因素相關的人文信息,相應棲身于抽象名詞的文化概念也同樣具有“人際對話性”即商榷性、討論性、可接受性的特質,而這也為認識和分析不同社會個體、不同民族意識中的文化概念內容提供了一種策略,因為客觀上不同人和不同民族對同一文化概念對象的認識和體會可能存在某種差異,從而使文化概念成為了解個體和民族心智的一種重要而特殊的精神渠道。
此外,文化概念格式塔(內容)具有多維、立體的實質。文化概念本體可以向多方面映射,生發出多種不同的文化聯想信息,格式塔內容相應具有多面相、多層面性,一個格式塔多層次交叉、衍射出來的文化信息甚至可能相互矛盾,這既同社會群體理解和使用文化概念的社會、歷史環境和知識背景等客觀條件有關,又同文化主體對概念對象事物的領悟、讀解及對它所持的情感、態度以及與該事物的交流互動等主觀因素密切相連。表面上看,這是文化概念格式塔內容層面的問題,而背后起決定作用的卻是人對文化事實對象及相關事物的認知、觀念和態度的非單一性乃至民族性格的因素。因此,文化概念格式塔的這一本質屬性深層次上反映出人的心靈的豐廣富足性以及情志意識的復雜性,并且直接相關于文化概念的聯想輪廓和次邏輯域。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格式塔還具有特殊的語言文化實質,它從文化想象的維度以靈動、知性的方式集中呈現出文化意識與語言意識的關系,形成基于文化概念的一種語言文化獨特面相。客觀而言,歷史文化語境中的語言意識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積極載體,“語言意識是民族文化和人內在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外現人如何認知世界和對待世界”(趙秋野 等,2013:78),語言意識既是文化意識的物質外化,更是文化意識的一種精神深化,從語言文化關系上審視,語言意識是最概括的文化意識體現,而文化意識則是最精確的語言意識(方式)。通過文化概念格式塔不難發現文化意識對語言意識的強大作用和滲透力。
3 結語
由此觀之,格式塔是在人的語言意識中對文化概念語義內涵的深度發掘,它有力揭示出民族文化語境中文化概念詞特殊的物的蘊涵和意識映射內容,映照出概念語詞獨特的語言文化涵指,借助一個個概念格式塔的分析可以展現民族心智中文化主體的思想實質和社會共識,有助于識解潛隱于文化概念背后的豐富而復雜的文化體驗內容。表面上看,格式塔只是借助事物關系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感知與心靈領悟,但深層上它代表并反映著文化概念的認知運作機制和民族心理屬性,是一種文化自洽、文化自我的互動方式。概念格式塔特有的內涵使它成為一個抽象的認知心理實體和基本的文化思維操作單元,具有特殊的文化統覺性、文化意識神入性(集體無意識性、認知擬象的物我同懷性、主觀意念與文化潛意識的特殊共在性等)、范疇錯置、次邏輯實質,并且在文化表現、理解上具有多維立體性(矛盾性)和對話性、交流性,概念格式塔相應可成為文化概念分析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憑借對語言文本事實中紛繁復雜的概念格式塔的文化認知深度解析,文化概念的深層聯想內容能夠逐步得到全面展現和深入揭示,并且一種文化的民族心智、民族意識和民族性格、民族特征都可以在概念格式塔中得以呈現,進而通過它可以得出較為充分、可靠的文化分析結論,建立起對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了解和認識。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對抽象名詞(指文化概念語詞——引注)的形式研究越透徹,意識對自身的理解就越深刻,語言世界圖景的表現就越是準確”(Чернейко, 1997: 336)。
參考文獻:
Зализняк, Анна А. 2000. Заметки о метафоре[G]∥ Иомдин, Л. Л. и др. Слово в тексте и в словаре.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82-90.
Карасик, В. И. 2002. Языковой круг: личность, концепты, дискурс[M]. Волгоград: Перемена.
Маслова, В. А. 2006. Введение в когнитивную лингвистику[M]. 2-е изд., испр.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Наука.
Раушенбах, Б. В. 1990. О логике триединост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1): 166-169.
Степанов, Ю. С. 2004.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M]. Издание 3-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Успенский, В. А. 1997. О вещных коннотациях абстрактных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х[G]∥ Успенский, В. А. Семиотика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а. Вып. 35. Москва: ВИНИТИ,146-152.
Чернейко, Л. О. 1997. 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мени[M].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ерсия.
Лассан, Э. 2002.Надежд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J].Respectusphilologicus, 2(7), http:∥filologija.vukhf.lt/2-7/lassan.htm
郭本禹. 2017. 沙利文人際精神分析理論的新解讀[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 86-96.
劉娟. 2007. Концепт的語言學研究綜述[J]. 外語與外語教學(1): 5-7,51.
彭文釗. 2004. 試論語言文化信息單位及其語義結構完形[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3): 31-37.
彭玉海. 2014. 動詞隱喻構架中的文化概念格式塔[J]. 外語學刊(5): 22-26.
彭玉海,彭文釗. 2016. 俄羅斯文化概念與民族世界圖景[J]. 外國語文(3):19-24.
孫俊才,石榮. 2016. 儒家文化的情感智慧[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 101-111.
王紅孝,徐玉臣. 2016. 隱喻心智計算中施喻者與受喻者的主體性及主體自洽[J]. 外語教學(2): 39-42.
趙愛國. 2007. 語言文化學方法論[J]. 外語與外語教學(11): 9-11,15.
趙秋野,黃天德. 2013. 從свой-чужой 的語言意識內容和結構看俄羅斯人的語言哲學觀[J]. 外語學刊(4): 78-82.
朱達秋. 2014a. 文化記憶與俄羅斯文學中的彼得大帝形象[J]. 俄羅斯文藝(2): 122-127.
朱達秋. 2014b. 作為記憶形象的多余人——俄羅斯文學與文化記憶[J]. 外國語文(3): 10-12,33.
朱振武,羅丹. 2015. 文化自覺與源語旨歸的恰當平衡——以白亞仁的譯介策略為例[J]. 山東外語教學(6): 5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