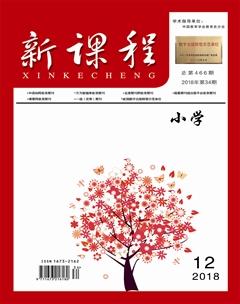搭好家校橋梁 讓孩子昂首前行
王克英
摘 要:山花爛漫、草長鶯飛的四月是師德師風培育月,每年的這個時候教師都會深入到學校部分孩子家中,以便更接地氣地了解這些家庭的真實狀況,零距離地傾聽這些家庭和孩子們的故事。
關鍵詞:橋梁;家校;家訪
2017年4月16日我去造訪我的家訪對象——建檔立卡、精準扶貧戶,學生小張的家庭。
小張是我校啟明班的孩子,2001年11月生,由我縣殘疾人聯合會審核鑒定為智力三等殘疾,自律性差,學習非常被動,屬于補作業“專業戶”。但較2012年初到我校時來說,已有很大轉變。
小張是個不幸的孩子,爸媽2008年離異,當時小張被法院判于母親撫養,但是跟著母親3個月后被爺爺接回家,然后一直和爺爺爸爸生活,幾年前爺爺去世,自此張家父子相依為命。張爸爸脾氣暴躁,好喝酒,對兒子的管教要不溺愛放縱,要不拳腳相加,在老師多次的誠懇批評勸告下,有所改變。
因為去小張家交通不便利,乘坐客車只能到村級主公路,與張家相距甚遠,愛人主動開車送我去家訪。我一路上腦中都在預設著張家的情景,家無主婦,來學校接送孩子都會滿身酒氣的張爸爸又會經營一個什么樣的家庭呢?我很自然地把他家的光景和亂、臟、差聯系了起來,我甚至還擔心張爸爸對我的到訪會不會排斥和不待見……
一路揣測和忐忑,兩個小時后我們在家長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來到了小張家——高橋鄉龍潭村二組39號。當我站在這兒,眼前的一切讓我對自己先前的種種設想而羞愧:張家并沒有預設中的雜亂不堪,相反我看見的是室外打掃利落干凈,衣服晾曬疏密有致,室內陳設井然有序,家具擦拭锃亮發光;而張爸爸的態度也與我預想中大相徑庭,沒有排斥和怠慢,手忙腳亂地擦拭坐椅透露出了主人內心的意外和高興,熱氣騰騰的茶水飽含了主人的熱情和感動……
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交流過程中張爸爸根本沒有往日接送孩子時的酒氣熏熏和語不搭調。他言辭誠懇,談了家里的勞作情況和經濟來源,更多的是關于兒子的成長問題。也許是因為兒子不在家更好說話,張爸爸對自己不能給予孩子完整的家庭深感愧疚,因為缺失母愛所以對孩子比較嬌慣,不舍得孩子去勞動;對孩子的不好的品行也深感頭疼和痛心,希望老師對孩子嚴格管教,長大后能走正道,能自食其力……針對張爸爸的煩惱及其對孩子的管教方式,我很真誠地談了自己看法,充分肯定了張爸爸的付出與艱辛,并就孩子的教育問題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張爸爸積極表示以后一定配合學校、老師,合力管好孩子,讓孩子不斷進步。
雖然這次家訪學生不在家,但我仍然覺得不虛此行。回到學校我及時將家訪情況向班主任進行了匯報,反饋了小張家人員結構、房屋居住、經濟來源等實際狀況,真實地再現了家長的生活、勞作習慣,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張家的實際困難以及家長的困惑、愿望和要求,并毫無保留的交換了自己的感受和建議。等到再次上學我及時找到了小張,就他假期去同學家一玩就是數天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和教育,告訴他爸爸生活的不易和艱辛,他應該在校好好學習,在家勤愛勞動來回饋爸爸的養育之恩,小張對我能親自登門家訪表示很開心,也為自己假期出去玩耍而自責羞愧,他答應我以后一定要聽老師和爸爸的話,做個討人喜歡的孩子。
常說家訪是橋梁,家訪是紐帶,這對于我們特教老師來說絕不是大話套話,更不是走過場搞形式。自進入特校以來我每一年每一學期都會家訪,而每一次家訪都會讓我的心靈受到一次撞擊。特教老師只有實實在在地走入這些殘障孩子的家庭,親眼目睹家庭的狀況,才能看見家長不為我們所知的另一面,從而避免“有色眼鏡”帶來的誤會和傷害;也只有親耳聆聽家長敞開心扉的訴說,才能真切地體會到這些家長內心的無助、迷茫甚至是絕望。這種感受絕不是電話里的詢問交流和路途碰面的搭訕寒暄能有的,而對于家長來說,他們手足無措地迎接我們的登門拜訪和立在屋檐下目送我們遠去久久不進屋都能讓我感覺得到他們被尊重、被關愛的感動…….
《師德規范》用24字概括了教師的職業特點、本質要求和時代特征,而愛和責任是其核心和靈魂。確實,育苗不可無水,教育豈能缺愛!而我們特教老師懷著真誠和關切走進孩子的家庭去碰觸家長、孩子深藏心底里的柔軟,繼而盡全力去安撫和幫助就是愛和責任的體現。老師應多家訪,多鼓勵,多幫扶,多落實,讓每個孩子學習日益進步,身體逐日健壯,哪怕只是蝸行般的速度,我們也要讓家長對社會對學校有信心,對家庭有奔頭,對孩子有希望……所以在通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家訪仍然是輔助教育教學必不可少的一種手段,這個傳家寶不能丟。
“讓每一個學生都在學校抬起頭來走路”,這是每一個特教人最質樸也是最極致的理想狀態,我想,只要社會、老師、家長永不言棄,我們的孩子即使肢體不能挺拔,但精神之軀一定是高昂的,因為他們的成長之路是一座我們家校共同搭建的橋梁,這橋梁讓他們一路無畏無懼,陽光成長!
參考文獻:
[1]陳愛萍.微動心思,搭建家校共教的橋梁:智障兒童教育中如何巧用微傳播與家長溝通[J].文理導航(下旬),2018(2):92.
[2]申淑敏.搭建班級家校橋梁,形成教育合力[J].河南教育(基教版),2009(2):34-35.
編輯 杜元元